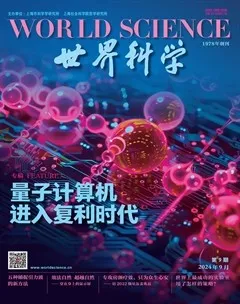劉昌勝:高度重視科學學研究,加速科技成果向新質生產力轉化
大力培育新質生產力,必須牢牢抓住科技創新“牛鼻子”。在前沿科技領域和關鍵技術領域,產業的力量日益凸顯,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許多突破性的創新成果都誕生于此。過去,高校是創新的引領者,但現在,高校想繼續擔當引領者,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大學校長劉昌勝在接受專訪時談到,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高校的首要任務是從源頭加大原始創新的供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創新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進一步重視深層次的“科學學”(Science of Science)研究,即從宏觀層面總結原始創新發生的規律,以應對局部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大學亟需打破教育的固有“慣性”,采取更果斷的行動開放辦學,拆除大學的“圍墻”,讓科技變革的思潮涌入這座“象牙塔”,培養一批能夠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的高質量人才。以下是訪談內容。
高度重視科學學研究,科學評估創新的 “成敗”
科技創新能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在您看來,要進一步促進新質生產力的釋放,在加大原始創新方面,我們還可以有哪些新作為?
縱覽全球,科技浪潮滾滾而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和生活方式都正在或即將發生巨大的變革。認識、把握并推動變革,起支撐作用的就是科技創新。如果把生產力比作一座金字塔,那么引領生產力發展的正是金字塔的尖端——那些影響力大、沖擊力強、引領性高的創新,能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并促進其發展。
可以說,沒有源源不斷的原始創新供給,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便無從談起。事實上,無論科學發現還是原始創新本身,都遵循著一定的軌跡和規律。然而,當前科學界對原始創新發生規律的研究尚顯不足。由于顛覆性、革命性的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我們更需要從宏觀層面總結規律,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局部的不確定性。因此,科學學作為研究科學和科學活動發展規律及其社會功能、影響的研究領域,將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要知道,科技創新的過程復雜且充滿挑戰。一般情況下,從資源分配來說,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總結成果各占1/3——這是一個較為合理的資源分配比例。然而,根據我的長期觀察,現在不少研究往往是“5%的發現、80%的解決、15%的總結”。講得更直接一點,我們在如何發現關鍵的科學和技術問題上,做得還遠遠不夠。
不言而喻,只有找對了問題,才能確定正確的方向,并進行有效的、前瞻的科研布局。這就要求科學家本身要具備提煉現象背后科學問題的能力,然后組織一批科研人員共同攻克難關,方能事半功倍。具體而言,要組織戰略科學家加強戰略研究,從具體的現象或國家重大需求出發,分析和提出關鍵的、抽象的科學問題,并制定正確的戰略研究方向和科學目標。這或將一定程度上破解原始創新難的問題。
在從原始創新成果轉化為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您認為目前還存在哪些裉節和堵點?
原始創新之所以困難,不僅在于我們對其發現規律缺乏深入研究,對相應的科研資助、管理和評價等問題,也缺乏系統的科學研究。
科技成果轉化率之所以偏低,一方面是因為原始創新的成果轉化周期長,甚至有些并不具有可轉化性,即轉化為人類的新知識或對世界的新認知;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一個科研活動的真相——失敗是原始創新和前沿基礎研究的常態,而成功只是少數。
打個比方,基礎研究和成果轉化的過程,猶如探礦和挖礦。我們通常注重挖礦的成績而忽略探礦的作用,而實際上,恰恰是探礦者的失敗,排除了大量的錯誤探索方向,定位正確的礦源,從而為后來的挖礦者鋪平了道路。同時,我們還需綜合分析科研失敗的原因。例如,有些科研失敗,是因為受限于當時的認知能力或技術水平,對這些科研活動開展評價時,應當站在歷史的角度,而非“事后諸葛亮”。
我們同樣以勘探舉例。過去,地下勘探的深度可能僅限于3000米,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現在已經能夠鉆探到5000米甚至10 000米。那么,如果當初在3000米深處未發現金礦,而最終在5000米或10 000米深處找到了,這并不意味當時技術水平的3000米深度勘探工作沒有找到礦是探索方向有誤或科研工作失敗。
可見,創新是一項失敗率高、充滿艱辛的任務。直面這個事實后,接下去我們要思考的是:到底是去做相對容易的事,還是去做難的事?可見,我們不僅需要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家那種百折不撓、甘于奉獻的精神,同時也需要營造一個更加寬容失敗的環境。要知道,有些科研人員默默無聞地奉獻一生,或許未能取得世俗眼中的成功,但問題是,誰又不渴望成功呢?那些經過努力卻依然失敗的嘗試,同樣具有意義,只是往往缺乏正面的認可。所以,評估失敗并非易事,需要區分是客觀條件限制還是工作敷衍了事,不能一概而論。
鼓勵更多的創新,需要有適宜的環境。其實,我們目前依然面臨著制度層面的剛性束縛等問題。例如,科研項目預算的精細管理,有時會限制研究的靈活性。基于基礎研究的不確定性,近年來,部分研究項目已開始實施項目經費包干制,這就是一項很好的探索,可避免研究過程中需要使用新的實驗材料和方案產生的經費報銷困難問題。
不同領域成果轉化速度不同,要善用分類管理“指揮棒”
如何優化科技成果轉化的機制,以應對研發周期長、風險高以及市場需求快速變化等多重挑戰?
古語云“厚積薄發”,基礎研究尤其如此,其創新成果同樣需要長時間累積,方能結出生產力的碩果。為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不同領域的科技成果轉化具有各自的特點和需求,這就要求我們善用分類管理的“指揮棒”,營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
就拿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領域來分析,兩者在轉化方面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生物醫藥領域的研發周期長,一款新藥的研發到上市往往需要五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以上,這是因為藥品的安全性測試必須經歷漫長而嚴格的過程。相比之下,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轉化速度則快得多,甚至半年都算慢了。其次,從科研“高產期”來看,生物醫藥領域的科研人員往往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學習,成果產出通常在四五十歲左右;而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人員則呈現出更年輕化的特征,比如視頻生成大模型Sora團隊的成員僅二十多歲,便取得了令人驚艷的成績。
盡管短期內,人工智能領域在產業規模及影響力方面創造了更為亮眼的成績,但生物醫藥領域的科技成果轉化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從長遠來看,生物醫藥對生命健康的貢獻無法估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其實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比如,其迭代過程需要大算力、大數據和大模型的支持,這就對硬件和電力資源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相比之下,人類大腦功耗低但運轉速度快,這是目前人工智能無法比擬的優勢。
不同領域的創新各具特色,轉化過程也各不相同。因此,在推動高質量創新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入了解各個領域的實際需求,從不同角度探索適合的解決方案。無論是頂層設計、管理制度、評價體系還是政策支持,都不能簡單地“一刀切”,而應結合各領域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短期和長期效益,以更加科學和全面的方式評價其意義。
高校作為科技創新的策源地,卻一直面臨科技成果轉化率偏低的問題。對此,能否結合上海大學的探索,談談您的看法和建議?
長期以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受到關注和討論。一方面,我們確實需要研究科技成果的轉化規律,提供有針對性的制度供給,解決其中的裉節、堵點,促進科技成果的產業化。另一方面,從科學的視角來看,轉化率不高也有創新規律本身的影響,因為成功往往來自無數次的失敗探索。從基礎研究到新質生產力的轉化,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對此需要有正確的認知。我們需要深入研究科學學的深層次內容,按照創新規律配置投放創新資源,多產出一些高質量的原創成果,提高創新成果的有效轉化率。
坦率地說,目前雖然有很多人在“挖礦”,但真正勇于探索的“探礦人”較為稀缺。一旦某個領域發現了豐富的“金礦”,各種資源和關注便會紛至沓來。然而,在此之前,那些長時間、默默無聞的探索工作,卻往往被忽視。原始創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巧妙地運用政策工具來支持并促進創新成果源源不斷地產生,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上海大學在價值文化層面倡導做有用的學問,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所需,開展有組織的科研,促進高價值的科研成果的產出。同時,學校也注重與校區所在區的協調,大力建設環上大科技園,針對科技成果的轉化規律和學科特征,加強扶持政策的精準供給,并提供專業化的服務,提高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國家需要什么就布局什么,大力培養未來領軍人才
發展新質生產力,亟須進一步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您認為大學應該在其中發揮哪些作用、做出哪些改變?
無論是原始創新還是成果轉化,人才始終是核心。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肩負著培養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需的高質量人才的職責和使命。如果大學仍舊“穿舊鞋、走老路”,顯然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
打造立體式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大學要有切實的作為。在上海大學,我們構建了“四層”卓越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依托首批國家試點學院——錢偉長學院,致力于培養基礎學科拔尖人才;為適應未來技術發展的人才需要,成立未來技術學院,培養引領未來的科技領軍人才;針對集成電路等關鍵領域的人才急需,設立微電子學院,培養卓越工程創新人才;面向全體學生,注重培養全面發展的創新人才。通過分層分類的人才培養模式,為學生提供了多樣化、個性化的發展選擇。
同時,上海大學還采取更果斷的行動開放辦學,積極對接新業態。學校改革教育模式,拆除大學的“圍墻”,通過引入產業界的頭部企業,建設卓越工程師學院,推動產教融合模式創新,構建產學研合作平臺,并優化課程體系,共同培養面向未來的卓越工程師。通過教育模式的創新,學校致力于培養能夠引領未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才。
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現代化,需要各方面的拔尖創新人才。高校該如何通過教育變革,培養創造新質生產力的戰略人才及應用型人才?
首先,基礎學科的根基要樹牢,大學應進一步強化基礎學科拔尖人才的培育。其次,大學再也不能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要站在國家戰略、社會需求的角度看教育。國家需要什么、社會需要什么,大學就布局什么、發展什么,不符合社會需求的學科專業,要大膽地關、及時地停。
對大學而言,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要跳出眼前的短期利益,站在未來看現在,從長遠發展的需求角度,前瞻布局具有發展潛力的未來學科、未來專業。
近年來,學校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在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方面,依托國家重點實驗室和省部級基地,并強化與國家實驗室、中國科學院相關研究所的合作,致力于提高科教融匯對教育教學的支撐反哺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在逐步優化學科布局和專業結構,加大本科專業動態結構調整的力度,布局“四新”專業,逐步淘汰傳統專業,力爭在“十四五”末,將現有本科專業數壓縮20%,并積極構建學科交叉的新格局,培養復合型創新人才。此外,進一步完善產教融合,我們還與行業龍頭企業共建一流育人平臺,形成以國家戰略需求、產業需求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機制。依據學校的戰略規劃,上海大學將通過優先布局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制造、數字經濟等專業,強化個性培養,培養未來領軍人才。
本文作者儲舒婷為《文匯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