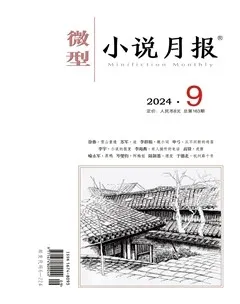過往
婦人的眼淚已經(jīng)流到了嘴邊,淚眼婆娑地望著前面。她站在步行街口的一棵柳樹下,柳樹的葉子已經(jīng)落光,落盡葉子的樹枝,枝丫錚然地直指天空。偶爾一兩只鳥飛過樹梢,發(fā)出一兩聲孤鳴。那樹好像與誰過不去,又好像和自己較著勁,表情不改地僵持著。
一年里,她每個月都來這座城市,有時是兩次,有時是三次。那些高鐵票用皮筋扎好了整整齊齊放在床頭柜里。
小美從米線館進(jìn)進(jìn)出出,早就看見了這個婦人。米線館已經(jīng)打烊了,這婦人還是以同樣的姿勢站在那里。
步行街也叫鹽河巷,傍晚以后,這里就成了美食街,蒸炒烹炸,人聲鼎沸,濃濃市井煙火氣。不知什么時候,這喧鬧的夜色里,來了一個安靜的畫畫人,像交響樂中的休止符,與這條街格格不入,顯得那么落寞和不相宜。畫畫人叫彭瑤,她攤子前擺了幾張用相框裝好的作品,都是素描人物。彭瑤一個人在那里靜靜地畫畫,她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畫板上。路過的人很少注意她,偶然注意的,目光里露出的是訝異。熙熙攘攘的行人,步履匆匆或是閑庭信步,少有在她攤子前停留的。
彭瑤學(xué)的是美術(shù)。大學(xué)畢業(yè)后,家里已經(jīng)給她找了個學(xué)校美術(shù)代課老師的工作。她不想回家,一畢業(yè)就和男朋友馬驥奔赴這座沿海城市。大三的暑假,他倆曾到這里旅游,去了蘇馬灣和海上云臺山,又去了連云老街,兩人被這座山海相擁的城市打動,認(rèn)為這里是他們的“詩和遠(yuǎn)方”。
那段時間,母親一天幾個電話,說的都是同樣的事情。她不想聽,常常不接電話。最后一次通話,母親幾乎是咆哮:“你要是不回來,以后就都不要回來。”她輕描淡寫地說:“好。”然后切斷了和家里的一切聯(lián)系。
生活不只是詩和遠(yuǎn)方。彭瑤找到了在培訓(xùn)機(jī)構(gòu)教小朋友畫兒童畫的工作,而馬驥不屑于干這樣的工作。他認(rèn)為自己是“大畫家”,是凡·高、列賓、徐悲鴻這樣的大畫家。他將來是要被寫進(jìn)“世界美術(shù)史”的,怎么能干這樣的工作呢?
那一年都是彭瑤在外面工作,而他,除了喝酒就是畫畫。畫掛在網(wǎng)上半年多,連圍觀的都沒有。他開始撕畫、燒畫。從這時開始,熱戀成了回憶,兩人開始爭吵。一點(diǎn)點(diǎn)小事都可能是引起兩人戰(zhàn)爭的導(dǎo)火索,相互對視都能心生怨恨。裂縫越來越大,直到有一天,馬驥的氣味在房間里消失,蕩然無存。
彭瑤還是選擇留在了這座城市。到了晚上,她會想家,想父母,越想越覺得父母不喜歡她,從小就不喜歡。一些往事沿著記憶的隧道爬了上來,越琢磨越覺得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晚上她坐在步行街畫畫,狹小的出租屋到了夜晚只會給她無盡的孤獨(dú)和思念。偶爾替人畫個素描什么的,晚飯錢就有了。如果運(yùn)氣好,或許房租就有了。當(dāng)然有運(yùn)氣好的時候,城市里舉辦明星演唱會,她畫了幾十張那個明星的肖像,半小時之內(nèi)被一搶而空,人們和瘋了一樣,她后悔沒多畫一些,白白浪費(fèi)了一個賺錢的好機(jī)會。畢竟,這樣的機(jī)會不常有。
她手里的筆在紙上舞蹈。一對大學(xué)生模樣的男女走到攤子前。
“把我們倆畫在一起。”那個男生說。
“不要不要,還不如去買兩個烤紅薯呢!”女生說。
“你說的對。”彭瑤微笑著對那個女生說。
“祝你們幸福。”彭瑤說。
那個女孩一臉迷茫,嘴里嘟嘟囔囔的。
夜深了,美食街開始打烊。
“姐,你怎么還沒走?”小美問她。小美是職高的學(xué)生,下午來米線館打工。小美也喜歡畫畫,經(jīng)常來看她畫畫。
“畫著畫著就忘記時間了,我把這幾筆畫完就走。”
“姐,柳樹下有個人一直往這邊看。”
彭瑤順著小美手指的方向看過去,一個淚眼婆娑的婦人站在那里。
“媽。”彭瑤小聲喊,眼淚落了下來。
選自《邊疆文學(xué)》
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