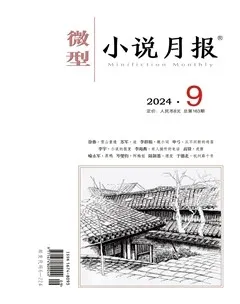替班
春末夏初,周書田家要燒瓦。
這瓦非燒不可,不能再將就、拖延了。再將就、拖延,進入雨季,雨水就要把房子淋垮。前些年房頂就開始漏雨,原因是多年來未曾添加過瓦,加之日曬雨淋,部分瓦自然開裂破損,未及時查漏補缺。一到雨天,室外下雨,室內也下雨,只好用壇壇罐罐接雨水。壇壇罐罐不夠用,盆盆碗碗也用來接雨水。有一次下大雨,把灶上的鍋也端來接雨水。
今年初春,周書田終于鐵了心,決定燒瓦。自家人挖泥、踩泥,然后請瓦匠做瓦。做瓦期間,一并也請了親戚、鄰居在自留山砍柴。自留山上的柴也是為燒瓦儲蓄的。這次一共砍了百多捆柴,多是松柏樹枝及灌木,都是耐燒的柴火。幸好燒瓦的窯是現成的——以前留下來的,只需稍加清理、修補,就能繼續使用。
瓦做好曬干,柴火也陸續從自留山搬運回來,窯也修補好了——萬事齊備,只等燒瓦。
周書田請了十二個精壯勞力燒瓦。這十二個人分成六班輪換燒火,每班兩人燒四小時。之所以需要這么多人,是因為燒瓦期間不能停火,窯內要保持連續不斷的高溫,泥坯才能變成鋼藍色的瓦,否則就是質量低劣的紅瓦。窯箍得緊湊就不會漏氣,不漏氣就保溫,這樣就會節省柴火,縮短燒瓦時間,一天一夜就能燒好一窯瓦。如果窯漏氣不保溫,耗費大量柴火,燒幾天幾夜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一窯瓦燒一天還是兩天,不確定因素多,不好一概而論,直到瓦燒好為止。
燒瓦是技術活,也是苦活、累活。考慮到燒瓦的人辛苦,周書田托親家杜良才割了幾斤鹽漬肉。杜良才在鄉街上食品站當刀匠。豬肉憑票供應,是緊缺物資。近水樓臺先得月,杜良才免票弄幾斤鹽漬肉不困難。
周書田老婆將幾斤鹽漬肉做成蒸肉。一日三餐,只有中午飯才端一碗蒸肉上桌。一碗蒸肉也是桌上的主菜。十二個人,十二片肉,一人一片,無多余的。吃午飯時,主菜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在座的人,大多還是只過年沾過葷腥,幾個月沒有吃過肉了。看見蒸肉,就像發現金子,眼睛發光,目不轉睛,饞涎欲滴。主人還沒有喊“挑菜吃”,十余雙筷子幾乎是同時伸向主菜。站在一邊的主人慌了,急忙提醒:“每人只有一片肉哦!每人只能挑自己的那一份哦!”偏偏就有人把主人的提醒當耳邊風,周詩能一筷子就搛了兩片肉,最終使周詩德無肉可搛。原因可能是兩片肉粘連在一起,周詩能未看分明,屬無意的誤搛,也可能是故意順手牽羊。既然肉已經被周詩能夾走了,到口的美食豈能放棄?這些數月未沾葷腥的人,指望他們像“孔融讓梨”那樣謙讓有禮,簡直是幻想,也是笑話。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問題是,對他們來說,倉廩是空虛的,胃腸填充后再慢慢來談禮儀。
本該周詩德吃的那片肉被周詩能吃了。一人吃一片肉,周詩能一人卻吃了兩片肉。如果把這事看成惡作劇的話,的確有些過分。周詩德沒有吃到肉,他也是個不愿吃虧的人,他生怕眾人不知曉,站起來黑著臉說:“你們也看到了,都有肉吃,就我沒有。哪個吃了兩片肉,大家心知肚明。吃了就吃了,我也不要求他把肉吐出來。我只要求輪到我燒窯時,吃了我那片肉的人自覺去頂替,接我的班。”
周書田尷尬地站在旁邊,說豬肉金貴、稀罕,不好搞,還是開后門才弄了幾斤,“吃肉”只是有那點意思,請周詩德體諒。
為了照顧主人的面子和緩解氣氛,周詩能當眾答應了周詩德這個別出心裁的要求。
燒窯雖然是兩人搭配,但燒一次窯時間長達四個小時,不是每個人都能堅持下來的。鬧鐘就放在窯門口不遠處,時間是提前調好了的,時間到了鬧鐘自動提醒。無人愿意在窯門口多待,哪怕只幾分鐘,往往是鬧鐘還沒有吵鬧,上一班的人就提前十多分鐘催促下一班的人輪崗。四個小時內,要用長木杈不斷地往窯底挑送柴火。每過十余分鐘,又要用長柄鐵鉤將窯底紅紅的炭渣刨出來,以免窯底被不斷塞進的柴火堵塞,導致窯底空間不足,柴火無法充分燃燒而不能提升溫度。初夏時節窯門口的溫度比秋冬時節燒窯時溫度更高。塞柴火的人、刨炭渣的人,面孔與手就被窯門里溢出來的高溫炙烤得火燒火燎,肌膚仿佛要熔化,汗流浹背,蓬頭垢面。被刨出來的炭渣大多還帶著明火就堆在窯門一邊,稍不留意就會燒穿鞋底。燒窯之苦,苦不堪言,像在接受火刑。
因多吃了一片肉,周詩能除了要經受自己當班的“火刑”,還要代替他人經受一次“火刑”。
次日午飯,桌上又有蒸肉。
周詩德對周詩能說:“肉我再讓給你吃,你繼續給我替班。”
周詩能紅著臉,連忙擺手道:“你自己吃,我不受這份罪。”
座中人哄堂大笑。笑聲把桌子都搖晃起來了。
選自《回族文學》
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