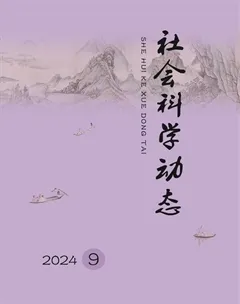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與中華文化認同
摘要: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龍母神話流傳廣泛、影響深遠,并深度融入當地民眾的生活之中。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產物,也是維系各民族文化記憶的符號載體。西南少數民族借助龍母神話,在本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完成了跨民族文化認同,最終上升到中華文化認同。以龍母神話為代表的民間文化資源是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文化資源,夯實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礎。
關鍵詞:龍母神話;西南少數民族;中華文化認同;民族共同體意識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西南少數民族龍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中華文化認同研究”(22CMZ021)
中圖分類號:I20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09-0106-07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1)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重要命題,學術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大多聚焦于政策解讀和理論闡釋,立足于田野調查的經驗研究較少。(2)實際上,各族群眾對民間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用來表達、呈現和增強對中華文化認同的案例,并不鮮見。加強經典案例的研究,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厘清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學理邏輯和社會基礎,而且可以為現實民族工作的開展提供抓手。
神話是由人民集體創造和傳承的口頭文學,不僅展現出民間社會的文化創造力和藝術想象力,更是承載文化記憶的載體和形塑文化認同的媒介。其實,民族就是“建立在共同的神話和記憶之上的共同體”(3),而且“用共享的記憶、神話、共同的價值觀和象征來界定的文化共同體或文化集體比其他共同體更具有穩定性和持續性”(4)。可以說,神話是表達、建構和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文化資源。有學者指出,以“同源共祖”神話(5)和“弟兄祖先”神話(6)為代表的中國神話資源,不僅彰顯了中華民族共生共融的生活現實,而且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
具體到西南地區,神話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已經成為西南各族群眾強化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譬如,《司崗里》和其他神話的不斷再生產,為佤族的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提供合理性(7);彝族史詩中的“月中有樹”神話中蘊藏著強化中華文化認同的豐富資源(8);景頗族目瑙縱歌通過景頗族神話、歷史的視覺化表意和儀式化實踐,表現出強烈的國家認同(9);壯族布洛陀史詩折射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演進,為增強壯族的中華文化認同提供了精神動力(10);德昂族通過激活龍陽神話對德昂族龍文化進行再生產,從而強化了中華文化認同(11)。相比于單一民族的神話研究,目前關于西南地區多民族共享的神話及其與中華文化認同關系的研究成果不多。本研究以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為例,旨在探討多民族共享神話在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以及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內在機制及邏輯,進而探究民間文化資源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作用。
一、龍母神話研究概述
龍母神話自先秦逐漸在民間形成,書面記載最早見于東晉時人顧微《廣州記》(12)與裴淵《南海記》(13),而廣為人知的南朝宋沈懷遠《南越志》(14)則是確定了龍母神話的基本情節。據文獻記載,早在漢朝,龍母事跡就被神化,民間出現了老百姓祭祀龍母、朝廷敕封龍母的記錄。(15)自此,龍母神話在時空流傳中不斷豐富,衍化出主題多元、內容多樣、文化絢爛的神話文本。到了清代,龍母神話臻于完備。
龍母神話研究大致分為三個時期。(16)第一個時期,是在20世紀初,以榮肇祖(17)、黃石(18)和黃芝岡(19)為代表的學者,開始關注龍母神話,主要探討了龍母神話的起源流變、思想變遷、母題歸類等問題。第二個時期,是從1980年代到21世紀初,學者們主要關注龍母神話的起源與流變。如,陳摩人探討龍母與百越民族的關系,認為龍母是駱越民族的頭領(20);劉守華側重探究龍子形象的變遷,并提出斷尾龍形象的出現是龍母神話的新發展(21);葉春生通過分析龍母神話,探討中華民族的起源問題,認為南方的長江流域、西江流域和北方的黃河流域一道構成中華民族的重要發源地(22)。第三個時期,是2000年以后,隨著民俗學研究范式的轉換,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要注重龍母神話背后的整體社會文化語境。如,葉春生呼吁將停留于文本研究的龍母神話拓寬至龍母信仰(23);蔣明智以粵西龍母信仰為例,系統探討了龍母神話向龍母信仰轉變的原因以及龍母信仰的歷史發展、特點和意義(24)。這一時期,龍母神話研究維度大大拓展,比如,探究龍母神話與嶺南自然、地理環境和生產方式的聯系(25);分析嶺南龍母信仰的地域擴展歷程(26);探討龍母神話與壯族文化認同關系(27)、壯漢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28)以及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聯系(29);討論嶺南地區龍母神話對東南亞的影響(30)。除了關注嶺南龍母神話外,也有學者開始探討嶺南龍母神話與北方的禿尾巴老李傳說的聯系(31)。
縱觀龍母神話研究,總體呈現出如下特點:首先,以文本研究為主,側重于文本考據的研究路徑,對龍母神話的現實傳承與發展關注較為薄弱;其次,集中研究嶺南粵西一帶的龍母神話,忽略了其他地域龍母神話,對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關注較少;此外,既有龍母神話研究側重于文本內在意義的發掘,而弱化了龍母神話在區域民族交流與互動、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中的活態作用。本文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龍母神話為研究對象,旨在梳理其歷史發展脈絡,進而探討其與中華文化認同的關系。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背景下,探討龍母神話與西南少數民族中華文化認同的關系,不僅有助于探究龍母神話在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發展格局中的地位,而且有利于發掘龍母神話的時代價值和社會意義。
二、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類型、傳承與發展
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歷史悠久、主題多樣、內容豐富,既有來自內地漢族龍神話的文化因子,又融入地方特色與民族文化,成為多元一體龍母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龍母的身份定位,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即“龍為龍母”“龍為人母”和“人為龍母”。
“龍為龍母”型龍母神話一般表現為“異類婚”。在此類龍母神話中,龍母大多承擔了考察凡人女婿品行的岳母身份,例如在壯族《老二和龍女》中,龍母與龍女變作又老又廢的人,考驗女婿老二的善良與智慧。(32)龍女神話則是此類龍母神話的一個亞型。此時龍女不再是“異類婚”的考驗者,而是神通廣大的異類妻。如在彝族《孤兒與龍女》中,龍女聽聞孤兒阿蕎的悲慘經歷與善良品行,主動奔為其妻,并幫助其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33)
“龍為人母”型龍母神話帶有鮮明的母系文化色彩。人們將神龍作為自己的母親,賦予本民族起源神圣感。如在拉祜族《龍生虎養鷹遮蔭》中,人世間唯一的男人天天燒香祭拜終求得龍女與之結合,生下雙胞胎。龍王知曉后,迫害龍女與男人致死,而雙胞胎在虎養鷹庇之下成長為人世間第一對人。(34)在德昂族《袞思艾和媽勒嘎》中,民族的祖先是龍女與太陽生下的三男三女,并受龍女悉心養育十六年。(35)
“人為龍母”型龍母神話較為完整地講述了人為龍母—人養龍子—龍子報恩的過程。如白族綠桃村龍母食綠桃而孕,生下小黃龍。小黃龍為報母恩與保百姓安居樂業,與黑龍大戰,平息洪患。此后每逢人母生辰,小黃龍回村祝壽。(36)彝族納蘇支系中有一婦女,夫死不改嫁,養一誕生于供桌之下的泥鰍。泥鰍長大化為金龍,還彝婦千丘梯田。(37)
龍母神話不僅是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深刻影響了西南地區的節日文化、民間崇拜和道德倫理。
在節日方面,白族密祉地區人民為感謝三位龍女相繼來到人間,造福一方百姓,在每年正月十五、十六兩天,壩子各村各寨都會扎兩個龍圩在壩子正中(現在的密祉街)聚會,一是讓龍女姐妹相逢,二是預祝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谷豐登。(38)哈尼族為感念為苦難的人們帶來五谷種、六畜種和金銀珠寶種的塔婆與孝順的龍王,每年收割莊稼前的農歷八月屬龍的日子,吃新米飯,過嘗新節。(39)
在民間崇拜方面,滇西白族崇拜九龍圣母。每年四月“繞三靈”盛會期間,當地人民都要到九龍圣母所在的龍母廟朝拜祭祀,在開展“耍龍”活動前,開光待出的龍也要到九龍圣母前朝拜辭行,以示崇敬。而同樣生活在滇西的納西族人民常到玉龍湖湖心的大柳樹下進行祭拜活動,以求萬事如意。這棵大柳樹便是納西族人民眾口相傳的龍女樹。西江水系的壯族等各族人民則將龍母視為最高神,在每年五月初八舉行龍母誕。
在道德倫理塑造方面,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中經常出現“龍母念蒼生”和“龍子報母恩”情節,深刻反映了西南少數民族對龍母勤勞、善良品質的推崇。在實際的道德實踐中也的確如此。西南各地龍母廟強調龍母與人為善、龍子孝順忠義的品質,并深度參與各類慈善事業,踐行龍母“積德行善”“利澤天下”的美德。
由此不難看出,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龍母神話已經形成口頭、文本與信仰相輔相成的完備體系,與西南少數民族日常生活深度相融,成為當地重要的審美意象和文化資源。
三、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與遞進式文化認同路徑
作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影響力較大的神話,龍母神話主題鮮明、內容豐富、文化多樣,是西南各族群眾在長期生產生活中文化積淀的產物,被有機融入西南各族群眾日常生活之中,深刻影響其文化想象、道德情感和信仰體系,成為其表達、建構和增強文化認同的重要媒介。
(一)本民族文化認同
在西南少數民族觀念中,龍是一種能呼風喚雨、懲惡揚善的動物,這使得龍母神話帶有強烈的神圣意味。借助于龍母神話,賦予本民族文化事項以神秘而浪漫的文化源頭,這成為很多西南少數民族增強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文化策略。
首先,西南少數民族喜歡將本民族具有文化象征性的地方風物與龍母神話聯系在一起,并通過這種方式表達民族獨特記憶。如白族《西山老祖》中,被漁郎解救的三位善良的龍公主,為能永遠看到彌渡壩開發后人間美好生活情景,化為彌渡壩中川西山上的三座白塔。(40)而凡胎肉體的漁郎又是如何才能完成解救龍公主的壯舉呢?漁郎灑下了數不清的汗水,磨掉了一層又一層的厚繭,終于把棍術劍藝練得滾瓜爛熟,樣樣精通,還練就了一身九牛難敵的力氣,才將三位公主從孽龍處救回。這是民族的光輝“歷史”。無獨有偶,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納西族《龍女樹》中,美麗聰慧的龍女無法阻止木老爺對“北”族兄弟的殺戮,悲痛欲絕,心肝俱碎,化為玉湖湖心亭上的一棵海棠樹。(41)納西人民聽說慘事,不約而同前去祭拜死去的龍女與“北”族同胞,表達了納西人對兄弟民族的關愛與對和平的渴望。這些光輝記憶能夠提升民族榮耀感,增強對本民族文化的價值認同與族群認同。而在回族《火龍和她的三個女兒》中,火龍二女兒遭受的無妄之災,引發火龍母女們的遷徙,從而導致象鼻溫泉溫度適中宜人、通紅甸溫泉的泉水又大又燙以及葫蘆沖溫泉的泉水小且溫熱的現象。(42)《龍井湖里的姊妹龍》將青龍街天氣變幻莫測的原因歸為白龍姐姐行云布雨時被人的炸石聲嚇后的心驚肉跳。(43)這種將本地區的不如人意的自然景物、自然現象,歸于人對神龍的冒犯,合理化了不如人意的自然景物、自然現象的存在,使得本民族人民自然接受此類建筑與景觀,使其成為本民族獨特的集體記憶,從而加強本民族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
其次,西南少數民族習慣利用龍母神話,賦予本民族的神圣物件以神秘性。苗族《龍女化銅鼓》中,龍女為給人們帶來歡樂,仿造龍宮的銅鼓樣式制作銅鼓模型,教青年們演奏。但制作真正的銅鼓不易,在多次失敗后,龍女受到神仙指點,縱身跳進翻滾的銅水里,將自己的血肉與銅水融合,終于鑄造出了銅鼓。苗族人民便將銅鼓看作龍女的化身,每當逢年過節或者紅白喜事,苗家都會敲起銅鼓。(44)《召波與龍女》中,苗族人民喜愛的葫蘆笙的前身是龍王賜予召波與七龍女的仙葫蘆。仙葫蘆先是幫助召波與七龍女實現了衣食無憂,在仙葫蘆不靈之后,被召波改造成葫蘆笙,以美妙的聲音給苗族人民帶來歡聲笑語。(45)西南少數民族借助龍母神話,完成對本民族獨特物產的附魅,提升其文化地位,增強本民族文化認同。
此外,西南少數民族將龍母神話與本民族的精神傳承聯系在一起。西南少數民族通過講述龍母神話,表達本民族道德與倫理取向,傳承民族氣質與精神。在傳說《小黃龍和大黑龍》中,小黃龍站在人民立場,與邪惡的大黑龍搏斗,表現出勇于拼搏的大無畏精神。(46)這展現出西南少數民族對拼搏精神的贊揚、對正義的推崇。
由此可見,西南少數民族在傳承龍母神話時,不斷融入本民族的文化符號,使其成為民族集體記憶,進而達到增強本民族認同的目標。
(二)跨民族文化認同
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本身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產物,并作為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因子,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推動了各民族的社會互動與文化交往,加強了跨民族文化認同。
首先,母題相似。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龍母神話,大多具有相似的核心母題。一是感生而孕,一般是直接感龍或者龍的象征物。湘西土家族關于族祖白帝天王誕生的神話言,白帝天王的母親便是一位喝虎奶長大的姑娘。有一次她在井邊提水洗衣,不慎將戒指掉落到井里,便寬衣解帶,赤身裸體跳入井中撿拾。這時,從井里躍起一條白龍,向她閃射三道白光,姑娘有了身孕,生下白帝天王。(47)峨山縣咱拉黑村的彝族有傳,“瑪賀尼”(未婚女)夢龍而感生子,繁衍百姓子孫。(48)二是化龍,在感生而孕型龍母神話中,龍子化龍通常是因為發生了與龍父有關的際遇。前文所提及的綠桃村龍母,龍子化龍是在機緣巧合之下穿了黃龍袍。(49)在白族《哀牢夷傳》中,季子是因龍舐而化龍。“獨季子背龍而坐,龍舐其背。”(50)三是斗龍,斗龍情節的出現大多是為了維護人民利益。大理流傳的《小黃龍和大黑龍》中,小黃龍在鄉親們的幫助下勇斗在洱海興風作浪的大黑龍,終將黑龍趕走,小黃龍也成為了洱海百姓的守護神。傣族《九隆王》中,勇士蒙伽獨的第九個兒子九隆為父報仇,勇斗九條毒龍,最終制服毒龍,獲得青黃色“種子”,以此造福人間。(51)四是行孝。白族《金龍報仇》中,龍子化為金龍,發水沖毀了欺負母親的財主家,為母報仇,并將母親接走享福。(52)壯族《禿尾龍》中,寡婦收養小蛇,小蛇變為巨龍報恩。(53)西南少數民族相似的龍母神話本身便是跨民族文化交流的結果,這將極大地幫助西南各少數民族借助龍母文化形成跨民族文化認同。
其次,民族互動。通過龍母神話,西南少數民族將本民族與弟兄民族編織在一起,形成同根同源的文化聯系,進而增強跨民族文化認同感。《后漢書·西南夷傳》記載:“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其子曰九隆。”(54)這便是廣泛流傳于西南地區的《九隆神話》。西南地區的白族、土家族、彝族、傣族等民族都信仰九隆神話,并認為本民族是哀牢人,即龍的后代子孫。這一方面使得各民族形成“弟兄祖先”情感連接,強化西南少數民族跨民族認同,另一方面與漢族龍文化產生互動,加強與漢民族的情感共鳴。
此外,文化共享。西南少數民族將龍母與節日起源聯系起來,例如“三月三”、祭龍節等多民族共享的節日。龍母神話隨著節日演繹,突破民族界限成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資源,幫助西南各民族形成跨民族的文化共同體。在壯族、侗族等原南越民族信仰的龍母神話中,龍子“特掘”在三月初三安葬了養母,因此每年“三月三”成為其祭拜龍母的共同節日。(55)祭龍節表達的是西南各少數民族對龍文化與龍圖騰的崇拜,具有共同的文化內涵。龍母神話及龍母信仰作為超越民族的地域文化因子,強化了西南各民族跨民族文化認同。
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的相似性、交流性和共享性,折射出西南各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過程與實踐。無論是回溯歷史脈絡,還是從現實出發,龍母神話已然成為加強西南各民族跨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文化資源。
(三)中華文化認同
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既帶有很強的地方性色彩和民族性內容,同時也與中華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充分展現出中華文化的多元一體性。(56)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的主題、審美和精神,與中華龍文化一脈相承,這也為其形成和強化中華文化認同提供了文化資源。
在主題上,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與中華龍文化高度類似。在中原地區流傳的龍母神話中,龍居住的龍宮大多在深海,形成“四海龍王”分治四海的格局。西南地區遠離海岸線,于是結合其所處自然環境特點,認為龍大多居住在樹木與水潭等地。彝族、壯族的神話認為龍生活在樹木之上,而普米族、布依族、納西族等民族則相信龍應棲息于龍潭。雖然地域有差異,但是按照主題來分,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主要分為族源神話、自然神話、英雄神話等類型,這基本上與中華龍文化的經典類型一致。可見,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不僅受到來自中原地區龍文化的影響,同時也使其與地方社會文化融合,但始終保持著核心主題的一致性。
在審美上,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與中華龍文化具有一致性。龍作為一種虛幻的神圣動物,其中投射了人民群眾的文化審美。比如,中華龍文化中蘊含著福澤利民、佑護蒼生、揚善懲惡的道德情感,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中的龍母也具有這樣的能力。彝族《孤兒和龍女》中,龍女懲罰貪得無厭的縣官時,雷鳴電閃、風雨四起,使得九龍河暴漲,卷起怒濤狂浪,奪去縣官一行人的生命。(57)在云南玉溪一帶流傳的《龍井湖里的姊妹龍》中,管天的白龍姐姐負責興云布雨,管地的青龍妹妹管潭泉細水長流。(58)可見,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雖具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但其文化屬性仍與漢民族保持一致。
在精神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龍母神話與中華民族推崇的孝道文化不謀而合。其具體表現有三。一是尊祖敬宗。在白族《九隆神話》中,第十子被龍父舔舐而不同于凡人,某種程度上已經取代最初故事中的“沉木”和龍父,因此在后續的故事中“沉木”和“龍”不再出現。但“沉木”和“龍”因“觸碰”而有恩于白族,于是白族將其作為祖先加以供奉,形成對“沉木”和“龍”的祖先崇拜與圖騰崇拜。(59)二是孝敬父母。龍子化龍后不離龍母,盡心侍奉龍母,承歡膝下。在龍母死后,以人類社會禮節埋葬母親,哭墳祭母都屬于此類。三是兄弟和睦。在很多西南少數民族創世神話中,創世女神擔任了龍母的角色,她不僅是龍的母親,也是人祖的母親,因此人祖和龍是關系明朗的兄弟。如壯族有神話講述,人祖布洛陀與女神米洛甲發生矛盾,出走到兄弟圖額(“龍王”)那躲避。(60)從龍母神話中傳遞出來的孝道文化,不僅成為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在交流互鑒中相互認同、相互欣賞的共同文化取向,也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價值追求。在此背景下,不同民族之間形成了共同的精神文化依賴關系,奠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西南少數民族對龍母神話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自發利用龍文化表達、呈現和強化中華文化認同。例如德昂族對龍陽神話進行創造性轉化,強調龍陽神話中的龍文化符號,高喊“我們也是龍的傳人”口號,強化了德昂族群眾的中華文化認同。(61)再如侗族、傣族等少數民族自覺傳續本地區漢族《二十四個望娘灘》等龍母神話與傳說,并利用本民族傳統音樂與曲藝加以演繹,共同承載中華民族集體記憶。(62)
有學者認為,中華文化認同包括三個層面, 分別是各民族的自我認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中華民族的一體性認同。(63)圍繞著民族認同的層次展開,也形成三重文化認同,分別是本民族文化認同、跨民族文化認同、中華文化認同。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恰如其分地對應了這三個層面,并呈現出遞進式的文化認同路徑。首先,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通過文化附魅的方式提升本民族文化地位,增強民族榮譽感。其次,借助龍母神話,西南少數民族構建了與弟兄民族“同根同源”的歷史記憶,同時與漢民族形成良好的文化互動,從而實現了跨民族文化認同。最后,龍母神話體現出的龍文化是中華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西南少數對其進行有意識的傳承與改造,強化了自身的中華文化認同。可以說,在歷史長河流轉和社會文化變遷中,龍母神話一直成為西南少數民族維系、表達和建構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并且完成了文化認同的螺旋上升,最后直達中華文化認同的高度。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背景下,以龍母神話為代表的民間文化再生產能夠幫助各民族在實現本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加強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進而形成跨民族文化認同,最后達到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效果。這也提醒我們,在民族工作中,需要注重發掘并利用以神話為代表的民間文化資源,并有意識推動其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其成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精神土壤,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礎。
四、結語
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龍母神話流傳廣泛、影響深遠。西南少數民族將龍母神話融入本地區本民族的民族起源、節日儀式、信仰崇拜等中,并且在本民族文化認同和跨民族文化認同基礎上,形成了中華文化認同。可見,西南少數民族龍母神話背后呈現出遞進式文化認同模式,這種從自我到大我、從局部到整體、從微觀到宏觀的遞進式模式,不僅是中華文化認同的演進軌跡,形成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而且也夯實了中華文化認同的社會基礎,進一步增強各族群眾的中華文化認同。
神話作為一種神圣敘事,承載著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記憶,影響著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神話不僅是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文化資源,而且也是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精神力量。更為重要的是,神話仍然影響著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社會實踐和文化情感,是一種活態的文化資源,能夠結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持續不斷為各族群眾的文化認同提供豐富的資源。因此,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該高度關注神話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努力挖掘其中被各族群眾接納和喜愛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充分激發神話的時代活力和文化創造力,使其成為增強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助力民族工作的開展。
注釋:
(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7日。
(2) 何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經驗研究:何以必要與何以可能》,《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3) [英]安東尼·D·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譯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52 頁。
(4) [英]安東尼·D·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版,第21頁。
(5) 王丹:《“同源共祖”神話記憶: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7期。
(6) 王丹:《“弟兄祖先”神話與多民族共同體建構實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路徑》,《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7) 參見 白志紅:《中緬邊境佤族神話傳說、資源與認同》,《民族藝術》2013年第6期;高健:《從開天辟地到“解放”來了——佤族司崗里神話的歷史表述》,《民族文學研究》2017年第3期。
(8) 李世武:《神話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的作用——以彝族史詩中的“月中有樹”神話為例》,《思想戰線》2021年第2期。
(9) 巴勝超:《文化交融理論視野下的認同敘事:以景頗族目瑙縱歌為例》,《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10) 李斯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演進——基于壯族布洛陀史詩的思考》,《民族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
(11)(62) 熊威:《中華文化認同與德昂族龍陽形象的激活》,《民族藝術》2022年第5期。
(12) 一說《南海記》。原書已散佚,書中所記龍母事跡目前最早見于唐代歐陽詢編撰《藝文類聚》卷9《水部下·浦》,“顧微《廣州記》曰:有蒲母養龍,裂斷其尾,因呼龍掘。人時見之,則土境大豐而利涉。”
(13) 原書已散佚,書中所記龍母事跡目前最早見于隋朝虞世南編撰《北堂書鈔》第138卷《舟部下·舫七·龍引舫還》,“《南海記》曰:有龍掘,浦口。昔蒲母養龍,龍取魚以給母。母斷魚,誤斫龍尾。人謂之龍屈。恒帝迎母至于浦口,龍輒引舫還。”所記較為簡略,甚至虞世南只是將其作為“龍引舫還”的例子。但較顧微《廣州記》,該記載補充了“龍為龍母捕魚”和“東漢恒帝迎龍母進京”的情節。
(14) 原書已散佚,書中所記龍母事跡目前最早見于北宋樂史編撰的《太平寰宇記》。其情節更加完整豐富,并將“東漢恒帝迎龍母進京”改為“秦始皇聘龍母”,將時間提前了300多年。
(15) 明初洪武九年(1376)《洪武詔書》,“爾廣東道肇慶府德慶州悅城孝通廟靈濟崇福圣妃之神溫氏者,豢龍為兒……漢初封為程溪夫人。”但當時最為權威的史籍《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書均未提及龍母,因此此記載難以確證。
(16) 徐亞娟:《近百年龍母傳說研究綜述》,《廣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17) 參見容肇祖:《德慶龍母傳說的演變》,《民俗》周刊1928年第9、10期;后收入其專著《迷信與傳說》,民俗學會1929年。
(18) 黃石:《關于龍的傳說》,《青年界》1931年第2期。
(19) 黃芝岡:《中國的水神》,生活書店1924年版。
(20) 陳摩人:《悅城龍母傳說的民族學考察——民間文學的橫向探索》,《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21) 劉守華:《中國民間故事史》,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40頁。
(22) 葉春生:《從龍母傳說看中華民族的兩大發源地》,《思想戰線》1988年第4期。
(23) 葉春生:《嶺南的掘尾龍和東北禿尾巴老李》,載《悅城龍母文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頁。
(24) 蔣明智:《悅城龍母的傳說與信仰》,《文化遺產》2008年第2期。
(25) 陳金文:《嶺南龍母文化散論——兼與葉春生、梁庭望、陳摩人等先生商榷》,《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4期。
(26) 王元林、陳玉霜:《論嶺南龍母信仰的地域擴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4期。
(27) 羅彩娟:《文化表達與族群認同:以武鳴壯族龍母文化為例》,《廣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28) 徐亞娟:《珠江流域龍母傳說的展演》,《民族文學研究》2010年第3期。
(29) 孫正國:《多民族敘事語境下中國龍母傳說的“雙重譜系”》,《民族文學研究》2019年第2期。
(30) 項青、梁娟美:《百越文化圈民族龍母卵生神話源流考——〈鴻龐氏傳〉越南始祖卵生傳說的解讀》,《紅河學院學報》2023年第1期。
(31) 季中揚、馬海婭:《龍母傳說的北向傳播與“禿尾巴老李”故事的來源》,《文化遺產》2019年第2期。
(32) 張聲震、農冠品編:《壯族神話集成》,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3頁。
(33)(57) 白庚勝、李洪文編:《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云南·漾濞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0、27—30頁。
(34) 思茅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思茅地區文化局編:《拉祜族民間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頁。
(35) 黃光成編:《德昂族文學簡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2頁。
(36)(49)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編委會編:《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5卷(瑤族、白族、土家族)》,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8、445—448頁。
(37) 楊正權:《西南民族龍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34頁。
(38)(40) 白庚勝、張彪編:《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云南·彌渡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5、58—60頁。
(39) 龍倮貴:《試析哈尼族動物圖騰崇拜》,《紅河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41) 羅楊、沙蠡編:《中國民間故事叢書·云南麗江·古城玉龍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152頁。
(42)(43)(58) 羅楊、吳才龍編:《中國民間故事叢書·云南玉溪·華寧卷》,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155、155頁。
(44)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中國ISBN中心出版2003年版,第356—357頁。
(45) 施中林編:《滇原遺珍》,云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218頁。
(46) 聶楊編:《中國民間故事》,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版,第89—91頁。
(47) 巫瑞書等主編:《巫風與神話·略述楚地求子風俗與性崇拜遺存》,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頁。
(48) 楊甫旺:《蛇崇拜與生殖文化初探》,《貴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50)(59) 李豐春:《白族孝文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4頁。
(51) 傅光宇編:《傣族民間故事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52) 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編:《云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 神話傳說卷 》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頁。
(53) 黃革編:《龍塘和龍溪》,《廣西少數民族民間故事》,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頁。
(54) 范曄:《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848頁。
(55) 董志文編:《話說中國海洋神話與傳說》,廣東經濟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1頁。
(56)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頁。
(60) 農冠品編注:《壯族神話集成》,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頁。
(62)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重慶市卷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重慶市卷》(下),中國ISBN中心出版1990年版,第602—603頁。
(63) 王希恩:《中華民族建設中的認同問題》,《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作者簡介:熊威,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79;潘明霞,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