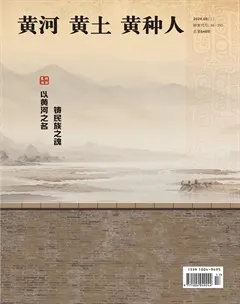黃河治理文化的時代價值
數千年黃河保護治理歷史,孕育產生了輝煌燦爛的黃河治理文化。黃河治理文化是黃河水文化的核心內容,是黃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梳理研究黃河治理文化孕育產生的歷史脈絡,多維度挖掘其蘊含的豐富歷史內涵,提煉其時代價值,對講好新時代黃河故事,賡續中華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根植于黃河流域的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翻開幾千年的治黃史帙,河決河安、河廢河興,無不見證著國家治理的張弛勤怠,無不關聯著流域人民的否泰禍福,無不映照著中華文脈的起落枯榮。一部艱辛的治黃史,濃縮了中華民族的苦難史、奮斗史、治國史。可以說,一部治黃史就是黃河文化的最好表達。黃河治理文化作為黃河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以黃河治理為特征展示在人們面前的一種文化形態,反映了從古至今中華民族與黃河的關系演變,其最基礎的內容是人們利用、開發、治理和保護黃河的各種實踐活動。其特殊性在于其孕育產生于黃河治理實踐,是以黃河為載體,以黃河治理活動為軸心所構成的文化集合體。深入挖掘黃河治理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對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關于黃河治理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相關資料的整體梳理、概述等方面,對黃河治理文化的特征和時代價值方面的研究還有所欠缺,亟須進一步挖掘和探討。
黃河治理文化的概念與內涵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哺育了中華民族。黃河寧,天下平。黃河治理成為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大難題。黃河治理主要是指消除黃河水患、疏通黃河水道等治水活動,而黃河治理文化則是指人們為了保護黃河、改善河道狀況和防止洪水災害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傳統和技術手段。也有學者認為,黃河治理文化就是中華民族在治理黃河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相關的文化現象,如治水精神、治水方略、治水經驗、治水教訓等。文化學上,一般將人類的文化現象劃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大類。按照這種分類方法,黃河治理文化則可以分為治河物質文化、治河精神文化、治河制度文化。
黃河治理文化體系龐大,內容豐富,囊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核心要素,蘊含著中華民族深層的文化基因。從早期農耕生產實踐,到近代革命實踐,再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實踐,黃河治理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內容體現出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黃河治理文化作為黃河文化的重要內容,包含以上三種類型文化要素。在數千年間同黃河水患作斗爭過程中體現出的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精神,在黃河之濱黃土地上繁衍生存表現出的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精神,以及以水為師、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開疆拓土、民族融合過程中的兼容并蓄特質等,無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動體現。遍布黃河兩岸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彰顯民族氣節的《黃河大合唱》等文藝作品,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形成了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和抗戰精神等偉大精神,均在硝煙彌漫的戰事中豐富了黃河文化中的紅色基因。自194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黃以來,防洪體系不斷完善,實現70多年伏秋大汛歲歲安瀾,生態環境持續向好,流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黃河保護治理過程中貫穿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人水和諧的治理理念以及保護治理技術的不斷進步,更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黃河保護治理領域的具體體現。
黃河治理文化的歷史脈絡
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而著稱,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歷史上黃河水患不斷發生,給當地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為了治理黃河,歷代先賢和勞動人民前赴后繼,不懈探索,正是在與黃河的不斷斗爭中孕育產生了一系列的治河文化。
堯帝時代有鯀筑堤治理水患的傳說。之后,禹因勢利導,黃河終得大治,順天應人的理念成為古代最早的生存智慧。春秋時期,位于黃河下游的齊國率先修筑堤防,各諸侯國紛紛效仿,水事爭端時有發生。這一時期,水利事業在社會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諸子百家競相論水,從他們的思想言論中可見當時華夏民族對宇宙的洞悉和生命基本原則的認識。
秦統一六國之后,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將黃河改名為德水,詔令“決通川防,夷去險阻”,修建統一的黃河堤防。
西漢時期,隨著黃河決溢日漸增多,黃河堵口技術也逐步發展。漢武帝親臨瓠子口治河現場,采用打樁填堵的方法,指揮堵口成功,開興利除害先河。著名的治河專家賈讓提出了人工改河、分流洪水和鞏固堤防的“治河三策”,第一次全面地對治理黃河進行了方案論證,較完整地概括了西漢治黃的基本主張和措施,對后世的治河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東漢時期,黃河水患進一步加劇,水利專家王景采取“筑堤、理渠、絕水、立門”的治理方略,平息泛濫已久的黃河水患,實現黃河長期相對安瀾的局面,史稱“黃河安流八百年”。
此時中國古代文化科學體系已經形成,許多生產技術已趨于成熟。西漢至南北朝這700多年間,經過一系列人工運渠的開鑿,南北水運網絡已經形成。到了宋代,岸埽、龍尾埽、馬頭埽等黃河埽工出現,成為黃河堤防工程的獨特創造。明代,治河名臣潘季馴又提出“束水攻沙”的治黃策略,把堤防分為遙堤、縷堤、格堤和月堤4種類型,形成一套堤防體系,挽河歸槽,束水攻沙,為黃河治理開辟了新的路徑。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黃河治理,先后實施4次大修堤,修建了龍羊峽、劉家峽、三門峽、小浪底等干支流水利樞紐以及一大批平原蓄滯洪工程,使黃河洪水得到有效控制,實現了由“治標為主”到“標本兼治”的轉變,黃河治理技術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進入21世紀,黨和國家對黃河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綜合治理、系統治理、源頭治理,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類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統籌謀劃,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
黃河治理事業的繁榮發展為黃河治理文化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進一步豐富了黃河治理文化的內涵。
黃河治理文化的時代價值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為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理念提供了原始基因。黃河治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民本思想貫穿始終。大禹治水,是黃河治理文化中民本思想的肇始。劉向在《說苑·君道》引“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于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于民也’”。說明治水目的是“利歸于民”。作于伊洛河畔的《尚書·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讓民本思想從黃河流域延傳播散。西門豹在鄴治水,以民為本,敢作敢為,興修民渠十二條引漳水,使鄴地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隋代開通了連通黃河、長江、淮河水運的大運河,成為溝通南北的經濟大通道,密切了南北經濟聯系,極大促進了黃河兩岸的經濟社會發展。元代工部尚書賈魯臨危受命治理黃河,除水患、救百姓,通漕運、興商業,造就了朱仙鎮的繁華,人們為了紀念他,就把一條重新疏浚的河改稱賈魯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理念,蘊含著我國古代民本思想發展的精粹。自古以來,治理黃河水患,就是興利除害,造福人民。
在延安時,毛澤東主席寫下《為人民服務》,成為共產黨人最鮮紅的精神底色。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第一次離京視察就選定了黃河,并發出了“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社會主義改革發展時期,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視察黃河,對黃河保護治理提出重要指示批示,興利除害、造福人民成為這一時期黃河治理文化的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發出“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時代強音,更是閃耀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黃河治理文化蘊含的民本理念與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高度一致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繼承黃河治理文化中“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并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之中,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天地人合一”的和合理念,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歷史智慧。生活在黃河兩岸的先民,經過數千年的黃河治理開發,萌發、孕育和發展出了“以水為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哲學理念,強調要把天、地、人統一起來,按照大自然規律活動,取之有時,用之有度,和諧共生。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用有形的“水”詮釋了自然規律的“道”。大禹治水因勢利導,遵循河流的自然秉性,以“疏”代“堵”,治河13年,黃河不再肆意橫流,終歸大海。西漢治河專家賈讓在“治河三策”上策中提到,“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并“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不與水爭地”,因勢利導,依據河勢讓黃河水順暢東流,“有所休息”,就是遵循河流自然規律,實現人與黃河的共生共存。東漢明帝派王景治河,從滎陽至千乘修筑千里大堤,使河汴分流,黃河800年安瀾入海。明代潘季馴在前人治河的基礎上,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以清釋渾”等一系列治河方略,把過去單純的防洪轉移到治水與治沙相結合,同樣體現了根據自然現象的變化,“以律行事”。現代治河專家李儀祉在總結歷代治河經驗,并吸收先進科學技術的基礎上,提出了治理黃河要上中下游結合,治本與治標結合,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結合的綜合治理方針。這些在治河實踐中孕育發展的治河思想和治理方略,都遵循著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理念的歷史邏輯。
中華民族應對黃河水旱災害萌生的“天地人合一”的樸素生態智慧,為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及思想的提出和發展提供了歷史理論基點。遵循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思想,經過多年實施,黃河南岸干涸荒涼的庫布齊沙漠,逐步向生態綠洲轉化。經過持續多年的水土保持,時至今日,黃土高原一改水土流失嚴峻局面,主色調由“黃”變“綠”。“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已成為全社會廣泛共識。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民族品格塑造提供了歷史基因。從古至今,中華兒女與黃河的斗爭從未停歇,這種與自然抗爭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隨著黃河的流淌一直傳承至今,而今又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
面對滔天洪水,大禹帶領先民治理水患,雖歷經艱難萬險,仍不屈不撓,勇于抗爭,終成治水大業。大禹治水所蘊含的自強不息、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成為中華民族自強不息民族品格的最初“精神發源地”。此后從先秦到新中國成立前的2500多年間,黃河下游共決溢1560次,改道26次,北達天津,南抵江淮,中華民族始終在同黃河水旱災害作斗爭。一部治黃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與黃河水患抗爭不止的斗爭史。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手中,創造了黃河70多年歲歲安瀾的歷史奇跡,實現了黃河從被動治理到主動治理的歷史性轉變,這些都是黨領導人民不畏艱險、敢于斗爭的生動寫照。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黨領導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正在如火如荼進行,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我們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系列重大風險考驗。黨的二十大鮮明提出,“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是全黨必須牢牢把握的五個重大原則之一。要勝利實現我們黨確定的目標任務,必須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在新時代,我們要弘揚黃河治理文化中不怕困難、勇于斗爭的精神,以“刀刃向內”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斷在歷練中壯筋骨,在磨礪中強斗志,在摸打中增本領。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清廉為政”的廉政理念,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廉潔文化提供了思想土壤。廉政與否事關河政興廢,事關黃河安瀾,事關百姓福祉。在數千年的黃河治理史中,一代代剛正不阿、廉潔奉公的治黃先賢秉持清正廉潔的道德操守,權為民所賦,利為民所謀,其思想和行為成為黃河治理文化中最為璀璨的清廉之光。孔子的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如何為官,孔子給出的建議中有一條便是“欲而不貪”,反映了孔子的廉潔為政思想。林則徐在擔任東河總督期間,忠于職守,兢兢業業,“繪全河形勢于壁,孰險孰夷,一覽而得。群吏公牘,不能以虛詞進,風氣為之一變”。他還經常冒風雪核查垛料,懲處貪官,力除河弊。治河名臣栗毓美,因地制宜推出“拋磚筑壩”法,以磚代埽筑壩護堰,節省了大量河工經費。推行磚壩數年內,“三年未生一新工”“剛正廉介、夙寡嗜好”,處處盡職盡責。
廉潔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組成部分。2004年,時任黃委主任李國英提出,以河為鏡可以正發展,強調大力發展黃河廉潔文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廉潔文化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想腐的自覺。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的意見》要求把加強廉潔文化建設作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礎性工程抓緊抓實抓好。深入挖掘黃河治理文化中的廉潔文化元素,推動政治文化正氣充盈,帶動社會文化向上向善,尋求崇廉懲貪、廉榮貪恥的最大公約數,增強反腐敗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擔當。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唯治為法”的法治理念,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提供了原始法理基因。無法不成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貫穿數千年黃河保護治理史的深層邏輯是以治河法規為載體的法治理念。為實現對黃河的有效治理,歷朝歷代都制定了有針對性的典章制度,其傳承有序的法治理念為深入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提供了法理支撐。
秦統一六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規,其中與黃河防洪有關的法規條文有“決通川防,夷去險阻”。西漢時期的治河法規在設置治河官員、河堤防守隊伍組織和經費等方面都有相關規定,并對黃河河堤修守職責設置了嚴格的刑法規定。唐朝頒布了我國最早的水利管理法規《水部式》,對組織人員、堤防檢查維修制度、修守管理報批制度等作出規范規定。金代頒布的《河防令》,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針對黃河治理頒布的法規,對河防要事都作出了明確規定。元代的治河法規,較為詳細地反映在《通制條格》中。《明律》將有關水事違法條文編入《工律》,分《營造》與《河防》兩卷,其中《河防》是首次創立,同時明代還制定了黃河“四防二守”制度。清《康熙年間治河》《道光二十九年的防汛章程》是清代關于黃河筑堤和防汛的重要規定,清代的防洪法規在《清會典》《大清會典事例》中都有比較集中的反映。民國時期,1942年頒布的《水利法》,對黃河保護治理等工作也有相關規定。新中國成立后,依法治河理念貫穿始終。為推進黃河保護治理事業,相繼制定出臺了《黃河水量調度條例》《黃河防汛管理工作規定》等一系列制度條例。2023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黃河保護法》,是我國第一部針對黃河流域的基礎性、綜合性和統領性的專門法律,以法律形式對黃河保護治理作出制度性安排,實現“江河戰略”法治化。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大一統”的共同體意識,為增強民族認同感、維系國家統一安全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撐。梳理總結中華民族與黃河水患作斗爭的數千年歷史過程,可以得出“國家太平,黃河安瀾綿延;國家動蕩,黃河水患不止”的歷史結論。大禹治水“分九州”,將原本相互隔絕獨立的聚落群體融合為相互依存的實體,并誕生了最早的國家形態——夏朝。西漢政權強而有力,黃河幾次決口均得到有效堵復。而在魏晉南北朝,乃至后期朝代更替戰爭紛紛之時,黃河得不到有效治理,往往會因河道改道而堤決水潰。同時,各方勢力為了自身利益相互掣肘,也嚴重制約了對黃河水患的治理。除了黃河泥沙沉積增多導致的河道抬高等自然因素外,“以水代兵”等人為破壞黃河河道的事例也不勝枚舉。明清時期,對黃河治理實行黃淮運綜合治理,關注黃河、淮河與運河三者之間的治理關系,綜合統籌運用鑿設新水道以分水等多種治水手段,實現黃淮運的和諧統一。
新中國成立后,提出了興利與除害相結合的治河方略,推進黃河上中下游綜合治理。20世紀90年代,黃河下游斷流不止,黃河遭遇嚴重生存危機。1999年,按照國務院授權,黃委對黃河水量實施統一調度,首開大江大河統一調度先河。進入新時代,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提出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統籌謀劃,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統一”的思想依舊是新時代黃河保護治理邏輯之一。
我國最早國家形態的形成源于對水的治理需求和實踐。因水而成的家國情懷,也伴隨了黃河保護治理歷史全過程。而因黃河治理而形成“大一統”觀念,成為中國民族精神中的主流意識。
因河而興的黃河流域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地抱在一起”,對中華民族“同根同源”這一身份的認同感不斷深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更加鮮明有力。
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著“應物變化”的創新理念,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了思想動力。大禹汲取前人治水的教訓,創造發明了測量工具,提高了治水的技術水平,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疏川導滯”。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于河水泛濫之時,反其道而行之,收縮河道,淤灘固堤,借流沖沙,保證了黃河的安瀾。清朝靳輔、陳潢等人,在前人治河的基礎上,著眼全局,統籌治理黃河、淮河和運河,取得積極成效。清朝河道總督吳大澂在進行鄭工堵口時,注重西方科技的運用,曾嘗試使用鋼筋混凝土進行堵口。新中國治理鹽堿地,排水沖鹽堿,淤灌造糧田,將黃河中下游寸草不生的“牛皮堿地”變成了廣袤的糧田。
新中國成立后,治河技術也不斷應時而變,從早期的“寬河固堤”“蓄水攔沙”,到如今“攔、調、排、放、挖”的立體防護模式,治河技術賡續不斷的創新創造成為實現70余年黃河安瀾的密碼。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黃河治理文化中蘊含的革故鼎新、應物變化、創新創造思想,不斷推進治河方略和技術發展演變,并在治河實踐和社會發展中得到拓展延伸,賡續不斷。深入推進創新型國家建設,要傳承好黃河治理文化中的創新理念,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研發,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黃河治理文化蘊含的民本理念、和合理念、斗爭精神、廉政理念、法治理念、共同體意識、創新理念等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進入新時代,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更應全方位深入挖掘黃河治理文化的豐富內涵,結合新時代創新發展黃河治理文化,讓其迸發出新的文化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堅定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文脈,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