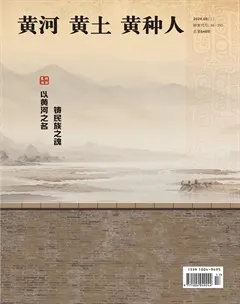黃河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傳播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被尊為“四瀆之宗”“百泉之首”。黃河和黃土孕育了河湟文化、關中文化、河洛文化、燕趙文化和齊魯文化。黃河文化是發生在黃河流域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總和。它不僅包括這一流域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等經濟內容,還包括人們的社會規范、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等。
黃河文化的形成及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黃河文化源遠流長,凝聚了深厚的歷史積淀和人文精神,是中華文化的主體。從秦漢至宋代,黃河流域的文化不僅達到了中國歷史時期的頂峰,且在世界范圍內也居于領先地位,并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文化的代表。這一時期的黃河文化形態多姿多彩,內容豐富厚重,并蘊含著巨大的創造力。
黃河流域是世界農作物繁育中心和世界早期動物馴化中心之一。黃河文化隨著原始農業的產生而形成,是在黃河流域孕育生長起來的旱地農業文化。新密李家溝遺址農業定居文明,發現了距今10500—8600年前的石器、陶器和豬、馬、牛、羊等動物標本,表明中原地區的原始農業已經孕育產生,該區域有可能已培育了粟、黍等農作物。位于黃河與淮河之間的嵩山地區,應是中原農業起源的中心區域,也是中國農業起源的核心地帶。中原地區的農業起源和發展,對中華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對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裴李崗文化是距今8000—7000年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裴李崗遺址中發現有墓葬、房基、灰坑、陶窯等,出土器物有斧、鏟、鐮、石磨盤、磨棒、三足陶器,還有碳化的粟、棗核、核桃殼,以及豬、羊等動物的遺骨。裴李崗文化有關遺存中出土了不少農業生產工具,為早期農耕文化的發達提供了實物證據,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盤、石磨棒,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糧食加工工具。
大河村仰韶文化上限距今6800年左右,下限距今4400—4100年。大河村遺址發現了大量的彩陶,大河村房屋建筑遺跡所展示的房屋建造技術被認為奠定了中國傳統建筑的基礎。同一時期,黃河上中下游與裴李崗文化年代大致相當的考古學文化還有老官臺文化、磁山文化和北辛文化,其中發現有聚落遺址,炭化粟粒、黍、油菜籽,磨制石器,等等。黃河流域農業的產生,使得黃河流域的先民最早進入定居的農耕階段,他們在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不僅創造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化,而且培育了黃河文化的萌芽。
繼裴李崗文化之后,中國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是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發展起來的。仰韶文化繼續發展至龍山文化,黃河中下游以中原為核心的史前文化進入到快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中原地區逐漸發展成為東亞大陸文化的核心區域。黃河中下游地區龍山時代形成的文化成果為夏商周三代早期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河東位于今山西西南部,上古時期堯、舜、禹的都城皆在河東。河內為黃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廣大地區,歷史上為商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河南指晉、豫兩省黃河以南,周公在此營洛邑、成周與王城,是周人活動的主要區域。夏商周三代都邑均在河洛地區,三代文明及諸侯國文明是形成黃河文化的淵源和基礎。
從秦漢隋唐至北宋,是黃河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一直是中國的經濟重心所在。秦漢以來,鐵器被廣泛使用,鐵犁和牛耕得到推廣,推動了耕作技術的進步。伴隨農業工具技術的發展,黃河流域的耕、耙、耢防旱保墑技術體系形成。農業的發展離不開天文歷法,這促進了黃河流域成為中國天文學的發源地,也是天文學最為興盛的地區。如在這里形成了二十四節氣。以天文學、數學、物理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科學技術在宋元時期發展到了高峰。黃河流域歷代先民在治理洪水、除害興利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水利科技知識。如對黃河信水的認識、“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堤岸的修守制度和技術、黃河的埽工技術等。古代中國以瓷器制品享譽世界,而瓷器脫胎于陶器制品工藝的不斷進步。從史前時期直至北宋,地處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陶瓷制造技術以其工藝精良、高雅秀麗的特點長期引領時代風潮。紡織工藝作為黃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發軔到基本定型都是在黃河流域完成的。如以麻布為代表的植物纖維紡織技術,以絲綢為代表的動物纖維紡織技術、紡織物染色印花技術和紡織機具在世界上都占據領先地位。歷代王朝以黃河流域為中心,逐步構建出完善、緊密的水陸交通網絡,實現了政令傳達的暢通及物資運輸、貿易往來的便捷迅速,形成了一批區域政治、商業中心。黃河流域金屬冶煉技術以冶鐵技術為代表,在漢代以后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廣泛應用在農業、交通工具、兵器、建筑構件、生活用品鑄造等領域,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中原地區由于地處水陸要沖,交通便利,農商發達,礦產資源豐富,冶鐵技術在古代中國長期處于領先地位。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等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的發祥地都在黃河流域。王朝都城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西安、洛陽和開封這3座古都皆位于這一區域。在制度層面,產生了相對集中的政治制度。秦漢實行三公九卿制,皇帝執掌國家大權,以三公輔佐,九卿分理庶政。隋唐時期,演變為三省六部制。封建國家的治理能力較前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黃河文化通過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斷補充和豐富自身。秦朝統一中國,建立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和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漢民族正式形成,黃河文化也因此獲得更好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民族大遷徙和民族大雜居,出現了規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黃河文化在這一時期吸收了匈奴、鮮卑、羯、氐、羌等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化以及江南文化。隋唐時期,黃河文化在對少數民族文化采擷吸收同時,與當時世界上7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開了文化交流,使自身文化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元明清時期是黃河文化的衰微期。隨著宋室南遷,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隨著都城遷移,黃河流域經濟重心地位的喪失,以及理學思想僵化導致的社會禁錮,黃河文化失去了昔日吸收、消化異質文化的自信開放特色,逐漸走向衰落,文化模式保守定型,缺乏創新活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啟了中國發展的新局面。通過對黃河流域環境的治理,社會秩序得到恢復,民生經濟日新月異,教育文化建設有了長足發展,為黃河文化的再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人文底蘊。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現代化建設,給黃河文化的再生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過程中,通過實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保護傳承弘揚以黃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展示對傳統思想價值體系的認同與尊崇,讓黃河文化歷久彌新,適應新時代發展的需求,推動黃河文化再鑄輝煌。
黃河文化的傳播
夏商周早期,黃河文化的核心位于黃河中游晉南、豫西、豫北交界區域,司馬遷《史記》稱為“三河(河東、河南、河內)天下中”,是“中國”概念的發源地。隨著西周禮樂文明、宗法制度的定型,以及其后秦、漢、唐等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和地理疆域的拓展,黃河文化不斷向北、向南輻射擴散,同化吸收異質文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壯大奠定了堅實基礎。
匈奴是古代中國北方著名的游牧民族。西漢建立后,與匈奴維持了長時期的和平與物質、文化交流,黃河文化逐漸滲透擴散至塞北地區,開啟了匈奴漢化的歷史進程。東漢時期,匈奴再次分裂為南、北匈奴,南匈奴率先歸附并逐漸被漢族同化,改漢姓、遵漢俗,漸漸同化于以漢族為主體的歷史進程之中。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歷代君主多仰慕黃河中下游地區先進的漢族文明,并與當地漢族士大夫聯姻。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實施了全面漢化的改革措施。把首都由北方平城(大同)遷至黃河流域腹地洛陽;禁胡語而說漢語,改鮮卑姓為漢姓,鼓勵上層官僚與漢族通婚;采用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制度和賦稅體制。這些措施,大大促進了中國北方地區的民族融合,北方少數民族吸收了以漢族為主體的黃河文化、精華,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進步和社會穩定,黃河文化亦吸收了異族文化的新鮮血液,進一步煥發生機活力。
楚國雖然被中原黃河流域諸國視為南蠻,但其始終以周天子封臣身份開拓疆土,遵守宗周禮法制度并不定期地朝貢,融合同化南方諸民族,使楚國文化充滿生機和活力,亦間接使中原黃河文化向長江流域不斷擴散傳播。秦滅六國,在中國首次形成了書同文、車同軌的大一統局面,把黃河流域關中地區的秦國制度文化在全國推行。西漢建立后,在政治制度上承襲秦制,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秦代的官僚體系和法治思想;但吸取秦亡的教訓,在治國思想和文化上亦融合了楚制和楚文化,形成了長期穩定的社會局面。秦亡后,舊將趙佗割據嶺南自立,建立南越國。趙佗原為恒山郡真定縣(今河北正定縣)人,其在嶺南實施漢越融合的政策,鼓勵漢族軍士和當地婦女通婚,并把黃河流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制度文明推廣實施。
黃河文化以開闊的胸懷接納、吸收、消化異質文化的同時,又以強大的力度向外輻射,其中漢字、儒學、律令、天文歷算、醫學等科技成就影響深遠。中國和朝鮮半島山水相依,歷史文化淵源深厚。早在先秦時期,漢字、農桑已輸入朝鮮半島。《漢書·地理志》記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把黃河流域先進的農耕文明推行到朝鮮半島,提高了當地的生產力水平。推行“八條之教”,以中國禮制文明教化當地百姓,禁止民眾擅殺、偷盜,制定婚喪嫁娶禮儀,使得朝鮮民無盜賊,崇尚信義,夜不閉戶,民風淳樸。戰國秦漢之際,由于戰亂,黃河流域大批人遷徙朝鮮半島。隋唐時期,新羅選派大批留學生學習中國的物質文明、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社會風俗,等等。朝鮮王朝時期,以朱子為代表的理學成為建國指導思想,朱子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流思想,并成為此后朝鮮王朝的官方哲學。在各種禮儀制度的規范下,社會秩序更加穩定,在朝鮮社會形成了崇尚理學的風俗,影響至今。
大約在晉代,漢字經朝鮮傳播到日本。隋唐時期,日本為吸取中國先進的文化、技術,積極而全面地向中國學習,先后派出了5次遣隋使和13次遣唐使,并有留學生和留學僧同行,積極學習中華文明,建立律令制國家。7世紀,日本仿照唐朝的教育制度,中央設國學、地方設學校傳授經學、律學、漢文學、書法、算法等。主要體現在日本對以黃河文化為核心的唐朝文化的主動學習。日本在封建社會時期持續關注并引入中華文明成果,從漢字到唐詩,從音樂到繪畫,從儒家典籍到禪宗思想,從服飾起居到建筑樣式,都帶有鮮明的唐風遺韻。
中南半島的其他國家和南洋群島國家,由于海陸交通便利,從物質器具、科學技術、語言文字、藝術宗教到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典章制度,黃河文化曾大量且廣泛地傳播到東南亞地區,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嶺南設桂林、南海和象郡,自此開啟了越南的“北屬”時期,也標志著中國封建王朝的郡縣制度在越南生根發芽。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在相當于今天越南的中部和北部地區設立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開啟了對越南地區的實質開發。最顯著的表現就是,兩漢時期,中國封建王朝在越南大力推行禮教,儒家思想和漢字開始傳入越南。儒家思想逐漸成為越南封建時代的核心思想,貫穿于越南的各個領域。漢字也作為傳入越南社會的第一種文字,逐漸成為越南的官方正式文字。從秦朝到唐朝的1000余年中,越南一直是作為中國的藩屬國而存在,中國封建統治者在當地大力推行郡縣制度。在駐地官員及大量流寓越南的中原人文學者、商人、農民以及手工業者的努力下,先進的漢文化得以在越南廣泛傳播。這一時期在越南歷史上被稱為北屬時期,也是中國文化深入越南北方的重要時期。
從秦漢時期起,漢字開始在越南地區逐漸傳播和發展。自秦漢至隋唐,越南作為中國南疆的郡縣,思想文化上逐漸接受了儒家思想。如《后漢書》記載東漢時期交趾太守錫光、九真太守任延,“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促使當地由“人如禽獸,長幼無別”的原始狀態邁入儒家禮法文明體制之中,百姓感激敬畏,生子后乃至以其姓冠名。
在唐代,粟特人將中國的造紙術、絲綢工藝、金銀器、陶器等傳入中西亞、歐洲。黃河文化還影響遼河流域,穿過西伯利亞,通過白令海峽與北美、中美產生了聯系。
黃河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主體,千百年間已深深地影響東亞、南亞,并逐漸流傳,輻射到全世界。以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科學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對整個人類文明的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黃河流域的科學技術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重在為農業社會服務的傳統科學技術,它代表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水平,是中華傳統科技文明的象征;它對周圍地區(如長江、淮河流域等)的科技發展產生直接影響,推動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科技進步,對人類文明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
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汲取中國智慧、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不斷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創造中華文化新輝煌。”
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有助于正確認識中華民族的根、鑄牢中華民族的魂。黃河文化的根和魂表現為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主要在黃河流域,表現在中華民族誕生、發展和融合的核心地區在黃河流域,也表現在中國城市和商業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區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更表現在中華傳統思想起源和傳承的核心區在黃河流域。
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有助于挖掘黃河文化精神內涵。在中國史前文化乃至進入文明社會的發展進程中,黃河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黃河文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堪稱中華歷史文明的核心。黃河流域作為文化交融之地、文明輝煌之鄉、人文薈萃之區、精神鑄造之源,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堅持文化傳承創新,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結合起來。
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有助于深化黃河歷史文化資源開發,推進文化產業健康發展。打造優勢文化產業,大力發展文化旅游,如古都文化游、尋根拜祖游、武術文化體驗游等。汲取黃河文化優秀素材發展文化演藝、影視動漫和文化會展,創新表現形式,打造文化精品。精準定位、深入挖掘,打造有特色的黃河文化產業園區精品等。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是事關民族復興和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有助于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