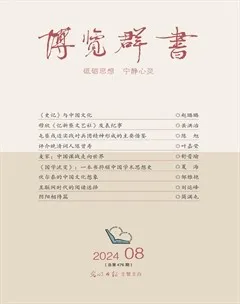屯墾戍邊實踐對兵團精神形成的主要借鑒
自漢代開始,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并陸續開展屯田,形成了屯墾戍邊新局面。漢朝以后,歷代中原王朝時強時弱,和新疆的關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的管治時緊時松,但任何一個王朝都把新疆視為故土,行使著對該地區的管轄權。“屯墾興,則西域興;屯墾廢,則西域亂。”歷史實踐證明,歷朝歷代在新疆開展多種形式的屯墾戍邊,對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文化交流,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兵團精神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屯墾戍邊實踐中凝練產生的,歷朝歷代屯墾戍邊經驗,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的歷史支持,為兵團精神的形成注入了豐富的歷史內涵。
歷朝歷代的屯墾戍邊實踐
西漢前期,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區,并不斷進犯中原地區。漢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軍事和政治措施反擊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派遣張騫兩次出使新疆,聯合月氏、烏孫等共同對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3次出兵重創匈奴,并在國內其他區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漢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漢朝細君公主遠嫁烏孫昆莫獵驕靡時,在烏孫國的眩雷(今伊犁河谷)即開始了屯田,史稱赤谷屯田。公元前101年,漢駐軍屯田于輪臺、渠犁(今輪臺和庫爾勒)兩地,并置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務。公元前60年,控制東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漢,西漢統一新疆,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立都護府烏壘城(今輪臺縣境),總領天山南北兩道,屯田遍及西域各地。輪臺、渠犁、焉耆、龜茲(庫車)、車師前(吐魯番西)、樓蘭(今羅布泊周圍)、伊循(今若羌縣東米蘭)、姑墨(阿克蘇)、赤谷(烏孫國都,今伊塞克湖東南)等地都是重要屯田區。公元前68—62年,西漢相繼派兵駐車師交河,設置戊己校尉專司屯田。西漢時期屯田近70年中逐漸形成都護、戊己校尉、曲侯和屯長四級管理體制,直屬中央大司農管理,屯田士卒兩萬余人。公元8年,王莽篡國建立新朝后,西域大亂。公元25年,劉秀建立東漢,沿襲西漢管理,繼續設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管理西域,屯田區擴大到伊吾廬(今哈密)、金滿城(今吉木薩爾縣)、柳中城(今鄯善縣魯克沁一帶)、高昌壁、疏勒(今喀什疏勒縣)。公元123年,東漢改西域都護府為新疆長史府,繼續行使管理西域的職權。
三國曹魏政權繼承漢制,在西域設戊己校尉。西晉在西域設置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管理軍政事務。三國兩晉時期,北方匈奴、鮮卑、丁零、烏桓等民族部分內遷并最后與漢族融合。327年,前涼政權首次將郡縣制推廣到西域,設高昌郡(在今吐魯番盆地)。從460年到640年,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建立了以漢人為主體居民的高昌國,歷闞、張、馬、麴諸氏。魏晉南北朝的將近400年內,中原政治勢力此消彼長,對西域的管理雖相對削弱,但派遣官吏、推行中央政令從未中斷過。隋代,結束了中原長期割據狀態,擴大了郡縣制在西域地區的范圍。突厥、吐谷渾、黨項、嘉良夷、附國等周邊民族先后歸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理大為加強,先后設置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統轄天山南北。于闐王國自稱唐朝宗屬,隨唐朝國姓李。宋代,新疆地方政權與宋朝保持著朝貢關系。高昌回鶻尊中朝(宋)為舅,自稱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貢。元代,設北庭都元帥府、宣慰司等管理軍政事務,加強了對西域的管轄。1251年,西域實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權設立哈密衛作為管理西域事務的機構,并在嘉峪關和哈密之間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蒙古、沙州6個衛,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務。清代,清政府平定準噶爾叛亂,中國西北國界得以確定。此后,對新疆地區實行了更加系統的治理政策。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實行軍政合一的軍府體制。1884年在新疆地區建省,并取“故土新歸”之意,改稱西域為“新疆”。
隋代隋煬帝即位后積極經營西域,于公元610年在西域設伊吾郡,在伊吾大興屯田。唐朝在西域的屯田始于公元630年,截至公元791年,歷時161年,以軍屯為主,有軍就有屯,在11個屯田區中,有7個是西域戰略要地,主要分布于伊州(今哈密地區)、西州(吐魯番地區)、烏壘(今輪臺縣策大雅鄉)、于闐(今和田附近)、庭州(吉木薩爾縣一帶)、輪臺(唐輪臺、烏魯木齊南部烏拉泊古城)等地。東起巴里坤,西至楚河畔,南到昆侖山,北至準噶爾,屯田遍及天山南北。唐朝設置支度營田使專管西域屯田,屯田人數5萬余人,共屯田3.33萬公頃,西域屯田出現繁榮局面。唐朝中道衰弱之后,以至五代、兩宋時期,西域屯田相繼衰微結束。
元代新疆屯田長達20年,軍屯與民屯并舉,后因撤出軍隊,屯田遭到破壞,以至明代逐漸廢弛。主要分布于哈密力(哈密西北)、別失八里(今吉木薩爾縣北護堡子)、滕竭兒(今阜康)、亦里黑(今伊寧)、曲先(庫車)、可失哈爾(今喀什)、斡端(和田)、阇輝(且末)等地。有屯軍2萬余人,屯民3.7萬戶,屯田6.6萬公頃。
清朝時期,新疆地區屯墾空前發展。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政府派蘇德爾募兵到哈密、巴里坤和木壘等地屯田。1725年,清軍在阿爾泰舉辦屯田。后屯田范圍遍及南北疆。清代屯田共經歷195年,屯田主要分布在東疆地區巴里坤、哈密和吐魯番3地;北疆地區木壘、奇臺、吉木薩爾、阜康、烏魯木齊、昌吉、呼圖壁、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今烏蘇)、晶河(今精河)、伊犁、塔爾巴哈臺(今塔城)和阿爾泰等13地;南疆地區喀喇沙爾(今焉耆)、新平(今尉犁)、卡克里克(今若羌)、庫車、阿克蘇、烏什、巴爾楚克(今巴楚)、喀什噶爾、葉爾羌以及和田等地。1840年以前,清朝前期在新疆共有屯丁12.67萬人,屯田20萬公頃。1840—1850年,布彥泰、隆迎阿任伊犁將軍,新疆屯墾掀起第二次高潮,先后墾荒83萬公頃。1864年后,新疆爆發戰亂,浩罕國阿古柏和沙俄乘機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區,屯墾事業遭到毀滅性破壞。1878年,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1884年建立甘肅新疆行省,左宗棠、劉錦棠大力倡導戍屯,新疆屯墾事業出現第三次高潮,1905年全疆新墾荒地64萬公頃,至1911年辛亥革命時,耕地增至70.3萬公頃。屯墾事業的發展促進了新疆經濟的復蘇和文化的發展,鞏固了祖國邊疆。
1912年新疆積極響應辛亥革命,1912—1928年,新疆發展民屯,使新疆耕地由70.3萬公頃增加到80.1萬公頃,基本解決全疆軍民衣食問題。1928—1933年,新疆屯墾遭到極大破壞。1933—1944年,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大力支持下,新疆執行兩個三年計劃,建立屯墾委員會,第一次創辦機械化農場,興建水利工程,使耕地從30.8萬公頃增加到112萬公頃,糧食產量增加到58.65萬噸。1944—1949年,新疆屯墾事業再次衰落,北疆屯墾遭到破壞,南疆屯墾陷入癱瘓。
歷朝歷代屯墾戍邊的實踐經驗
作為歷朝歷代治國安邦的基本國策,屯墾戍邊彰顯了胸懷家國的情懷與擔當。中華民族一直是一個崇尚愛國的民族,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動力。歷朝歷代屯墾戍邊史就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史,是無數戍邊人無私奉獻、為國守邊的生動篇章。屯墾軍民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扎根邊疆,肩負起保家衛國、屯墾戍邊的歷史使命,為屯墾戍邊實踐持續凝聚內在力量,為國家在邊疆地區筑起一道歷經兩千多年的安全屏障。歷朝歷代中央政府都把穩定新疆、固邊戍邊、保衛領土作為國之大事而倍加關注,派出大量兵力常駐新疆,如漢朝駐新疆的軍隊長期保持在數千人左右。唐朝武則天時期,僅安西都護府直接管轄的“漢兵”就達3萬余人,其他歸都護指揮的少數民族軍人尚未計入。乾隆統一新疆后雖然實行了“北重南輕”的軍事布防戰略,但據統計,南路包括哈密在內的駐軍人數也有8000余人。這些常駐新疆的軍隊,平時操練屯田,戰時則行軍戰斗,為穩定邊疆社會局勢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加上不同歷史時期的民屯,形成了維護新疆穩定,行使國家管轄權的重要保障力量。
數千年來無數中華兒女奮斗拼搏的歷史已經把勤勞勇敢沉淀為一種強大的民族精神。這種勤勞勇敢的優良傳統使屯墾軍民在面對邊疆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嚴峻的社會形勢時,不畏艱險,開拓進取,將亙古荒原變成良田,創造了人類開發史上的一個個奇跡。這是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的傳統在開發建設邊疆中的生動體現。歷朝歷代屯墾戍邊促進了新疆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農業開發,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當地政治、經濟、社會穩定,為新疆地區發展以及與內地大規模、持續性的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質條件。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就是真實寫照。兩漢時期,內地各類屯墾人員為新疆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工具,如先進的冶煉技術,極大地提高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水平。隋唐時期,內地水利灌溉工程技術、大型石碾及其他食品加工工具、食品制作技術及手工業技術也被帶到新疆。元代,大量內地農民和能工巧匠遷入新疆,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糧食產量大增,不僅滿足了本地軍民的糧食需求,而且還成為遠征中亞和歐洲的蒙古軍隊的重要糧草供應基地。在清代,農業經濟在天山北部得到快速發展,結束了“南糧北運”的歷史。同時,大量內地人員遷入新疆進行兵屯、民屯等,不僅直接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而且還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為新疆近代經濟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我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華民族具有強大凝聚力、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歷朝歷代屯墾軍民始終堅持發揚民族團結、和睦互助的優良傳統,同各族人民共同開發祖國遼闊的疆域,共同書寫悠久的歷史,共同創造燦爛的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的民族精神。在屯墾戍邊歷程中,歷朝歷代屯墾軍民與邊疆各族人民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形成的共同理念,不斷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與發展的歷史根基。新疆歷史上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民族團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歷朝歷代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墾戍邊,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屯墾戍邊體現的是國家行為,代表的是國家意志,貫徹的是國家認同理念,執行的是國家政治軍事戰略。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是維護好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國家的最高利益,不僅捍衛了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保護各族人民不受外來壓迫,促進了邊疆各族人民的共同發展,提高了當地的生產生活水平,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和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提升。這種在共同生產生活中凝聚形成的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根深蒂固,形成了磅礴的團結奮進、和睦互助的力量。
自古以來,由于地理差異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新疆和中原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呈現多元狀態,存在南北、東西差異。自漢代以后歷經各代,新疆和內陸地區通過遷徙、聚合、戰爭、和親、互市等,經濟聯結和文化交流越來越緊密,屯墾戍邊更為這種溝通聯結增加了動力、注入了活力。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區就是中國向西開放的門戶,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傳播的重地,這里多元文化薈萃、多種文化并存,比如道教從中原地區傳入新疆,佛教從印度經過新疆傳入中國,都是最好的寫照。中原經濟文化和新疆經濟文化長期的互通有無,既推動了新疆的發展,也同樣促進了中原地區的發展。盤點2000多年的屯墾戍邊史,其中蘊涵的開放包容和融合發展的歷史內涵,為包括先進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融合、發展提供了歷史舞臺,不斷豐富著新疆和內陸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渠道、載體、形式,使兩者之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兵團精神對數千年屯墾戍邊實踐經驗的繼承和發展
愛國主義精神是兵團精神形成的內核,是兵團精神的根和魂。在兵團精神形成過程中,愛國主義更多被聚焦于確保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以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實現,表現在實踐中就是兵團承擔著屯墾戍邊的職責使命。愛國主義精神貫穿于兵團發展壯大的各個歷史階段,貫穿于兵團精神形成的各個階段,在長期實踐中變成了兵團人的普遍價值認同。這種價值認同超越了時空界限,是對扎根邊疆、奉獻邊疆的生動呈現,有力刻畫出“我為祖國守邊疆”的精神印記,實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愛國主義的升華延續,使兵團精神從形式到內容傳承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比如,早在兵團艱苦創業之初老一輩軍墾人“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真實寫照以及新時代兵團改革發展穩定事業中涌現出的“七一”勛章獲得者——邊境線上的“活界碑”第九師一六一團職工魏德友、“一生只做一件事、我為祖國當衛士”的第十師北屯市一八五團職工馬軍武等愛國戍邊先進典型,都是用最平凡的堅守、最質樸的情感、最熱血的實踐生動詮釋了愛國主義的忠誠大義。
在黨中央大力開發建設邊疆的號召下,廣大兵團人從祖國四面八方朝著共同的理想會聚一堂,用青春年華、聰明才智,為屯墾戍邊、維穩戍邊事業發展、為民族團結和睦、為邊疆繁榮穩定作出了特殊貢獻。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大批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山東、浙江、江蘇等地的知識青年,告別繁華都市、支援邊疆建設,把新的思想、文化和風尚帶到兵團,為兵團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人力和智力支撐。這些支撐的背后反映出一代又一代兵團人埋頭苦干、不計得失的奉獻精神,即聽從黨的召喚,扎根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正確處理國家與集體、集體與個人的利益關系;牢記全心全意為新疆各族人民謀利益的宗旨,努力贏得普通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等。廣大兵團人在屯墾戍邊、維穩戍邊偉大事業中堅定履行自身職責和義務,執著于無私奉獻的道義人格,為其所可為、為其所當為,接力抒寫出新的歷史奇跡,使得兵團體制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殊存在,為兵團精神的形成注入了豐富內涵。
對于兵團而言,艱苦創業有著十分特殊和深刻的含義。一方面,嚴酷的自然環境極大制約著兵團的現實發展,搞開發建設意味著要付出更為艱苦卓絕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偏遠、物資相對匱乏,更需要兵團人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艱苦創業成為發展兵團事業的必然選擇,作為一種精神標識深深融入兵團人的血脈,貫穿于兵團發展壯大全過程。兵團從創業時起就提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仗劍扶犁,情滿天山”“戈壁灘上蓋花園”等理念。在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堅韌意志力和頑強戰斗力的支配下,兵團人用勤勞雙手接續創造出舉世矚目的塞外綠洲文明,彰顯出“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奉獻”的可貴品質。兵團人正是憑借著迎難而上、勇不退縮的精氣神,白手起家,在天山南北、塔克拉瑪干和古爾班通古特兩大沙漠邊緣以及自然環境極其惡劣的邊境沿線設點布局,歷經無數艱難困苦在荒漠上開辟出一片片適宜生存的綠洲,建立起現代農業、工業和新型城鎮,創造了人類改造戈壁沙漠的奇跡,為新疆繁榮穩定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兵團的艱苦創業史,不僅為兵團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價值引導,同時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尚勞勤行”“以勞為美”等理念的進一步繼承和發揚。不論多么艱辛的環境,兵團人始終堅定認為革命理想終將實現,始終堅持正向價值,以樂觀主義精神面對挫折失敗,即便是“屢戰屢敗”,也要“屢敗屢戰”,在曲折發展中不斷壯大綜合實力、加快經濟發展、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為實現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而不懈奮斗。特別是老一輩軍墾人,寧可苦了自己這一代,在開發建設邊疆中“與風沙同行,與野獸為伴”“吃粗糧、喝咸水、住窩棚”、不畏“水到頭、路到頭、地到頭”,與天地斗、與地斗,其樂無窮,創造出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提升生產力水平,改善各族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這種無私奉獻中透著樂觀主義的精神狀態,正是彰顯了歷朝歷代戍邊人堅定的信仰,充沛的激情,以及強有力的執行力,堅守“一定能勝利”的信念。
長期以來,廣大兵團人始終飽含開拓進取之心,將先進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實踐全過程各環節,特別是在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探索中,積極發揚敢于拼搏、勇于爭先的時代精神,先后創造出兵團機械化大農業、農墾特色庭院經濟、全民小康連隊等一系列新鮮事物,不僅開創了新疆現代大農業的先河,也開創了新疆現代工商建交和科教文衛等事業的先河,實現了沙漠變綠洲、荒蠻變文明的巨大成就。與此同時,五湖四海兵團人又源源不斷把祖國各地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引入新疆,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多元的兵團文化,為促進各民族生產生活水平提升、增進各民族團結協作互助注入了強有力的精神動能。兵團事業發展始終與時代潮流同步,實現了科學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機統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兵團人敢于拼搏創新,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大無畏勇氣推動兵團黨政軍企“四位一體”特殊體制機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機融合,建立并完善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雙層經營體制,經濟發展活力得到快速提升;在工業、商業、服務行業改革企業領導體制,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按照“全民、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在堅持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前提下,積極支持興辦集體工業、商業,鼓勵和扶持職工個人辦廠、設店、開作坊,改革單一國有經濟結構,順應了改革開放后國內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大趨勢。與此同時,兵團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對地方各族群眾起到了積極示范帶動作用,為構建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樹立了良好榜樣。這一系列敢破敢立、敢闖敢試的一往無前的開拓進取精神,正是歷朝歷代屯墾戍邊團結奮進、和睦互助、開放包容、融合發展歷史內涵的生動展現。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文化發展促進中心紀委書記、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