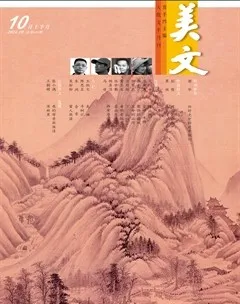對面是書柜
一
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子里,有一張靠著窗戶的書桌,一個擱放復印傳真一體機的木架,一個能夠伸縮調節的單人沙發,旁邊是一個方形小茶幾,擱放水杯和零碎雜物。此外的地方便都是書柜。六個直抵天花板的書柜,嚴嚴實實地遮住了兩面墻,完全相同的樣式,普通的刨花板材,一個書柜的中間橫隔板被壓得彎曲了,另一個書柜門的合頁損壞變形,難以關嚴。
這是我的書房,布置毫無特色,書柜材質也普通廉價,無法與一些朋友們或者高檔或者充滿設計感的書房相比。但我并不曾感到慚愧惶惑。就好像在一家餐館里享受了足夠豐盛的美味,為什么還要在意杯盞不夠精美呢?
每天下班后,回到這間屋子,站在兩排書柜前,望著滿柜的圖書,真正有一種放松之感,仿佛倦鳥歸巢,悠然愜意,心滿意足。盡管這很可能會被人嘲笑為書生迂腐,我卻是真實地享受這一點,其確鑿之感絲毫不用懷疑,就像閱讀一本新書時,耳邊的沙沙聲和手指翻動紙頁的細膩的觸覺。
飲水思源,有時我會想到它們匯聚到這里的過程。
書的積累,是在數十年的漫長時光中漸次完成。它們從不同的地方來到這些書柜里,仿佛每年征兵季從四面八方奔赴同一支部隊的士兵。但接兵的人會記得,這些相互之間原本素不相識的新兵,分別來自哪一個省份,是城市還是鄉村。有一些書,我也依稀能記得購買時的環境背景,周邊街巷的模樣,不同季節里光影閃爍的情形。
有一些書的扉頁上,很鄭重地記著購書的時間和地點,它們對應的是個人藏書史的早期階段。這本詩人戴望舒翻譯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散文集《西班牙小景》,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次旅行的收獲。那時我從北京乘坐了幾十小時的火車到福州,換乘長途汽車到廈門,然后繼續一路南行直到廣東汕頭,為了去看一看建立不久的汕頭經濟特區。我在福州西湖邊上的一家書店,購得這本薄薄的小書,在此后幾天的旅途中隨時翻上幾頁。當時我參加工作不久,新的生活正在眼前緩緩展開,時常會感到內心激情涌動,對作品中彌漫著的時光流逝的憂傷,麻木凝滯的生活的哀愁,一種源自古老文化的衰弱無力感,還有一層隔膜,直到二十年后重讀時方才有了深切的感受。當時印象更深的,是在泉州街頭看到的惠安女的奇特的打扮,是車窗外低矮的丘陵上連綿無盡的荔枝樹,綠油油的葉子在陽光下閃亮。
這本署名“山東大學中文系《杜甫全集》校注組”的《學詩訪古萬里行》,則讓記憶閃回到另一個方向,大西南群山環抱中的成都盆地。在成都春熙路熱鬧的街頭,我買到了這本書。它是師生作者們沿著杜甫的平生行蹤實地考察的記錄,自然包括詩人在安史之亂后“漂泊西南天地間”的流亡歲月,也成為我接下來的杜甫草堂之行的向導之一。草堂時期是詩人難得的一段安寧時光,他寫下了不少表達內心愉悅的詩篇,成為其苦難生涯中的一抹罕見的暖色。這本書連同此前的一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普及版《杜甫詩選》,引領我進入了浩瀚深邃的杜甫詩歌世界,其后數年間搜集了多種版本的杜詩研究著作:仇兆鰲的《杜詩詳注》,錢謙益箋注的《杜工部集》,馮至先生的《杜甫傳》,我的大學老師陳貽焮的皇皇三卷本百萬字《杜甫評傳》……從一顆偉大詩魂中發出的精神光芒,從此長久地閃耀在我的眼前。
我的履痕自然不限于上述地點,因此也就有更多的書,在跨度很大的時光中,從天南海北次第走進這間書房,棲身于不同的書柜里。這些書籍扉頁上的題記,讓我想到西安古都巍峨厚重的古城墻,華北縣城雨后的清新寧靜,太湖邊江南小鎮上秋日濃郁的桂花香氣。一些生命的記憶,留存在這些封面已經泛黃起皺的書中,就像氣味被密封進瓶子里。
當然,書柜里大多數的書籍,還是來自棲身數十年的這座城市。它們在來此安家之前,曾經分別暫居于王府井書店、西單圖書大廈、海淀書店,還有名頭沒有那么響亮的眾多書店。尤其是那些從古舊書店淘得的舊書,記憶最是鮮明。有數年之久,當時還是單身漢的我,周末休息日的一個常規節目,就是騎著自行車,連續不停地逛多家舊書店:琉璃廠海王村書店,東單南口中國書店,東花市大街中國書店,新街口中國書店,最后一站是海淀鎮的數家舊書店……線路事先規劃好,依據的是多多益善的原則。一天跑下來疲累不堪,但一回到宿舍,把一天的收獲擺放到桌子上,翻閱摩挲,濃郁的愉悅很快就充溢胸間,將倦怠感驅逐殆盡。如今回想起當年的這一幕,恍若隔世。
當然,我也并非不懂得與時俱進,近年來的圖書,大多都是網上下單,三五日內就送上門。沒有了那些奔波和期待,但附著其上的回憶,也失色了不少,可見任何便捷總是要付出相應代價。尋覓很久的一本書終于在某家書店一處不起眼的角落里被發現,耐心細致地清潔修補另一本書臟污漫漶的封面,這一類的快樂,非同道者難以體會。
書的積累最初是緩慢的,一是因為囊中羞澀,買一本書不免要斟酌躊躇,二是當年的出書數量遠不及今天。因此,那些書雖然買得最早,但因為讀得用心細致,記憶也最為清晰,仿佛一個人的少年階段,世界新鮮明亮,如朝日之初升。隨著時光推移,購買越來越不成為負擔,于是書柜迅速擴容,書籍急遽增多。但這些書反而看得不深不細,甚至還有不少從來沒有翻閱過,仿佛幽處冷宮的佳人,再無望受到寵幸。因為書房日益逼仄擁擠,更因為未來屬于自己的時光越來越少,近年來我基本上不再購入新書,仿佛一位老人開始注意養生節欲。
書柜里還有一些是贈書。當它們映入眼簾時,往往會疊加浮現出一張張面孔。
譬如張中行先生的著作,《負暄瑣話》《順生論》《流年碎影》《詩詞讀寫叢話》等等,幾乎占據了半層書柜,其中好幾冊的扉頁上有他的簽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間宿舍里,我曾數次親炙他的神采和教誨。附近的沙灘紅樓,便是先生年輕時就學的地方。一位和藹平靜的老人,閱盡人世滄桑,看遍云翻雨覆,晚年火山噴發一樣寫下那么多文字,溫婉絮叨波瀾不驚中,透露出豐厚淵深的國學素養,對民主自由理念的篤信執著,那正是五四前后那一代知識人共同的風骨。
先生如今已經化作云煙,但其著作仍在不停地印刷傳播,今后也還會有一代代的讀者,印證了“書比人長久”。通過書寫抵抗虛無,讓生命獲得恒久的寄托,這是寫作者共同的追求,而寫下的書籍,便成為他們生命存在的另一種方式。
二
與書柜材質粗糙及擺放隨意一樣,我的書柜里的圖書排列也甚為凌亂,毫無章法可循。
曾經走進過幾個朋友的書房,書按照內容門類分別排列,秩序整飭,讓人肅然起敬。如果那時我恰好戴著帽子,說不定會忍不住脫帽行禮。我的書柜里看上去卻總是雜亂無章,同一層擱板上的數十本書,彼此之間風馬牛不相及。一卷《樂府詩集》挨著一冊《植物分類學》,一部以史料考據嚴謹客觀而備受贊譽的歷史著作,與一本描繪火星移民的想象力馳騁的科幻小說為伴。一部研究原始社會巫術與宗教的名著,毗鄰一冊量子力學理論的普及讀物,盡管能看出后一本書的作者煞費心血,努力放低身段,以一種面向補習班學員的口吻言說表達,可惜我讀來仍然如墜云里霧里。這些書籍挨挨擠擠,看上去未免有幾分古怪,讓人聯想到時裝設計中的混搭風格。
當然,如此這般也并非我的本意。在藏書量可數可控的最初幾年,它們倒也大致各安其位,只是隨著數目不斷膨脹,整理起來變得費力,索性隨心所欲,不再為它們劃定居住區域,翻過一本書放回書柜時,看哪里尚有空隙就隨手一插,于是原來想象中的柵欄撤除,邊界消失,書籍們胡亂排隊,變成了如今的樣子。仿佛一場大災后,臨時聚集在一起的來自四面八方的難民,操著各地的鄉音方言,彼此間并無關系。
誠實地講,這種外觀上的雜亂無章,倒是從來不曾帶給我真正的困惑。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說,看上去缺乏頭緒無從把握的后面,其實有著一條潛隱的線索。就好像鼴鼠在地表下挖出的縱橫交錯的通道,乍看很凌亂,其實有著嚴密精巧的結構。我知曉這些圖書之間聯系的邏輯和脈絡,我清楚個中的草蛇灰線。聯絡圖就存放在我的心里。
有一些書之間的連接顯而易見。尋繹最初喜愛文學的緣由,不知有沒有人和我一樣,不是因為跌宕驚險的間諜故事,尋死覓活的愛情悲劇,而是從著迷于書中的風景描寫開始。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我還是中學生,課余時間的一大愛好,就是抄錄當時能夠看到的文學作品里的自然風景描寫段落,記在一個本子上。魯迅《社戲》里的故鄉景物,孫犁《荷花淀》中的白洋淀風光,屠格涅夫《獵人筆記》對俄羅斯中部廣袤平原和森林的描繪,都讓我心馳神往。此后多年中,我離開故鄉走向遠方,這一處文字叢林也急遽地擴展疆域,有了更多的樹木種類,更多的籠罩和覆蓋,隨著腳步的邁動一路伴隨伸延。哈代的英格蘭鄉村,都德的普羅旺斯田園,川端康成的京都郊野,都次第進入我的閱讀視界。雖然我早已不再抄錄,但心儀依舊。這種喜好一直延續到今天,目光投注的對象范圍更加廣闊,內涵更為豐厚。譬如美國的自然生態文學,兩百年間幾代作家的積累蔚為大觀,從梭羅《瓦爾登湖》到奧爾森《低吟的荒野》,風景之上又疊加了思想和哲學。那么,在以上這些跨越了地域時代和語言、看上去差異多多的書籍之間,誰說沒有一種親屬般的關系?
聯系還會跨越媒介形式。幾冊印象派的畫冊摞在一起,斜放在書柜的中間一層,書頭書腳緊撐著上下兩處的木板。這些畫作分別屬于梵高、莫奈、雷諾阿和西斯羅。因為開本大,它們只能以這種局促的姿勢容身。我時常抽出一冊翻上幾頁。畫家對大自然形色光影的捕捉,比文學描繪更為直接。陽光跳躍顫動,照在烏鴉的羽翼上,照在游船上午餐的人們身上,也照在婦人鑲著花邊的帽沿上,又在她的臉上投下一片陰影。麥田里的陽光金黃熾烈,睡蓮上的陽光清涼柔和。繪畫當然是自足的,但借助文學語言,對其中的情調意蘊會把握得更為準確細膩,就像閱讀過梵高和弟弟提奧的通信后,更能理解他的美學追求。文學和藝術由此而相通相證。風景當然不僅僅袒露于陽光下,沉靜陰郁也自有其魅力,像在俄羅斯畫家列維坦筆下,伏爾加河兩岸的荒涼破敗,墓地十字架上空籠罩的陰云,表達的是另一種色調的精神和心情。此刻一冊《列維坦畫集》就站在旁邊的書柜里,謙遜地陪伴著法國的同行們。
不同書籍因內在關聯,聚合成為一種生命共同體,這個生命體擴大的過程,萌生、發育和繁衍之間,也有跡象可循。整整四十年前的大學暑假前夕,去湖南實習,在武昌火車站等待換乘時,于附近書店里買到一本黃裳先生的《金陵五記》。原本當成散文游記來讀,不期卻看到了一角晚明歷史的天空,對那個時期的興趣由此而生,此后數十年間,書柜里陸續進駐了若干有關這段歷史的書籍:《南明史》《明季稗史》,夏完淳《續幸存錄》、孔尚任《桃花扇》、余懷《板橋雜記》、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從正史到野史,從事件到人物,從史學筆法到文學呈現,從親歷者的記錄到后世人的傷悼,這個譜系逐漸地豐滿。它們連接在一起,拼接出了一段明清易幟的動蕩歲月,抵抗與殺戮的血光將江南的天空映紅。我至今還記得四十年前江城那個濕熱的夏日午后,如果不是為了消磨漫長的候車時間,我也就不會來到書店并購買那一本書。機緣的建立,最初往往出于某種偶然。
相對于上面這些算得上比較醒豁的聯系,其他一些書籍之間的關系鏈條,就顯得模糊了,只有當事人自己才清楚。譬如這一本張承志的《北方的河》,以理想主義的高亢吶喊,引發了一代青年的強烈共鳴,我也是其中的一員。誰會想到,小說作者本人也未必認可,在我內心中,曾經將它和尼采、薩特等人的作品列入同一脈精神血緣。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意識形態的堅冰融化,個人的聲音在集體背景中凸顯出來,多少年輕人都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當作自己的圣經,尼采“成為你自己”的大聲疾呼,薩特“存在即選擇”的冷靜辨析,在眾聲喧嘩中分外響亮。這些人物和思想,發出的都是不甘于茍且平庸、不屑于盲目跟從的叛逆之聲,都關涉到一個人的生命姿態,都與時代腳步的邁動產生了共振。青春的充沛激情和生命力,成為擁抱它們的動力。今天,四周彌漫著優雅而又萎靡的氣息,望見那些曾讓人熱血賁張的書,靜靜地躺臥在書柜的某個角落里,多年未曾翻動,耳畔隱約響起了某句悼亡的樂聲。
憶想這些書籍聚攏的過程,眼前浮現出一個畫面:幾棵稀疏的樹,彼此隔著一段距離站立,每一棵樹都不斷地生出氣根,分蘗出枝條,長成一棵棵新樹,并各自向周邊蔓延,漸漸地聯結在一起,成為一片蓊郁的樹林……一個人的藏書由少到多,由單純到龐雜,數量的擴大和內容的豐富,其實呈現的也是這樣一種圖式。許多屬于不同時代、眾多國度的書,因為這樣那樣的某種關聯糾結,聚合在一起,無數的磚石構建出一座樓廈。當然,這座書籍建筑的施工圖紙,只有書的主人才清楚。
由此出發,一個稱得上夠格的愛書人,是天然的世界主義者,是地球村合格的公民,狹隘與他無緣。與此相關,一個人在書房里浸淫久了,也會成為一個謙抑的人。他會對蒙田的那一句“我知道什么呢”產生深刻共鳴。是的,我只知道自己的無知。知識培養見識,見識造成修養。所以,為什么那么多的大師,通常都十分和藹低調。這不是故作姿態,而是自然真實的人格展露。
書籍是博物館,存儲著發生過又消逝了的一切:夢想和爭斗,功業和榮耀,情愛和仇恨,青春的激情和垂暮的幻滅。它們以過去完成的方式,映照著鮮活的現在進行時態。太陽底下無新事。世界的秘密藏在阿里巴巴的山洞里,書便是開門的芝麻。想到這一點,會產生一種慰藉。
因此,博爾赫斯才會說:天堂就是圖書館的模樣。
三
書房的主人站在自己書柜前的時候,通常會是至為歡愉的時光,是享受的極致,庶幾與幸福相類。此刻萬物皆備于我,他有一種君臨天下的感覺,一時間忘卻了現實中的種種煩憂。眾多文章都寫到過這種快樂,將愛書人的自戀表達得淋漓盡致。
心情總是會訴諸于姿態動作。在這樣的時刻,通常會伴隨著某種目的性模糊甚至闕如的行為。他從書柜里抽出這本翻上幾頁,又拿出那本讀上幾行,取舍之間充滿了隨意性。這樣的畫面會不定時地出現,手臂伸出又收回,腳步挪移目光游走,具有某種屬于個人的儀式感。對他來說這是一種真實的愜意,雖然在旁人眼里顯得有幾分可笑。
有一些書,他看到時會很愉快,類似見到兒時的玩伴,友情終生不渝。如果他像我一樣出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大概率會讀過管樺的《小英雄雨來》、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以及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等等。它們連接著少年記憶,也是最早的文學啟蒙。如今雖然時過境遷,我不會再去閱讀,但它們仍然受到善待,享受著榮休的待遇,在書柜十分逼仄的空間中保留了位置。還有一些書,看到它們時仍然會覺心動,仿佛多少年后邂逅了初戀對象,不過那種思慕不休輾轉反側的感覺消失了。時光和經歷改變了許多。
但并不是所有的面孔都是友好的。一排擁擠的書脊中,時常會閃現出一個表情陰郁的家伙,它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是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和《巴黎的憂郁》,諸如此類。它們散發出孤獨、幽暗和陰冷的氣息,仿佛是一種讓生命窒息的迷霧。這些書中表達的情緒,是一個人本能地躲避拒斥的,但它們此時端坐在書柜里,仍然也是我請來的,并非自己翩然飛至。毋寧說,這是隨著生命的展開,意識到生活中彌漫著荒誕絕望之后,主動向有關書籍尋求解釋的結果。胸懷向著世界的豐富復雜性敞開,旨在獲得確證,但最終還是為了求得解脫和超越。
因此,僅僅用愉悅感來描述讀書,還是過于簡單了,它畢竟不是出席一次好友聚會,至始至終言笑晏晏。事實上,書籍喚起的是復雜多重的情緒反應。書籍容納和記載了一切,自然界的電閃雷鳴,人世間的喜怒哀樂,個體生命的一切境遇和感受,分別濃縮在一本本不同的書里,書房中充斥著難以分辨分貝的各種回聲。因此,面對著塞滿了書柜的數千冊書籍,也就是面對生活的全部和整體。一個人的閱讀行為,既是印證自身的經歷境遇,也是發現個體之外的豐富與廣大。那么,這些凝結了不同作者生命精血的書籍,當被賦予精神食糧的意義時,便仿佛是高能量的壓縮餅干。
書籍的盛衰存亡,也像是潮汐的漲落。秦滅六國后,為了鉗制思想,將諸子百家著作悉數焚毀。南北朝時期,南梁為北周所滅的江陵之難,十幾萬冊珍貴古籍化為灰燼。這樣的情形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其實也不用稽古述往,在我的少年歲月,可讀的書就少得可憐,就像那個物質匱乏時期的冬儲大白菜,長達幾個月里都只能吃它,此外別無選擇。但如今已經遠非昔日,書籍無比豐盛,這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選擇適合自己胃口的精神食糧。
那么,我需要一份什么樣的食物?就像口味會變化一樣,對它們的選擇也會隨著年齡而變化嗎?“對一個人是毒藥,對另一個人是蜜糖。”這句西諺是不是也適合某一本具體的書籍,從而證明價值的相對性?當靈魂受傷得病時,什么樣的書具有藥石之效?
我也曾經有過與劫難相守相伴的時刻,痛苦仿佛潮水淹沒頭頂,仿佛暗夜吞噬光亮。那些日子里,我從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中,從蘇東坡樂觀豁達的詩詞中,從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那一部出色地表達了斯多葛哲學的隱忍思想的《沉思錄》中,獲取信心和支撐。即便被視為消極遁世的佛教,我也從其緣生緣滅的基本理念中汲取了一種勇氣——既然諸行無常,那么苦難也該會和幸福一樣,無法凝滯,難以持久,將會適時減弱或者消退,呼吸也會逐漸由窒息變作通暢。
由此可以說,不同的書,會分別對應著生命的某個節段,印證著生命的某種狀態。當一個歐美國家的兒童合上《愛麗絲漫游奇境記》,拿起一本蒙田隨筆,似懂非懂但饒有興味地翻看時,生活的廣闊和復雜開始在他眼前展開,雖然他此刻的心智尚難以理解字句間的蘊涵。一個在華夏文化氛圍里長大的古代讀書人,從先秦儒學到宋明理學,內圣外王、修齊治平的種種理念,都會在他的靈魂中打下印跡。如果他盛年不再、壯志難酬或者怠倦了世事紛紜、官場溷濁,選擇面對世界的喧囂轉過頭去,那么他會把目光投向《莊子》,投向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在江上清風與山間明月中安放一顆倦怠的心。
這樣的讀者數點著自己的藏書,仿佛在回看一路走來的腳印,一番感慨,幾多唏噓。書籍此時變成了一面面鏡子,映照出的是主人肺腑里的峰巒溝壑。他知道自己的精神表情中,某一道笑容是某一本書的投影,某一個音調來自某一本書的回聲,就仿佛不同的食物提供各自的營養。書籍增加的過程,與他的心靈的開疆拓土相同步。這樣,書籍就會成為精神能量的不竭來源,仿佛《山海經》中的息壤化育萬物,或者希臘神話中的不老泉汩汩流淌。因此,站在書柜前巡檢自己的擁有的主人,此刻或許有一種靈魂出竅的感覺,會感覺到有一雙眼睛,在高處俯視它所寄寓的那一具肉身,如何從牙牙學語的孩童,漸漸成長,變得骨架堅實,肌肉豐滿,長成此時此刻的樣子。這般種種,都可歸結為一句話,即人與書的關系的建構。
看到過一個說法,輕易不要給人看你的藏書,這樣別人會對你的分量底細,有一個準確的掂量。這當然是戲謔之言,但其中倒是有不少真理。你的書柜所呈現的,就是你的靈魂的模樣。你被剝光了衣服,軀體袒露著,任人指點長短,評說肥瘦。
知曉了這樣的內在機制,再來審視某些行為乖張的愛書人,會覺得他并不比迷戀權位者更為可笑。他享受一種類似帝王南面天下的君臨之感,但并不產生真實權力運作中的眾多危害。他不過是被書籍的魅力俘獲,為文字的神奇陶醉。一股看不見的電波,從字行間篇頁中迸發出來,照射進他的靈魂。
少年高爾基在閱讀巴爾扎克長篇小說《驢皮記》時,對其中出色的描寫技巧驚愕不已,曾把書高舉起來,翻開一頁,想透過陽光的照射,看看其中隱藏著什么魔法。這個畫面,其實是關于書籍魅力的一個最好的隱喻。
四
因愛好而迷戀而集書不止的過程,經常會帶給人一種幻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只要有意愿,一個人就能夠累積起眾多的書。該是基于這一點,在行為和意識之間似乎產生了某種曲折隱秘的關聯,一個潛在的聲音告訴他,他的生命會無限延長,衰老和死亡只是一種觀念上的存在。這一種潛意識鼓勵了他,讓他停不下腳步,雖然這完全是兩回事。
但是,總有某個時候清醒會降臨,認識到未來時日無多,即使看瞎幾雙眼睛,也無法讀完他已擁有的滿坑滿谷的收藏了,更遑論還有新書源源不斷地進入。那么,這般孜孜矻矻挖山不止一般的行為,其意義何在呢?
在《四季隨筆》里,晚年的喬治·吉辛借虛構的主人公之口,發出自己無奈的感慨:“那些不能一讀再讀的書呵。”一個覺悟了的愛書人的嘆息,只會更為深入剴切,他會想到無法越度的絕境,一切悲哀的巔峰,即生命的消失。諸行無常,萬法皆空,一切都會消逝:我自己,連同我此刻面對的這些書。
這樣的時刻,他不免會顧念身后書籍的下落,就像一個有責任心的父親,會牽掛自己過世后兒女們的生活。在我活著時,它們備受寵愛,即便因為年齡增加帶來了惰性或者病痛,懶得去整理,擺放得凌亂不堪,但不必擔心會被拋棄,仿佛中古時期那些士族門閥破落了的后代,盡管往昔奢華不再,但也風雨不侵衣食無虞。不過一旦我故去,情況就會大為不同,它們不可能長期踞守于等待出售或挪作他用的房子里,早晚會被驅逐,就像家世最終敗落得極其不堪者的子女,要外出討一條生路。那么,它們的去向會是哪里?公共圖書館的捐贈處?舊書流通市場?
如果是這樣,還算不錯。我的一些藏書中,扉頁上簽著知名作家學者的名字,多數是贈送給別人的,我從舊書店或地攤上購得。何以會如此,無從知曉也沒有必要去探究。它們到了我手中,或者到了同樣喜歡書的別人手中,畢竟都是不錯的歸宿。但更常見的情形,恐怕是被賣到廢品收購站,等待打成紙漿。
捷克作家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的中篇小說《過于喧囂的孤獨》,把這種困窘描繪得最為真切透徹。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廢紙回收站的打包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蒼蠅成堆、老鼠成群、潮濕惡臭的地下室里,給書籍澆水,再用壓力機碾碎后打成紙漿。其中不乏珍貴的圖書,像歌德、席勒、尼采等人的著作。他把這樣的圖書挑揀出來,藏在身上帶回家中,晚上一邊喝啤酒一邊閱讀,“嘬糖果似的嘬著那些美麗的詞句”。這樣的工作他干了三十多年,為知識和智慧被無視被毀滅而憂傷。小說的結尾是,他將自己打進了廢紙包,和書籍一起飛升到他心目中的天堂。
我的思緒沒有駐留在這個悲劇結局上,而是忍不住地向回追溯:這些被化為紙漿的書籍,是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到不同人家的或者華麗或者簡陋的書柜中,被認真閱讀或是僅僅裝點門面?它們曾經被一雙什么樣的手掀動書頁?在主人的生命歷程中,它們是否產生了某種影響?它們必定曾經有所不同,雖然今天殊途同歸。
這樣想下去,一幅書籍的命運圖式便在眼前展開:從逐漸積累聚集,成為一支頗具陣容的隊伍,到不斷散落飄零,不知所蹤,多么像是人生歷程的一面鏡像。終有一天,此刻眼前的一切,眼睛看見的,手指觸摸到的,連同圍繞它們生發和展開的經歷和心情,外在和內在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就仿佛從來不曾存在。
想到這一點難免會黯然。那一刻,古典詩詞里的那些吊古傷懷之嗟,物是人非之嘆,都可以移來給這種情緒做注腳。誰會知道為了買到這本《美的歷程》,當年我跑了幾次書店?誰會在意我曾經花五元錢買了一本薩特《存在與虛無》中譯本,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個價錢足夠幾個人下飯館美餐一次,而要命的是,這本磚頭一樣厚重的書我迄今未讀完一頁。
郁悶如云霧一時彌漫。但深入想下去,也總能夠找到排遣化解的辦法。一切有形的房屋器具,金銀珠寶,無形的盛名令譽,豐功懿德,最終都不屬于自己,都會化為烏有,仿佛掬水滿捧,都會從指縫間流盡。“大都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白居易的這句詩,揭示的正是一切事物必將衰敗的定律。既然如此,又為什么不能接受書籍的流散?皮之不存,誰會在意附著其上的毛?生命已經不存在,作為派生物的東西又有什么好說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五說過一句話: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這句話被稱為昏君名言之最。不過客觀地講,去除倫理的考慮,從某種超越的意義上看,這種態度中倒是有一種曠達和決絕。
僅僅退一步講還不能完全服人,迎面而來的說法才更容易有效力。如果說上面白居易的詩句及背后的觀念,令人想到是佛教的成住壞空輪回無休的基本教義的話,那么,好像一只手掌的正反兩面,佛家的另一個并行的論斷是萬發緣生皆系緣分。它可以從相反的方面,讓人了悟這種關系的本質,從而產生出新的感悟。一切現象的存在,說到底都是諸多因素的湊泊,這些書籍得以共聚一堂,也是因為情感心志、空間時間各種成分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充滿偶然性的存在。當這些條件發生異變,書籍的境遇也就跟著改換。緣起了,它們四方來集聚居于斯,緣散了,它們勞燕分飛流徙各處。認識到這點,還有什么不可以釋然的呢?
這樣,事實還是同一個,但由于打量的角度不同,帶來的卻是迥異的感受。就好像電腦上的視力測試游戲,將鼠標光標稍稍點擊一下,圖像轉動角度,虬髯大漢變成了秀發美人。
這種想法,很自然地通向這樣的結論:且不管今后山河如何傾覆,先享受此刻的月白風清。古代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的《魯拜集》里,有一首詩值得再三吟誦:
心底不應留下憂傷的痕跡
應把歡樂的書卷一頁頁翻啟
痛飲甘醇,歡天喜地地過活
有誰知道還在世上勾留幾許
是的,關鍵是當下。意義就存在于當下。不論是哲人深奧的宏論玄思,還是蕓蕓眾生喜歡的心靈雞湯,都說到這一點。盡管不過是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但此外也找不到更能夠帶來寬解的說辭。
此刻,我仍然在自己的書房里,在幾十年中辛苦搜羅聚集的數千冊書中間。它們真實地寄身于書柜里的每一層擱板上,或站立或躺臥,或莊肅或慵懶,各自挾帶了一份歲月侵蝕的痕跡。機緣之線尚未斷裂,虛無還是將來的事情,還在一個遙遠縹緲的地方等待。
這就夠了。朝著書柜里的某本書,我又一次伸出了手。
(責任編輯: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