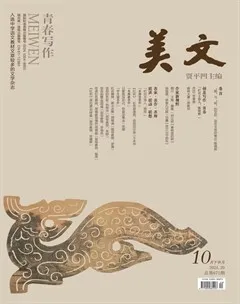思想情感的傳遞行云流水
我認為不拘一格的寫作手法使散文這一文體更直接、更易于情感表達。當一種感受、一種情感涌上心頭的瞬間,文字是匱乏的,但可以用敘事、抒情、議論的方式,用比喻、擬人、通感的修辭表達。此時,這些方法引出的語言就是最貼近真實情感的文字。而散文可以囊括這些表達方式、修辭或任意的寫作手法。因此它是直接的,也是簡單的。
其次,因果邏輯、時空順序是一類文章的準則。而散文對取材不限制,在組合思緒片段時,不論是記憶片段、思考片段,都沒有嚴格的限制。這易于放大作者關注的片段,突出情感最濃郁的點。這種超越時間空間的關聯若能配合上文字的耦合,往往能造就出乎意料的效果。
在散文中,我希望表達的情感是連續地流淌在整篇文字當中,能夠打動讀者,被讀者理解。這些情感或激昂或平靜,像與人交談一般有緩有急,使文章的構造時緊時松,思想情感的傳遞行云流水,舒卷自如。
《秦嶺》的感悟是從日復一日的學習,從我在秦嶺腳下反復的思考中得到的。這種反復讓思考失去意義,讓我覺得我只是與秦嶺面對面看著,無語,思想從身體里流出,攤在外面。在這樣的對視中,我重新認識了秦嶺,不是通過它去比喻自己,而是走進一座山的生命里。好像它的思緒也流淌出來,被我感知,讓我再平靜地回歸生活。
《十四號線》(注:西安地鐵十四號線是一條漫長的穿過郊區通向機場的旅途)體現了一些對加繆荒誕哲學的認知。我的角度是出于個人行程之中空間變化的剝離感,從日常生活的抽離中感受生活。在這種剝離后的情境下,或是從行文遞進的角度,自然地引出對人生中荒誕哲學的三點反思。《海天彼端》的情感更純粹一些。“彼端”一詞本容易引發對“與世隔絕”的想象。我在巴厘島的所見所聞,對這海島的感觸,也如“與世隔絕”般自由、安逸。文末對離別的感觸在成文后更加深刻,我在一遍遍離別、回憶中,體會著不重逢的感觸。
《別讓美在指縫間流逝》中,我用諸多的例子勾勒出美這一主題。美是易逝的,又是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從例子中不易觸及的美回歸到生活,聽從圣人的感召珍惜美,珍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