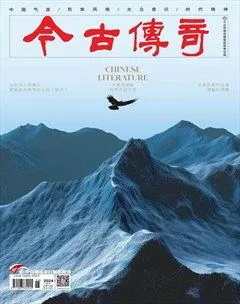把人物丟到漩渦里熬煎
2023年10月22日,在湖北省作協與中南民族大學聯合主辦、楊彬教授組織的葉梅作品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向陽。他身上有一種莫名的熱烈的親近感,給我留下美好印象。今年4月,我讀到了向陽的散文《38次列車,我永遠的墨綠色》(《長江叢刊》2024年第4期)。他深情地回憶乘坐38次火車的經歷。原來是38次列車,現在是Z38次列車,這是一條從武漢直達北京的貫通南北的鐵路大動脈。1997年,他為了趕在香港回歸前夕參加北京的紀念活動,乘坐38次列車第一次進京。不料,他突然生病,疼痛難忍,得到心地善良的女車長、列車員、老中醫等陌生人的無私幫助。他感嘆:“人的一生命中注定有一些福分,因為某種機遇與某些善良的人結緣而獲得幸運。……我的感謝信只是漫天星辰中的一顆,就像我只是他們相助過的無數乘客的一員,但我作為受恩之人,必須心存感恩之心,必須寫出這份心聲。”他的散文印證了我的印象。
作為從恩施走出來、在京城干一番事業的土家族作家,向陽始終秉持著赤誠之心、感恩之心、敬畏之心,重情重義又有點游俠氣質。他似乎總是無可救藥地拼命伸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敏感觸角,如饑似渴地搜尋、接收、密布、通聯各種訊息,以正面硬剛的方式來回應這個時代最真實、最切中肯綮的呼聲。向陽始終保持著青年人的那種火熱激情,在文學創作、影視編劇方面頗有建樹,在商業經營等方面頗具頭腦,而且在哲學、法學、宗教等方面的鉆研很下苦功夫,是一位有深廣追求的全能型作家。
因為工作的緣故,他出入影視圈,抱持積極入世的心腸,保持時刻在場的姿態,試圖復刻出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光榮與夢想”“偉大與卑鄙”,這使得他的小說具有影視文學、網絡文學的特性。他的最新長篇小說《最后追訴》、此前的《善良密碼》和即將出版的作品,構成熱烈燦爛的“人性三部曲”,袒露了他的勃勃雄心。
《最后追訴》的語言是雄辯的,也是鮮活的。雄辯,是因為其中有大段大段針砭時弊、鞭撻人性的宏論,滲透著專業的法學知識。鮮活,是因為他一頭扎進市場經濟的滾滾紅塵中,投身于火熱的當代生活中,自帶熱氣騰騰的氣息。這部作品既是在拷問法律、道德與人性糾葛的現實主義力作,又時刻充盈著、閃現著、呼喚著一種這個時代極為珍稀的理想主義情懷。
誠如中國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吳義勤在研討會致辭時所言,向陽作品從法學倫理角度切入,這是文學性生長的巨大空間。他的作品,在善與惡的博弈糾纏中,在罪與罰的痛苦掙扎中,寫出了人性的深度,寫出情感的驚心動魄的畫面,讓人回味無窮。
回到故事層面,《最后追訴》構思縝密,故事離奇,情節精巧,推進很快,反轉總是出乎意料,是一部很好讀的小說,特別適合拍電視劇。小說的開頭,平地一聲雷,因為一次偶然交通事故,潘多拉盒子被打開,十五年前的一樁舊案浮出水面,將很多罪惡的人和無辜的人牽連進一個巨大且難解的漩渦中,讓人心潮難平、思緒萬千。
向陽下筆非常狠,一開始就把人物丟到漩渦中“熬煎”,講述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故事。江紓媛和劉敏捷,是貧賤夫妻。魏雅思與宋清平,是中產夫妻。韓雯和章則是富豪夫妻。三對地位懸殊、家境懸殊,價值觀迥異的夫妻,被突然置于極端環境,圍繞著“救孩子”“呼吁強奸犯獻血”“是否立案”“訴訟對決”等線索展開。一個個拷問人性的問題,將這三對組合,在價值觀上不斷拆散、重裝、組隊,他們一會兒攜手對方,一會兒互相傷害,最終指向“救贖”主題。
初看開頭,或許能大抵猜到后面的故事脈絡。這是因為向陽敢于揭開謎底講故事,那是出于自信。為什么?好的小說,不只是講故事,而是怎么講故事,怎么講出情節的跌宕起伏、講出情感的百轉千回、講出氛圍的撲朔迷離、講出精神的回蕩共鳴,引人入勝。
當然,這些人物出場是不是太急了點?故事邏輯起點是否經得起推敲?人物的性格塑造是否有點臉譜化?這到底是湊巧的傳奇故事,還是真實生活?這些疑問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
當我讀到一半,對魏雅思和江紓媛的好感慢慢消退,特別是她們千方百計地阻止劉敏捷和宋清平的立案時,我一度鄙夷前者是圣母心泛濫的“白蓮花”,一度同情后者的無可奈何的悲愴。也許是性別意識在作怪,又或者是看待問題的方式有別,說實話,我實在無法理解她們的想法和做法。但是,隨著我的閱讀深入,隨著這些人物不斷地義憤填膺、慷慨陳詞、怒吼笑罵,不斷地袒露他們內心的千瘡百孔與掙扎、糾結和痛苦,我開始慢慢理解并同情。這就是讓人又愛又恨、避無可避的真實生活啊。
人啊,只有在極端環境里淬煉過,只有在艱難生活中熬煎過,才明了痛徹心扉的苦楚。借用法學、倫理、案件來營構的故事也許是傳奇的,人物的內心卻是真實生活中“熬煎”過的滾燙、熾烈、滄桑。法律的寬嚴、法官的自由裁量、是否以罰代刑等等,是困擾著人類的永遠難題。因為法律能夠在一定層面定義、裁決、懲戒罪惡,但是不能天然消滅人性深處的罪惡感。向陽用了一個很形象的詞:“靈魂的白血病。”
著名作家、中國散文學會會長葉梅認為,向陽的創作始終是在茫茫紅塵中尋覓、傾訴、救心。正如《最后追訴》引用耕云法師的話:“救世道,莫過于救人。救人莫過于救心。把顛倒心變回安穩心。”
誠然,一個罪惡之人實現真正的救贖,就要依靠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語),也要依靠情感的力量。著名作家鄧一光曾說:“它只想告訴人們,人最可貴的不是英雄品質,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軟弱和恐懼之心,這是上蒼給予人類阻止自我毀滅的最后法器,正是因為有了它,我們才有可能,或者說最終不會成為魔鬼。擁有捍衛恐懼的權利,人類才能繼續前行。”
道德是理性的約束,情感是感性的生發。以情動人,才能以理服人。文學擁有無法言說的情感力量,可以真正從靈魂深處去探尋、描摹、觸摸、撫慰人心世界的幽微罅隙或光明。《最后追訴》給了一個光明的結尾,在江紓媛聲淚俱下的陳述下,罪犯章則的心防最終被突破,選擇了懺悔自首,做回了人,實現了自我救贖。
但是,《最后追訴》在此戛然而止,沒有進一步探討救贖問題,沒有探討人性與社會的深層關系,是很可惜的。這讓我想起司湯達的名作《紅與黑》的主人公于連。
章則和于連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相似性。章則原本只是平民子弟,憑借自己的撩妹心理學,終于傍上了富家女韓雯,實現了階層躍升。其實在圍繞強奸案訴訟對決過程中,章則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因為他害怕失去處心積慮獲得的榮華富貴與地位。章則最后的懺悔與覺悟,也許是出自本能,未必經得起思想的錘煉,未必能對更廣泛的世道人心造成更大的震動。
在《紅與黑》中,于連入獄、公審時,公開宣稱不祈求任何人的恩賜。他說:“我絕不是被我同階級的人審判,我在陪審團的席上,沒有看見一個富有的農民,而只是些令人氣憤的資產階級的人。”于連,首先是作為自然人的懺悔,然后才是作為社會人的宣戰,以死亡的名義而宣戰,這讓救贖這個主題得到極大升華,也讓于連“這一個”人物具有更典型的社會現實意義,具有更強烈的思想穿透力、藝術感染力。
進而言之,章則的懺悔并沒有給我很大的沖擊,反倒是江紓媛的“真”讓我肅然起敬。我們常說,優秀的文學作品總是要勸化世人、有益人心的,要寫出一顆真善美的心靈。為什么把真擺在第一位?真善美的表達,都應該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真是善、美的前提。失真的東西一定不善不美。真實的力量源于什么?真實本身具備無懈可擊的力量。
向陽銳利地揭示人性,探尋善的力量,始終不忘對真的追問。在《最后追訴》的結尾,江紓媛不得不出庭陳述15年前的受辱經歷,這種在大庭廣眾之下再度撕開傷疤的真實,很殘忍,很有力量。江紓媛說:“我在法庭的陳述完全就是事實,不存在幫助誰、背叛誰、害了誰。我絕對不會因為任何其他事宜導致我的真實被誤解。”
這涉及“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問題,關乎的是現實主義寫作的路徑問題,體現的則是作家的創作觀。湖北省作協2022年舉辦魯迅文學院湖北作家高研班,著名作家梁曉聲應邀授課,他強調文學需要弘揚人性之善,提出現實主義寫作的路徑問題,“現實主義文學寫人,實際上有兩種:不僅僅應寫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還要寫人在現實中為了責任和使命應該怎樣做、能夠做到什么程度。歷史乃從前之現實。‘文學即人學’,實際上就是這兩種文學創作的結合。”
在我看來,優秀作家敢于向茍且的真實說不,敢于向理想的真實致敬,才能用虛構來鑄就藝術真實的豐碑。優秀作家的虛構可能比真實更真實,因為優秀作家具備更深廣的悲憫情懷、人文立場,具備對現實生活、歷史與未來的總體把握,具備對生活原貌的審美超驗表達。
正如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夏潮在研討會總結時所評,向陽是一位有信仰有思想的作家,有著清醒的文藝觀,在近些年的創作當中越來越注重思考法學、哲學、宗教、人性等問題,思考怎么弘揚人類共同價值觀,怎么弘揚真善美,怎么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探討的是人的精神如何充盈起來。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文藝家就應該在滾滾紅塵中認真地感受、體察生活的煙火氣,一轉身回到斗室里,虔誠地品味孤獨、寂寞、悲憫,在出入之間,努力探尋藝術真諦,方能讓作品保持飛翔的姿態。
陳智富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魯迅文學院兒童文學培訓班學員,湖北省委宣傳部項目評審專家,湖北省文聯第八屆文藝評論高研班學員,湖北省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秘書長,《湖北作家》執行副主編,武漢文聯首屆簽約評論家。著有《你為什么當作家》。
(責任編輯 王仙芳 349572849@qq.com)
- 今古傳奇·當代文學的其它文章
- 影響力人物——張曉亮
- 楊公堤
- 芭茅草
- 暮色中的深情呼喊
-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 隱入深海的雄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