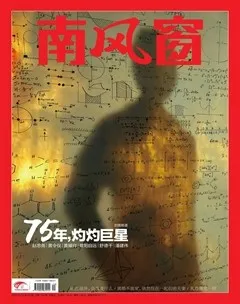當代資本主義正在“封建化”

西方人對當代社會的感受似乎已經被一種絕望情緒主控:資本主義不僅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經濟系統,如今就連給它想象一個合乎邏輯的替代選擇也不可能了。
然而2020年以來,當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們看到了不同的跡象。他們一方面主張在數字革命之后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倒退,一方面將這種倒退解釋為資本主義被取代或者消亡的一種可能,由此形成了技術封建主義思潮。
法國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的論著《技術封建主義》今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借助這本書,我們會看到當代西方左翼思想家正在如何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
本書開頭講述了一個發生在1990年的插曲:美國特勤局持搜查令闖進一家位于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小公司,查獲了一份名為《賽博朋克》的手稿。手稿的作者、游戲設計師洛伊德·布蘭肯希普,設想了一個反烏托邦的游戲世界,在那里,富可敵國的巨型企業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就像封建領主一樣,對其控制下的空間和居住其中的個體行使權力。
迪朗發現,當代社會圖景與這個游戲設定有某種相似:數字技術和智能算法不僅帶來了生活的深刻變革,更創造出新的統治形式和管理制度,造成社會“巨大的倒退”。迪朗認為,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再封建化”。例如,硅谷的科技新貴就像中世紀的封建領主一樣,通過壟斷數字資源,向平民(用戶)收取租金,從而捕獲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大多數利潤;需要為公共資源支付租金的平民,則被置于類似農奴的地位。
公共空間的消失
迪朗mbqzJVi/wGkvLPcnERkN2w==發現,2000年之前,名列前茅的公司多是石化、零售和金融集團,20年之后,無論是榜單上的名字還是人們對“大公司”的想象,都被高科技公司替換了。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臉書……這些科技公司只用了極短的時間就從“硅谷新貴”成為當下經濟秩序的主導者。
事情并沒有到此為止。
數字革命之后,技術產權和用戶數據作為無形資產,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最重要要素。然而由于掌握產權和數據的人是社會中的極少數,科技不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般智力”,而是經過科技巨頭的壟斷,成為具有稀缺性的技術特權。這種稀缺性讓產權的出租成為可能。
對于“手機成癮癥”,技術封建主義提供了嶄新視角:那不是成癮,而是一種新的奴役手段。
科技公司的獲利方式,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的邏輯,而與封建主義有相似之處:科技寡頭通過數字圈地搶占網絡空間,將我們的日常生活引入數字平臺,攫取用戶數據,再向用戶收取租金,就像封建主對農奴做的那樣。
數字科技的發展,讓無形資產更深地嵌入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經濟體制。數字平臺、軟件服務已經呈現出“基礎設施化”的趨勢,很多打工人可能一時半會沒法想象這個場景:假如現在微軟公司從地球上徹底消失,你要用什么給客戶講解PPT——PowerPoint。首先,你要怎么解釋這是一種什么東西?
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遭到了“數字殖民”。工作依賴于辦公系統,出行依賴于優步/滴滴,用餐依賴于外賣軟件,從地鐵口出來到公司那一小段距離,則依賴于共享單車軟件。至于那些尚未被數字化的需求,就成了互聯網初創企業津津樂道的“風口”。
以社交媒體為例,這個經過數字轉化后的公共空間并不是免費的。如果我們想進入一個廣泛的平等的交流空間,我們需要向一個特定的人(或者組織)繳納入場費。在外賣平臺、通信軟件、社交媒體上繳納租金的農奴,換取的是在技術的許諾誕生之前,原本無門檻屬于我們的生活空間。
在越來越多的便利店、餐館,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圖景:店員的職責不再是滿足我們的需求,而是教會我們如何使用點菜機和自動收銀機——那些顯然正在試圖替代他們的產品。

齊澤克認為,“這就把我們這些用戶置于向作為封建主的公共資源所有者支付租金的農奴地位”。所謂的用戶生產內容(UGC)則收編了我們為網絡平臺無償付出的數字勞動,如果沒有使用者(而不是研發和設計人員),平臺則沒有生產力可言。
那些在初創階段以工業資本主義貴族和官僚制國家資本主義為反叛對象、以冒險精神和財富神話為許諾的互聯網科技公司,手中的神話一旦成型,就會立刻成為新的保守派,成為“普通人甚至是傳統資本家不可跨越的階層”。迪朗在這里論述了“加州意識形態”的形成和本質。
所謂的“加州意識形態”,是20世紀60年代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與加州新企業家對自由市場原則的擁護相結合的產物。這二者的結合點理應是新技術的未來潛力,然而這很有可能只是一個障眼法。
在迪朗看來,問題在于,他們并沒有創造出真正的未來,而只是在數字空間占據了新的領地,致力于把原有的生活方式數字化。把硅谷新貴與舊式資本家區分開來的是,前者的財富積累并不來自生產中的剩余價值,而來自向用戶收取的租金。
國內學者藍江這樣描述技術封建主義視角下的科技企業:“擁有云資本的新貴們可以躺在自己的互聯網領地上,不斷地從云農奴、云無產階級和附庸資產階級身上吸血;他們仿佛中世紀的封建貴族一樣,不事勞動,也不怎么生產。”
赤裸零工
梭羅的瓦爾登湖式生活,在今天已經不再是某種基于個人選擇的神話,“退出現代生活”面臨比單純地重建古典主義更嚴厲的代價。

因高度數字化的趨勢,日常生活對一個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人來說變得更困難了。疫情期間,如果一個人不能順應時代完成對自己的數字化改造,他將寸步難行。并且,在越來越多的便利店、餐館,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圖景:店員的職責不再是滿足我們的需求,而是教會我們如何使用點菜機和自動收銀機——那些顯然正在試圖替代他們的產品。在《技術封建主義》中文版的推薦序當中,藍江指出:“人們成了數字化時代的農奴,成為高度依附于云封地的存在物。一旦人們脫離了這些云封地,脫離了數字化空間和數據,便會墮落為這個時代的赤裸生命。”
很多傳統資本家也不能逃出云封地的管轄。雅尼斯·瓦魯法基斯曾說:“進入亞馬遜網站,你就退出了資本主義。盡管那里有買有賣,但你已經進入了一個不能被視為市場的領域,它甚至不是數字市場。”
人們不得不疲于奔命,唯一對抗算法的辦法是退出,但代價是成為數字社會的赤裸生命。
提供產品的生產商,成為了緊緊環繞著數字平臺的“附庸資本家”,它們必須獲得平臺的準入才能開啟互聯網時代的新游戲;尤其在消費者已經與購物平臺形成深刻依賴的情境下,傳統廠商不得不接受平臺作為交易的中介——當然,它們要為每一筆交易向平臺所有者支付地租;而這個游戲還沒有結束,進入平臺的商家不得不服從數字平臺制定的所有規則,系統根據好評數量、交易金額等各種指標分配不同等級的曝光(或者說流量),而這些主要由用戶提供的數據攸關商家存亡。平臺由此實現了對商家的自動化管理。這套管理手段,在迪朗看來,已經完全是制度的邏輯,而不是技術的邏輯。
在《技術封建主義》的第二章,迪朗提出,數字技術締造了一種“增強人類”——滿足了任何一種數字需求的技術和服務,是對有限的人類的延伸。但是,這種“增強人類”跟“社會化的人”一樣,無法脫離一個大的語境、一個擁有算法的“大他者”。
運行大數據的系統,是以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不可見的方式運作的。龐大的數據聚合了海量的“個體行為”,它會產生超越性的力量,對個體行為進行反饋甚至指導,這個時候個體很難清楚地認識自己。齊澤克甚至認為,通過自我學習和自我完善的算法運行的數字云,已經成為一種最新的“神圣實體”,它甚至很大程度上能夠擺脫創造者的控制。
用戶在數字平臺進行點贊、評論、轉發、往信息流里發布新內容,這些行為既是娛樂,也是勞動。盡管“勞動、休閑、消費、生產和游戲的交織使對剝削的理解更加復雜”,但正如特雷博爾·肖爾茨在《數字勞工:互聯網既是游樂場也是工廠》當中提出的,“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的行為被激活為可被貨幣化的勞動”已成事實。從宏觀層面來看,一個人人都能進入的系統,反而更容易讓個人選擇成為少數寡頭的經濟資源。
用戶同時成為平臺的農奴和勞工,被稱為“零工”的服務提供者則揭示著“依賴”的另一面。
成立于2009年的優步(Uber)公司,在短短幾年里為世界帶來了一種以靈活自由為優勢的網約車模式。但問題也顯而易見,這些被系統松散地組織到一起的司機,與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難以界定。2016年,兩位英國司機將優步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平臺將司機視為“雇工”(worker)而不是“自雇者”(self-employed)。這意味著,優步公司需要為平臺數以百萬計的司機繳納社會保險等勞動福利,會給優步帶來約為20%~30%的額外成本。
數字經濟挑戰了傳統經濟模式,與后者配套的企業理論、勞資關系認定,都不得不做出調整。居伊·斯坦丁將這些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雇傭關系模糊、在網上接零散工作的勞動者,稱為“流眾”。 當代科技企業通過算法和產權,實現對“流眾”的勞動剝削,并且通過評價等級、生物識別、算法監控等技術手段,保證剩余價值最大化。
人們不得不疲于奔命,唯一對抗算法的辦法是退出,但代價是成為數字社會的赤裸生命。這時候我們也會意識到,技術甚至正在重新定義我們對現實主義的理解。
全面發展的人
對技術封建主義假說來說,一個充滿矛盾的說法是,技術“推動”了社會的“倒退”。
技術封建主義試圖解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技術的進步沒有帶來一個文明高度發展的社會,反而造成了更嚴重的兩極分化:一邊是超越傳統資本家、占據大量財富的科技新貴,一邊是受制于數字平臺、朝不保夕的零散勞動者。
自由主義在算法邏輯面前被削弱了力量。對那些將競爭視為良性機制、呼吁反壟斷的自由主義主張,來自數字世界的回應是,拆除數字堡壘意味著數據不能再以超大規模聚合,這會降低算法的精確性,最終導致使用體驗不佳。某種程度上,消費者的需求本身反而正在促使壟斷的形成,迪朗將其稱為“一個競爭政策無法阻止的累積過程”。數字資產的中心化因其內在邏輯幾乎無法避免,對數字平臺的依賴是數字經濟內在的前景,“是自由主義在算法時代吃人的未來”。
為什么“與工作相關的痛苦在當代肆虐”,部分原因就是當代工作陷入了一種“神秘感”。
“人類文明正沿著一道山脊走向完全歸屬于資本的無望時刻。”迪朗的論述,始終建立在對無形資產獲利方式的分析基礎上,他在最后一章再次解釋了“地租”的含義:對勞動力的剝削依然是獲取剩余價值的核心方式,但是數字資本利用捕獲機制,減少對剝削的參與,脫離生產過程,通過收取租金,從全球剩余價值的總量當中獲利。
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如是設想了文明的衰落:“科學這一社會發展的普遍產物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應用,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而不是勞動的生產力。”
迪朗緊接著解釋了為什么“與工作相關的痛苦在當代肆虐”,部分原因就是當代工作陷入了一種“神秘感”。在資本主義的漫長歲月當中,人類一次又一次成為卡夫卡筆下面對迷宮的K,只不過這次,有關官僚科層體制的隱喻被更神圣而不可見的數字系統替換。
人利用技術獲取了對世界的強大掌控,而這種強力卻又無時無刻不被置于技術編碼的固定系統,成為當代社會人與技術之間一種痛苦的悖謬。對越來越多的人而言,勞動力與現實之間的聯系被切斷,迪朗認為正是這一點造就了痛苦的“打工人”,他們的生活存在著對不可知的系統的悲觀:“個人什么都不是,資本才是一切。”
不過,迪朗在本書的末尾進行了一種富有辯證色彩的展望。盡管技術進步帶來的前景看起來并不是玫瑰色的,但與此同時,“在山脊的另一邊,歡笑的溪流和郁郁蔥蔥的山谷散發著解放的希望”。他解釋,擁有自由之軀的零工相比在社會體系當中固定地擔任螺絲釘的職工,更有可能成為馬克思所說的“用那種不同社會職能當做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盡管眼前一切渺茫,但在技術封建主義的催化之下,寡頭與流眾之間的巨大裂縫,蘊含著推動社會轉型的能量。
當然,無論是想象世界末日還是想象資本主義的末日,想象總是容易的,在真正意識到那壓迫我們的何以成為“不堪忍受的力量”之前,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這也是為什么迪朗會強調技術封建主義是一種“假說”。
最后引用一句齊澤克的話,其中他又引用了本雅明:“當我們完全接受我們生活在‘地球飛船’上這一事實的那一刻,當務之急就是在所有人類社群之間實現普遍團結與合作。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寫的那樣,我們今天的任務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列車前進,而是在我們所有人都陷入后資本主義野蠻狀態之前,拉動緊急剎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