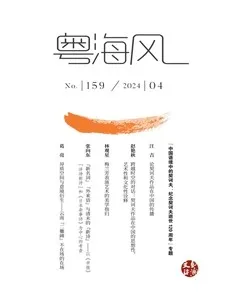新時期文學的在地經驗與世界想象
摘要:《花城》雜志自1979年創刊起即以“南國”特色和“海洋”屬性作為明確的辦刊定位,鮮明的在地性顯示出其與眾多新時期文學期刊的顯著區別。《花城》通過刊發香港文學和本土作家域外題材創作、譯介世界文學等途徑建構世界想象,較早參與到新時期文學與世界對話的進程中,并承擔了時代文化心理與文學價值觀念變革的媒介功能,呈現出中國當代文學新的整體性與面向世界的可能性,也為反思世界文學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提供了一種視角。
關鍵詞:《花城》 新時期 在地經驗 世界想象 世界文學
文學期刊是當代文學生產和傳播體系中的核心架構,新時期以來在文學價值觀念革新、話語空間開辟、審美趣味形塑、文化訴求表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新時期文學場域重建的重要平臺。《花城》雜志1979年4月于廣州創刊,最初以叢刊面世,1979至1980年間共出版7期,創刊號推出后旋即售罄,單期最高銷量65萬份。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刊物也隨之改為雙月刊,陸續創辦各類增刊,并開設“花城文學獎”。20世紀90年代以后相繼推出一批新人新作,成為先鋒小說的重要陣地,與《收獲》《十月》《當代》并稱當代文學期刊“四大名旦”,影響力不容忽視。目前學界成果較多關注《花城》自90年代以來的期刊行為及其在中國當代文學傳媒市場化、數字化轉型進程中所發揮的媒介功能[1]。將《花城》視為當代文學期刊典型個案,探討其與上述重大議題之內在關聯固然無可厚非,然而這一宏觀思路也導致《花城》的地方性、獨特性長期遭受遮蔽。故此,本文將以《花城》在1979至1980年間出版的7期叢刊(以下簡稱“早期《花城》”)為對象,結合時代歷史文化語境,通過對其價值定位、編輯實踐及話語表征的分析,深入考辨早期《花城》借助在地經驗與世界想象在新時期文學與世界對話過程中所承擔的重要功能,以及對新時期文學場域重建和價值觀念革新所產生的影響。
一、新時期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可能性
洪子誠先生在分析20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時指出:“對于當代文學如何處理外國文學的觀察、討論,不能只在外部展開。從方法的層面,如何從靜態、外部描述,進到內部的結構性分析,以呈現民族化過程的復雜狀況,是要重點關注、考慮的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發現,當代文學民族化建構和‘世界化’的實踐,是攜帶不同文化成分、具有不同文化觀念和想象的作家、理論家,特別是文學‘主政者’在當代博弈、沖突的過程。”[2] 這番表述提示我們:世界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結構性存在,一直以來未曾因為種種外部因素區隔而失卻對當代文學在創作、思潮上的作用功能;相反,它更為深刻地揭示了當代文學內部不同觀念之間的交相辯駁,從而真切地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學在自我身份建構過程中所置身的復雜情境,凸顯出這一過程中諸多混雜性、探索性實踐的價值。
早期《花城》正是新時期文學將世界文學內化到自身結構中的一種探索性實踐。這一實踐在新時期政治、文化語境嬗變中展開,也與刊物所處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經濟領域的銳意革新也輻射到社會環境與文化領域。1978年,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宣布恢復活動后不久,廣東文藝界便積極行動,參與到新時期文學場域重構的歷史進程之中。1978年12月,廣東省文學創作座談會召開,周揚、夏衍、林默涵、張光年等人受邀到會,周揚以《關于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為題進行講話,講稿于1979年2月被《人民日報》全文刊發,1979年3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在此報告中周揚提出“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藝術”的概念并進行系統闡發,認為新時期文藝工作的重點應轉移到“反映新時期人民群眾的生活和斗爭”和“回答時代所提出的各種新的問題”,表達群眾“內心深處的真實思想和情感”,[3] 旨在明確文藝的獨立屬性與主體地位,推動新時期文藝生態全面革新。此文所傳達出的文藝指導思想不僅成為1979年11月周揚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總報告《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理論基石,也奠定了廣東新時期文藝工作方針。
在此背景下,《花城》雜志應運而生。相較于北京的《十月》、上海的《收獲》、南京的《鐘山》等新時期文學名刊,《花城》自創刊起就對其“身份”——“南國”特色和“海洋”屬性——有明確認識。刊名“花城”受秦牧散文《花城》啟發而生,既彰顯了鮮明的地域特色,又包蘊著新時期文學百花齊放、不拘一格的文學精神。早期《花城》在辦刊方針和編輯理念上都顯現出相當開放的世界視野,設置了“外國文學”“海外通訊”“流派鑒賞”等具有鮮明海外色彩的欄目,并刊發香港文學作品與批評,發表本土作家域外題材創作,大量譯介世界文學。在1982年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花城》是國內最早刊登馬爾克斯獲獎感言的刊物。早期《花城》的價值定位表現出與世界文學交往對話的明確意圖,而其在編輯實踐與話語表征方面則顯現出不同文學與意識形態觀念之間的交相辯駁,反映了新時期文學在自我身份建構過程中所置身的復雜情境,也為反思世界文學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提供了一種視角。
二、早期《花城》對香港文學
與世界文學的引介
劉再復將新時期中國文學界對世界文學的接受視為繼五四以來又一次巨大浪潮,是“‘全面拿來’的局面,也是‘全面輻射式’的影響”,[4] 其特征在于側重對20世紀歐美多元文學價值和新審美取向的吸收。如果從這一全局性視野出發審視早期《花城》對域外文學的譯介傳播實踐,不難發現其背后的動因、邏輯與新時期文學“走向世界”的整體思潮有觀念上的同構性,但與此同時也顯現了對新時期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獨特思考。
《花城》創刊號發表了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短篇小說《斷層之南》(余杰譯)。小說以舊金山的階級分化為主要內容,斷層之北是商業區,斷層之南是貧民窟。主人公加州大學教授弗里迪德·拉蒙德臥底南區進行工人階級社會學研究,最后親自組織并參加工人罷工,徹底脫離了教授階層,成為新的工人領袖。在小說末尾的“譯后記”中,編者著意強調小說主題在于表現資產階級學者通過實際斗爭而成長為工人運動領袖,反映了美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斗爭。杰克·倫敦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被稱為“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他出身貧寒,青少年時期有輾轉多地做苦役的經歷,成年后受到斯賓塞、達爾文、馬克思等人思想的影響,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前期作品多反映美國社會勞資矛盾,在蘇聯受到肯定。也正因如此,杰克·倫敦是冷戰期間極少數作品仍在中國發行的美國作家之一,新時期之前中國文學界對其作品的批評與詮釋主要停留在意識形態層面。可見早期《花城》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十分謹慎,沿襲了20世紀50至70年代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主潮,有限度地邁出“走向”世界文學的最初步伐。
自第2期開始,“外國文學”欄目發稿數量有所增加,刊登了美國作家杜魯曼·卡坡特(今譯杜魯門·卡波特)的小說《一壺銀幣》(杜漸譯)和蘇聯作家馬雅可夫斯基的小說《官僚制造廠》(汪飛白譯),及文學評論《卡坡特及其小說》。杜魯門·卡波特生于1924年,于20世紀40年代初登上文壇,代表作為1966年出版的非虛構長篇小說《冷血》。卡波特成名于冷戰期間,其前期創作大量運用意識流手法,帶有鮮明的超現實主義色彩,其筆下的主人公多為性格孤僻、內心畸形的小人物;后期則致力于基于真人真事的報道性寫作,引發非虛構小說寫作潮流。
從現有資料來看,《花城》是中國最早譯介卡波特作品的文學刊物。《一壺銀幣》以作家熟悉的南方小鎮為背景,通過兩個藥店老板爭生意的矛盾,描寫了轟動小鎮的“酒壺里有多少錢”的競猜活動,以同情的筆觸寫出窮孩子“蘋果籽”參加競猜以獲得獎金給姐姐鑲假牙的經歷,充滿溫情,南方色彩濃郁。在《卡坡特及其小說》中,譯者杜漸著重對卡波特小說的形式創新進行推介,指出小說所采用的新新聞體通過內心獨白、意識流、回想等展示人物性格,報道真實,鋒利,有生命力,“以解救文學被現代化大眾傳播媒介屠殺的危機”。第3期刊發了美國作家小庫特·馮尼格的短篇小說《貼鄰》(馮亦代譯)。馮尼格被譽為黑色幽默大師,《第五屠宰場》是其代表作。小說以諷刺語調嘲諷美國生活中家庭教育與社會環境的沖突,《花城》也是較早將黑色幽默派介紹到中國的刊物。以上兩例足以說明早期《花城》在新時期伊始便能夠及時把握世界文壇動態,以先鋒性文學觀念和審美標準對外國文學作品進行選擇、過濾,推動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新時期的傳播與經典化。
第4期刊發的《永久占有》(作者格蘭姆·格林,今譯格雷厄姆·格林,杜漸譯)和第7期刊發的《十全十美的女仆》(作者阿加莎·阿克里斯蒂,樹玉譯)均為英國推理小說。前者寫新婚妻子收到舊情人的信而導致夫妻間的猜忌;后者是短篇集《馬普爾小姐的最后案件》中的一篇,講述馬普爾小姐破獲的女仆殺人案。《永久占有》將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有機結合,通過莫名而來的情書展露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十全十美的女仆》則呈現了偵探小說的經典敘事結構,二者均為中國讀者提供了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同時也呼應了即將盛行的通俗文學熱潮。此時中國當代文壇依然以純文學的精英趣味為主,早期《花城》已經開始表現出和凝重的主旋律相區別的通俗性與先鋒性并存的文學審美品格。由此觀之,《花城》編輯的文學嗅覺是非常靈敏的,能夠將世界文學經典與當代中國“解放思想”潮流、讀者日益變化的文藝心理和市場化閱讀需求聯結起來,通過對世界文學這一“結構性他者”的選擇性引介回應了新時期文學自我建構的強烈訴求。
早期《花城》雖然在世界文學譯介數量與影響力方面難以與同時期《世界文學》《外國文藝》等專門性期刊相匹敵,但在香港以及海外華文文學引介方面卻是獨領風騷的。《花城》創刊號開設“香港通訊”專欄,首篇刊發曾敏之的通訊《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曾敏之祖籍廣東梅州,是著名報人、作家,時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合會會長,長期致力于向內地推介臺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稿頭附有曾敏之與編輯的通信,交代了此文的來龍去脈:“《花城》出版,可喜可賀。承囑報道海外文情,現趕寫了一篇,約四千字;并附香港作者阮朗的小說《愛情的俯沖》。海外文談,以后還可以續寫;也許接觸面更廣些或更深些,我當盡力效勞。”[5] 從信函中不難捕捉到以下信息:一、《花城》編輯部關注內地以外華文文壇,有意識地在刊物中設立專欄,以“報道海外文情”為宗旨;二、專欄的開設并非短期構想,而有周密的長期規劃;三、曾敏之不僅寫稿,還負責組稿,是香港文學與內地期刊的交流媒介。這表明自《花城》創刊伊始,編輯部即已明確“面向海洋”的辦刊定位,從地理空間最近的香港和東南亞開始,拓展刊物視野,有計劃地逐步拓展文學空間版圖。《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一文以不長的篇幅介紹了港澳和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狀況,信息量頗大,曾敏之對幾地華文文學代表性刊物、作家、華文文學發展的特點都進行了精到點評。這是新時期中國內地文學期刊發表的第一篇介紹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的文章[6],一時成為標志性事件。該專欄第2期刊發曾敏之的《尊嚴與追求》,介紹了香港作家海辛、何達、原甸、洪荒、舒巷城、谷旭等人的創作。雖各有側重,但篩選與評價標準仍以現實主義為尺度,對香港文學的本土性、主體性和差異性關注不足。第3期“香港通訊”專欄的《新加坡漢語文學掠影》(作者曾敏之)、第4期“花城論壇”專欄的《雜談人物描寫》(作者林真)、第5期“香港通訊”專欄的《香港詩壇一瞥》(作者原甸)等文章也承襲了相似的評價標準,這表明在現實主義美學原則主導下,當時中國內地文學界、學術界對香港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的接受視角仍然比較單極化,這種情形要到20世紀90年代才逐漸改善。
除“香港通訊”外,《花城》自創刊號開始就設有“香港來稿”欄目,首篇刊發的是阮朗的小說《愛情的俯沖》,講述香港少女阿華自幼被生父拋棄,幾經輾轉被賣到雜技團表演,生活困苦。當她終于在歐洲女記者安妮的幫助下準備與男友阿祥私奔之際,卻被生父和雜技團老板之子設計害死。小說以現實主義為基調,表現出強烈的社會問題意識;同時又在敘事中營造巧合,凸顯商業社會光怪陸離的都市景觀,呈現出通俗文學的特點。小說中的地理空間具有世界維度,呈現出香港文化的開闊性,也有助于表現世界主義、人道主義主題。
從第3期開始,“香港來稿”欄目擴充為“香港文學作品選載”,每期刊發作品數量顯著增加,體裁也更為多樣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反映出刊物在有意識地強化自身的“海洋風格”。第3期的7篇短篇小說均為都市題材:劉于斯的《小姐的新衣》采用擬人手法,以服裝店新衣的身份敘事,充滿時代感與都市時尚氣息;海辛的《廣場上的單車隊》講述貧寒青年的創業故事;陶然早期作品《誘惑》則以六合彩開獎為敘事內核,表現都市青年在沉重生活壓力下的茫然心態,頗具現代主義色彩;舒巷城的《雪》講述失業的香港青年搭乘飛機去英國,經停曼谷、巴基斯坦、羅馬的途中經歷和忐忑心情;陳浩泉的《銀色的夢》虛構臺灣少女巴巴拉和李珍珍懷揣明星夢到香港,卻被電影圈的聲色犬馬裹挾失去自我;白洛的《二上九龍灣》則以一家人生存境遇的變遷映射香港社會發展歷程;劉以鬯的《除夕》側重描寫主人公因兒子病逝而借酒澆愁,以時空交錯的意識流手法強化了人物的痛苦心緒。
這一批作品以反思性視角書寫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經濟繁榮、物質生活豐富的表層特征,深刻揭示了身處其中的個體內心隔絕、孤寂、漂泊、茫然、焦慮之感。從效果上看,通俗小說的情節模式和現代主義敘事技巧對人物心理真實的刻畫,均為新時期文學提供了新鮮經驗,使讀者領略現實主義之外的文學風景,契合了他們的文化心理需求;同時也以都市生活的種種“奇觀”吸引讀者的閱讀興趣,迎合了方興未艾的文學市場化趨勢,有利于刊物銷量節節攀升。
根據學者顏敏的研究,新時期初包括《花城》在內的中國文學期刊均采用“專欄化”策略刊載香港以及海外華文文學,將其作為內容與形式的特殊單位,構成了相對獨立的傳播空間,從而強化了香港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的獨特屬性。[7] 這一傳播策略上的獨特性建構與作品題材內容上的奇觀化相結合,共同形塑了香港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的“他者”形象,強化了早期《花城》的“海洋屬性”,為讀者開辟了本土以外的文學視野,回應著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文化與文學的癥候性關聯。而《花城》借助政策與地緣優勢邀請香港作家來粵參加座談會等舉措,愈發證明了新時期文學與廣闊世界對話的可實踐性。
三、新時期作家的域外行旅與世界想象
《花城》自創刊號伊始開辟《海外風信》專欄,主要刊載中國作家的海外游記散文,前三期刊發了廣東作家華嘉、杜埃和畫家林墉、王維寶出訪泰國、巴基斯坦和日本的游蹤記述。四人分別時任廣東省文化局、文聯、畫院文化官員,隨官方代表團出訪,其域外游記自然也帶有比較強烈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在詳述域外見聞的基礎上追溯兩國交往歷史,同時表達了對未來國際文化交流的樂觀暢想。法國學者巴柔在論及文學中的異國形象時曾指出,作家對異國的書寫大體有三種基本態度——狂熱、憎惡與親善。[8] 上述游記明顯是基于親善態度對異國形象的建構,體現出中國作家積極尋求與世界互識互認、平等對話的情感姿態,不僅折射出新時期中國社會集體想象的一般情態,也可被視為新時期文學意圖將自身納入世界文學范疇的努力。從第4期開始,《花城》將域外游記的觀照視野拓展至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刊發了《愛荷華掠影》(作者夏易)、《瑞士“隱士城”——盧塞恩》(作者葉君健)、《赤道心花——喀麥隆散記》(作者賀季生、陳孝英)、《在哥本哈根鬧市》(作者李惠英)等文。在上述游記中,作家亦以肯定為主調對域外自然、人文景觀進行描述,出現大量對中外人民友好情誼的描寫,表現出文化對話的積極心態。
與域外游記中基于友善心態與認同情感建構出的扁平化異國形象相比,早期《花城》刊發的域外題材小說、詩歌中則塑造了更為復雜的異國形象,從中折射出新時期文學內部不同思潮與話語的交往對話。創刊號上發表的中篇小說《雪白的鴿子》(作者王文錦、方亮)即是一例。小說采用倒敘手法,以化工廠職工孫小紅收到美國專家漢杰來信為線索,引出孫小紅關于1976年在水處理車間與漢杰共事的回憶。美國做派的漢杰之于封閉了數十年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典型的異類,他“頭戴蘋果綠塑料輕便安全帽,系帶很隨便地勾在下嘴唇邊,使得下巴那撮山羊胡子得意地翹起來,短袖牡丹花圖案的上衣僅扣上最下面的一個扣子,露出了兩臂和前胸濃得發黑的汗毛,掛在脖子上的金色十字架晃來晃去,灰白的頭發從兩鬢一直覆蓋到齊耳根,活像鋸了角的一只老山羊”。[9] 中國工人與漢杰之間的關系則進一步隱喻了一個巨大的充滿沖突的政治文化語境:在交往初期,工人們對漢杰有著明顯敵意和排斥,雙方矛盾重重。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杰以其工作要求嚴格、投入忘我、嚴謹認真漸漸贏得了中國工人的認可和尊重,漢杰也對工人們產生了基于道德情感的認同,并一改對中國工業技術落后的刻板印象,與技術員老區一同解決了技術難題。巴柔認為,異國形象作為社會集體想象物“帶有一種深刻的雙極性:認同性和與此相輔相成的相異性,相異性在這里被視作身份認同的對立和補充”。[10] 也就是說,異國形象并非對現實的真實反映,而是注視者將自身的文化想象轉換到隱喻層面的產物,是社會文化觀念和價值體系的表征。對他者形象的相異性書寫實則是反視自我的一種方式。《雪白的鴿子》中的美國專家漢杰正是一個具有典型雙極性的異國形象,他既玩世不恭,倨傲自大,也善良,嚴謹,忠于職守,還有對宗教的虔誠,對人性的敬意,其形象無疑具有符號 表征作用。小說設置了一個地緣、政治、文化二元對立的框架,使文本內部具有相當開闊的張力,建構起一個自我與他者互動的話語場。作者在敘事中很好地把握了沖突的節奏,將漢杰與中國工人之間的關系對標中美兩國長期以來的政治軍事沖突與和解,在世界歷史進程的坐標系中構建小說情節,表現冷戰后國際關系的新變化。小說雖迂回地流露出當代文學長期內化的意識形態取向,但又未止步于政治說教,而是更為強調文化溝通的可能性。漢杰這一人物作為新時期中國文學中較早出現的異國形象,表征出民族文學在走向世界文學過程中所發生的深層變異,這恰恰也說明新時期文學已經開始生成一種與世界展開對話的新形態。
《花城》創刊號刊登了詩人蘆芒的遺作《“媽媽婭”傳奇——羅馬尼亞詩抄》。此詩源自蘆芒訪問羅馬尼亞期間的采風所得,羅馬尼亞民間傳說記錄了該國被外國侵略者占領時,小女孩懷念被侵略者殺害的媽媽而不停呼喚。詩人以重章復沓的方式將女兒對母親深切的思念之情的傾訴表現得淋漓盡致。素有“中國馬雅可夫斯基”之稱的蘆芒在“文革”中受到嚴酷迫害,平反后他將狂放的詩情投射在異國傳說中,借以表達對自由的贊頌、對暴政的反抗。新時期文學中的異國形象承載了基于歷史語境的思想與情感的復雜混合,它作為在歷史斷裂時刻新生成的文化想象,避免了類型化、模式化的命運,而以多元豐富的形態于新時期文學中不斷涌現,彰顯出新時期文學與世界文學交往對話的迫切性與可行性。
在跨文化交往過程中,人們常常既保留對根源的認同,同時也有強烈的走出家園邊界的跨文化心理,二者互動促成了世界意識的生成。正是基于這種走出邊界、想象異邦的心理,早期《花城》刊發了數量可觀的本土作家域外題材作品,其中既表現出與世界對話的強烈愿望,也以對異國形象的書寫凸顯出新時期文學的主體性,反思了世界文學的西方中心主義范式。
結 語
早期《花城》對自身的定位為“立足廣東,面向全國,兼顧海外”,因為“地理位置毗鄰港澳,歷史淵源上廣東華僑遍世界”,所以“《花城》要豐富多彩,要刮上一點‘海洋風’,……更多樣,更新鮮,更活潑,更深刻,更美”[11],借助地理的比鄰、血緣的勾連、交流的便捷等多重歷史與現實機緣,早期《花城》較早地突破了當代文學的地緣和觀念桎梏,形成鮮明的“南國特色”和“海洋意識”,為新時期文學與世界的對話提供了有效途徑。
正如伊格爾頓所言:“文學形式的重大發展產生于意識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它們體現感知社會現實的新方式以及藝術家與讀者之間的新關系。”[12] 早期《花城》刊載香港文學和本土作家域外題材創作、譯介世界文學的話語實踐可被解讀為一個動力學過程,客觀上在當代文學內部建構了世界空間,也催生出具有世界視野的讀者群體,在文學文本中呈現改革開放初期社會轉型的思想文化邏輯,并承載了國家意識形態、市場和文學場域互動的基本生態,呈現出中國當代文學新的整體性與面向世界的可能性。
本文部分內容已收錄于單昕著《本土經驗與世界語境》(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一書,在本刊發表時有較大改動。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24YJA75100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東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
注釋:
[1] 此類成果如朱新亞《傳統紙媒突圍背景下〈花城〉雜志的轉型之路》(《出版廣角》,2020年第19期),常維佳《文學轉型時期的〈花城〉研究(1990—2010)》(中國礦業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朱艷玲《新媒體時代純文學期刊轉型探索——以〈花城〉雜志為例》(《揚子江評論》,2016年第4期),賈化冉《期刊轉型中的〈花城〉》(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4年)等。
[2] 洪子誠:《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15—16頁。
[3] 周揚:《關于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廣東省文學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頁。
[4] 劉再復:《筆談外國文學對我國新時期文學的影響》,《世界文學》,1987年,第6期。
[5] 曾敏之:《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花城》,1979年,第1期。
[6] 饒芃子:《大陸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概況》,《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年,第1期。
[7] 顏敏:《在雜語共生的文學現場——“臺港暨海外華文文學”在中國大陸文學期刊中的傳播與建構(1979—2002)》,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8]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頁。
[9] 王文錦、方亮:《雪白的鴿子》,《花城》,1979年第1期。
[10] 同[8],第121頁。
[11] 本刊評論員:《不斷自問——〈花城〉兩年》,《花城》,1981年,第1期。
[12] [英]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