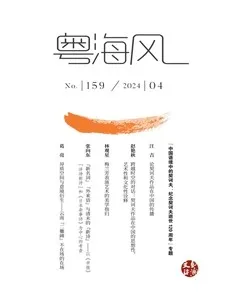從酒樓茶館時空體透視契訶夫和魯迅小說中的國民性
摘要:契訶夫和魯迅分別是俄、中兩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他們都以短篇小說的利刃揭露了所在國家的社會問題和國民性格弱點。魯迅曾被稱為“中國的契訶夫”,這兩位作家在小說的藝術風格和思想意蘊上有極強的共通性。本文從時空體的視角,探討這兩位作家小說中的酒樓茶館時空體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和國民性格特點,揭露了俄國極端的酗酒文化和中國從眾的看客群像。本文既是巴赫金時空體理論在實踐上的應用,是對文學創作中時空體類型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契訶夫和魯迅在時空藝術方面比較研究的創新和探索。
關鍵詞:時空體理論 酒樓茶館時空體 契訶夫 魯迅 國民性
一、時空體理論與酒樓茶館時空體的特點
俄國著名學者巴赫金(1895—1975)借用愛因斯坦的時空相對論中的術語“時空體”(хронотоп),將其引入文藝學中。該詞取自于希臘語chronos(時間)和topes(空間),即“時空”,強調時間和空間的不可分割性。[1] 該術語一般譯為“時空體”或“時空型”,有時也音譯為“赫羅諾托普”。巴赫金在《長篇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一書中專門研究了小說中的時空體問題,分析了從古希臘羅馬小說、中世紀小說到拉伯雷小說中的時空體類型,對小說的時空體類型和體裁類型在文學史的演變關系進行了論述。
巴赫金指出,時空體就是“文學中已經藝術地把握了的時間關系和空間關系相互間的重要聯系”[2]。文學時空體中的時間和空間密不可分,“時間在這里濃縮、凝聚,變成藝術上可見的東西;空間則趨向緊張,被卷入時間、情節、歷史的運動之中,時間的標志要展現在空間里,而空間則要通過時間來理解和衡量”[3]。時空體強調時間和空間的不可分割性,“更具體地說是時間和空間相互結合形成的某種相對穩定的模式”[4]。巴赫金認為,時空體具有體裁意義、描繪意義、情節意義,并且,文學形象和文學語言也具有時空體性質。
除了從歷史詩學角度研究的幾種時空體類型,巴赫金還歸納了現代小說中幾種常見的時空體類型,比如:田園詩時空體、外省小城時空體、道路時空體、城堡時空體、貴族莊園時空體、沙龍客廳時空體、門坎時空體,等等。巴赫金在該書的結尾指出了他理論的未完成性,也就是說,他提出了文學時空體的理論基石,但不可能羅列所有的時空體類型,因為文學中的時空體類型是不斷豐富發展的。
本文提出的“酒樓茶館時空體”正是以巴赫金的時空體理論作為理論基礎,主要借鑒了巴赫金提出的“沙龍客廳時空體”,以研究契訶夫和魯迅小說中的“酒樓茶館時空體”的時空特點。“沙龍客廳時空體”的特點在于:“從情節和布局觀點看,是在這里實現人們的相會,在這里開始故事糾葛,也時常在這里結束故事。最后還有極其重要的一點:在這里出現對小說具有特殊意義的對話,揭示出主人公各種性格、‘思想’和‘欲念’。”[5] 沙龍客廳里提前安排的“相會”讓不同的人們在此聚集,他們之間的對話可以展現人物的性格特點和內心世界,同時還能反映社會等級和人物關系,具有情節布局的意義。
另外,沙龍客廳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屬性,在這里“歷史內容、社會公共內容同個人的內容、甚至私下色情的內容兩相交織;……無論歷史時間還是傳記和日常生活的時間,它們那些具體可見的特征,都濃縮、凝聚在這里;與此同時,它們相互間又緊密交織,匯合成時代的統一標志”[6]。外來的客人與主人在沙龍客廳里“相會”,該空間承載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時間、傳記時間和歷史時間,因此該時空體兼具個人色彩和社會公共色彩。
法國哲學家和空間理論學者亨利·列斐伏爾(1901—1991)在《空間的生產》一書中將社會空間分為三大類:G(公共領域),M(中間領域),P(私人領域)。[7] 依據列斐伏爾的理論,沙龍客廳屬于“私人性的公共領域”,雖然位于私人家中,但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而酒樓、茶館則屬于完全的“公共領域”,是典型的公共空間。
因此,“酒樓茶館”可以被看作具有完全公共性質的“沙龍客廳”,在這個時空里,人們同樣實現了相會和交談,既包括提前安排的熟人“相會”,也有偶然的陌生人“相會”,不同人之間的對話能展現社會的風貌和時代的思想特征。該時空體在酒樓、茶館的空間里展現了日常生活時間和歷史時間,二者緊密融合。
一方面,酒樓、茶館的主要功能是供人休閑娛樂,人們在此飲酒、喝茶、吃飯,該時空里的人物一般呈現出輕松、真實的日常生活狀態。在酒樓、茶館里的對話體現了人物的性格、思想、等級、關系。國民性格特點,尤其是國民劣根性在這種輕松的日常生活時間中展露無遺。
另一方面,由于酒樓、茶館是典型的公共空間,它具有強烈的社會公共色彩,相比于沙龍客廳減少了私密性。人們進入酒樓、茶館比進入私人的沙龍客廳要容易得多,因而酒樓茶館時空里的人員流動性比沙龍客廳更大,它的空間對外聯結性比沙龍客廳時空更明顯。因此,“酒樓茶館時空體”里的人物關系更加復雜,可以展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交流和碰撞,能更鮮明地呈現歷史時間的脈搏,揭露深刻的社會問題。
可見,“酒樓茶館時空體”的時空特點正體現了時空體的本質要素——時間與空間不可分割,二者相互結合形成某種相對穩定的模式,并對文學作品中的情節、人物形象形成重要影響。本文將從時空藝術的視角比較契訶夫和魯迅小說中“酒樓茶館時空體”的特征,以及該時空體折射出的社會問題和國民性格特點。
二、契訶夫筆下的酒樓時空體:
極端的酗酒文化
契訶夫的小說只描寫了酒店、飯館等空間,沒有寫到茶館,因此本文只研究他筆下的酒樓時空體。在契訶夫的小說中,酒店、飯館這類公共休閑空間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醉酒之人,也有酒后閑談的人,還經常發生奇聞逸事。
比如:在鄉村小酒館里酗酒互毆的農民們(《太太》,1882);在農村小酒館喝醉酒就公然暴揍妻子的后備兵德雷胡諾夫(《你和您》,1886);在牙醫家不敢向舊相識借錢,而在“文藝復興”飯館里卻泰然自若地向男人們要錢的交際花萬達(《熟識的男人》,1886);在城郊酒館喝酒胡鬧的富裕工廠主弗羅洛夫(《醉漢》,1887);等等。
在契訶夫的酒樓時空體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現,人們社會地位的對比得到強化。《醉漢》里的富裕工廠主弗羅洛夫倚仗自己有錢,在飯館揮金如土,任意捉弄飯館里的伙計、琴師、歌女;而底層勞動人民為了獲得富人的一點施舍,可以完全拋掉尊嚴,在富人面前裝傻賣乖。《牡蠣》展現了城市里的貧富差距,富人豪擲十盧布,只為“欣賞”饑餓的小男孩生吞牡蠣,小男孩因吞下牡蠣殼胃痛難耐,他父親卻后悔沒向富人先生討要幾個錢,而把錢浪費在吃牡蠣上;眾人對小男孩生吞牡蠣的圍觀表現了大城市里人們的冷漠無聊。貧富差距、人們的階級和社會地位的對比在酒樓時空體里得到鮮明的呈現。
另外,人際之間的矛盾沖突在酒樓時空體里更容易被激化,人們在酒精的刺激下更容易做出過激的行為。比如:《太太》里的馬車夫斯捷潘喝醉后與哥哥謝敏扭打成一團;并找到被父親趕出家門的妻子,本想帶她逃去庫班,但妻子的謾罵激怒了他,他失手打死了懷孕的妻子。《你和您》和《邂逅》里鄉村小酒館的斗毆打架也展現了酒樓時空體里容易被激化的人際沖突。
第三,酒樓時空體作為一個公共性強、人員流動大的時空,這里經常發生對話和信息交流,人們的閑談展現了世道人心,體現了歷史時間和日常生活時間的交織。比如:《上尉的軍服》里的裁縫師傅美爾庫洛夫在酒店里炫耀自己常為大官們做官服,他給上尉做完官服被拖欠工錢還挨了一頓打,他反而夸贊上尉是“真正的老爺”,這體現了俄國社會官僚對民眾的欺壓,以及民眾畸形的奴才性格。《歹徒·目睹者的陳述》通過小飯鋪里外國人觀看日食的行為記錄了俄國出現日全食奇觀的歷史事件,體現了歷史時間,而當地人對此事的誤解表現了當時俄國民眾科學常識的匱乏。《邂逅》里的農民庫茲瑪整日游手好閑,他偷走虔誠的基督信徒葉甫烈木為教堂募捐到的26盧布,到小酒館買酒喝,不承認偷盜,反而揍老人一拳。后來他在葉甫列木的開導下認罪懺悔,但轉眼又溜進小酒館酗酒打架。這反映了農民酗酒成性、道德敗壞的社會狀況。《出事·車夫的故事》講述了農村小酒館里一位農民因吹牛露富被強盜滅口的故事,體現了當時農村民風剽悍,盜賊橫行的社會問題。
綜上,契訶夫小說的酒樓時空體除了表現俄國社會存在的貧富差距、官僚對人民的欺壓、普遍的道德敗壞等社會問題,還突出展現了俄國人重要的嗜好——酗酒。酗酒的嗜好折射了俄國底層人民的貧窮和俄國人普遍具有的好走極端的國民性格特點。
酗酒現象在俄羅斯的農村、縣城和城市都十分普遍,無論是底層的窮人,還是上流社會的富人都愛酗酒。小說《嚴寒》(1887)里談到俄羅斯嚴寒的氣候導致人們愛喝酒,因為酒能使人在冬天感到暖和。然而,除了氣候因素,對于底層人民來說,貧窮和懶惰才是他們酗酒的深層原因。道德敗壞的根本原因是底層人民普遍的貧窮,酗酒和貧窮又互為因果。正如《新別墅》里鐵匠羅季昂的妻子斯捷潘尼達抱怨的:“人一窮,罪過就多,心里有了苦惱就會不住地罵街,像狗一樣,說不出一句好話,什么事都干得出來……”[8]
酗酒文化給底層民眾帶來極大的危害,酗酒不僅導致打架、家暴、偷盜等惡行,有時甚至鬧出人命。窮人們因為酗酒變得更加貧困,又因貧困抱怨生活,更嚴重地酗酒,酗酒和貧窮互為因果,構成惡性循環。比如:《父親》(1887)里的老父親穆薩托夫因為酗酒將生活弄得一團糟;《農民》(1897)里的大兒子基里亞克常年酗酒,打老婆;等等。因為酗酒陷入赤貧的例子在契訶夫的小說中不勝枚舉。
貧窮是導致底層勞動人民酗酒的重要外部因素,而對于富人和普通人來說,酗酒文化的內在心理因素則是俄羅斯人好走極端的民族性格。俄羅斯人喜歡借助酒精的刺激作用抒發情緒,追求絕對的自由和徹底的放飛靈魂。
在《太太》中,農民馬車夫斯捷潘平日在面對地主太太的驅使和父親、哥哥的壓榨時,總是逆來順受,只有在小酒館喝得爛醉時,才變得血氣方剛,與哥哥謝敏大打出手,并打算帶妻子逃去庫班。酒精幫助老實巴交的斯捷潘增加了反抗的勇氣,卻也讓他失去了理智,最終因為酒后誤傷懷孕的妻子,釀成悲劇。
在《醉漢》中,富裕的工廠主弗羅洛夫在酒館里因為不滿意菜品而掀翻整桌飯菜,而當茶房端上紅酒和美味佳肴后,弗羅洛夫卻一味灌白酒,啃面包。他一會兒命令琴師、歌女、韃靼男孩表演滑稽的節目,一會兒向律師控訴他對妻子的憎恨,一會兒又拿香檳酒砸碎電燈和掛畫。弗羅洛夫在醉酒后的恣意胡鬧中并沒有感受到快樂,只是借酒勁發泄內心的煩悶、空虛和不滿,一面撕破他人和自己虛偽的面具,一面在酒精的作用下游戲人生,揮霍生命。
俄國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分析過俄羅斯民族心理中存在崇拜酒神的非理性主義因素,指出俄羅斯人普遍具有愛走極端的性格傾向,“俄羅斯的精神就在于此,指向最后的和終極的,指向一切方面的絕對存在,指向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愛”[9]。
中國學者汪劍釗在比較中、俄兩國民族心理結構時也指出俄國人好走極端的傾向和對非理性主義的偏好。他指出:“俄羅斯人的思維與西方的傳統思維不太一樣。它不講究邏輯論證,對理性持排斥態度,更多地信奉啟示的精神。……俄羅斯則由于其特殊的自然—人文背景,科學的傳播存在著很大的障礙,資本主義進程特別緩慢。即使出現過羅蒙諾索夫這樣的科學天才,也并不曾培養起民族意義上的理性精神。”[10]俄羅斯人性格里這種混沌、蒙昧、狂醉的“酒神狂歡”因素正是受到非理性精神的驅使,導致了俄羅斯人好走極端,迷戀絕對存在和絕對自由的民族性格特點,這正是俄國人酗酒成風的內在心理根源。
總之,酒樓時空體是契訶夫小說中重要的時空體類型,這里匯聚了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人群,展現了人與人之間復雜的關系和矛盾,凸顯了俄國當時各方面的社會問題,更是展現俄國底層民眾因為貧窮而酗酒的悲慘生活,反映俄國人愛走極端,偏好非理性主義,追求靈魂絕對自由的最佳時空背景。
三、魯迅筆下的酒樓茶館時空體:
從眾的看客群像
魯迅小說中的酒樓、茶館時空十分常見:《孔乙己》《明天》《風波》這三篇小說都描寫了魯鎮的咸亨酒店。《阿Q正傳》寫了未莊的酒店,小說《藥》描寫了華家茶館,《長明燈》寫了吉光屯灰五嬸的茶館,《祝福》提到縣城的酒樓福興樓,《在酒樓上》的故事發生在S城的一石居酒樓。楊義先生指出,“舊中國作為宗法制社會流行的是酒店茶館文化”“魯迅寫的‘魯鎮’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茶館酒店文化”。[11] 可見,酒樓茶館時空體在魯迅的小說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魯迅筆下的酒樓茶館時空體都發生在農村和小城鎮的大時空體背景下,由于20世紀初中國農村和小城鎮的人們消費水平和經濟條件的限制,普通人最常去的公共娛樂場所就是酒樓和茶館,他們在這里尋求單調生活中的調味品——獲取新的信息、談資、笑料。在酒樓茶館里,人們不僅飲酒喝茶,更熱衷于談論時事八卦,酒樓茶館是人們進行信息交流的重要場所,也是反映社情民意和時代動態的重要空間。酒樓茶館時空體承載著人群匯聚、信息交流和娛樂消遣的多重功能,是普通勞動人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
熊家良說:“魯迅曾說中國人多為‘示眾的材料’和‘無聊的看客’,這‘看’與‘被看’往往便是借助于小城的酒店茶館來進行。夏瑜的經歷成為華家茶館茶客們的談資,孔乙己的遭遇作了咸亨酒店顧客們的‘下酒菜’,單四嫂子在間壁酒店藍皮阿五、紅鼻子老拱等酒鬼不懷好意的惦記中守著天明……”[12] 可見,酒樓茶館時空體是一個“看/被看”的時空,是“看客”聚集的時空;另外,酒樓茶館時空也是輿論和信息的集散中心,它也是“說/被說”的時空。
咸亨酒店在魯迅的多篇小說中出現,它代表了魯迅小說中酒樓時空體的一系列突出特征:它是魯鎮居民消遣娛樂的場所,這里既是信息集散中心,也是人群匯集的中心,既是看客的舞臺,也體現了公共空間的社會等級化。
《風波》里的七斤就是從咸亨酒店得知“皇帝坐龍庭且須有辮子”的消息,可見酒店是小城鎮或村莊里消息最為靈通的地方。《明天》和《孔乙己》刻畫了咸亨酒店里的看客群像: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總是打單四嫂子的歪心思,直到酒店打烊還醉醺醺地唱著挑逗的小曲;酒店的酒客們習慣于揭孔乙己的傷疤,眾人以嘲笑孔乙己為樂。
咸亨酒店是一個充分等級化的公共空間,柜臺外站著喝酒的是做工的短衣主顧,屋子里坐著喝酒點菜的是穿長衫的主顧,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13]。他在酒店里顯得“不倫不類”,他在這里沒有自己的位置,這使他成為被多數人嘲笑、凌辱的少數人。而孔乙己即使被眾人嘲笑,即使被丁舉人打折了腿還要用雙手爬著來咸亨酒店,一則是因為他喜好喝酒,二則是因為他需要到酒店這個公共空間尋求存在感。“孔乙己自己覺得他是讀書人要高短衣幫一等……于是他就到短衣幫聚會的公共空間——咸亨酒店來了……”[14] 但即使是短衣幫也看不起落魄書生孔乙己,酒樓時空體放大了人們之間的等級差別和孔乙己的心理落差。
酒樓時空體充分反映了孔乙己無處安身的尷尬社會處境,他抱著讀書人高人一等的封建舊觀念,希望在公共性極強的酒店時空體里被看到,被認可,但他屢次受到酒店里看客們的奚落。“公眾的步步進逼——說穿他的隱情、揭戳他的‘傷疤’,讓他不斷地陷入難以擺脫的尷尬和困窘,失去他最看重的尊嚴,失去做人的資格,最后陷入死境。”[15] 孔乙己的落魄、自尊和困窘,看客們的冷漠、殘忍、麻木都凝集在咸亨酒店的一陣陣哄笑聲中,酒樓時空體對于展現人物性格和人物關系的描繪意義和推動故事發展的情節意義在這篇小說中得到全面的體現。
《阿Q正傳》里未莊的酒店也具備與咸亨酒店類似的功能,它也是未莊消息最靈通的地方。當阿Q從城里發財回到未莊,他首先去的就是酒店,向眾人展示他裝滿銀錢的大褡褳和新夾襖,用現錢打酒。阿Q正是因為知道酒店是未莊的輿論中心,所以他數次拋頭露面都是在酒店。與咸亨酒店類似,未莊的酒店也不乏無聊、冷漠的看客。當阿Q調戲小尼姑時,“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勛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為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才放手”[16]。酒店里看客們的圍觀滿足了阿Q好面子的心理,鼓舞他繼續欺侮小尼姑,可見看客們絲毫沒有同情心,將自己無聊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與酒樓時空體類似,茶館時空體還具有傳播信息、聚集人群、展示看客群像的這些特點。不過,與酒店不同,“茶的提神作用在風俗中往往深化為秩序、明辨是非的前提,并與一種儀式相關。魯迅成功地賦予茶館以嚴肅、尊卑分明的文化秩序形式”[17]。人們常常在茶館里討論公共事務,建立起某種文化和社會秩序。另外,茶館時空還承擔起“說/被說”的敘事功能,該時空里人們的談話“往往包含著對事情的評價……又通過人物對這件事的看法顯出他的性格和精神世界”[18]。這些特點在《藥》的華家茶館和《長明燈》的吉光屯茶館都有鮮明的體現。
《藥》借助華家茶館將華小栓的病和夏瑜革命這明、暗兩條線串在一起,茶客們對夏瑜革命的言說展現了不同人物的地位等級、性格和立場。康大叔一出場,華老栓殷勤地上茶,滿座的茶客也畢恭畢敬地聽他講話。可見康大叔作為掌握革命黨問斬消息的劊子手,在茶館中地位頗高。當封建反動勢力的代表康大叔輕蔑地詆毀革命黨夏瑜時,茶館里的茶客們也隨聲附和地罵夏瑜“賤骨頭”“發了瘋了”。可見普通群眾的思想保守落后,以及看客們的冷漠殘忍,茶館里這段對話表現了當時人民群眾與革命黨之間深厚的隔閡。華家的茶館是當時中國小城鎮社會的一個縮影,國民的愚昧、冷漠和初代革命者的無畏、天真都借由這里的茶館時空體得到充分的展現。
《長明燈》里吉光屯的茶館則是封建農村社會的縮影。如果說華家的茶館折射了小城鎮時空體里看客們的冷漠和麻木,那么吉光屯里灰五嬸的茶館則反映了農村時空體里農民們的守舊和愚昧,此處茶館時空體的功能與小說《藥》中的類似,不再詳述。
而《祝福》里的福興樓和《在酒樓上》的一石居這兩處酒樓與咸亨酒店、未莊酒店不同,這里的主人公是新式知識分子,而非閑人看客,因而并不突出展現該時空體匯聚人群、交流信息的功能。
《祝福》里“我”為了逃避魯四爺家封建迂腐的壓抑氛圍,打算第二天進城去福興樓吃一頓物美價廉的魚翅。這與《在酒樓上》里“我”回到家鄉S城去一石居酒樓喝酒的情形類似,都是新式知識分子回到家鄉后為了消解客中的無聊。小說《在酒樓上》講述了“我”在一石居酒樓偶遇舊友呂緯甫的故事。呂緯甫從一個朝氣蓬勃、銳意革新的進步知識分子變成懶怠、頹唐之人。呂緯甫初見“我”時還略顯生分,但幾杯酒下肚后就開始袒露心扉,講起他回鄉辦的兩件以失望和潦草收場的事情(給小弟遷墳卻找不到骨殖,給順姑送剪絨花而順姑已病死)。他十年來的生活像“繞了一點小圈子”,回到了原地。
這兩處酒樓時空體與前面酒樓時空描寫看客群像的情況不同,它展現了中國文人傳統的酒肆文化:文人飲酒與農民、市民閑人飲酒不同,后者或為貪杯,或為閑聊談天,而文人飲酒更注重以酒會友,借酒抒懷。此處并不強調該酒樓時空的“公共性”,而側重描寫人物的對話,展現人物的觀念碰撞和思想交流,表現了“五四”落潮之后啟蒙知識分子的迷茫和彷徨。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魯迅筆下的酒樓茶館時空體主要刻畫了看客群像——看客正是魯迅最深惡痛絕的一類人。魯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19] 喚醒沉睡的國民,改造國民劣根性,正是魯迅進行小說創作的初衷。酒樓茶館時空里的看客以消費他人的痛苦為樂,既源于他們空虛的靈魂,也因為中國人熱衷于從眾的心理。
咸亨酒店里并不是每位酒客都了解孔乙己的偷竊黑歷史,可只要有一個人嘲笑孔乙己,眾人便覺得有趣,跟著一起哄笑,這是出于無聊的從眾心理。華老栓的茶館里并不是每位茶客都覺得夏瑜是“瘋子”,但是因為康大叔下了定論,罵夏瑜“不成東西”,于是其他人也都附和著痛罵這位革命者,這是出于對權威勢力的畏懼以及對革命者的不了解而產生的從眾心理。在吉光屯灰五嬸的茶館里,一開始闊亭主張除掉想要吹熄長明燈的“瘋子”,人們就都往這個方向想;而當灰五嬸說到“瘋子”的祖父做過官,“闊亭們”便不敢貿然接受打死“瘋子”的建議,這是出于對封建禮俗的敬畏而產生的從眾心理。
“從眾”意味著和大部分人站在同一立場,意味著更加安全,意味著無須獨立思考,也無須承擔責任。正如吉光屯的閑人闊亭提出眾人一齊打死瘋子的建議,“大家一口咬定,說是同時同刻,大家一齊動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后來什么事也沒有”[20],這種法不責眾的思想正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群眾暴力”。正如《烏合之眾》里所說的“群體是匿名的,因此是免責的”[21]。
中國傳統文化由儒、釋、道互補形成,其中儒家文化處于核心地位,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在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朱熹在《中庸章句》中指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22] 這與俄羅斯人愛走極端的民族性格形成鮮明對比,“中庸”正好是“極端”的對立面,指不說過頭的話,不做過頭的事,取平庸之見即可。中國人的“從眾”心理從本質上就是源于對“中庸”之道的推崇。莊子提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23] 的“無是非觀”也與儒家的中庸精神不謀而合。人們排斥一切過激思想和行為,因此推崇大多數人的庸見,站在眾人集體的背后才是最安全,也是最不偏不倚的選擇。
作為匯聚人群的公共性場所,酒樓茶館時空體是最適合塑造人物群像和展現從眾現象的時空。“公共空間是人們群聚的地方,最易形成群體場景……而模糊的群像性質,也讓他們有了足夠的代表性……也許,在茶館和酒店這樣的公共空間里,魯迅還想借群體場景來表達他的一種思想,即‘群眾暴力’。”[24] 無論是《孔乙己》里眾酒客對落魄文人孔乙己的羞辱、嘲笑,還是《藥》里康大叔為首的茶客們對革命者夏瑜的鄙薄和謾罵,還有《長明燈》里吉光屯的茶館內茶客們商議對付“瘋子”的對策,都是以“眾”凌“寡”,是多數人對極少數人的身體或精神的戕害。魯迅借助酒樓茶館這種公共性極強的時空體舞臺集中展現了這群具有從眾心理的冷漠、麻木的看客,直指中國國民性格的劣根性。
以上可見,魯迅小說中的酒樓茶館時空是匯聚人群和信息,使人們產生聯結的公共性時空。該時空體展現了人們的社會等級差別、性格特點、思想立場,刻畫了一群冷漠、麻木的、愚昧的看客群像,體現了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群體暴力”,折射了時代觀念的保守落后與國民性格的從眾心理,并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
結 語
綜上,契訶夫和魯迅小說中的“酒樓茶館時空體”將人物的日常生活時間和宏觀的歷史時間濃縮于具有強烈公共屬性的酒樓、茶館空間中,形成相對穩定的時空模型。這類小說借助該時空體中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矛盾,突出描寫了某類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在人物極其放松的日常生活時間中展露其國民性格弱點。同時,酒樓茶館時空體里人們的對話體現了信息和思想的交流,折射了不同時代和國家的人們的思想和社會問題。
從國民性的角度來看,契訶夫筆下的酒樓時空體表現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和不同階層等級的對比,描寫了人與人之間激化的沖突矛盾,突出展現了俄國人的“酗酒”文化,體現了俄國人好走極端、偏好非理性的國民性格特點。魯迅小說中的酒樓茶館時空體則集中刻畫了冷漠、麻木的“看客”形象,反映了中國人慣于從眾,偏好“中庸”之道的國民性格特點。
俄國民眾鐘愛非理性的酒神文化,愛走極端;中國國民追捧“中庸”之道,傾向于觀望和從眾,這兩種對立的民族性格特點分別展現在二人小說的酒樓茶館時空體中,文學的藝術時空反映了社會文化的風貌,這充分證明了巴赫金的時空體理論對于文藝研究的方法論意義,該研究對于比較兩國民族心理結構、文化傳統有重要意義。
契訶夫和魯迅通過酒樓茶館時空體描寫了各自國家普通人民的生存狀態,揭露了人物的靈魂病癥。這兩位作家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和對社會問題的關照體現了作家的良心,表現了他們對各自國家人民群眾相似的態度: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們既同情人民的疾苦,也敢于揭露本國國民性格的劣根性,都以藝術時空的鏡子折射出歷史現實時間的弊病。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注釋:
[1] 盧小合:《藝術時間詩學與巴赫金的赫羅諾托普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72頁。
[2] [俄]巴赫金:《小說理論》,白春仁、曉河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頁。
[3] 同[2],第274—275頁。
[4] 潘月琴:《巴赫金時空體理論初探》,《俄羅斯文藝》,2005年,第3期。
[5] [6] 同[2],第448頁。
[7] [法]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劉懷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227頁。
[8] [俄] 契訶夫:《契訶夫文集(第10卷)》,汝龍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95頁。
[9] Бердяев Н. 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90. С. 32.
[10] 汪劍釗:《中俄文字之交:俄蘇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11] 楊義:《楊義文存·第四卷 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頁。
[12] 熊家良:《茶館酒店:中國現代小城敘事的核心化意象》,《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13] 魯迅:《吶喊》,載《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頁。
[14] 余新明:《〈吶喊〉〈彷徨〉的空間敘事》,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第95頁。
[15] 李莉:《中國現代小城鎮小說》,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
[16] 同[13],第523頁。
[17] 畢緒龍:《“魯鎮”:魯迅小說的敘述時空》,《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9期。
[18] 同[14],第89頁
[19] 同[13],第439頁。
[20] 魯迅:《彷徨》,載《魯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頁。
[21] [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頁。
[22] 〔宋〕朱熹:《大學中庸章句》,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頁。
[23] 〔戰國〕莊子:《莊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32頁。
[24] 同[14],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