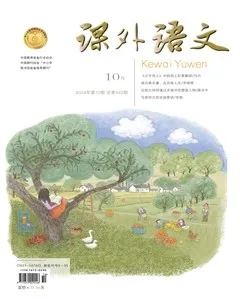《琵琶行》中的『跨文化﹄交融與和解
很多文學作品都深刻描繪了當時的時代文化背景,比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文章中寫生活日常,融情于景、情景動人。所以,文章看似在寫具體的情景,本質上還是在寫文化。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可以很好地借鑒這種寫作方式,讓我們的寫作更具內涵和深意。
對于很多人來說,文化似乎是一種高屋建瓴、虛無縹緲的事物,但實際上,我們身邊處處都是文化的影子。文化本質上是一個民族歷史、傳統、宗教、價值觀念、社會組織、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綜合體。而“跨文化”交流也隨時都在發生,每一次“跨文化”交流融合的過程,都是一次深刻的身心理解與融合。比如當我們轉換地域,用一種異質的視角來看待全新的地方,就是一種“跨文化”的解讀,而這種從不了解到了解的過程,就成為很多名人常常提及的內容。
地域變化給人帶來的改變是深刻的,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白居易的作品《琵琶行》中品味一二。從《琵琶行》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原本意氣風發的詩人被貶黜到邊陲之地后內心的迷茫和憂憤。白居易借著琵琶女的感情經歷映射出自己內心的痛苦和無助,表達他對繁華如花易逝的種種無奈。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長篇敘事詩的名作,《琵琶行》主要講述的是詩人因送別朋友,而偶然遇到來自京都的琵琶女,進而邀請至送別船上彈奏。在彈奏中,作者感懷琵琶女的遭遇,也感懷自己遭遇的故事。下面,我們從“跨文化”的視角,來解讀這篇作品。
一、獨在異鄉的身份認同危機
從“跨文化”的視角來看,《琵琶行》中,最大的文化差異體現在地域文化上的不適應。這一點我們需要結合白居易的生平來進行解讀,這也是《琵琶行》寫作的背景。唐憲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遭到誹謗,說他的母親看花時墜井去世,而白居易卻寫過有關“賞花”和“新井”的詩,有傷教化,因為這個不成理由的理由遭到了貶黜。白居易不得不從京都千里迢迢來到江州成為一名司馬。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生活在不同價值觀、規范等差異很大的文化背景中時,個體文化認同的建構和發展會遇到很大的阻礙。如果積極融入文化,建立一種認同感,就會實現身心和諧,反之,就會出現煩悶和陰郁的情緒。所謂詩人不幸詩文幸,很多詩作文章,也都產生于詩人的人生經歷的巨大變化時期。白居易也不例外,這篇《琵琶行》就是其在身心備受折磨的時候寫下的。
在《琵琶行》中,我們可以輕易看到作者對江州文化的種種不適應。“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司馬是一個閑職,過去的白居易身居高位,在皇帝身邊運籌帷幄,指點江山,但如今驟然變成了小小司馬,身無要職,其中的冷落凄苦,著實讓人難以承受。他對江州地區也充滿了怨念,進而還出現了身體上的疾病。身處偏僻之地,沒有美妙的音樂聊以慰藉,讓作者內心更加生出一種巨大的割裂和不適應感。“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這句話以景寫情,通過對一系列凄苦意象的描寫,來展現作者的難過。最后,“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即使是美好的季節,也只能自己默默獨酌。身處偏遠,沒有了故交舊友的陪伴,身邊沒有傾訴的對象,作者的一腔愁緒無處抒發,加上作者并不認同自己是江州的文化成員。文化認同是一種價值選擇,認同某種文化就意味著選擇了一種存在方式。作者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歸屬感,形成了身份認同的危機。
二、遠離主流文化的認同危機
除了地域文化上的認同危機,作者還存在一種遠離主流文化的認同危機。原來身在京都,作者身居廟堂之高,身處京都文化圈,必然是“憂其民”,人人都有一腔報國情懷,朋友之間講述的也都是國家大事、政治要事。在驚心動魄的政治角斗場上,白居易想來經歷了很多激流險灘,但他始終堅持著自己“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但是身處江州之后,白居易的憂國憂民似乎變成了笑話,自己的影響力消失了,沒有人再去聽他講話。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雖然白居易被迫離開京都,身體上離開了這片文化故土,但是精神上仍然將自己視作京都文化圈中的一員,因為聽到琵琶女彈奏有京都聲,就邀來一曲,可見一斑。這些都使得白居易在面對異質性文化時必然產生強烈的沖突。在此之前他以“兼濟天下”為志,但如今卻似乎再也沒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作者實際上也經歷了一場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江州,他找不到自己的知心之人,沒人理解自己的心境,這讓作者內心的愁苦不斷升級。
在《琵琶行》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有著很高的音樂造詣,其對于音樂意象的表現,古往今來人人稱頌。但是作者關閉了自己,認為潯陽地區沒有絲竹管弦之樂,“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展現了作者對于江州本地音樂的理解。以至于在聽到琵琶女的彈奏之后,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好音樂感受,“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也可以使用這種對比手法,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情感沖擊,進而更好地展現內心情感。在寫到來自京都文化圈的琵琶女彈奏時,作者描寫得極盡華麗,從“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小試牛刀,到“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的形象刻畫,我們從作者的筆端,仿佛身臨其境聽了一場美妙的音樂盛宴。
三、鏡像互文下文化交融與和解
在雅克·拉康的鏡像理論看來,任何人都是通過與他人的交往來認識自己的,而他人身上和自己相似的殘影,形成了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從這個理論來看,白居易和琵琶女,實際上形成了一種鏡像。白居易看似寫的是琵琶女,但實際上處處寫的都是自己,通過展現琵琶女的悲慘遭遇,來實現對自己當下處境的一種傾訴,也在反觀琵琶女的人生選擇中,展現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實現與自我的和解。在這個過程中,白居易實際上無意之中打開了自己封閉已久的內心,將自己與江州這個文化圈實現了一次短暫的共鳴,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來展現這種融合和和解。通過寫藝術境界之上的共鳴,實際上寫出了作者如何實現自我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危機的和解,所以這也是為何作者最后會“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在《琵琶行》中,琵琶女演奏了三次。第一曲,琵琶女的彈奏主要是排解自身,有著天涯無處覓知音的孤獨寂寥。文中寫到“忽聞水上琵琶聲”“尋聲暗問彈者誰”,也因為“錚錚然有京都聲”,打開了作者的心防。第二曲,琵琶女大展身手,用嫻熟的技術為作者彈了一曲美妙音樂。是“大弦嘈嘈”“小弦切切”,是“間關鶯語”“幽咽泉流”,這是琵琶女長久壓抑的情感噴薄。琵琶女的第三次彈奏,作者沒有直接描寫,而是轉而寫她的身世,來側面展示,最后“凄凄不似向前聲”的琵琶曲,彈者與聽者心靈相通。琵琶女是白居易塑造的琵琶女,在白居易眼中的琵琶女是經過了白居易意識選擇和語言改造的。通過對琵琶女的描寫,我們可以對比看到白居易的人生寫照。年輕時的白居易得到皇帝的重用,奮發有為,報效朝廷,甚至還做著宰相夢,如同琵琶女“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結果卻卷入黨爭,遭受排擠,被貶到蠻荒之地。 這一遭遇和琵琶女何其相似,琵琶女因為“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而不得不轉變了人生道路。但其中和琵琶女悲慘命運相對的是,白居易雖然境遇和琵琶女相似,但是白居易顯然想寫出自己的選擇。“弟走從軍阿姨死”展現了白居易的反戰意識,“暮去朝來顏色故”展現了白居易一定的自省意識。也正因為看清了自己已過氣,“暮去朝來顏色故”,白居易后來對待官場慎之又慎,遠離是非旋渦。與后來白居易選擇“獨善其身”的人生選擇形成了一定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