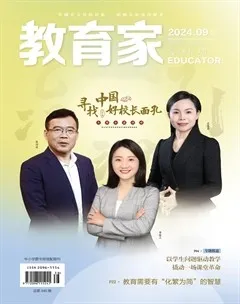以學生問題變革課堂的教學“況味”
在以學生問題驅動教學變革的過程中,教師可能會遇到哪些情況?又會在教育實踐中品嘗到哪些“滋味”?本刊編輯部與一些教師進行了交流。
●酸 小學數學教師 顧峻崎
課堂上,孩子們不再是正襟危坐的狀態,而是興奮地參與教學活動,師生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享受著教與學的快樂。這是我初次接觸問題化學習時,在一次教研活動中看到的場景。那時我已經執教了10年,發現隨著年級的提升,很多孩子對數學學習乃至所有學科學習的興趣漸漸降低。那節課上,師生間的氛圍打動了我,我開始嘗試實施問題化學習。
和之前更側重知識傳授的教學方式相比,問題化學習看起來效率沒有那么高。怎樣在備課中窮盡學生的問題?如何應對課堂上學生洶涌而來的問題?學生問的問題并非教學重難點怎么辦?低年級學段,學生東一句、西一句,爭著提出困惑怎么辦?和很多初接觸的教師一樣,這是我所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好在通過不斷調整,課堂上的秩序逐漸構建起來。我也發現將課堂從失控變成可控最為關鍵的一點是,教師要進行有效“推拉”,引導學生在零散的問題中串起一條主線。十幾年的實踐過程里,在面對不同學生、不同情境時,我仍會不斷遇到各種新問題,也曾動搖過,要不要持續費心費力地這樣做?最終我的答案是,作為一名教師,出于對教育倫理的認知和教育良心的自覺,要想堅定地把學生培養成一名終身自主的學習者,我們自己首先要成為問題化學習者。
酸與甜可能是一種動態平衡。這些年我去往各地授課,課堂上越來越亮的眼睛,學生下課后爭著搶著要簽名,千方百計打聽我的地址,要父母寄土特產給我,等等。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對問題化學習的最高褒獎。某次,我去一個比較偏遠落后的地方上示范課,課后一個學生找到我,問道:“老師,上海都是這么上數學課的嗎?”我說:“每一個喜歡上課的老師可能都會這么上。”他停頓了一下說:“老師,我怎么才能考到上海去?”在很多個這樣的故事里,那些懷疑一點點散去。
因此,個人所經歷的所謂“酸”其實不算什么,我想在成為學科團隊主持人,向各地教師推廣問題化學習時嘗到的那些“酸”更值得反復咀嚼。要讓教師們以新的視角去審視自己的課堂,突破原有的教學設計,換一個角度去理解學科和學生問題,變革教學是困難的。有些教師難免認為,這也是一種“模式”,可能會隨著管理者的變更像陣風般吹過,所以有時只是應要求在被聽課時作出些調整。為教師提供可供參考的課堂、喚醒他們的專業自覺,這是我們仍在持續的努力。
●甜 高中生物教研員 張燕
在教育實踐中,我很早就意識到要“以學為中心”,也看過不少教學理論,嘗試過不同的教學策略。2018年,我開始深入接觸問題化學習,在一次次參會、聽講后我發現,這可能是更適合我的課堂變革路徑,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到了高中,往往很少有學生會在課上主動提出問題。工作中,老師們有很多共同交流的機會。當談起某個班級時,一些老師會提道:“這個班的孩子比較悶,很多時候我一個話題講下去都沒人回應。”而在我的印象中,那個班級的學生總在發問、討論,課堂氛圍很活躍。我想,這大概是實施問題化學習帶來的變化。
實際上,在實施問題化學習之前,如果有學生在課后叫住我問我些問題,我就會感到挺滿足了。因為這說明那節課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且大概是精彩的。實施問題化學習之初,學生依然不敢提問,我會在教學中注重觀察他們的神情,讓他們表明自己的疑惑。漸漸地,他們的狀態變得松弛了,明白只要是真實的問題,我都很鼓勵。與學生學習狀態一起提升的,還有他們的核心素養。在不少學生心中,生物是理科中的文科,學習生物只需要背一背、練一練。而在問題化學習中,他們經歷了提出問題、不斷追問、拆解問題、形成問題系統的過程,自然地體會到科學探究的要義。我也不需要再不厭其煩地去糾正他們的認知偏差,學生在學習中意識到科學思維的重要性,學習表現也有了明顯的提升。
實施問題化學習4年后,我進入區教育學院成為一名教研員。得益于此前的思考與實踐,在深入課堂與教師溝通時,我能發現他們在課堂教學中需要改進的方向。比如在一些看起來形式精巧、注重學生主體的教學設計中,設置的問題可能只是“為問而問”,而在適宜地調整后,課堂上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在一位位師生和一節節課堂的反饋中,我所收獲的“甜”難以盡述。
●苦 初中語文教師 丁昊琰
入職三年,我從教以來就嘗試以學生問題引領課堂教學。其實,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使我習慣于作為一名回答者,因此,開展這種以學生的學為主體,引發學生提問、追問的教學方式著實給我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和很多最初嘗試運用這種教學模式的老師一樣,我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學生提不出問題,尤其是他們升入七、八年級后,開始在意自己的提問是不是好問題,故而干脆選擇不發言。有時即便我想方設法引導他們提問,課堂上依然是一片沉寂,令師生雙方都尷尬不已。坦誠地講,相較于傳統的灌輸式教學,這種鼓勵學生提問的教學模式需要花費我更多的精力,卻難以讓我在短期內看到更明顯的教學效果。備課過程中,我會準備大量材料并進行充分預設,思考學生可能從哪里發現問題。可是,一位老師的設想怎么能保證覆蓋全班學生發散的思維呢?有些問題總令我感到意外,為了應對這樣的突發情況,我的大腦需要臨場飛速運轉,心里也會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這對于本就缺乏教學經驗的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記得去年某節公開課初次試講,臺下學生的提問意識和主動性都很強,需要教師對課堂擁有更強的把控能力。那節課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通過品讀《錢塘湖春行》中的詞句和寫法,了解詩人是如何表達喜愛之情的。我原本的設計是引導學生圍繞詩中意象提問,不料在剛開始上課時,就有學生提問:“詩人怎樣寫出了對錢塘湖的喜愛之情?”我一下子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沒想到這堂課最終的教學目標竟被他跳至第一個環節來探討,而在我愣住的階段,他又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想法,更讓我亂了陣腳。那么,這堂課后面要上些什么內容呢?我只能故作鎮定地拉著學生回到原先關于意象的問題上來,導致整堂課的邏輯都很混亂。
平時上課,我也常遇到無法把控課堂的情況,尤其是當有學生滔滔不絕地發言時。一次,一名學生提問后還主動問:“請問有哪位同學想對我作補充?”很快就有其他學生接過話頭回應,他們之間形成了一段非常順暢的互動,讓我不好打斷他們,但后面的內容漸漸“跑題”,還花了很長時間,導致我的課堂只能被他們牽著走。
●辣 小學語文教師 張伶俐
我從2009年開始研究小學語文問題化學習,積極投入到課堂實踐研究。在我看來,問題化學習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培養學生主動、積極的思維,以此來解決學科的、自我的9IucgZ1ia/ahYE2LiAg+tmHtN9y1no1Wo03NysXUYss=困難。
傳統的課堂,發現問題基本上是由老師完成,大部分老師上課,都是一段引導語之后,以問題切入。當然,我們不能說這樣的課就不是好課,但這個問題是老師按照學科要求提出的,是老師認定的要點,未必是學生感興趣的。
在問題化學習的課堂中,發現問題應該是第一個環節。這個過程中,學生會激烈地討論甚至爭論。比如在講老舍的《養花》這一課時,學生們圍繞中心句“有喜有憂,有笑有淚,有花有果,有香有色。既須勞動,又長見識,這就是養花的樂趣。”展開了火熱的討論。有學生問:“憂怎么會是養花的樂趣呢?樂才應該是養花的樂趣。”經過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他們逐漸明白:那些看似負面的情緒,如擔憂和傷心,也是養花樂趣的一部分?。
再如,課上時有學生犯較明顯的錯誤,惹來其他學生哄堂大笑。這種情況下,老師一般會說:“你看大家都笑了,說不定是你錯了,讓我們聽聽別人怎么講。”或者會說:“誰來說一說,他錯在哪里?”但問題化學習的課堂不會這樣。我會請學生們提出一個問題,幫助這位犯錯的學生再將思維往前走一步,引導他找到自己錯在哪里,甚至是自己改正或者優化。
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都是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學生的思維品質。在講巴金的《鳥的天堂》這一課時,因為文本中沒有明確這一作品的創作時間,所以有學生就提出了問題:巴金先生是幾歲創作這一作品的?然后,馬上就有學生說:“巴金是百歲老人,那么這個問題就有好多好多答案了。”于是,我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使這個問題更加聚焦。有學生說:“可以問是作者幾十歲創作的。”怎樣更聚焦呢?直到有學生說:“可以問這一作品創作于哪一時期。”
聚焦“幾歲”,會有100種可能;聚焦“幾十歲”,也有10種可能;聚焦“哪一時期”,只有3種可能。這就為繼續探究問題奠定了基礎。作品的創作時間其實是一個“死知識”,學生在網上就能查到答案,但如何將它變成一個好問題,對學生進行一種思維訓練,是教師在問題化學習中應該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