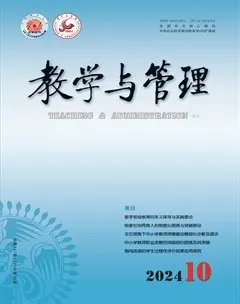統編小學語文教材蟲字旁漢字字理解析




摘 要 字理識字是《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倡導的識字方法。蟲字旁漢字在統編小學語文教材中高頻出現,但“蝙蝠蛙螺蚌”等很多蟲字旁漢字記錄的并不是蟲子類動物,“蠶繭雖蛋虹”等蟲字旁漢字,看似簡單的常用字,在進行字理識字教學時卻面臨諸多難點。文章以漢字學理論為指導,通過梳理“蟲(蟲)”音義演變,從歷時角度揭示了偏旁“蟲”的構字含義為“動物的通稱”,基于此對教材字表中收錄的46個蟲字旁漢字的構字理據分組深入考察,展示了探求字理的方法,即依規范字現狀解析字理,借異體字、繁體字、古文字或古文化溯源解析字理,以期疏解教材難點,為教師備課提供參考,充分發揮字理育人價值。
關 鍵 詞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字理識字;蟲字旁;漢字學
引用格式 張新.統編小學語文教材蟲字旁漢字字理解析[J].教學與管理,2024(30):81-84.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以下簡稱《2022年版課標》)在首次提出“義務教育語文課程培養的核心素養”[1]的同時,就識字方法首次提出了“字理識字”[2]。字理識字是基于漢字系統,遵循漢字構造原理和演變規律,探求漢字構字理據的識字方法。漢字構字理據表現為漢字形、音、義之間的聯系,字理的存在取決于漢字的根本性質是表意性。字理解析能夠深入漢字內核,彰顯漢字內隱的系統和規律,對漢字內蘊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思維闡釋得最為深刻。探求“字理”不僅有利于提高識字效率,更是從語言、思維、文化等方面切實提升學生核心素養的有效路徑。
本文擬以漢字學理論為指導,通過梳理“蟲(蟲)”音義演變,從歷時角度揭示偏旁“蟲”的構字含義,基于此對教材字表中收錄的46個蟲字旁漢字的構字理據分組深入考察,展示探求字理的方法,以期疏解教材難點,為教師備課提供參考,充分發揮字理育人價值。
一、偏旁“蟲(蟲)”構字含義探析
解析合體字的字理,首先須梳理其表意偏旁的構字含義。“蟲(蟲)”作為偏旁構字時所表示的含義,與其作為單音詞所承載的詞義具有一致性,二者相生相成。
“蟲字旁的字大都和蟲子有關”,該構字規律是基于“蟲”在現代漢語中的釋義提出的。探求偏旁“蟲”的構字含義,不能僅停留于現代漢語層面,需要回溯到上古造字時代,需要同時對“蟲”與“蟲”音義的歷時演變進行梳理。
1.上古造字之初,“蟲”與“蟲”音義不同
“蟲”古音huǐ,本義毒蛇,甲骨文寫作,是象形字,象盤臥在地的蛇,后寫作“虺”。
“蟲”音chóng,本義蟲子,是會意字,從三蟲,“小蟲多類聚,故三之以象其多”[3],“蟲”本指外形似蛇或幼蟲似蛇,好類聚的微小動物,即蟲子。蟲子是動物中種類及數量最多的群體,古人通過以部分借代整體使“蟲”的語義擴展,產生引申義“動物的通稱”,此義在上古處于強勢地位,為常用義。“五蟲”涵蓋了人在內的所有動物[4]。
2.上古“蟲”代替“蟲”參與造字,二者音義趨同
求簡易是漢字發展的一大定律,“蟲”因筆畫少便于書寫,造字時代替“蟲”充當聲符或形符,由此“蟲”音義趨同于“蟲”,常用義為“動物的通稱”。“蟲”的本義為毒蛇,由戰國時期出現的后起字“虺”承擔。
3.中古以來“蟲”與“蟲”音義相同
“‘蟲’字詞義范圍亦即外延的縮小,最晚到唐代已經完成”[5]。中古至今,“蟲”的常用義為“蟲子”,較之上古時期的常用義“動物的通稱”,詞義范圍縮小。很長一段時間里“蟲”作為“蟲”的俗體存在[6],“蟲”的詞義范圍亦隨之縮小。在現代漢語規范漢字中,“蟲”行而“蟲”廢,“蟲”被視為“蟲”音義相同的繁體字。
4.現代漢字里偏旁“蟲”的構字含義固化
“動物的通稱”早已固化在蟲字旁漢字的構形之中,不會受到“蟲”“蟲”后世語義變化的影響。針對“蟲字旁的字大都和蟲子有關”的構字規律,教師應隨著學生認知水平提升和識字量增加,適時進階為“蟲字旁的字大都和動物有關”,這樣就能解釋“蝙、蝠、蛙、螺、蚌”等漢字為什么是蟲字旁,也不難理解課文《景陽岡》(五下)中“虎”為何稱作“大蟲”。
二、教材中蟲字旁漢字“字理”解析
“偏旁”是合體字的直接構字單位,一般分為表意、表音、記號三類。下文考察的漢字,除“觸、獨、燭、濁、融”五字中偏旁“蟲”表音,其余皆表意。《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運用“六書”理論探求漢字形音義之間的聯系,《說文》中的“部首”是文字學原則的部首,是兼具字形和字義歸類作用的表意偏旁,如“舅”收在《說文》男部,而非臼部[7]。
《義務教育語文課程常用字表(3500字)》[8](以下簡稱《常用字表》)共收錄59個蟲字旁漢字,其中有46個出現在統編小學語文教材(一至六年級)識字表、寫字表中,詳見表1,其中46個漢字均為形聲字。以下將主要從字理解析方法的視角對它們分組考察。
教學中要求識記的是現代漢語規范漢字(以下簡稱規范字),規范字系統是經歷長期發展演變,并經過整理規范而成,字理情況復雜,在教學中解析構字理據應“從現代漢字實際出發,尊重歷史與傳統”[9],遵循科學適切的原則。凡是由規范字現狀可說明理據的,不必溯源;規范字構字理據喪失或部分喪失,無法現狀分析,才借助異體字、繁體字或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進行溯源解析。這里的溯源是就近探求構字理據,不是面面俱到考究漢字源流演變。
1.依規范字現狀解析字理
表1中1、2兩組例字依規范字現狀便可解析字理,如“蝶”(收在二上識字表、四下寫字表,以下僅寫教材冊數),本義蝴蝶,從蟲、從枼,枼亦聲。“枼”是“薄木片”,蝴蝶翅膀輕透如薄木片。教學中不必追溯小篆“蜨”字,蝶本作“蜨”,從蟲,疌聲。另外,“螢”(一下、四下),從蟲、從熒省,熒聲。“螢”“熒”楷書繁體分別寫作“螢”“熒”,規范字已統一簡化,則無需涉及繁體字。
第2組例字在小學識字教學中,解析字理宜簡易操作,僅作現狀分析,不必追溯繁難的古文字。“蠶”(二上、五上),從蟲,天聲。“蜂”(二上、三下),“飛蟲蜇人者”,從蟲,夆聲。“蜜”(二上、三下),“蜂甘飴也”,即蜂蜜,從蟲,宓聲。“蚊”(一下、四上),“嚙人飛蟲”,從蟲、從文,文亦聲,“從文”因蚊身有花紋,“文”本義花紋、紋理,后寫作“紋”。
“蠶、蜂、蜜、蚊”,古字形分別為“蠶、蠭、、螡”,均收在《說文·部》,“”音kūn,后寫作“昆”。在“蟲子”這一義項上“”“蟲”沒有區別,“”是“蟲”的簡寫,許慎分部細密,設為兩部[10]。但在簡易律的競爭機制下,最終還是構意功能相同、字形最簡的“蟲”占據了上風,然而在競爭中還是出現了一部分從“”的漢字,《說文·部》收字25個,除“蠢”等本義與蟲子動作有關的三個動詞,其余字頭都是蟲子等微小動物的名稱,且有7字列有從蟲的重文。
“蠶”“蠶”現是音義相同的繁簡字,但它們原本是音義有別的兩個字。“蠶”最早見于小篆,“蠶,任絲也。從,蠶(cǎn)聲。昨含切”[11]。段注:“‘任’與‘蠶’以疊韻為訓也。言惟此物能任此事”[12]。簡體字“蠶”《說文》未收,但在《爾雅·釋蟲》中已出現詞語“蜸蠶”(qiǎn tiǎn),即蚯蚓[13]。“蠶他典切”[13]。
那么,“天”作為“蠶”字的偏旁僅表音、不表意,“‘蠶’可認為從蟲、天聲,與‘蠶’從朁聲古音相近”[14]。
另外,初中段將學習的“蠢”,其規范字中保留了“”,要析為從,春聲,“蠢,蟲動也”[15]。
2.借異體字溯源解析字理
第3組“強”(三上、三下)檢字法原則的部首是“弓”,漢字學原則的部首是“蟲”,考察字理依據后者。解析“強”的字理需借助異體字,“秦代以后‘強’字的發展因其聲符‘弘’的不同寫法而分為兩系”“一寫作‘強’,一寫作‘強’。現以‘強’為規范字,‘強’作為其異體被合并”[16]。“強,蚚也,從蟲,弘聲”[17]。“強”本義蚚,即米中小黑蟲,但本義罕用,主要被借為彊弱之“彊(qiáng)”,后世以“強”代“彊”,“彊”字漸廢。“彊,弓有力也,從弓,畺聲”[18],“彊”本義硬弓,引申指強壯、強盛等。“強”的構字理據借助異體字能梳理清楚,則無需追溯籀文等古文字。
3.借繁體字溯源解析字理
解析第4、5組漢字的字理需借助繁體字。“雖”(二上、三下)的繁體字“雖”,“雖,似蜥蜴而大,從蟲,唯聲”[19],本義罕用,多假借為連詞雖然、即使。通過分析“強”“雖”,可見形符有時偏居一隅,并非所有形符、聲符各占一半。
“蠟”(三上、三下)的繁體字“蠟”,從蟲,(liè)聲,“蠟”是動物等產生的油質,可制作蠟燭。《說文》未收繁體“蠟(là)”,《蟲部》收有“蠟”,音qù,從蟲,昔聲,本義是蠅的幼蟲。顯然“蠟”“蠟”本是音義不同的漢字,后“蠟”被用作“蠟”的簡化字,“蠟”的本義由后起字“蛆”承擔。
“繭”(僅收在五上識字表)的繁體字“繭”,“繭,蠶衣也”[20],段注:“從糸、從蟲、從芇,芇聲。……蟲者,蠶也。芇者,僅足蔽其身也”[21]。
第5組例字共同點是蟲字旁居右,這里的偏旁“蟲”是聲符“蜀”或“蟲”的簡省。“觸”(二下、三下)、“獨”(一下、三下)、“燭”(三上、三上)、“濁”(四上、四上)在《說文》中分屬角部、犬部、火部、水部,它們的繁體字都以“蜀”為聲符。“觸”本義是以角撞物,從角,蜀聲。“獨”本義是單一,從犬,蜀聲。從犬,因“犬好斗,好斗則獨而不群”[22]。“燭”本義是照明用的火炬,從火,蜀聲。“濁”本義是河流名稱,即濁水,從水,蜀聲。簡化字“觸、獨、燭、濁”是宋元以來略寫聲符的俗字。另外,“融”(三上、三下),本義是炊氣上升,從鬲,蟲省聲[23]。,籀文聲符不省寫。
左形右聲的形聲字雖多見,但并非一概而論,不能就第5組例字推出,蟲字旁居右均不表意的結論,初中段將學習的“蝕”就出自《說文·蟲部》,“蝕”本義是蟲等蛀傷物,教學中可借楷書繁體“蝕”分析為形聲字,從蟲、從食,食亦聲,不必追溯到字形復雜的小篆。
4.借古文字溯源解析字理
第6組例字“蛋”(二下、二下)是個后起字,是小篆“蜑”的俗寫。解析“蛋”的字理需追溯到小篆“蜑”,“蜑,南方夷也。從蟲,延聲”[24],“蜑”是我國古代南方少數民族名,如“胡夷蜑蠻”[25]。蜑人(后寫作“蛋人”)以舟為家,以漁為生,以蛇虺為圖騰,所以“蜑”“蛋”都從蟲。“(蛋)音但,古作‘蜑’”“俗呼鳥卵為蛋”[26]。
第7組例字“蛇”(二上、四下)可直接依規范字進行現狀分析,從蟲,它聲。但深入考察“蛇”字源流,需追溯相關古文字。“蛇”本字是“它”(一上、二上),“它,蟲也,從蟲而長,象冤曲垂尾形。……蛇,它或從蟲”[27]。“蛇”在《說文》中不是字頭,作為“它”的重文出現。《說文》以“蟲(虺)”釋“它”,因它、蟲二字的甲骨文字形相近,皆象蛇之形,區分在于“它”垂尾而行,“蟲”屈尾而臥,“曳尾而行者難制”[28],草居的先民常被蛇侵擾,見面互問“無它乎?”
“它”被借為代詞,“蛇”承擔了“它”的本義,二字各司其職。“它”與“蛇”古韻同在歌部,聲母均為舌頭音,因語音演變,后不同音。
經歷代不斷發展,“它”的古字形逐漸符號化,像蛇頭的部分演變成“宀”形,像身尾的部分演變成“匕”形。識字教學中“它”常被誤認為是合體字,統編教材就將“它”作為偏旁“宀”的例字欠妥。楷書中的“它”應是一個傳承式獨體字,上部“宀”無音義,是古文字傳承保存下來的非字象形符號,與表示房屋的“宀”形同質異。教材中類似的“要、果、朋”等常用字都是獨體字,將非字象形符號誤解為成字部件,進行無理拆分則無法講解。
5.借古文化溯源解析字理
漢字是在中華文化的浸潤中產生和演變的,借助古代文化背景疏解構字理據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虹,螮蝀也。狀似蟲。從蟲,工聲”[29],螮蝀(dì dōng),虹的別名。今天我們知道“虹”(一下、六上)是天象,在古人看來“虹”是天上龍蛇一類司雨的動物,民間稱“虹”為兩頭龍,“虹”的甲骨文“”是象形字,身形如弓,兩邊有兩個龍頭。雨過天晴虹橫貫天際,古人認為虹弓身探頭在黃河喝水,以補足下雨時損失的水分,殷墟卜辭就有“虹自北飲于河”[30]。形聲字“虹”是后起字。古人認為虹不僅有生命,且區分性別,“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暗者為雌,雌曰蜺”[31],今稱主虹、副虹,后“霓虹”聯合成詞。結合古代文化背景,能夠將字理講解得形象透徹,利于學生構建合理的知識結構。
三、字理識字教學建議
1.明晰字理識字教學要求
《2022年版課標》要求在第一學段就要開始字理識字教學,“觀察字形,體會漢字部件之間的關系”[32]。“初步體會漢字結構的主要特點”“學習部首檢字法,嘗試發現漢字的一些規律”[33],從以上“學段要求”及語言文字積累與梳理學習任務群中該學段的學習內容,清晰可見《2022年版課標》關于第一學段字理識字的課程目標與教學導向。字理教學貫穿整個義務教育階段的識字教學,每個學段都有相應的要求和學習內容,最終幫助學生養成“獨立識字的能力”,能夠“體會漢字蘊含的智慧”[34],達成“有探究漢字規律的意識,在社會生活中能根據字音、字形、字義三者的關系準確認讀、正確理解遇到的生字新詞”的學業質量[35]。
2.適切開展字理識字教學
誠然識字課不是漢字學課,上文有些分析只能作為教師的儲備知識,課堂上要考慮到學生的接受能力,不能為字理而字理。比如“繭”字,雖出現在高學段字表中,但完全按照繁體字分析字理,還是有難度的,那么在教學“繭”的字理時,教師可以如是說:“繭”字的造字理據完整地呈現在繁體字中,簡化漢字時只保留了其中的一個形符“蟲”,以及聲符的“艸”。“繭”以蟲為形符,因“繭”的本義是蠶成蛹前吐絲做成的外殼,這里的“蟲”是吐絲的蠶,如此分析簡潔明了。教師一定不能主觀臆斷,只依簡化字將“繭”理解為“草蟲”,不僅講解不清,且會擾亂漢字系統。
3.教師提升字理教學素養
表1中例字,單純從外顯的形音義看都很尋常,但在識字教學中常易被曲解。識字教學中不僅要對漢字進行靜態現狀考察,也要有動態溯源。字理是一種識字方法,也是識字的底層邏輯,使用字謎、兒歌等其他識字方法時同樣不能違背字理、不能隨意拆解漢字。科學適切地開展字理教學,需要教師自覺地利用漢字學理論知識武裝自己,王寧先生指出“不能因為教學內容顯示出的知識不多,就認為教育者所需的知識也很簡單。應當說,小學識字教學是一個尖端的課題,在這個領域遇到的問題,需要大量的漢字學成熟理論作支撐,才能處理得當”[36]。《2022年版課標》課程實施部分增加了“教學研究與教師培訓”,在語文教師必備知識中“語言學”[37]列于首位,體現了漢字學等語言學知識在語文教學中的根基性。當然教師的知識儲備猶如一條河,取之于河的那一滴水必然靈動而充滿生機。
字理識字的必要性不只是為了識字的數量和速度,關鍵目的是在探求構字理據的過程中引領學生正確認識和理解漢字,進而熱愛漢字。遵循漢字固有的系統和規律進行教學,學生被激發出的興趣才是有生長點的,獲得的知識才能轉化為能力、升華為素養。唯有把漢字作為表意文字的文化基因、科學理念根植于學生的心底,識字教學方能不負其奠基的使命而助力學生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2][8][32][33][34][35][37]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4,22,70,8,20,11,42,55.
[3] 王筠.說文釋例[M].上海:世界書局,1983:63.
[4] 戴德.大戴禮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7:228.
[5] 王暉.“蟲”“蟲”字初義與意符“蟲”旁類屬范疇演變考[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1(06):163-169.
[6][14][16] 李學勤.字源[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1170,1168,
1159.
[7][11][15][17][18][19][20][23][24][27][29] 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291,283,284,279,270,279,271,62,283,285,282.
[9] 王寧.漢字構形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19.
[10] 李海霞.蟲部字及其文化蘊含[J].文史知識,1992(09):121-124.
[12][21][22][28]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74,643,475,678.
[13] 郭璞,邢昺.爾雅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86.
[25][26] 張玉書,陳廷敬.康熙字典[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1124,1124.
[30] 胡厚宣.甲骨文合集釋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558.
[31] 孔穎達.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04.
[36] 王寧.漢字教學的原理與各類教學方法的科學運用(上)[J].課程·教材·教法,2002,22(10):1-5.
[作者:張新(1974-),女,江蘇省連云港人,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文學院,副教授,碩士。]
【責任編輯 王秀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