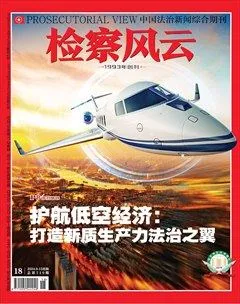張翎: 母語與鄉愁

母語給我的感覺,像一根細細的鐵絲,我可以運用我的想象力,把它彎曲成任何一個形狀。母語又像是一支蘸滿墨水的毛筆,只要有一張宣紙和一些清水,就可以暈染出無數層的灰。用母語我可以寫出傳神的境界,而在第二語言中,我卻只能停留在“達意”的層面。有過了“傳神”的體驗,我不滿足于僅僅“達意”。所以這些年,我一直堅持用母語寫作。
堅持用母語寫作
記者:你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已經獲得了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為什么又去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攻讀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之后從事聽力康復師的工作呢?
張翎:我從小就想成為作家,但一直有一堵高墻橫亙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我知道工作僅僅是支撐寫作夢想的工具,但我也不想選擇一個過于勉強自己的職業。我希望有一份收入穩定、又能與人打交道的職業,經過調研,最終選擇了聽力康復師的職業。這份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那些經歷對我的寫作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記者:在加拿大生活,再來看國人的生活,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地方?
張翎:作家不是上帝,每一個觀察視角都有死角和盲點。假如把生活比喻成樹林,那么生活在樹林之中的人,可以觀察到樹木的細節,看得見枝葉也能設想到根的狀態。而像我這樣很早離家、常年生活在海外的人,已經失去了觀察細節的有利地形。我太遠了,看不清樹了,但我看得見樹林。失去了細節,得到了整體——這是我阿Q般的自我安慰。我無法改變現狀,只能利用我的審美距離,設法寫出一些角度不同的作品。
記者:1998年,你是怎么寫下第一部小說《望月》的?
張翎:《望月》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最初發表于1998年。當時我已經出國十多年,生活終于安定下來。出國頭十年里我只回過兩趟國。在《望月》中,我把出國十幾年里堆積的濃郁的鄉思之情全然傾瀉,至今讀來,依舊動容。雖然是長篇處女作,由于情緒已經在漫長的等待中經過了充分的醞釀和沉淀,寫起來是行云流水的感覺,絲毫沒有初入行者的忐忑和猶豫。現在看來,那些濃郁的思鄉情,在當今這個通信和交通極為便捷的年代,未免顯得有些矯情。但我不能用現在的成長,來否定當初的心路歷程。《望月》在我的作品中,始終有一個獨特的位置。
記者:你的英文非常好,還是選擇用母語來創作,并且在國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是怎么考慮的?而這本《歸海》一開始是用英文寫成,和中文寫作的感覺是不是很不一樣?
張翎: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完成了九部長篇小說和十幾部中短篇小說集。我選擇用母語寫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用母語可以最貼切地表達想要表達的情緒。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說,只要他的第二語言經過足夠的訓練,是完全可以勝任用第二語言構架小說結構和故事情節的。但是情緒和氛圍的描述,卻是母語所賦予的一種特殊能力。母語給我的感覺,像一根細細的鐵絲,我可以運用我的想象力,把它彎曲成任何一個形狀。母語又像是一支蘸滿墨水的毛筆,只要有一張宣紙和一些清水,就可以暈染出無數層的灰。用母語我可以寫出傳神的境界,而在第二語言中,我卻只能停留在“達意”的層面。有過了“傳神”的體驗,我不滿足于僅僅“達意”。所以這些年,我一直堅持用母語寫作。
記者:有人評價說張翎的小說已經沒有了鄉愁,其實你的創作還是有很多人生經歷的影子,你覺得自己是個沒有鄉愁的作家嗎?
張翎:在通信和交通落后,或者存在著被隔絕的狀況下,鄉愁是自然而然的產物。在通信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我可以一年里回國好幾趟,再拿“鄉愁”說事兒,就有些“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思了。
記者:馮小剛根據你的小說《余震》拍攝了電影《唐山大地震》,因而使你的小說為更多的讀者所關注,這篇小說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張翎:這部電影感動了很多人。但從作家的角度來說,我不認為《余震》是我最好的作品,還有很多地方沒來得及仔細鋪陳開來。但是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作為小說家的命運,它使得我的發表之路變得暢通。從那以后,主動約稿的刊物和出版社漸漸多了起來。
記者:和馮小剛導演合作劇本,對你之后的小說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張翎:馮小剛導演經常和劇組說的一句話是:這個場景、這句臺詞背后的邏輯在哪里?他為什么這么說、這么做?劇本非常關注的是人物行為的背后邏輯。當一個人物、一個行為的內在邏輯是存在并且健全的,那么即使把對話刪除之后,留白之處依舊有著強大的“地基”,經得起叩問。這個思路對我有很大的啟迪,我寫小說時會更加警醒,關注事件背后的潛在邏輯,盡最大努力做到“意料之外”的情節一定要處于“情理之中”。
女性作家的選擇
記者:新創作的兩部長篇小說,這個系列叫“戰爭的孩子三部曲”,而不是“戰爭三部曲”,為什么特別強調“孩子”?
張翎:因為我的關注點并不在戰爭本身。我沒有直面戰爭,書中關于戰爭的篇幅也不多。我更想探討的是戰爭、災難遺留下來的長久創傷。這種創傷可能會一直延續到一個人生命的終結,甚至有可能延續到后世身上——所以用了“戰爭的孩子”。《歸海》里的母親春雨以及女兒袁鳳,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戰爭的孩子”。
記者: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歸海》寫的是一對溫州母女的故事。這自然讓人聯想袁鳳是不是以你的母親為原型來創作的?
張翎:《歸海》里的母女并沒有基于某一個真實人物,她們是一群人的合體,或者說縮影。
在我長大的過程中,受我母親家族女性的影響很大。我外婆在戰亂和災禍的年代里,生下十一個子女(不計小產)。其中十個長大成人——這在那個嬰兒存活率極低的年代,幾乎算是奇跡。更加難得的是,她的十個孩子,無論男孩女孩,都得到了那個年代算是相對良好的教育。那個龐大的家族像一條又破又大、到處漏水漏風的木船,而外婆卻硬是把這樣的一條船在風雨飄搖中行駛到了岸邊。我是聽母親外婆講家族女性的生存故事長大的,她們的人生軌跡無比精彩。她們的經歷和性格給我后來的寫作和審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無法抑制想寫她們的強烈愿望。《歸海》的人物身上肯定留著她們的精華氣血。但和我其他小說本質上一樣,《歸海》里的人物都是虛構的,盡管背景和故事細節都是真實的。發生在許多人身上的散亂細節,被集中安排在了一個虛構人物身上,所以你可以說《歸海》是100%真實的,也是100%虛構的。
記者:作為一個女性作家,你是不是在小說中更關注女性的命運?
張翎:一個當代作家寫歷史事件,已經要經歷跨年代的想象。一個女作家要寫歷史年代中的男性,在經歷跨年代想象之外,還要進入跨性別想象,這個困難會加深。我寫女性居多,一是因為女性在戰爭文學中經常是缺席的,二是因為同性更容易進入共情。我對那種靠耐心堅韌存活下來的女性有極大的尊重,寫她們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