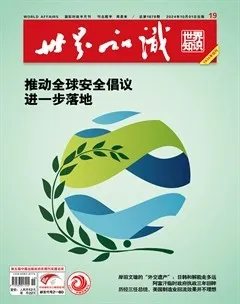拜登政府修訂核戰略:新的對抗性敘事

隨著烏克蘭危機延宕深化,美俄矛盾演變延展為波及全球的激烈對立,雙方屢屢展示“核肌肉”,加劇了國際社會對核沖突的擔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今年3月警告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不信任將核戰爭風險提升到數十年來的最高點。最近美國媒體披露,同樣是在今年3月,拜登總統簽署了一項高度機密的核戰略修訂計劃,即“核武器使用指南”(Nuclear Employment Guidance)。
用“核大棒”維系霸權地位
核戰略涉及大國重器的建設重心以及核武使用的原則底線,相關調整修訂一向牽動全球核安全、核軍備局勢,更是國際關系和全球安全形勢演變的重要“風向標”。盡管美國高層尚未公布該戰略,對細節內容也諱莫如深,但結合媒體和官員迄今為止透露的信息看,至少有三個特點值得關注。
首先,首次明確將中國置于美國核威懾架構的核心考量當中。美國官員稱,此次核戰略調整的最大動因是應對“中國擴充核武庫”帶來的“威脅與挑戰”。據報道,美國的新核戰略是基于來自五角大樓的這樣一個估計:中國的核武庫規模到2030年將增至1000枚核彈頭,到2035年增至1500枚,與目前美、俄各自公布的處于部署狀態的核彈頭數量大體相當。
其次,不斷強化“核武軸心”的戰略敘事。據報道,新戰略重點關注俄羅斯、中國、朝鮮、伊朗的“核威脅”,強調在過去任何單一競爭對手僅憑核威脅就挑戰美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如今鑒于中俄關系的發展,朝伊在烏克蘭危機中明確挺俄的立場和行動,這些國家將會在核領域強化“聯手抗美”的能力,因此美軍要做好“與數個核國家同時發生核對抗”的準備。
第三,渲染核武器更新換代的緊迫性,重點是升級“三位一體”核力量,陸基方面計劃用400枚新型“哨兵”洲際導彈替代老舊的“民兵-3”導彈,海基方面將把美軍歷史上建造的最大潛艇、第五代彈道導彈核潛艇“哥倫比亞”級投入現役以替換“俄亥俄”級,空基方面升級B-52J戰略轟炸機,部署新一代B-21“突襲者”轟炸機,等等。
總之,美國此次核戰略調整旨在強化其核優勢和核威懾,可被看作是其更深投入大國戰略競爭的“應激”步驟,而即便是那些即將“下崗”的武器,也明顯領先于其他有核國家的大部分裝備,反映出美國用龐大核武庫來支撐其獨霸地位的偏執心態日趨嚴重。
服務于大國競爭戰略
以逐步聚焦大國戰略競爭為基本背景,過去三任美國總統對核戰略進行了強化性質的調整。用“零核世界”話術在上任之初輕易拿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奧巴馬,離任前批準了總額約3600億美元的核武庫升級方案。特朗普上臺后提出“核重建”計劃,大幅提升核武器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對外實行更激進的“先發制人”核戰略。拜登政府延續了核領域的“做強”基調,2022年《核態勢評估》報告以“繼續秉持‘不首先使用’和‘只用以反擊核攻擊’的原則將使美國面對不可承受的風險”為由,暗示“不排除在本土、海外美軍或盟國面對非核戰略威脅時使用核武器”。
近年美國推行的“一體化威懾”戰略包括了對核“三位一體”、核指揮、控制和通信(NC3)及核武器基礎設施的現代化,以構建“強大高效的核威懾體系”來應對其他國家的挑戰,并重申對盟國的威懾承諾。五角大樓要求在2025財年為“三位一體”核部隊及相關作戰行動提供492億美元預算。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未來十年美國核力量的現代化項目成本將達7560億美元。
在核經費、核現代化項目升級等方面加大投入,是美圍繞大國競爭這場“豪賭”進行的“加注”。美軍雖叫囂打一場“讓對手看不懂的戰爭”,卻對在常規沖突中的取勝前景沒有把握,轉而尋求通過核武器來增加勝算。美國積極把陣營對抗的敘事引入全球核力量格局當中,將與異己國家的沖突風險渲染為“核沖突風險”,為其擴充核武庫并利用美英澳三邊安全同盟(AUKUS)機制進行核擴散謀取“合法性”和財政支持。
拜登簽署的新核戰略重新繪制了全球核安全拼圖,表明美國正重估其在全球核秩序中的角色與責任,為可能的多邊核對抗做準備,強化其維護核威懾有效性、維護盟友安全、鞏固全球霸權的決心。這一調整將把不穩定的大國關系和停滯的全球核軍控引入更危險雷區,可能觸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進一步加劇核軍備競賽風險,也將惡化美國那些無核盟國的安全困境。
美國是奉行雙重標準和單邊主義的核大國,對全球核軍控風險的上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近些年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公然向無核武器國家輸出成噸的武器級核材料、幫助建造核武器平臺,造成橫向核擴散的事實;堅持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為基礎的核威懾政策,升級載具、打造小型化彈頭等,加深縱向核擴散的風險;持續為想象中的“敵人”量身定制核威懾戰略,而對大多數無核國家連“消極安全保證”都拒絕提供。
大國博弈比拼的是綜合國力和戰略耐力。美國曾用“星球大戰”拖垮了蘇聯,如今意圖挑起核競賽,通過全領域競爭逼迫中國落入“成本疊加”的陷阱,背上巨大的財政負擔與資源消耗。與此同時,隨著美俄關系的惡化,兩國《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即將到期,雙邊軍控體系幾近崩潰,美國急欲拉中國入局,開展雙邊和小多邊形式的核軍控對話,既為探聽中國的核虛實,也要以此遏制中國的核戰略態勢發展。經驗表明,核軍控往往是緩解大國沖突風險的“泄壓閥”,如今美俄兩個核大國的核戰略均在從均勢平衡到恐怖平衡轉變,大國間的核軍控對話和磋商還能不能繼續,議題和談法會發生何種變化,共識點還存不存在?將給全球核戰略穩定和核安全走勢帶來深遠影響。
冷戰后美國的核武器生產體系經歷大規模縮減與重組,這意味著其要重啟并維持高效的核武生產能力,面臨技術、人才、關鍵基礎設施和民眾支持等方面的挑戰。此外,誰是美國下屆總統仍撲朔迷離,新一屆政府的核戰略將會進行怎樣的進一步調整,還是全盤繼承目前的規劃,仍需進一步觀察。不管怎樣,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以國際合作而不是大國對抗來促進全球戰略穩定與核不擴散體系,才是實現國際核安全的真正路徑。
(作者分別為國防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