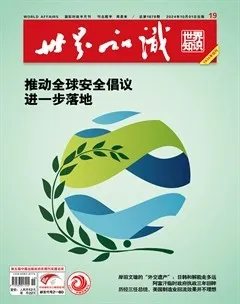歷經三任總統,美國制造業回流效果并不理想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為解決制造業空心化問題、保障供應鏈安全、提高美國經濟競爭力,美國政府持續推動制造業回流。雖然民主、共和兩黨分歧較多,但在制造業回流問題上存在高度共識,政策力度持續加碼:奧巴馬政府開啟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將制造業確定為核心產業,通過公共投資、補貼以及稅收減免等政策加以重振,但主要以市場因素為主,政策力度一般,實現回流的速度較慢;特朗普政府以大規模減稅、貿易保護和發展傳統能源產業等政策為抓手,制造業開始加速回流;拜登政府進一步加大公共投資力度,出臺了美國歷史上力度最大的產業政策,為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半導體、新能源等高技術產業提供大量補貼,推動回流趨勢進一步鞏固。
持續取得進展的一面
制造業回流崗位逐漸增多。制造業回流創造的就業崗位來自兩類公司,一類是美國本土公司回流的崗位,一類是外國公司通過外商直接投資(FDI)進入美國帶來的崗位。據Reshoring Intiative估計,2010至2023年兩類公司創造的就業崗位總計189.8萬個,約占因離岸外包損失崗位數的40%。制造業回流崗位創造主要集中在2017年以后。特朗普時期(2017至2020年)為58.5萬個,拜登時期(2021至2023年)為87.6萬個。
制造業增加值持續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增速較快。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以2012年不變價計算,1988至2007年從9210億美元上升至2.065萬億美元,年均增速4.6%。全球金融危機后,雖然制造業增加值增速有所放緩,但仍持續增長,2011至2023年從1.964萬億美元升至2.291萬億美元,年均增速1.27%。并且,2017至2023年制造業增加值增速平均值為1.65%,顯示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執政時期政策效果更為明顯。
制造業薪酬不斷上升。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奧巴馬時期,美國私人非農企業全部員工制造業平均時薪從2009年1月的22.76美元上升至2016年12月的26.32美元,增幅15.6%。特朗普時期,受新冠疫情沖擊,制造業薪資增幅有限,從2017年1月的26.39美元上升至2020年12月的29.02美元。拜登上臺后,制造業薪資增速再度上漲。2021年1月至2024年7月平均時薪從29.04美元上升至34.06美元,增幅達17%。
制造業建造支出大幅增長。制造業建設支出是衡量制造業增長水平的領先指標。美國商務部普查局的數據顯示,美國私人部門制造業建造支出從2011年1月的299.87億美元上升至2020年12月的736.38億美元,十年增幅146%。拜登上臺后,制造業建造支出大幅增長,從2021年1月的760.90億美元升至2024年6月的2347.82億美元,三年半增幅達209%。其中,計算機、電子和電氣建造支出增幅最大,從71.92億美元大幅升至1354.26億美元,增長了17.83倍。
哪些產業在回流
美國制造業回流集中在少數行業,主要包括電氣設備/器具/組件、電腦/電子產品、交通運輸設備和化學品四個行業。據Reshoring Initative統計,在2021至2023年美國制造業回流共帶來的87.6萬個就業崗位中,電氣設備/器具/組件回流崗位最多(29.3萬個),主要來自電動汽車電池的投資;電腦/電子產品排名第二(21.4萬個),由半導體/芯片驅動和太陽能驅動;交通運輸設備排名第三(10.8萬個),主要是因為電動汽車生產增加帶動交通運輸設備增長;化學品排名第四位(9.5萬個),主要來自藥品、氫氣等可再生燃料以及電池所需的稀土類化學品的增長。
制造業回流崗位以中高技術為主。Reshoring Initative的數據顯示,2010至2021年,美國制造業回流崗位中的高技術、中高技術、中低技術及以下崗位占比分別為25%、42%和33%。2022年以來,美國制造業回流崗位技術等級明顯上升。2022年,高技術和中高技術崗位占比分別為58%和28%;2023年高技術和中高技術崗位占比分別為49%和38%。出現這一趨勢,可能是因為拜登政府重點扶持的行業均為高技術行業。
制造業回流崗位來源國家較為集中。Reshoring Initative的數據顯示,2010至2022年,美國制造業本土企業回流崗位來源國家排名前四位的分別是中國、墨西哥、加拿大和韓國,崗位數占比分別為51%、17%、7%和6%。FDI回流崗位排名前四位的國家分別是日本、德國、中國和韓國,崗位數占比分別為16%、15%、13%和10%。2023年,美國制造業回流崗位數來源國排名前四位的國家分別是韓國、中國、日本和德國,崗位數占比分別為14%、12%、12%和11%。
不及預期的一面
雖然制造業回流取得一定效果,但遠未達到美國政府的預期。
一是制造業就業人數和增加值占比持續下降。Wind數據顯示,2010至2023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非農就業人數的比重從8.9%持續下降至8.2%,處于歷史最低水平;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11.9%持續下降至2023年的10.3%。雖然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和增加值占比下降速度較2010年以前有所放緩,但并未逆轉下降趨勢。
二是制造業薪資增速落后于其他行業。2019年以前,美國制造業薪資低于商品生產平均時薪,但高于服務生產平均時薪。2020年后,制造業薪資開始明顯低于服務業,并且與商品生產持續拉大。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2024年7月美國制造業、商品生產、服務生產平均時薪分別為34.1美元、35.8美元和34.9美元。
三是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1987至2011年,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總體保持增長態勢。圣路易斯聯儲的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從1987年一季度的45.57升至2011年一季度的107.73(以2017年為基期100)。此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開始持續下降,至2020年二季度降至96.1。再之后雖出現回升,但幅度有限。2024年第二季度,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為98.81。
四是工業用電量未出現增長。美國能源信息署的數據顯示,2023年全美工業部門電力零售額為1.02萬億千瓦時,與2022年相比僅上漲0.4%,甚至低于2007年的1.03萬億千瓦時。并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至今,工業用電量占用電總量的比重總體維持在25%至26%之間,未出現趨勢性增長。
五是美國自給自足能力沒有明顯提升。美國推動制造業回流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提高自給自足能力,減少貿易逆差,然而效果未達預期。根據Reshoring Initative編制的用以衡量自給能力的自給自足指數,2013至2021年美國這一指數從2.85降至2.38。2023年,這一指數上升至2.52,但也僅恢復至2019年的水平,并且很可能是因為新冠疫情后供應鏈修復所致。
諸多因素制約回流效果
一是高利率。由于美國通過關稅等手段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再加上以“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方式改變了全球供應鏈格局,其商品生產成本不降反升,通脹水平居高不下,這也導致利率不得不維持在較高水平。而制造業利潤率普遍不高,投資規模又偏大,過高的利率將提高企業生產成本,影響回流前景,并非美聯儲開啟降息通道所能在短期內解決。
二是基礎設施老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每四年對美國基礎設施進行一次評估,分為“A”至“F”分成六個級別。2021年評級為“C-”,即“有重大缺陷的平庸水平”。該協會2021年度的評估報告中指出,到2029年,美國基礎設施融資缺口為2.55億美元,在財政赤字高企背景下,重振基礎設施面臨巨大挑戰。
三是人才缺乏。美國制造業回流面臨的最大困境之一是人才資源不足,制造業勞動力缺口涉及建筑工人、焊工、半導體工程師等各種職業,尤其缺乏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人才。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23年12月制造業職位空缺60.1萬個。德勤2024年的研究顯示,到2033年美國制造業將產生190萬個工作崗位空缺。雖然美國政府正在通過改革教育與培訓體系、優化移民政策等措施增加勞動力供給,但迄今為止效果有限。
四是政策不連續。盡管兩黨在制造業回流的目標上一致,但具體政策存在分歧。例如,民主黨支持新能源產業發展,而共和黨偏好傳統能源;民主黨主張利用多邊貿易體系和規則,而共和黨堅持實行單邊貿易保護和制裁;民主黨主張實施寬松的移民政策,而共和黨傾向于通過限制性入境移民政策保護本土工人利益。這些分歧導致企業面臨較大的政策不確定性,對回流效果也產生不利影響。
五是補貼不可持續。隨著政府補貼逐漸耗盡,新的產業轉移和FDI流入正在放緩。當前,美國政府債務水平較高,國會預算辦公室2024年6月發布報告稱,2025至2034年的累計赤字將會大幅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無法繼續提供每年數千億美元的補貼,一旦停止,回流將大幅放緩。
總體來看,雖然美國制造業回流取得一定進展,但效果有限。美國促進制造業回流的諸多舉措加大了自身通脹壓力和財政負擔,破壞了全球貿易環境。一國制造業的持久競爭力從根本上取決于制造業自身的發展,貿易保護和產業政策只是促進因素。重振制造業需要完善的產業鏈、發達的基礎設施以及充足的勞動力等條件,而全面建立這套體系難度極高。從現有條件看,美國制造業缺乏持續回流的基礎,回流前景并不樂觀。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