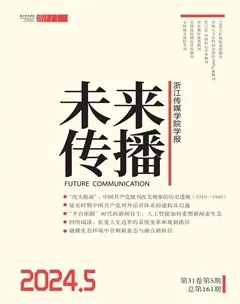影游融合視域下交互式電影游戲的敘事嬗變
摘 要:早期數字游戲在情感表達上的不足,致使游戲的電影化類似于一種“跨媒介”的摹仿。好萊塢電影呈現出明顯的游戲化傾向,而數字交互引擎在電影中的缺失,使之成為一種“偽互動”的戲仿。全新的交互式電影游戲兼具電影的講述性再現、戲劇的模仿性演繹、游戲的交互性模擬三種特性,平衡了敘事與互動的關系。影游融合從傳統的寫實主義美學轉向“擬像世界”的化身敘事,進而生發出人機交互敘事。數字游戲正試圖以空間化邏輯來替代傳統電影中的時間性思維。集電影凝視性與游戲互動性于一身的交互式電影游戲,為未來影游藝術的敘事嬗變和重構,提供了新的認知模型與敘事范式。
關鍵詞:影游融合;交互式電影游戲;人機交互;敘事嬗變
中圖分類號:J9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5-0117-08
面對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動作捕捉技術的迅猛發展,數字媒介的革新正在不斷突破人類想象力的邊界。近年來,好萊塢電影亦深受數智變革影響,涌現出如《頭號玩家》《瞬息全宇宙》等多元化的影游融合作品,呈現出影游融合的電影多模態,重塑著電影的敘事體驗與審美感受。電影從“再媒介化”邁向人機交互是一個全新的影像敘事階段。誠然,電影與數字游戲的本質不同,但在對世界的認知與體驗模式上尚存較強的互補性。在影游融合場景下,重構電影的敘事模式,從“再媒介化”敘事延展到“化身”敘事,將流于觀影之被動接受向觀者主觀深度參與、情感互動的實質性突破,實現人工智能時代,電影敘事模態的又一次嬗變和重構。
依托于數智賦能的交互式電影游戲,亦受人工智能影響而逐步成熟,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電影敘事性和游戲互動性,為用戶搭建了高度真實的虛擬世界,建構了豐富的場景/劇情交互方式,提供了高維的代入感和參與感,并試圖在話語層面重構時空敘事法則。本文根據瑪麗-勞爾·瑞安的數字媒體敘事理論,探討影游融合過程中電影的“再媒介化”敘事,以及敘事性與互動性調和的問題。
一、 理論回溯:“可能世界理論”與“多世界闡釋”
德國哲學家、數學家威廉·萊布尼茨在1710年出版的《神義論》一書中,正式提出了“可能世界”這一術語,并對“可能世界”理論做了最初的闡釋。萊布尼茨認為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一個,具有最大的完滿性,這種完滿性就如同他作為微積分的創始人,將我們生活和相愛并且消亡于其中的可感世界,替換成為一個量的幾何實體化的世界,從而使我們今天在理解實體化的世界映射進影游世界成為一種“現實”。
20世紀初德國學者普朗克等物理學家創立了量子力學,透過計算解釋無法直接看見的現象,用以觀察微觀物質世界。1935年,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提出了有關貓生死疊加的思想實驗,并最終導向一個著名的假說:如果將宇宙也比喻為一只“薛定諤的貓”,那么宇宙是否也是一個“多重世界”疊加的世界的問題。如果每個事件的選擇節點會同時形成多個宇宙,那么“當你開箱的一瞬間”,是否已經選擇了一個自己宇宙演化的方向。作為一個“多重世界”疊加的宇宙,當我們關注了某一宏觀特征時,宇宙的其他世界就退相干,使宇宙呈現某種確定性。而“多重世界”中的分化節點形成的不同宇宙亦被稱為“平行宇宙”。
1951年,休·埃弗里特利用數學導出了符合定律的量子的“多世界詮釋”,在當時并不能為多數物理學家接受。直到1970年,被譽為量子力學奠基者的布萊斯·德維特接受了埃弗里特的觀點,他寫了一篇關于“多世界闡釋”的文章發表在《今日物理》上,文章指出“宇宙在不斷地分裂成許多宇宙,這些宇宙相互間是不可見的,但它們都同樣是真實的世界”[1]。該理論還探討了“薛定諤的貓”,并闡明“量子躍遷會發生在每一個星球、每一個星系,宇宙中的每一個偏僻的角落。每次量子躍遷都會將我們地球上的世界分裂成無數個自我復制品。” [1](39)此后,埃弗里特的“多世界詮釋”才重新進入科學界的視野,并不斷擴大其影響力。隨著近現代對“暴脹宇宙學”與“超弦理論”認知的逐漸普及,大眾也終于開始慢慢了解“多元宇宙”,并逐步接受量子力學的“多重世界觀”。
萊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論”與量子力學的“多世界闡釋”遙相呼應,為科幻小說家、影視藝術家們打開了多元世界藝術創作的大門。量子世界的“不確定原則”,為“多世界詮釋”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注腳。受其理論影響者開始相信“多重世界”中的任何一個選擇都會導致全新的“平行宇宙”的誕生。從此,一種全新的認知世界的多模態邏輯開始逐步深入人心。
1991年,敘事學家瑪麗-勞爾·瑞安“將可能世界思想同言語行為理論、人工智能、計算機技術等學科相結合。”[2]為數字時代的敘事學做出了原創性的貢獻。瑞安指出:“可能世界理論的重要性不局限于為虛構性提供了一個邏輯的和現象學的說明,它最大的意義是對敘事理論的貢獻,即提供了一個敘事性的認知模型,超越了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3]經過瑞安等敘事學者的努力,“可能世界理論”開始作為受眾的一種認知心理范式,參與到新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游戲等藝術創作中,并在數字媒介中建構、演變、創生出諸如交互式電影游戲、互動式沉浸戲劇等跨媒介的融合敘事樣態。
二、“可能世界理論”影響下的模態結構與虛擬性
“可能世界理論”為經典敘事文本單一、線性的時空觀,提供了新的模態邏輯,模態即“可能性”。適逢數字時代的電影創作者、游戲設計者們,嘗試在這個嶄新的模態框架內,探索虛擬與現實世界的中間地帶,并逐步呈現出數字媒體敘事的重要特征——“敘事宇宙的模態結構”[3](648)與虛擬性。
電影中“文本現實世界”與游戲化“虛擬世界”的共生態,呈現在銀幕上,構成了數字時代影游融合的第一種常見的模態結構——雙重世界模態,該模態中的兩個世界總是互為鏡像。在影游融合驅動下,“虛擬世界”總是以游戲化特征呈現,而游戲世界中的角色形象又總是電影中人物心境的虛擬投射。正如“未被認證的可能事態,在此被稱作虛擬性,在敘事世界里散布著許多虛擬世界的星云,如信念、幻覺、虛構、恐懼、意圖、計劃等。敘事性就在于文本世界中現實和虛擬之間的相互運動,運動軌跡形成各種故事”[4]。文本現實世界作為一個外部指涉場域,“虛擬世界”作為一個內部指涉場域,兩個世界通過“跨世界的同一性”原則重疊且相互影響。如《刺殺小說家》中關寧失去女兒后,內心生出的暴戾情緒,都投射為小說《弒神》中異世界皇都的角色形象與冒險情節,電影現實世界中人物與電影中小說虛擬世界人物的一一對應,為“跨世界通達”提供了依據,使電影中小說情節發展對電影現實世界產生的影響變得有章可循。由上述案例可見,“雙重世界模態”中的游戲世界多是內心世界的表征,利用敘事的虛擬性特征,將電影現實世界人物的心境與情緒外化為“虛擬世界的星云”,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不斷交互,延展了時空的維度,拓寬了想象的精神場域。
第二種結構為平行宇宙模態,理論物理學認為,世界在本體論上是一個飄忽不定的量子世界,我們當下的生活之所以呈現為單一的經典世界,是因為我們已經將一個共享的世界模型強加于現實之上。而“多世界闡釋”的提出,打破了固有模型的觀念束縛,讓各種“平行宇宙”間有了競爭性共存的可能。“多重世界”的影像化呈現,“平行宇宙”的嵌套化表達,“數據庫敘事”的本質體現了關系本體論的隨機主義,是對互動敘事的引合。近年來,好萊塢電影“平行宇宙”題材層出不窮,如《蜘蛛俠:平行宇宙》《奇異博士2:瘋狂多元宇宙》等。在《瞬息全宇宙》中,伊芙琳遭遇了家庭和事業的雙重崩潰,導演通過一個類似游戲機制的設計——做一件極小概率的事,形成時空跳躍。伊芙琳開始穿梭于“平行宇宙”間,化身為電影明星、功夫高手、戲曲演員等。“平行宇宙模態”的不可預知性使敘事宇宙間充滿著張力。隨著時間的演化,某些平行宇宙在“文本現實世界”中得以具象化,而未具象化的亦未完全蒸發掉,而是作為一種“虛擬態”蟄伏在可能世界中,直到敘事封閉或是坍縮為不可能世界,而這種電影現實世界與諸多平行世界之間的相對運動則構成了影片敘事宇宙發展的不竭動力。
第三種結構為“里世界”循環模態,這種敘事模態顛覆了康德稱之為“現象領域”的部分,即處于時間、空間和因果關系間的知覺領域。“可能世界理論”為數字游戲與電影的融合搭建了互通的橋梁,數字時代的電影也偶爾跳出“凝視”的審美性,不再執著于“現實的漸近線”,而轉向“虛擬世界”想象性的模擬體驗。受到數字游戲“存檔復活機制”的影響,電影中的角色也可以一次或多次地復活、不斷輪回,即重復地將角色帶回故事的起點。如《羅拉快跑》中羅拉在完成任務時,通過“存檔讀檔”出現了三種結局,對應著羅拉在相同情境中做出的不同選擇,導致不同的情節走向。《失控玩家》里蓋不斷地死亡與重生,重復著相同的劇情。蓋與米莉的偶然相遇,激活了游戲里隱藏著的情感密碼,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并最終完成對“綠洲”與現實兩個世界的拯救。“里世界”重生循環的敘事手法,絕不是情節無意義的簡單重復,而是復現玩家在游戲過程中的成長。從陌生到熟悉,在無數次的失敗中,獲得成長的真諦,最終抵達理性的彼岸。這種復現的講述方式,深受后現代超文本敘事與數字游戲的影響。電影的情節因為不斷重復,而顯得不那么重要。這就意味著,故事本身充當一個腳本,觀眾參與其中做一個模擬的游戲。每次模擬都會形成一個差異化的虛構世界,敘事表征為某一情態下特定的事件或者角色的命運軌跡,一般性意義的產生需要通過比照性思考,闡釋終而得以顯現。
三、影游融合的影像實踐:對“再媒介化”敘事的反思
博爾特與格魯特在《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一書中表述“我們將一種媒介在另一種媒介中的表征稱為再媒介化,我們認為再媒介化是數字新媒體的界定性特征。”[5]從口語、書寫、印刷、廣播、影視,再到數字游戲,每一種新媒介的興起,都催生出符合自身特性的敘事樣態與審美特征。作為“第九藝術”,游戲與生俱來的強互動性,一向被敘事學者們視為數字時代“終極敘事”預言的主要特征之一。可是在我們等待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技術變得足夠強大來實現《星際迷航》中的“全息甲板”神話時,對于影像文本中敘事性與互動性不可兼容的爭論卻從未停息。當下的影游融合研究多集中于電影媒介受到游戲媒介的影響,而忽視了早期游戲媒介亦受到電影媒介的強勢沖擊。電影與游戲各自的“再媒介化”在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技術變得越來越強大的今天,對影游融合敘事的反思與重新認知顯得尤為迫切。
(一)游戲的電影化——一種“跨媒介”的摹仿
“新的視覺媒體正是通過對透視繪畫、攝影、電影和電視等早期媒體的致敬、駕馭和重塑而實現其文化意義。”[5](296)“博爾特與格魯特認為,再媒介化過程只是在引入數字媒介技術時才開始的,新媒介之所以新,就在于他們重塑舊媒介的特別方式。”[2](109)同早期的電影并不被傳統的文學、戲劇等強勢敘事藝術認可一樣,早期的電子游戲受到時代的技術限制,同樣需要小說、漫畫一類的周邊媒介來進行故事的補充。計算機數字技術的發展,終于使數字游戲的視聽呈現逐漸逼近電影化的程度。
游戲的電影化,這種敘事手法最初誕生于角色扮演游戲。可在大眾審美意識中,“數字游戲”這一術語依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通常被認為是以犧牲故事內涵和角色深度為代價的引人入勝的游戲開場動畫特效展示。提升情感影響力成為數字游戲繼提升畫面質量之后的又一個新命題。游戲欲再次從電影藝術中獲取靈感,來深化它的角色塑造與情感表達。
電影的情感敘事魅力,通常來自導演對認知層面的精準控制。通過鏡頭設計與蒙太奇語言的運用,對信息進行有選擇的展示或遮蔽,從而制造懸念與焦慮感。逐步積累情緒,適時釋放,使其影響力最大化,進而調動觀看者的情感應激反應。因而電影的情感傳達方式被形容為“類社會性的”。而游戲“自我中心”的情感傳達方式,卻總是受限于個體角色對事件的了解與體驗,同時具備了更多的自主性,玩家的選擇往往決定了事件的發展方向,從而影響著玩家的情感體驗。
早期數字游戲情感表達上的缺陷,造成了游戲的電影化類似于一種“跨媒介”的摹仿。“游戲對于媒體化經驗的持續模仿,是通過攝影機鏡頭——而非人類肉眼——將景觀數字化重構之后強調出來。”[6]如《使命召喚》《榮譽勛章》等戰爭游戲,讓玩家感受到的并不是對戰爭的體驗,而是對戰爭電影的視覺化摹仿。開場動畫特效的視覺奇觀,使數字游戲的畫面效果得到了極大的提升。過場動畫、橋接場面的流暢性與平滑感也不斷得到改良,卻依然讓玩家覺得游戲仍是在不斷追逐電影化的高清美學奇觀。游戲設計師Sam Barlow在《想象力與游戲敘事》演講中說:“數字游戲或許是實現‘真實感’的最佳媒介,因為游戲就是創造虛擬現實。”[7]誠然,“真實感”并不一定意味著要像電影一樣去再現生活的“真實”,畢竟“真實”與“真實感”并非兩個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數字游戲致力于達到的“真實感”更不應該是一種對于逼真的“電影感”的摹仿,而忽略數字游戲自身的藝術潛質。如其在感官層面的具身體驗,情感層面的模擬沉浸,敘事層面的強互動性。游戲必須運用自身的優勢,探索人工智能時代賦予的與眾不同的特質,才能獲得震撼的藝術表現力與持久的生命力。
(二)電影的游戲化——一種“偽互動”的戲仿
“再媒介化”的另一面還應該包括“舊媒介重塑自身以應對新媒介挑戰的方式。”[5](15)亨利·詹金斯認為“所謂媒介融合,指的是跨越多重媒介平臺的內容流動、多重媒介行業的合作、媒介受眾追逐各種娛樂體驗的遷徙行為。”[8]“杰夫·戈爾迪尼爾指出新一代的導演為‘PlayStation游戲機一代’,他們‘以嶄新的方式打亂敘事……打亂時間、空間、打亂故事的性質和結構’,并且‘將數字游戲和網絡的拼貼感帶入自己的電影中’。”[6]數字媒介技術的日趨成熟,為影游融合帶來了新的契機,而交互性與沉浸感成為數字媒體敘事的新寵。數字游戲天然的虛擬化身機制亦展現出與未來“元宇宙”虛擬世界無縫融合的無限遐想。由此,影游融合的影響主體發生了翻轉,游戲開始對電影呈現出一種流行的反哺態勢。許多電影導演公開表示正向游戲生產邁進,如斯皮爾伯格、彼得·杰克遜等,好萊塢電影也呈現出一種游戲化傾向。
但是,在影游融合的過程中也遇到敘述性與交互性不兼容的矛盾。“可能世界理論”為打通電影與數字游戲的融合敘事提供了可能性,因為兩種敘事形態共享了一個隱喻——“可能世界”。鮑德里亞曾將電影的放映機制與柏拉圖的洞穴隱喻相聯系。他認為不論是從“可見世界”到“可知世界”的靜觀,還是從外向內的回返,“凝視”始終是電影最基本的審美體驗。簡單來講,“看電影”的過程是一種“被動式”的接收與闡釋,而游戲更像一種“主動式”的參與和體悟。數字游戲的特性是由數字環境所塑造的,“莫雷歸納出數字環境的四個主要特征:程序性、參與性、空間性和百科全書性。” [9]前兩種特性都是成就交互性的內在機制。它的本體論在于建構一種計算機與人的交互,使計算機按照程序規則,基于玩家的行為做出條件性的反應。具體到數字游戲中,“所謂互動是指游戲者輸入條件變量,模擬系統對此做出反應甚至相應改變虛構世界的狀態。”[4](216)所以,玩家玩游戲是一種與計算機的交互敘事,這種敘事不僅是游戲設計師的設計,更是通過人機循環所共創的故事,具有一種主動與“不確定性”的審美體驗。
“數字理論家幾乎無一例外地承認:互動性乃是新媒介同舊媒介之間最根本的區別特征。”[2](96)游戲學家朱爾曾說過“你不能同時既互動又敘述。”[10]反觀近來好萊塢電影的游戲化趨勢,只是一種對游戲“交互性”的戲仿,數字交互引擎在電影中的缺失,使觀眾并不具備對故事有任何實質的戲劇性操控。如《勇敢者游戲2:再戰巔峰 》中的化身情節,觀眾并不具備游戲中的角色選擇權,因此無法獲得專屬的情感體驗,何談互動。如果說,數字游戲應該是對人類內心世界體驗的想象性模擬,那么此類電影只能算是對當下數字游戲“交互性”的一種時髦戲仿,即為一種“偽互動”。
而另一些電影會通過適當植入“游戲界面”視覺元素的方式,來迎合同樣作為游戲玩家的觀眾的喜好。如《歪小子斯科特》《硬核亨利》等。難道電影通過一百多年構建起的詩意與美學,將退化為血腥與暴力的淺層次視覺快感?威爾·布魯克爾曾言:“與電子游戲這樣一種級別較低的媒介結合,結果就是將電影降低到一個更加沒有價值、更加邊緣化的境地。它舍棄了任何對于嚴肅藝術的追求,卻贏得了一種新潮時髦的姿態。”[6]顯然,顧此失彼的膚淺戲仿,興許能博得一時眼球,卻并不能長久。棄電影之所長,屈就游戲之所短的流行風潮,其持久性令人懷疑。在數字時代,亟須一種更高維的影游融合樣態,全面調和敘述與互動的關系,為觀眾打開“元宇宙”的大門。
四、走向數字媒體敘事的嬗變——交互式電影游戲敘事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演進,電影和數字游戲已成為當代影像敘事發展的主要推動形式。鑒于計算機生成圖像技術與動作捕捉技術的成熟,一種趨近于“照相現實主義數字成像”的影像美學日趨極致。這種具備數字吸引力的新高清美學的崛起,極大程度模糊了現實與虛擬世界的邊界。數智革新為二者帶來了新生與迭代,進而創造出全新的數字虛擬互動樣態。
“敘事媒介反映了人類對現代世界體驗方式的演變,數字媒介的虛擬化本質表征著后現代社會主體性的消逝與人類經驗的零散化。”[4](208)電影作為當代主流的視覺文化奇觀,首當其沖受到影響。從《黑客帝國》中虛擬對現實的模擬,到《阿凡達》中虛擬化身的異世界再生,再到《瞬息全宇宙》中虛擬化身的多元世界共生。好萊塢電影看似不斷趨于游戲化敘事轉向,實則昭示出鮑德里亞所預言的圖像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擬像世界”的來臨。鮑德里亞認為“在最后的一個階段,表征堆棧的各層次相互坍塌,于是我們棲居于擬像之中。”[11]而“擬像世界”中虛擬化身的越界想象,正不斷沖擊著人類千百年來,靈魂受困于單一、速朽肉體的精神禁制。
“虛擬化身”敘事的勃興與其在“元宇宙”端的無限想象,實則映射出人類對于精神不朽與數字永生的執念。“通過虛擬界,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不僅對實在界和指涉界進行清算,而且還滅絕了他者……世界的——為虛擬現實所驅散。”[11](220)“跨越不同世界”的“可能世界”隱喻,游戲化的“虛擬化身”敘事,致使一種新的數字敘事美學逐步構建,新的影游融合樣態正在形成,它將無限接近于“終極敘事”的想象。在此背景下,交互式電影游戲(又稱互動式電影游戲)逐漸成熟。
(一)交互式電影游戲的誕生與成熟
1967年,捷克導演拉杜茲·辛瑟拉編劇并執導了黑色喜劇《自動電影》,并在蒙特利爾世博會捷克館首映。觀影時觀眾可以通過紅綠按鈕來進行投票,根據多數觀眾的選擇,影片劇情也會呈現出不同發展路徑與結局,后世將之視為歷史上第一部互動電影。1983年,由Cinematronics公司發行的《龍穴歷險記》,是第一個引入了FMV(全動態影像)的電子游戲,玩家可以通過簡單的按鍵操作完成“騎士救公主”這一經典的迪士尼童話敘事。由此,1967—1994年這一時期開啟了早期交互式電影游戲的初始發展階段。
如今,交互式電影游戲作為一種結合了電影和游戲元素的多媒體娛樂形式日趨成熟,通過觀眾/玩家的參與,形成一種具備強敘事性的交互式體驗。交互式電影游戲通常包含了多個情節分支和多個結局,用戶可以通過自己的選擇和行動影響故事的發展走向。這種形式的電影游戲以其獨特的交互性和沉浸感,為用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虛擬娛樂體驗。如今,這種以電影的方式表現,使用FMV的真人或動畫來完成的視頻游戲,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真人實拍,全動態影像呈現,如《夜班》《復體》等;另一種是真人動作捕捉,游戲引擎建模,如《暴雨》《底特律:成為人類》(以下簡稱《底特律》)等。
(二)敘事性與互動性的調和:人機交互內生敘事
在交互式電影游戲中,傳統的單視角、單線性敘事方式被舍棄,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求選擇不同的路徑和視角來探索故事,從而實現更加靈活和互動的參與形式。而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兼容敘事性與互動性的問題。游戲設計師克里斯·克勞福特曾說:“它授權玩家選擇。每項互動性應用必須授予玩家合理程度的選擇。沒有選擇就沒有互動性。這不是經驗法則,而是不折不扣的原則。”[11](95)交互式電影游戲的強互動性,使其敘事的表現、交流與體驗方式也有別于傳統電影。電影基因賦予的視聽敘事屬性與游戲基因賦予的交互引擎屬性,只是讓游戲設計師自上而下地構建好了世界觀(電影化敘事)與游戲規則(交互引擎內生敘事),卻并未形成敘事閉環。用戶自下而上透過設計師預留的QTE(快速點擊反應事件),在多線性的分岔路徑中進行抉擇,引發蝴蝶效應,導致最終劇情走向。二者的調和,使得用戶能夠通過模擬、自生、參與的模式進行故事創作,使其兼具了電影的講述性再現、戲劇的模仿性演繹、游戲的交互性模擬三種特性。
在《底特律》的最后章節《馬庫斯的革命》中,用戶化身為仿生人的領袖,當仿生人被人類軍隊包圍后,如果用戶選擇“引爆裝置”,那么戰爭將不可避免。如果用戶在最后時刻選擇放棄抵抗,而自焚殉道,人類社會將會對仿生人產生普遍同情,從而導致未來二者共存的社會格局。用戶根據內心想法的不同選擇,將導致虛擬世界截然相反的局面的產生,從而給其內心帶來極為震撼的情感沖擊。而未選擇的“虛擬態”,則會在多次自發性重啟與不同視角選擇的模擬體驗后,使用戶獲得不同命運的獨特體悟。交互式電影游戲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電影的線性與時間、邏輯與因果,而設計師自上而下的規則設定,用戶自下而上的人機互動作為其自生敘事的內生機制,較好地調和了三者的關系,繪制出形式精巧、維度多元的數字敘事圖景。
(三)游戲敘事的空間化轉向:“以空間置換時間”
長久以來,數字游戲對“不間斷時間”與“不間斷空間”有著過度的癡迷。在由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射擊視角兩種主要攝影機位主導的游戲中,角色在游戲場景里的不間斷運動、360度主觀視角的不間斷觀察,總是讓畫面呈現出一種寫實主義長鏡頭美學的紀實感。布魯克爾曾說“電子游戲的主導攝影形式更貼近藝術電影而非主流好萊塢電影,電子游戲的‘現實’是巴贊式的現實,而非愛森斯坦式的。虛擬攝像機一旦開始記錄就不可逆轉,直到結束才會切斷。”[6]然而,交互式電影游戲在諳熟傳統電影的視聽法則之后,逐步探索出適合自身特性的原創性的人機交互敘事。又由于其天生的數字媒介特性與游戲基因,使其敢于挑戰基于時間的線性敘事傳統,并試圖在話語層面重構敘事的時空比重。
借由人類的想象力,數字游戲正試圖以空間化邏輯來替代傳統電影中的時間性思維,即“以空間置換時間。”[2](127)一種具有強交互性的沉浸敘事手法——“環境敘事”橫空出世。它由迪士尼前設計師Don Carson根據多年來從事迪士尼樂園景點設計的感悟而創造。即如何構建一個“空間”,能夠把觀眾帶入想象的世界。在這個特定時空中用“旅行體驗”來取代傳統舞臺表演的“線性體驗”。這一重空間,輕時間的嶄新理念與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經典敘事模式背道而馳,卻與游戲“擬像世界”中構建沉浸式敘事的初衷一拍即合。
雖然瑞安認為“如果事件在時間上沒有固定順序的自由浮動,時間本身就會消失,因為我們的時間感覺總是依托于瞬息和事件相交替的線性邏輯。因此沒有順序,就沒有因果關系和邏輯連續性。”[12]但是游戲設計者們卻認為對“環境敘事”而言,一條條的信息就像一塊塊的“拼圖”,玩家的想象力就這樣不停地被激活去組合各種信息,完成最后的拼圖。“環境敘事”通過設計精巧的環境元素,以空間的方式向玩家傳遞信息,引發玩家的想象力和探索欲,從而增強游戲的沉浸感和情緒的感受力。通過玩家自主的場面調度,發現隱含的敘事信息,喚起個體聯想與情感意象,從而為自生敘事提供養分。這種追求深度參與的隱性敘事方式,需要玩家進行細致地觀察、探索和解讀,才能獲得更深層次的化身敘事體驗。
(四)融合敘事的沉浸體驗:游走于“凝視”與“化身”之間
交互式電影游戲充分地利用了自身數字媒介的包容性,復刻了數字游戲中的“環境敘事”基因,重置了時間與空間在部分敘事中的主導關系。又最大限度地融合了電影的線性邏輯,使得故事的因果關系得以保留。同時,恰當運用游戲世界的空間想象力,開發用戶的“演繹推理”能力,通過劇情中的場景、道具、音效等環境元素來間接構建敘事世界。在“環境敘事”段落,用戶化身虛擬游戲角色參與的強互動性,打破了戲劇中的“第四面墻”,由此用戶從被動接受的“他者”,轉變為敘事世界的主動參與者。
作為影游融合的產物,交互式電影游戲集電影凝視性與游戲互動性于一身,引導用戶在虛擬世界中不斷地切換自身的體驗狀態,這或許為數字時代的“終極敘事”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如《底特律》中每個章節的開端,多是電影化的世界觀搭建,情節的鋪陳與角色的出場。這時用戶是不能控制角色的,只能通過“凝視”沉浸于其中,“第四面墻”的隱現,讓用戶的體驗更似一種“歷時性的缺席”。而在交互引擎啟動的部分,人機互動開始運轉,虛擬化身機制瞬間激活,用戶迅速從上帝視角的“凝視”,化身為主體性的參與,這時用戶的體驗更似一種“共時性的在場”。用戶再不能如旁觀者般被動地接受敘事,而需在“擬態模型”中親身下場,通過主觀的判斷與理智的抉擇,也勢必會經受人性與道德的拷問,并且無處隱蔽。當然,最終的沉浸式體驗還取決于體驗者與虛擬化身之間的關系,敘事體驗的平衡或是一場心理認同與外在旁觀之間的妥協。
五、結 語
隨著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的成熟,游戲開發者能夠提供更加逼真的虛擬體驗和更高維互動的游戲玩法,也必將為用戶提供更加沉浸式的敘事體驗。“全息甲板”的極致沉浸神話,似乎已不再遙不可及。Sam Barlow 認為:“故事應該是一種讓受眾同時體驗感性情緒與理性思考的機制,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感性情緒和理性思考會錯開時間出現,故事卻是能讓它們同時發生的機制。”[7]經典的故事體驗總是通過讀者或觀眾與文本世界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感”,運用想象力彌合事件的“虛擬態”,再通過人類的共情能力獲得感同身受的情感體驗。“第四面墻”的存在總在提醒觀眾作為局外人的身份,須臾間的“走神”,或能讓觀眾跳出敘事所編織的想象世界,回到現實生活進行比照性思考,進而獲得對于個體生命的獨特感悟。數字游戲的沉浸機制卻讓玩家直接化身為“虛擬世界”的角色,它的強互動性,使玩家不再是旁觀者,而是親歷者。技術的進步,不斷搭建和再造出愈發真實的虛擬世界,人工智能又進一步擴展了數字生命的邊界。當虛擬世界變得比現實本身更加逼真時,人類在不斷追求人機交互、極致沉浸的狂潮中,或許還應保留幾分靜觀的理性,維持幾分“凝視”的從容,讓觀眾/玩家在不停扮演人性操控者與故事共創者的同時,仍能獲得電影般超然沉思的審美體驗,也許那才是數字媒體藝術“失而復得”的理想的融合范式。
參考文獻:
[1][英]約翰·格里賓.尋找多重宇宙:平行宇宙的瘋狂世界[M].常寧,何玉靜,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39.
[2]張新軍.數字時代的敘事學:瑪麗-勞爾·瑞安敘事理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96-127.
[3]Marie-Laure, R.(2006).From parallel universes to possible worlds.Poetics Today,27(4):647-648.
[4]張新軍.可能世界敘事學[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1:109-216.
[5]Jay,D. B.& Richard,G.(2000).Remediation.Massachusetts: MIT Press.
[6][美]威爾·布魯克爾.數字眼,CG眼:電子游戲與“電影化”[J].于帆,譯.世界電影,2011(1):40-44.
[7]Sam,B.Making her story—Telling a story using the player’s imagination.game developers conference.Retrieved March 14-18,2016, from https://youtu.be/JuADjLZjCe4
[8]Henry,J.(2006).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9]Janet,H.M.(1997).Hamlet on the holodeck.New York:Free Press.
[10]Jester,J.(1998).A clash between game and narrative.Retrieved April 17,2001,from http://www.jesperjuul.dk/thesis
[11][美]瑪麗-勞爾·瑞安.故事的變身[M].張新軍,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95-220.
[12]Marie-Laure,R.(2002).Beyond myth and metaphor:Narrative in digital media.Poetics Today,23(4):581-609.
[責任編輯:華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