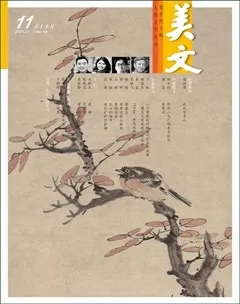鄭州二七廣場考古紀實
緣 起
那一年,聽聞二七廣場附近的東方紅電影院要拆掉了,心中不免蕩起幾分惋惜,雖說不是鄭州本土人士,但是,往來于鄭州大街小巷之間,難免不經意地撞見,破舊的外表與高速發展的都市氣質有些不太相符。但是,它對鄭州人而言,卻有著特殊的意義。這里盛放著他們靚麗的青春,儲存著他們年少的歡樂,他們曾在這里仰望星空,也曾在這里瞭望世界。這座古樸的電影院就是鄭州這座城市記憶的存放點。其實,除了電影院,那些古代的建筑都曾是歷史的見證者,因此,我對它們總會生起幾分尊敬,幾分愛戴。正如一個笑話所講 “聰明的女生一定要嫁給考古學家,因為,年紀越大,他們會越喜歡”。話雖如此,我們是要保留古老的東西,留住城市的根脈。但是考古學家的胳膊終究抱不住所有的喜歡,人類的進程是走向未來,城市的車輪終究是向前的,我們也要不斷地向前走,讓城市活在當下。
那一天,秋風乍起,手持一紙紅頭文件,我們一行人來到東方紅電影院舊址時,機械化作業給予人類選擇與思考的時空非常有限,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片拆除后的下凹空地,下沉的地表與四周高聳的藍色圍擋相比,顯得拆遷區空曠且遼遠,圍擋下的喬灌木郁郁蔥蔥,雜亂無章地野蠻生長,張揚著生命的活力。
面對這遼闊的工地,蔥蕤的生命,我們一行人,感到并不輕松,恰如生命的兩面,總是悲喜交加。為了城市的發展,這塊地已被重新規劃,考古勘探工作中,發現了大量商代遺存與古代墓葬。最關鍵的是,在擬建區內發現了大面積夯土遺存!這樣的勘探結果,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憂。建設用地位于鄭州商城外城墻附近,根據現有文物保護規劃,鄭州商城西城墻恰好穿過這片建設用地,這一區域屬于鄭州商城二類建設監控地帶,文保范圍內發現城墻,自是天經地義的事,不必大驚小怪。令人費解的是,這條夯土城墻分布的并不均勻,而且僅局部分布,并沒有成條狀分布,這樣的城墻又讓人生疑。面對這種復雜情況,國家文物局綜合考慮,令省文物局對這一區域發現的夯土進行定點試掘,以確定夯土墻的范圍、分布與性質。正是這樣的緣起,我們一行人,初來這個工地,頓感壓力在肩,這就是這次發掘最初的模樣。
那天,我在考古發掘總日記上,寫下了“2017年9月25日。二七廣場考古工地項目開工,編號2017ZEL”,一場尋找商代城墻的發現之旅隨之開啟。
城墻疑蹤
這個工地涉及國家級文保單位,國家、省、市文物局和我們單位都對這次試掘非常重視,通過謹慎的研究和綜合考慮,院領導讓單位商周組大牛姜楠同志任領隊,由我作為執行領隊,技術員的配備也是深思熟慮,抽調了有豐富田野考古經驗的王廣才和年輕新秀鄧燕兩位同志做技術員,這樣的隊伍可謂年齡結構老中青,技術力量也是呱呱叫。國慶節前,我們試掘小隊進駐了二七廣場考古工地。根據勘探所見夯土分布的范圍,我們一南一北,布了兩條東西向的探溝,規格3米×35米,試圖用這兩條探溝解決夯土分布范圍、結構、性質與時代的問題。為了排除外界的干擾,選擇北側探溝時,我們盡可能將其排布于北部混凝土樁分布區。當時,我認為這一區域的地層與堆積除了水泥樁的擾動外,其他干擾因素會很少。所幸,北側探溝在混凝土樁林立的逼仄空間里得以順利放線。線剛放完,未挖幾天,技術員就只剩王廣才一人了,年輕的小鄧請假回家了,年輕同志,新婚燕爾,離別總是不太好呀。
由于是試掘,因此,工地進展比較慢,揭開覆土后,兩條探溝的模樣就立馬顯現了出來。南側探溝,編號TG1,表現出表里如一,開口層的土質與下清土層基本一致,均為黃色粉砂狀生土。這樣的地層堆積,頓時讓整個發掘小組心如死灰。正當大家情緒非常低落時,北側探溝,編號TG2的西側,則出現了大面積灰土,并且成層狀分布,這些灰土的出現,讓我們多少有些欣慰,也帶來了希望,于是工作重心向北側傾斜。隨著工作的開展,北側探溝內的文化層堆積日益明顯,但是,地層堆積看似成層分布,卻與夯土的堆積存在一定的差異。一般來說,夯土的土質、土色上下一致,并且成層分布,土質堅硬且密實,層層相接處,多有夯窩。而我們清理TG2西側的疑似夯土堆積時,文化堆積卻表現的非常奇特,與夯土相似,又不完全相同。首先,堆積看似分層,但是顏色差異很大,上下銜接層的顏色差異明顯,灰一層,褐一層。堆積方式也不同,地層相接處,分層明顯,土質堅硬、密實,但是未見夯打的痕跡,比如夯窩。此外,有一種怪異現象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地層中發現了大量的商代陶片。商代城墻堆積中,發現商代的各種陶片,是正常堆積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文化堆積中的陶片數量過多,且形制較大,就有點匪夷所思。畢竟,在夯具強大壓力下,能夠茍且偷生,不粉身碎骨,能全身而退者終究是少數。因此,地層中不同材質的商代大塊陶片密集出土,加之未發現夯窩,頓時讓我們對片塊勘探所見的疑似夯土區域的堆積產生了懷疑。
工作在質疑中不斷向前推進,值得慶幸的是,兩條探溝的東側均發現了兩座墓葬,其中,南側的兩座,墓道完全顯露,經過擴方,基本確定了墓葬整體范圍,那是兩座平行分布的漢代墓葬,坐南朝北。這兩座墓葬出在王廣才師傅負責的探溝里,按照慣例,他就直接負責了這兩座墓葬的發掘與清理。而北側探溝中的兩座墓葬,顯現出的僅是墓葬的墓室位置,為了找全墓葬的分布范圍,在混凝土中間,大費周章,甚是折騰人,經過好幾天的奮斗,我們終于搞清了墓葬的分布范圍與形制,令我們詫異的是,北側的兩座墓葬,墓室雖為平行狀態,但在墓道位置,西側墓葬的墓道向東呈拐彎狀偏向,并與東側墓道連為一起。負責人鄧燕便來問我,這個墓道何故如此?看著她疑惑的表情,我便問她:“聽過‘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嗎?”她點點頭。隨后,我便告訴她,這或是漢代流行的夫妻合葬墓的一種合葬方式。男女問題是人類社會經久不衰的熱點,男女合葬也是古代墓葬中永恒的話題,從史前到明清都在流行,只是埋葬與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聽完后,鄧燕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但是,她還是慨嘆了一句:“唉,這又何必呢,如此大費周章,活著的時候,在一起都未必快樂,在死后還要在一起,真累呀。”看著她心事重重的樣子,我連忙說道:“生活是個漫長的過程,其實還是幸福更多一些。”
隨著工作的進展,北側探溝中的灰土堆積已經大部顯現出來,這個已被清理出來的遺跡,進一步確認了我們最初的判斷,這種文化堆積很可能不是夯土。如果不是夯土,那又會是什么呢?那天,我站在探溝一側,看著規整的東西兩壁,坑內堆積成層且有陶片出土,但又不是城墻的基槽,又會是什么呢?突然靈光一現:“壕溝!”兩字跳入我的腦海,我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一想到這里,我連忙跳進探溝中,用手鏟刮了刮堆積的邊緣,進一步確認了這個遺跡幾個關鍵性位置。遺跡屬性的這個發現,也得到了領隊姜楠的認可。基于夯土墻體(基槽)變壕溝的發現,我們在堅持原有發掘計劃的同時,增加了一些新的工作任務,對發掘區內的四壁進行掛剖,如果這處遺跡真是城墻壕溝,那么城墻就一定在附近,并且會在工地下清后的四壁上有所顯現。于是,吳金濤同志被抽調過來,承擔了這項重要工作,通過對四壁剖面大范圍地刮剖,我們并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探溝中的遺跡是灰溝,原本疑似的夯土墻應該就是灰溝內的文化堆積;探溝中的四座墓葬是新莽時期的遺存。
隨著工作的開展,日子將臨隆冬,我們的工作在肯定與否定中來回搖擺,生活也在希望與失望中來回橫跳。終于,一個初冬的上午,我們迎來了專家組的檢查,這是國家文物局對工地質量把控的關鍵一步。那天來的專家,都是國內早已名滿江湖的大學者,這些專家在河南和商周考古深耕多年,且多有建樹。專家組在現場對發掘的遺跡進行了檢查,并對出土的器物進行比對。在聽取了我們的工作匯報后,專家組對我們的發掘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同了我們發掘小組的結論,并且認為,該區域可以進一步開展工作,以確定遺址區內其他遺跡的屬性與年代。結合專家組的建議,就在我們積極向國家文物局匯報的時候,一場大雪來臨了,在這場大雪中,我們暫停了野外工作,轉入了室內整理。一個冬天挖出來的陶片,除了墓葬中的器物粘對起來的較多外,灰溝出土的陶片,多不成器,這樣的結果恰如我們的城墻之旅,無功而返。
全面發掘啟動
2018年秋,我們幾近快忘卻二七廣場的發掘事宜,國家文物局的批文終于到了,批準了我們全面發掘的申請,并再三叮囑我們注意重要遺跡現象,時刻上報發掘情況。
又是一個深秋季節,我們的隊伍又回到了二七廣場這熱鬧非凡的區域。發掘現場與墻外繁華的街道、擁擠的人群相比,著實冷清不少,加之一年的擱置,有些區域的草木仍在肆意地瘋長。這次隊伍進場時,我們一共是七個人,我、鄧燕、黃晨、王笑笑、黃靜鈴、程方和劉心怡,后四人是山東過來實習的學生,單位鑒于她們需要過田野考古關,就派她們四人來二七廣場這個遺跡較多的工地,以滿足她們的實習要求。于是,我就指派鄧燕負責這幾個女生的日常工作、學習。因為,我一直覺得鄧燕是好孩子,這個來自關中西府的農家兒女,善良、單純、質樸、勤奮。她有著關中地區樸素的情感與操守,她秉持這種高尚的情懷在工作中實施著自己的節奏,頗具古風的做事方法,有時會顯得不近人情,不太適合當今的世下,那樣,對自己過于苛刻,會讓自己活得很累。也許,是她工作的樣子常常會讓我想起曾經的自己,那個曾經無枝可依的浪子。讓她做學生們的帶路人,我是想讓這些娃娃們在有一天,突然想起曾經的這段經歷,她們的大姐頭沒有把她們帶到邪路上去。即使這樣,在一個冬月的上午,我接到黃靜玲的電話,電話那邊哭的是梨花帶雨,竟無語凝噎,無法言說,在其平靜之后,我才搞清楚,因為她做了件冒風險的事情,被鄧燕及時制止并批評了幾句。因為此女天生靦腆,加之后怕,面對這種事情便瞬間崩潰。
這種工地,因為前期的建筑層比較厚,文化層前期早已破壞,加之后期清理建筑層時,也多有損傷,這里的文化層基本不見,發掘起來,并不費勁。盡管地層堆積不好,我們還是嚴格遵守國家文物局的要求,按照探方法對工地進行了布方,科學發掘。而工地上,我們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就是遺跡數量眾多,埋葬深。通過初步發掘,我們發現有些商代灰坑的深度可達6至7米,這樣的深度,讓我們在安全上出現了很大壓力,如果要保持灰坑的原狀態,那么商代方形灰坑越往下越小,對發掘帶來很大不便,若將人置于7米下的豎井中作業,如果發生垮塌,后果將不堪設想。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采用邊發掘、邊擴方的方法,在已經不斷下清的過程中,逐漸擴方,通過擴方,我們可以在安全的防護下,逐漸清理遺跡內堆積。同時,這一區域的漢代墓葬也非常的深,多在4米左右,更有甚者,在6至7米左右。鑒于我們挖灰坑的方法,我們對墓葬也采取了這種方式,這樣在清理起來,盡管有些費事,但是,安全系數卻很高。
相比于其他的考古基建項目,我們的這個項目不僅僅在技術上有較高的要求,是國家文物局關注的重點項目,同時,在理論上也有高標準,工地上四個嗷嗷待哺的實習生,她們的性格差異很大,王笑笑同學果敢大膽,黃靜玲謹慎細心,程方內向寡言,劉心怡文靜默然。雖然四人各有性格,但是終究是實習生,相比于其他成熟的技術員,這些來實習的學生對我們的工作提出了高要求,畢竟,作為她們的實習老師,不僅僅要告訴她們怎么做?并且也要告訴她們為什么?當凡事都必須有個“為什么”的時候,我頓時就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加之學生們對于知識的渴望,她們對工地所有的事情都覺得新鮮,都感到好奇,并且會時常提出問題,有些問題我們尚可以應對,但是對有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我們也時常不知該如何回復。看見漢代的人骨,就會問:“這些人為什么是這個樣子?”“他們的骨頭為啥這么粗?”“他(她)的腿為什么這樣細呀?”這些無厘頭的問題正中我知識盲點,我便不敢再說話,害怕說錯話,給了她們不正確的答案,免得誤人子弟,那種糾結常會讓我這個須眉大漢變得有些像裹腳的女人,不敢邁開步子前進。為了解決這些女同學的問題,我們只好在田野工作中開辦了臨時的理論培訓班,通過講授考古理論知識和田野技能,來規范問題的出處與方向,通過這樣的方式,終于把這些脫韁的野馬拽回她們原本該待的地方。
2018年的考古工作在時間的流逝中,迎來隆冬季節,當大雪覆蓋著整個工地的時候,四野皆被大雪掩蓋,只有那些被清理完的遺跡,就像一個個眼睛,張望著蒼穹,打量著這個熟悉卻又陌生的世界。
開啟2019年
2019年的春節剛過,迎春花才剛剛綻放,我們在二七塔旁的工地又開始忙碌了。今年是工地計劃完工的一年,于是,我們的工地迎來了一批增派的技術人員,陳陽、趙福樂、高宏、景亞茹等人,此前,這四人在鄭州南崗劉挖明代墓葬(可見拙作《鄭州南崗劉明代墓葬發掘記》,《大眾考古》2022年10期)。他們的到來大大增強了整個工地的技術力量,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問題——桌子周邊坐不下了。在增加了幾個桌子后,我們依桌坐下了,那時候,整個工地整齊有序,生氣活潑,安逸悠遠。
初春的中午,太陽光穿過二七塔頂,灑落在我們的工作室前,我們掩了工地大門,瞬間會將外面的喧鬧隔絕起來,于鬧市之中得一片清凈地。擺起一排長桌,上面擺滿了各色的菜肴,五顏六色,冷盤熱菜,葷素搭配,大家圍桌而坐,觥籌之間,頓生江湖與廟堂僅有一步之遙的錯覺。畢竟,工地圍墻外是繁華的二七商圈,我們隔墻而看,百年德化也只是幾步的距離,外面的繁華喧囂熱鬧與墻內幽靜自得形成了明顯的反差。墻外的高樓大橋,霓虹電光是現代科技的杰作,圍墻之內所能看到的是灰坑水井,墓葬窖穴是古人的文化殘存。墻外的世界是我們的,也曾經是他們的。歷史的輪回中,他們從古代一路走來,生于斯、葬于斯,他們是這一片熱土的曾經。當歷史向我們流淌,我們是這片熱土的現在,但是,終有一天,我們也會像他們一樣成為歷史。因此,工地大門不再是一道普通的門,它如同一個時空的轉換臺,門內,我們與古人對話,門外,我們與現代共享繁華。而這個特征在大家的穿著打扮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我們隊伍中的女同志們在上班與下班時,常常是兩套裝備。由于大都是青春靚麗的女孩,進門后,立刻換上藍色工作服投入工作,下班后,大家紛紛換上時尚的外套,展現出現代人的婀娜,原本藍色的海洋頓時就泛起五彩斑斕的花朵。尤其是景亞茹同志,身材高挑,干起工作進退有度,打扮起來也是格外時尚,成為工地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開始后,我們發現了隱藏在這片熱土下太多的秘密,商代的窖穴、戰國的水井、漢代的墓葬等等,這些遺跡中的各種出土物也是各具特色,商代的陶斝、戰國的陶罐、漢代的銅鏡、唐代的三彩、明清的瓷碗。其中,商代與漢代的遺存與出土物最豐富,商代的遺跡多是方形窖穴,這種窖穴的形制非常規整,口部多為長方形或方形,豎穴土坑式,深度多在4至6米左右。坑內堆積非常豐富,坑底也多有完整的陶器發現,因此,我們采用擴方法對其清理,也收獲了不少完整器。如陶鬲、陶斝、陶豆、陶盆、陶簋、陶壺、陶甗、陶甑和卜骨等。盡管出土物如此的繁雜,與漢墓比起來,還是有些相形見絀。
漢代墓葬在這片土地上分布的非常密集,且多為西漢時期,清一色的洞室墓,分為兩種,空心磚磚室墓和小磚磚室墓,前者略勝。這些漢墓為我們的發掘工作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因為,此地發現的漢墓多保存完整,極少被盜,其中一座就被我們小隊號稱“專業第一”的黃晨同志遇上,那是一座形制巨大的西漢晚期墓葬,局部殘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發掘至墓底,竟然只發現了零星的五銖錢,對此墓清理花了很多心血的小黃,頓時,就仰天長嘆,不能自抑。相比于小黃的手氣,鄧燕的運氣就比他好多了,畢竟她挖出了一座唐代墓葬,還挨了批評。那座唐代墓葬在早期清表時已被破壞,發掘區域的基坑壁上可見殘部,因為掛在了壁上,鄧燕看見了這個遺跡,遂將其進行了清理,經過一陣忙碌之后,發掘出了一堆文物,銅鏡、手鐲、裝飾品等等。當我看到這些器物后,當即就批評了鄧燕,并立刻停工,開了一個業務短會。因為,裝飾品被清理回來后已經全部散落,不能成形。面對這種情況,我告訴大家:考古不是挖寶,是科學研究的工作。一座墓葬有無隨葬品都是古人真實生活的寫照,即使被盜,也是墓葬歷史的一種呈現,因此不能有主觀得失,而要客觀地記錄,嚴肅地對待。同時,田野考古也不是單純的器物清理,更不是清土豆式的挖寶,田野考古學最主要,最核心的就是原生情景,當一件器物被粗暴地剝離出其原生場景,那么這件文物的價值就會打折,所以對于復合型文物,最好是保持原狀,而不要輕易地清理,最好是全部提取,放入實驗室再進行操作。這次會議之后,我覺得大家在文物的提取上有所精進,更加的科學。后來,我聽聞小黃在別的工地就完整地提取了一件唐代的頭飾,并放入實驗室進行考古,這或許就是知識的力量吧。
這些漢墓不但沒有被盜,而且出土物非常豐富,但是與墓葬的形制相比,我們更喜歡后者。這些漢代磚室墓數量眾多,空心磚上多有圖案,雖多為單一圖案,但是偶爾也可見飛鳥走獸,樓閣華車,這些多變的紋飾點綴著寂寥的墓室,豐富著古人的生活,也開闊著我們的視野。除去這些耳目之娛,合葬墓著實刷新著我們的認知。異穴合葬是這個墓地普遍的流行方式。兩座墓葬之間,或以過道相連,或以墓道相通,他們似乎在用一種近乎倔強的方式在踐行曾經的愛情誓言。
這種異穴方式的男女合葬很好理解,但是同穴的男女合葬墓似乎就不好解釋了。“難道他們都是同一天去世的?如果不是,這樣是不是有些太殘忍呢?愛情會消失嗎?”這些問題來自于那個裝扮時尚的女生,她一直以“多問第一”在我的團隊存在,不知就問,因此也比別人更加精進。呵呵呵……工地一陣笑聲之后,我覺得似乎得說些什么,要不這個笑聲不就成為了掩飾尷尬的道具了嗎?我隨即問道:“你看過一個名叫劉文科的人,寫的碩士論文《黃河流域史前男女合葬墓研究》嗎?”女孩子抿著嘴,搖了搖頭,卻笑得更開心了。我說:“那就聽劉先生給你講道。”
其實,古代兩口子同時去世的事情有,但只是偶然現象。在漢代,人們思想還是很開放,所謂“仲春之際,奔者不禁”,月上枝頭,人約黃昏,男男女女,那是多么開放的生活,我們現代人都不敢想,更不要說干。那時候的人不像宋元以后,那么的拘謹,尤其是明清之際,女人由于禮教的限制,不要說穿熱褲,就連與男性說話都不允許,因此,以死殉節的人或比較多。
因此,判斷這個問題,首先是看田野發掘的場景,必須從靜態的現象去推斷動態的過程。在漢代或者其他時代墓葬中一旦發現了合葬墓,即使是夫妻合葬,我們也要時刻保持警惕,畢竟野外考古工作是可以確定他們埋藏過程的唯一方法。考古現場是一切研究的基礎。如果野外工作馬虎就會造成室內研究結果的失誤,就像這座夫妻同穴合葬墓,究竟是什么樣的埋葬方式,要從埋藏細節與靜態端倪中去觀察,而不能僅僅看現狀,現狀是靜態的,而埋葬過程是動態的。如果只從靜態的視角看問題,那么考古學就會很簡單。考古學要“透物見人”,就必須看到這個動態的過程。你看,這個墓葬,墓室比一般的墓室略寬。其次,它的左右兩側建筑材料也不一致,一側為小磚,一側為空心磚,隨葬器物也分兩堆擱置。同時,墓室的人骨也表現出有差異,最為重要的現象就是竟然有一個陶罐被擱置在墓門外側位置。這些現象,說明了什么呢?只有一點,就是事出蹊蹺必有內因。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現象,而一切的證據表現出這個靜態的結果并不是原始狀態,也就是這個靜態現象是多個動態過程造成的。比如,墓葬的建筑材料存在差異,墓門上竟然有陶罐,加上人骨差異,都凸顯出此墓葬曾二次擾動過,也就是男女在合葬過程中存在先后的關系,其中,一人先逝,隨即被埋入此墓葬中,后其配偶死后,也埋葬于此,形成合葬。這個過程是動態的,比如前期所用的材料是一種,后期所用墓葬材料是一種,在墓穴擴建時,先逝者多會被擾動,骨骼會有擾亂,因此墓葬會有異常情況。而墓葬在擴建時,將先逝者的一件陶器擴建時刨出,在埋入第二個人時,又將其與先逝者混埋一處,于是就出現了你看到的這個情景。
“那么,誰先,誰后呢?”小景看著這座合葬墓,又問了一句。
“那個先走的人,一定是被傷害最深的人,因為埋葬較早,多被后者擾亂打破。因此,這種合葬關系中,就是被打破者,遺骸有局部擾動的一般都是先行者。”講完之后,我笑著對她說,其實可以看一下,我的論文,盡管通篇寫得不咋樣,但是在合葬這個動態關系這塊,寫得還較為精彩。
考古大會戰
一直以來,覺得二七大會戰的標志性事情應該以郭向坤、任麗娟、秦德寧三人的到來比較妥當,畢竟,他們是從別的項目組抽調過來的人員,用以增加我們的人手,而且秦德寧、郭向坤原本就是獨立的小隊。他們的到來,為我們項目組不但增加了發掘實力,而且也大大地擴展了我們的食譜結構。郭向坤師傅雖出生于河南偃師,但曾定居新疆,無師自通,燒得一手西域好菜,尤其是新疆大盤雞更是拿手絕活,每逢佳節或天雨時節,他便親自掌勺,烹制佳肴,尤其是那肉的鮮香,辣椒的濃烈,土豆的綿長,恰如其人,粗糲中有些柔軟。飯后,他總是拿個小凳,坐在一堆陶片堆中,靜靜地拼接,嘗試各種方式,總是將看似無法成型的殘破陶器拼接成一個近乎完美的器物,在他手上修復出的商代陶器最多,無愧于妙手之稱。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都在想這性格如此火爆的人,竟有如此細膩的心態,他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呢?當然,在他負責下,工地西側的重點區域,原本懷疑是壕溝位置,在全面揭開后,所謂的壕溝,向南漸收,成為了一個不規則的灰坑。或許這就是考古的魅力,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層會是什么?或許就是人們給你挖的一個大坑。
隨著工地的全面揭開,挖溝的挖溝,挖坑的挖坑,挖墓的挖墓,一派熱鬧的景象。但是由于大氣管控的要求,已經發掘區域必須用防塵網進行遮蓋,工地位于市中心,只好遵循安排,為天藍藍做出考古人的貢獻。凡事有利有弊,天藍了,腳下卻不穩了,我們的發掘自東而西,而門在東開,因此,我們出土時,要經過長長的且暗藏玄機的已發掘區,這個區域大坑套小坑,坑坑相接,每次途經,總要十分小心才好,這就正應了,生活不僅有眼前的二七塔,也有腳下的大坑。而現在,還要加蓋防塵網,風險系數明顯攀升,每次路過,如同過雷區。雖然,掉進坑的事情不常發生,即使掉進去,多半會被網子兜住,如同掛在樹上的二師兄,除非體積過于龐大,才會塵埃落定(腚)。
但是,落坑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那是一個中午時分,高宏在穿越“坑區”時,一不留神就掉進坑里去了,說時遲那時快,在文物保護區,頓時躥出一個高大黑影,直奔高宏而去,只見他三步并作兩步,瞬間就來到高宏身邊,一把抓起落在坑里的高宏,將她拽上坑來,又是拍土,又是噓寒問暖。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個黑影就是我們的文物保護專干吳金濤。受到驚嚇之后,面對這突如其來的一系列變故,瘦小的高宏一臉緋紅,連忙推開小吳。站在遠處的我們,也被這一系列動作搞得如同丈二的和尚。但,頓時,我們大家彼此一笑,就全明白了,怪不得這兩天有奇事頻發,現在不都有答案了嗎?于是,中午,我們多加了好幾個菜,讓這兩個年輕的“地下黨”轉成地面“正規軍”。由此可知,掉進坑里,也不一定都是壞事,有些就是“天作之坑”,比如郭老師挖的那個大灰坑,高宏掉進去的這個小灰坑就都是。所以不要畏懼坑,保不齊那是件好事情呢?怪不得人常說,吃虧是福呀。
鑒于高宏的這天作之坑,當天下午,鄧燕帶著工人,用我們的標桿與警戒帶因形走勢地在發掘區標記出了一條安全通道,并對危險區域進行了加固和標識,這樣,這一片危險區域中就走出了一條坦途。這個做法恰被下午檢查工地的杜新院長發現,盛贊不已,并且全院推廣。事后,杜院長給我講,這次檢查工地,發現鄧燕變化挺大的,比以前更加的大方和自信了,不像以前那樣沉默不言。其實,歲月給予人們的東西,不僅僅有蒼老,也有成長。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2015年深秋,鄧燕初來我的項目組時的模樣,恬靜無語,默默跟在工地現場負責人梁亞男的身后,膽怯地張望著這個世界。在這幾年里,她與我合作,謹慎而負責地干著工地上所有的事情。這個對愛情大膽,堅忍的女生結束了與男友長達八年的愛情長跑,終究修成正果。雖然婚姻和我們所熱衷的愛情并不一樣,但是我堅信,一個心中有愛,認真負責的人,一定會過好她的這一生。我還是希望她能對自己不要過于苛刻,其實,有時候,過度完美也是一種傷害。
再美好的華章終有落幕的時刻,考古會戰也一樣。在發掘區域我們清理出商以來多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的器物也不可勝數。原本位于工地西側的疑似夯土層在三年來的發掘中,從原來的城墻,變為了疑似壕溝,再從壕溝變成了一個灰坑。這樣的喜劇對于一個靜止的遺跡而言并沒有什么,因為,它已經深埋于此達三千年之久,它從未說過自己是什么,說它是什么的人恰是不斷變化的我們。雖然,每一次,我們都覺得自己這次判斷是正確,但是,當6ad47c2f4a58dc79f2866070f0dbc5d9塵埃落定,我們才發現,這一切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但是我們深知,每一次變化,我們都距離真相更近了一步。
答案揭曉后,省、市文物局都安排了專家對這個工地進行驗收。那天,我將做好的PPT放給來檢查的專家看時,五味雜陳,畢竟,一件事情終于結束了。
完整收官
工地驗收結束后,我們一直保持著工地的原貌,靜等國家文物局的檢查。這段時間里,我們掩起門來,歲月過得很慢,將挖出來的陶片,慢慢地修整、粘對,有不少都可以修復成完整的罐子。當然,代價也是慘重的,雙手沾滿502膠水是小事,有時候,甚至被膠水燙傷。有一天上午,我們在修陶器的時候,一不留神,陽光下飽吸熱量的膠水就滴到了小景的手上,瞬間,白皙的手背化為緋紅,幾秒后就騰起一個大泡,如此情景,大家急忙去找了些冰塊敷上,過了陣,大泡才有所收斂,然后,大家才笑著說:“這下可破了手相了。”吃一塹,長一智,此后,我們再修陶器時,就格外地注意,唯恐被繼續破相。
等待的日子,時間雖然很慢,卻是工地資料查漏補缺的好時機。當一些細微工作要去補充時,鄧燕就和看工地的大叔一起合作工作。突然有一天,我看見小鄧的丈夫小李在幫忙干活。細問之下,才知道,看場大叔在工作時,扭了腰,鄧燕深感這是她的責任,于是讓丈夫請假,來這邊幫忙。我當時心想,何必呢?但又一想,善良的人原本如此。
2019年終究過去,我們的工地又一次完全覆蓋在白雪之下,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這次冬藏的時間非常的漫長。
2020年,我奉命前往二七工地蹲點,那時節,整個昔日繁華的二七廣場門可羅雀,零星的幾個人不是急救的大白,就是穿紅馬甲的志愿者。那時候的二七工地,從里到外都沉浸在一種肅殺的氣氛中,墻外了無聲音,墻內聲音了無。我搬了張桌子坐在工地一側,伏案改寫稿子。未過幾日,疫情緩解,我和鄧燕便將二七的出土物標記完整,全部運送回單位。
那天中午,我找到文印室張帥,希望她能夠加快二七工地發掘報告的出具,她二話沒說,便投入工作,第二天清晨,她將發掘報告交到我的手中時,一臉的疲憊。
終于,歷時兩年多的二七工地,終于完整收官。
(責任編輯: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