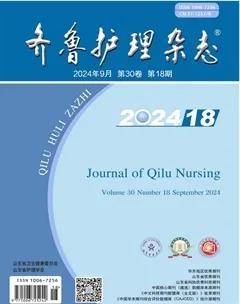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相關因素分析及積極心理學干預策略




【摘要】目的:分析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相關因素,探討積極心理學干預策略。方法:選取2021年6月1日~2022年6月30日收治的80例顱腦腫瘤患者作為研究對象,采用社會影響量表(SIS)評估患者病恥感,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其影響因素。結果:80例患者SIS評分為(59.78±9.91)分;分析結果顯示腫瘤類型、預估生存期、受教育程度、醫療費用占家庭年收入比、生活質量、自我效能感、自尊水平、照顧負擔、與醫護人員交流頻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lt;0.05);腫瘤類型、醫療費用占家庭年收入比例、照顧負擔、自尊水平是影響患者病恥感的獨立危險因素,預估生存期、生活質量、自我效能感、與醫護人員交流頻率是影響患者病恥感的獨立保護因素(Plt;0.05)。結論:預估生存期、醫療費用占家庭年收入比、自我效能感、照顧者照顧負擔、自尊水平、與醫護人員交流頻率是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獨立因素,應注重提升患者自尊及自信心等積極心理,提高護患交流頻率,同時對其主要照顧人也應給予適當積極心理干預。
【關鍵詞】顱腦腫瘤;病恥感;回歸分析;積極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R473.73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006-7256.2024.18.025文章編號:1006-7256(2024)18-0084-04
顱腦腫瘤指原發腫瘤或經轉移形成的繼發腫瘤等顱腔內病灶,其中惡性顱腦腫瘤疾病進展快、病死率高,而腦部結構復雜,部分良性腫瘤也因腫瘤位置靠近腦干等重要中樞神經難以切除根治,導致復發風險較高[1]。根據疾病發作部位及進展不同,臨床表現出一定差異,但大多存在頭痛、顱內壓升高、視力及認知功能減退等占位性病變特征,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病恥感由精神疾病患者表現出因疾病所致被排斥感及自我污名化的負性情緒體驗發展而來,后被廣泛應用于各醫學領域中[2]。顱腦腫瘤對患者生活質量造成顯著影響,患者對比原先生活狀態產生心理落差可引發病恥感,自覺家屬照顧負擔加重可出現自我污名化加重其病恥感,不良情緒可影響其后續作息及飲食管理。對此,在顱腦腫瘤患者日常護理中給予積極心理干預改善其心理健康,始終以積極態度面對疾病對提高患者治療配合度具備正向意義。本研究對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旨在為積極心理學干預提供改進方向。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選取2021年6月1日~2022年6月30日我院收治的80例顱腦腫瘤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影像學結果符合顱腦腫瘤診斷標準[3];原發性顱腦腫瘤;首次接受治療;術后預估生存期≥6個月;年齡gt;20歲;有1名及以上主要照顧家屬(照顧時間≥4 h/d)。排除標準:合并心、肺、腎等重要器官功能衰竭;伴嚴重精神疾病或認知功能障礙;臨床資料完整。回顧性分析研究對象一般資料,男42例、女38例,年齡34~62(48.73±5.62)歲;腦膠質瘤66例,腦膜瘤14例;良性腫瘤44例,惡性腫瘤36例。
1.2研究方法征得醫院及患者同意后,向患者發放社會影響量表(SIS)、基本資料問卷、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健康調查簡表(SF36)、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自尊量表(SES),由患者填寫;照顧者負擔量表(ZBI)由患者主要照顧人填寫。所有調查問卷由醫護人員發放,控制填寫時間在1.5 h內,填寫完畢后當場回收。①SIS評分:由社會排斥(9條目,36分)、經濟保障(3條目,12分)、內在羞恥(5條目,20分)、社會隔離(7條目,28分)4個維度,24個條目組成,采用1~4分4級評分法反向計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病恥感越強,并將24~48分歸為病恥感薄弱,49~71分歸為病恥感明顯,72~96分歸為病恥感強烈[4]。②基本資料問卷:由我院自行編制,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年齡等自主填寫條目,受教育程度、家庭狀況、婚姻狀況、經濟狀況等自主勾選條目,由患者自主填寫或選擇作答。③SSRS評分:由主觀、客觀、社會支撐3個維度,10個條目組成,采用1~4分4級計分法正向計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社會支持越強,并將分數≤22分者歸為社會支持弱,23~44分者歸為社會支持中等,≥45分者歸為社會支持強[5]。④SF36評分:由軀體功能、角色功能、軀體疼痛等8個維度,36條目組成,極差法線性變換將總分轉換至0~100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生活質量越高,并將分數≥51分歸為生活質量高,39~50分歸為生活質量低,≤38分歸為生活質量極低[6]。⑤GSES評分:該量表為單維度量表,評估患者面對挫折時的自信心,由10個條目組成,采用1~4分4級計分法正向計分,總分10~40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自我效能感越高,并將10~24分歸為自我效能感低,25~35分歸為自我效能感正常,36~40分歸為自我效能感高[7]。⑥SES評分:單維度量表,評估患者自我價值及自我接納總體感受,由10個條目組成,采用1~4分4級計分法,5項正向計分條目,5項反向計分條目,總分10~40分,得分越高代表患者自尊水平越高,并將10~24分歸為自尊水平低,25~35分歸為自尊水平正常,36~40分歸為自尊水平高[8]。⑦ZBI評分:由個人負擔和責任負擔2個維度、22項條目組成,采用0~4分5級計分法正向計分,總分0~60分,得分越高代表被測者照顧負擔越重,并將21~40分歸為照顧負擔輕,41~60分歸為照顧負擔重[9]。
1.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3.0統計學軟件對本研究數據進行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獨立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Plt;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綜合調查問卷結果本研究共發放84份問卷,有效回收80份問卷,有效回收率95.24%。其中SIS社會排斥(16.87±3.62)分,經濟保障(9.82±0.87)分,內在羞恥(14.43±3.38)分,社會隔離(18.66±2.24)分,總分(59.78±9.91)分,整體病恥感處于中等水平;病恥感薄弱22例(27.50%),病恥感明顯31例(38.75%),病恥感強烈27例(33.75%)。
2.2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單因素分析見表1。
2.3變量賦值表見表2。
2.4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多因素回歸分析見表3。
3討論
顱腦腫瘤起病緩慢、后逐漸加重,惡性腫瘤及部分無法根治的良性腫瘤可反復發病,加重病痛及家庭負擔,許多患者因此產生病恥感,在面對自我污名化傷害下喪失求生希望。為提升治療希望水平及依從性,需對顱腦腫瘤患者給予針對性積極心理學干預。
病恥感概念最早見于艾滋病及精神疾病患者,隨后發展至其他醫學領域。本研究中顱腦腫瘤患者SIS總分(59.78±9.91)分,與同類型疾病比較發現其高于黑色素瘤患者,與青年宮頸癌患者水平相近[10],低于卵巢癌患者[11],整體處于中等水平。本研究顱腦顱腦腫瘤可見于各年齡段,35歲前發病率較低,之后發病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該年齡段患者多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發病后難以維持正常工作及生活狀態,家庭負擔增加是造成其病恥感的主要來源[12]。本研究結果可知,腫瘤類型是影響患者病恥感的獨立危險因素,預估生存期則為獨立保護因素。病情越重、死亡風險越高、患者心理承受壓力越大,患者難以面對死亡的恐懼,且存在對以往生活的留戀及影響家庭后續生活的強烈自責情緒。家庭方面醫療費用占家庭年收入比、照顧負擔是影響患者病恥感的獨立危險因素,生活質量為獨立保護因素。顱腦腫瘤患者發病入院后其家庭經濟收入下降,同時醫療費用支出再次降低家庭經濟水平,導致患者及家屬生活質量均下降;顱腦腫瘤患者臨床癥狀包括視聽神經障礙、肢體麻木等,嚴重者可引發偏癱、癲癇,患者縱向對比以往生活狀態產生心理落差,易放大自我異化心理[13];入院后患者家屬除面對經濟壓力外還需照顧患者,患者易產生自責心理。自尊水平是影響患者病恥感的獨立危險因素,自我效能感為獨立保護因素,說明高水平的心理調適能力更利于患者疏導病恥感等負性情緒[14]。自尊水平高的患者大多數更為自律,得知罹患癌癥事實后難以接受;自我效能感較高的患者往往更樂觀,具備治療后恢復生活質量的信心。此外,與醫護人員交流頻率也是降低患者病恥感的獨立保護因素,醫護人員具備豐富的治療及護理經驗,可向患者說明情況,引導患者以平和心態面對疾病,避免自我污名化,與醫護人員交流過程中患者可及時表達心中顧慮并獲取明確指導意見,宣泄心理壓力,以減輕病恥感。
回顧分析結果可知,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因素多來自患者對家庭牽掛及自身心理狀態,基于此,可定向改變積極心理學干預策略。首先,應協助患者盡快接受疾病事實以積極投入后續治療,此過程中應維護患者自尊心,避免其情緒失控導致發生過激行為;隨后應盡可能幫助患者樹立治愈信心,可配合以往成功治愈病例引導患者提升希望水平。在家庭方面,不僅應注重患者心理狀態,還應并重家屬心理健康,延長患者與家屬接觸時間,減輕家屬照顧負擔及心理壓力,改善其精神面貌。根據與醫護人員交流頻率對病恥感的影響,護理過程中應積極回應患者,對刻意避免交流者應主動對話,增加交流次數,心理干預過程中需確認患者狀態確保其干預效果。在此基礎上應格外關注惡性腫瘤易復發或預估生存期短的患者,利用往期疾病控制情況較好病例調動患者積極性,并盡可能營造舒適環境以減輕患者病痛,主動滿足患者及家屬精神需求,使其樂觀面對后續生活。
綜上所述,腫瘤類型、預估生存期、醫療費用占家庭年收入比、照顧負擔、自尊水平、生活質量、自我效能感、與醫護人員交流頻率是影響顱腦腫瘤患者病恥感的因素。積極心理學干預側重點應為提升患者自我效能感,維護其自尊水平,提升住院期間生活質量,并將干預對象延伸至患者家屬,以幫助患者樂觀面對疾病結局為最終目的。
參 考 文 獻
[1]趙慶府.觀察顯微外科手術經不同入路治療顱腦腫瘤的臨床療效[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17,20(5):100-101.
[2]李利平,孫建萍,吳紅霞,等.慢性病患者病恥感的研究現狀[J].解放軍護理雜志,2020,37(3):75-78.
[3]方三高,陳真偉,魏建國.2021年第五版WHO中樞神經系統腫瘤分類[J].診斷病理學雜志,2022,29(10):991-992,封3.
[4]李艷清,錢燕,嚴曉玲,等.簡體中文版社會影響量表的修訂及信效度檢驗[J].護理研究,2024,38(8):1336-1342.
[5]肖水源.《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應用[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1994,(2):98-100.
[6]李魯,王紅妹,沈毅.SF36健康調查量表中文版的研制及其性能測試[J].中華預防醫學雜志,2002,36(2):109-113.
[7]馬旻,艾自勝,石志道.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在中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信度效度檢驗[J].同濟大學學報(醫學版),2022,43(4):515-520.
[8]劉彥茹,王希林,王志仁,等.德國Galli心理劇治療對少年精神障礙患者自尊及療效的影響[J].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23,50(1):65-67,71.
[9]徐英華,林毅,李秋萍.癌癥患者家庭照顧者負擔量表的研究進展[J].中國護理管理,2015(2):246-249.
[10]楊芬燕,蔡靜,劉琴,等.青年宮頸癌患者術后病恥感及益處發現的相關性分析[J].中國醫藥導報,2020,17(6):70-72,76.
[11]楊榮,閆榮,袁芳,等.卵巢癌患者病恥感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J].護士進修雜志,2020,35(23):2128-2132.
[12]韓仁強,周金意,張思維,等.2015年中國腦瘤發病與死亡分析[J].中國腫瘤,2021,30(1):29-34.
[13]張衍,張輝,岳四海,等.顯微外科手術對顱腦腫瘤患者癥狀緩解情況和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16,19(10):53-54.
[14]雷羽輝,劉小紅,陳巧麗,等.心理危機干預技術結合安寧療護對癌癥晚期患者心理需求的影響[J].齊魯護理雜志,2020,26(9):47-49.
本文編輯:路曉楠2024-01-08收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