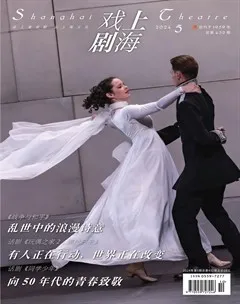生命的柔韌

日系輕喜劇《白條肉》是日本青年劇作家橫山拓也(Takuya Yokoyama)的經典獲獎劇本,經由上海戲劇學院師生的共同創作,2023年9月第一次作為中文版話劇《白條肉》在校內演出,獲得了一致好評。而后,2024年1月受邀首屆會昌戲劇季作為“小戲單元”的開幕“小戲”,同年3月又在上海茉莉花劇場成功完成了十場演出,可謂是在各個舞臺上大放異彩。
“白條肉”,日語原文為“エダニク”,是將牛或豬宰殺后,從脊骨處一分為二的肉塊。故事發生在“丸元肉食中心屠宰場”的“特別屠宰房”內,圍繞三位男性勞動者展開,他們分別是屠宰場工人澤村、玄田和誤入研磨室的伊舞。劇中澤村向伊舞介紹工作的細節,表示“在肢解的過程當中,肉上沾上血絲是不行的,最后從后背割開做成白條肉的時候,也必須漂亮地分半才行,不然就是工作失敗,我們這里就必須進行賠償”。可見,“白條肉”不僅是屠宰場工人工作的成果,也是他們工作壓力的體現。劇中三位主人公對于理想、工作、生命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見解,其中的矛盾與爭吵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讓觀眾產生共鳴。這不僅是一個關于職場壓力的喜劇,對于生命這一議題的思考與討論也有跡可循,在文本層面的思辨之上,也有劇場的創新實踐。
“活”在職場
劇場是一個藝術家與觀眾共同參與創作的空間,好的戲劇能夠與觀眾的思想交匯。這部作品貼近生活,貼近當代年輕人的思想困境。故事是小人物的生活軼事,即使觀眾沒有了解過屠宰場或屠宰工作,但因為這個故事本質上是勞動者的故事,劇中人物的行為與語言邏輯都符合我們普通勞動者的思維,因此容易與三位人物在職場中面對生活與工作、現實和理想的困境產生共鳴;同時,劇中對于這個職業的詳細描述以及專業詞匯穿插在臺詞中,不僅不枯燥,反而讓觀眾得以窺見“另一個世界”。
開場,我們便看見了一個水平傾斜的舞臺,像是半個長方盒子的空間,而盒子的對角直沖觀眾,地面呈現出一個被拉長的菱形,突破了傳統鏡框式舞臺四四方方的邊緣,營造出不平衡的感覺;一長一短富有“工業感”的水泥墻面,以及歲月流淌于其中的“舊質感”,在整體視覺上給人一種輕微的不安全感。舞臺上沒有多余的裝飾,但也并不空曠,一張放著炒面、漫畫與紙巾的桌子,一個鐵皮儲物柜,一排傾斜擺放的椅子,空中懸掛著傾斜的長條燈與地面形狀的失衡相呼應。
導演的理念是弱化與表演并不直接相關的視覺語匯,而舞臺作為角色內心世界的外化,雖然舞臺布景沒出現屠宰相關的意象,但有意設計為低矮狹長的舞臺空間暗示了劇中人物生活的環境,非對稱的空間也體現了人物內心世界的失衡狀態。這個地方便是整日與“生命”打交道的屠宰工人們在工作之余休息的地方,有些壓抑卻無法逃脫。
青年時期的個人理想與殘酷社會現實的割裂,是每個人都要攻克的課題。在戲劇開場之前,身穿一套白色工作服的澤村走上舞臺,為炒面泡好開水后,走下舞臺。開場之后,一束頂光打在桌子上那一盒炒面,圍繞著炒面的話題,澤村邊吃邊與玄田開始了日常的閑聊,他總是吃這一款“UFO炒面”來“重置”屠宰留在身上的氣味,表示連自己的兒子都無法接受這樣的氣味,并對兒子謊稱自己在肉食店工作。在日本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屠宰場工人曾經受到歧視,像澤村這樣的底層勞動者也在這樣無形的目光下用自己的職業與手藝養活家庭;同時又因為背負著作為家庭頂梁柱的責任,對這份工作的依賴程度十分強烈,也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危機。
面對突如其來的年輕小伙伊舞,澤村的態度發生了兩次轉變,最開始對于這個小自己三歲的啃老族,澤村是抱著面對所謂“后輩”的自豪感,試圖教育他的態度,而伊舞也虛心接受了。圍繞著工作這一議題,澤村和伊舞的事件營造了劇中第一個小高潮。一開始,伊舞自豪地向澤村介紹自己啃老的這十年中最“厲害”的事情,但實際上只是些無聊透頂的小事,他卻以這種無聊的事情為傲,澤村的“吐槽”引得觀眾大笑(吐槽在日本相聲或漫畫中是一種重要的角色表現技巧,源自日語“突つっ込こみ”)。緊接著,澤村反應過來伊舞正是自己任職公司的大客戶“伊舞農場”的準繼承人,直直地鞠躬并不停地道歉,一改先前的態度,演員的體態與神情變得惶恐起來,弓著背,連腳步幅度都變小了。角色地位快速轉換,以及澤村的強烈反差,觀眾們連連發笑。澤村這副看似窩囊的模樣,觀眾們想必十分理解并感同身受,能夠理解這樣一位職場人迫于無奈、害怕失去工作才委曲求全的心情。
第二次轉換,是戲劇的高潮,也是澤村的隱忍達到了極限的爆發。當伊舞在與玄田聊天中聽到玄田談到手工肢解時用了“可惡”一詞,伊舞一以貫之的信仰受到了沖擊,本劇中最大的矛盾開始顯現。“白條肉”也是對待生命的態度的標志。在流水線上用機器宰殺是無情的,手工宰殺則是懷有感情的,而這個感情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帶著對生命的尊重與感情剖出白條肉,是伊舞一家的信仰與原則,也是伊舞從小到大受到的教育與熏陶。另一邊,澤村面對失業危機,作為勸說兩邊的“中間人”終于爆發,三人在這個狹小的房間內搶奪、追逐,運用了鬧劇手法的場面,觀眾席間笑聲不斷。冷靜下來的澤村用手機拍下了玄田與伊舞的對峙,這是再一次身份的急劇轉換,表面看起來謙卑怯懦的澤村又一次地掌控住了舞臺,觀眾席又是一片笑聲。
“活”在劇場
導演李旻原提出了“新話劇”的概念,并在這部作品中成功地實踐,即演員身體表現如現實對話般放松自然,并強調演出當下的真實感受。在《白條肉》的創作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獨特的演出形式,每場同一句臺詞的語氣、動作、走位或許都會在一定的范圍中帶有些許的不同,尋求一種更能讓演員活在當下人物扮演的同時,又能與觀眾即時交流的有機表演方法。筆者有幸觀看過兩場《白條肉》的演出,分別是在2023年9月于上海戲劇學院新空間劇場的首演,與2024年3月于茉莉花劇場的《白條肉》第十場演出,感受到演員適應不同環境而創造出不同的舞臺效果。
回顧這部作品的首演作為一個例子,去年9月的上海依然有些悶熱,飾演玄田的演員在縝密的語言中不時地在走過桌子時抽出紙巾來擦汗,這樣的小舉動又恰巧與劇情中玄田緊張的心境相契合。在演出后的交流中也有觀眾對這一點進行了提問,想知道這是否舞臺動作的設計。飾演玄田的演員馬鴻飛表示,出汗是氣候與身體的原因,而在觀眾看來這樣小小的“差錯”更恰好地融合了演員的表演,將劇中人物慌張、焦躁的情緒表現得恰如其分。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可見,雖是基本貼合劇本的現實主義舞臺,《白條肉》并不是一場精準的、不容許偏差的“展出”,而是隨著各個因素可以改變的“當下”,這正是對“新話劇”演出方法的實踐與嘗試,舞臺上充盈著角色的生命活力,讓觀眾切切實實感受到“活”著的他們。
在這部作品中,表演以對話作為主體,盡可能地保留原劇本的特色與語言中的哲理性。劇作家橫山拓也的劇本以縝密凝練的語言著稱,劇情在螺旋上升的對話中逐層推進。同樣的,在導演李旻原的創作理念中,語言本身有獨特的魅力,語言本身就是一部戲的主體,而角色是被召喚而來的,在導演與演員的共同創作中正是利用了語言來召喚角色。
有別于中國傳統話劇體驗式地通過掏空演員的個人經歷去挖掘人物,在《白條肉》的創作中演員通過反復體會臺詞來尋找與人物的共鳴,那么人物的舞臺形象就逐漸形成了。整個故事像是一個生活的片段,《白條肉》的幾場演出都在體量較小的劇場內,演員與觀眾的距離非常近,在這個場域下,人與人之間會更容易產生連接,更容易感知到劇中人物并非對著觀眾說話的敘事者,而是仿佛真實存在于那個空間的真實的人。正如飾演澤村的演員黃灝龍在訪談中所說:“雖然我與劇中人物的生活經歷迥然不同,中日文化也有一定差異,當我在臺上說出來臺詞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就覺得這就是我想說的話,這個角色一直在我的身邊,一直在跟我前進,角色就是我的一個部分。”
在“笑點”密集的劇情中間,演員的表演節奏更需要與觀眾時刻保持即時交流,他們的表演沒有夸張f110f3884efabf56c89b6226c6bb5489的舞臺動作,甚至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日常生活中一樣自然地行動,像是活在舞臺上一般。劇中伊舞喜歡在說話中加入雙手在胸前“比槍”的手勢,尤其是在氣氛比較尷尬的時候,這個手勢加上伊舞嬉皮笑臉地說“對不起”,喜劇張力凸顯。重復是喜劇中的又一重要手法,伊舞在初次亮相就做出了這個手勢與兩位陌生的屠宰工人打招呼,這一個動作就在觀眾心里樹立了一個涉世未深的小青年形象;在之后的劇情發展當中,到了矛盾似乎比較嚴峻的時候,伊舞都會靠這個動作來緩解“尷尬”。通過這一手勢的重復,可以加深觀眾的記憶點,起到增加笑料的目的。有些情節或者動作本身并不能讓觀眾發笑,但如果它重復出現多次,再巧妙地配合劇情,就會產生一定的喜劇效果。
其實,職場壓力在普通大眾心里算是一個有些沉重嚴肅的話題,當舞臺上氣氛進入僵持的時候,觀眾會猶豫這個地方該不該笑,在簡短的停頓后,難掩笑意的伊舞對兩人嚴肅爭吵做出的反應,不斷地打斷澤村和伊舞嚴肅的爭吵,屢次把嚴肅的氣氛拉回到喜劇的氛圍中,觀眾們便會開懷大笑。如此的表演節奏,不至于讓觀眾陷入沉重的思考中,而是在輕松愉快的戲劇氛圍里,看著別人的故事,想著自己的生活。
“活”在當下
《白條肉》讓我們在舞臺上看見了底層勞動者的樂觀與堅強,看見了人生的無奈,看見了生命的柔韌。在社會生活中,如幾位勞動者一般的小人物多如牛毛,他們堅守著自己的理想與責任前行,也只有自己才能讓生活充滿期待。
生活提出問題,但不一定有解答,戲劇也是如此。在劇中,伊舞訴說著自己對于生命的理解與感受,但是不被玄田所理解,澤村也沒有表露出他真實的想法。對于這一議題,沒有具體的答案,也沒有孰是孰非。
故事的最后,三人的生活一切照舊,卻也都發生了一些小的改變:澤村幸福地說著自己的職業被兒子所理解,玄田則離開了讓他感覺到“太可惡了”的特別屠宰崗位,轉而被調到別的工作崗位,而伊舞則是參加學習手工肢解的研修。劇本的最后一句寫道,“然后,食用肉的肢解、加工工作明天也會繼續下去”,三人的生活還是要繼續;走出劇場,我們不得不面對社會與壓力,被時間推著走的我們也會繼續尋找“白條肉”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