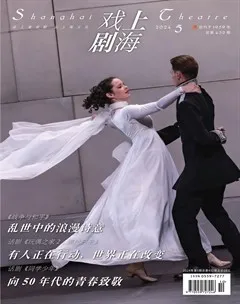熒屏有戲:戲曲與電視劇的對話
編者按:
人類歷史上第一臺電視劇到了1924年才被英國發明家貝爾德制造出來,與至少有數百年歷史的戲曲相比簡直是個小嬰兒,但是從傳播影響力來看,在20世紀下半葉電視曾一度代替戲劇(包括戲曲)、電影等藝術成為主宰,其中電視劇無疑成為人們最喜愛的觀看對象。而在此之前,戲曲被中國觀眾當作電視劇每天演出,觀眾不斷催更,明清時期誕生了長篇巨制的傳奇,后來的京劇和地方戲也出現了連臺本戲。那么戲曲這一傳統藝術與電視劇這一現代藝術能擦出什么火花呢?本期上海歌舞團編劇、上海越劇院青年創作沙龍成員魏睿與上海市劇本創作中心編劇高源、上海越劇院袁派花旦陳慧迪、上海大學博士后李培一起討論“戲曲與電視劇”之間的關系。
一、朝花夕拾,尋源問道
魏睿:中國戲曲藝術有悠長的歷史,而中國第一臺電視于1958年3月由天津無線電廠試制成功。由此,中國的戲曲藝術也陸陸續續地出現在電視熒屏之上。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戲曲藝術與電視的聯姻還是以復制或者記錄戲曲舞臺上的表演為主,而電視的輔助傳播作用則較為凸顯。80年代后,戲曲與電視劇之間才真正開始進入彼此調試和融合的發展之路。戲曲與電視劇,一個是古老的農業文明孕育的藝術,一個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兩者的“年齡”落差巨大,藝術本體特征也完全不同。可是,通過兩者不斷互通有無,彼此學習,揚長避短,也誕生了一系列令人回味無窮的經典作品。這些作品曾受人追捧,也曾飽受爭議。戲曲與電視劇的對話,究竟蘊含哪些未來創新藝術的可能呢?
李培:我準備的話題激進一些。現在的年輕人并不關注越劇電視劇上演,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越劇有沒有電視劇,而是越劇的承載方式和年輕人有代溝。試想,《靈魂擺渡》《太子妃升職記》可否成為越劇的網絡自制劇?《太子妃升職記》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性別轉換,越劇里女小生演繹男性風格更加自然,表演特色與《太子妃升職記》是相合的,而且也是古裝劇,在服道化美妝各個方面還可以有新的嘗試。
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拍一部越劇藝術網絡自制劇?所謂的網絡自制劇,主要分為三個,一是臺網劇,既在電視臺播也在網上播;二是獨網劇,由獨立的人制作;三是由純粹的由網絡運營方,像愛奇藝、騰訊制作的網絡自制劇的作品,可能很短,每集只有20、30或40分鐘。孟繁樹的《戲曲電視劇藝術論》中提到了1979年浙江臺的《桃子熟了》,還有上海臺監制的《孟麗君》,他認為這兩個作品代表著中國戲曲電視劇最實在的形態,因為它們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拍了實景。
高源:20世紀80、90年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戲曲電視劇,實際上只有兩個劇種參與——黃梅戲和越劇。原因在于,第一,我們長輩觀眾需要戲曲演員在電視熒屏上帶來戲曲故事,第二,當時的熒屏不像現在,沒有豐富的網劇,觀眾主要的娛樂是守著電視機看電視劇。
越劇在戲曲劇種中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劇種,帶有都市性藝術的爆款基因,而黃梅戲樸實易傳播,由于天時地利人和,便有了像韓再芬這樣的一批藝術家成為當時的熒屏偶像,如今上海越劇院之所以有一批忠實的粉絲,跟當時那一批爆火的戲曲電視劇有直接的關系。越劇和黃梅戲兩個劇種的血緣和基因契合了電視的傳播方式。
我覺得無論傳播媒介如何變化,人類都是需要故事的。我們中國獨有的章回體的小說,戲曲也有連臺本戲,包括到熒屏時代有了電視連續劇,其實都是有一條故事線在支撐的。像電視劇《戲說乾隆》,從結構而言也是一種章回體小說的變體,又如明清傳奇,以單元故事為結構,但是里面又有主線人物組成一個故事結構。愛故事存在于我們中國人的基因。當然現在的電視劇改編不是機械式地照搬來,觀眾可以看到現代人的價值取向。
二、曾經的戲曲IP
和如今的電視劇IP
陳慧迪:《甄嬛傳》是2011年首播的清宮劇,共76集,2013年,同樣根據原著小說改編的上海越劇的新編越劇《甄嬛》,也已經走過整整10年,我在劇中飾演安陵容這個“腹黑”的角色,作為演員這是極大的挑戰。當時我跟自己說,我不能排斥她,我要跟安陵容建立信任感,與她感同身受,理解她所做的一切,我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場指責她是個壞人。故事里的“瑪麗蘇”女主非常完美,幾t9qHDvQAAucLvLHCuDwKJg==乎沒有缺點,但是只生存于電視機里,現實生活中真的不可能有,我覺得安陵容反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小人物。比如說她一開始進宮其實很單純,身份比較低微,做事小心謹慎,但她被華妃盯上,如果不答應跟華妃合作,可能當場就斃命。我認為安陵容為了生存自保,珍惜生命,不想死,沒有錯,但是當她走出一步之后,就回不了頭,一步錯步步錯。特別感謝越劇《甄嬛》的編劇,將安陵容處理得更復雜,甄嬛滴血驗親時安陵容暗中派人給清河王去報信,這是重要的轉折點,讓我能演繹一個不一樣的安陵容。安陵容的唱詞也很悲慘,表達了做人做鬼不由己的矛盾心理,真是她的心聲。演完之后我發現,有很多觀眾很理解對我演的安陵容,我覺得挺欣慰的。
魏睿:從傳播學的角度而言,舞臺和電視都是戲曲的傳播媒介(也稱載體),彼此沒有高下之分,由于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的文化傳統、生活習俗、審美能力、技術手段等因素的不同,戲曲傳播的影響力和接受力有天壤之別。因此,當一個人評價說“我喜歡戲曲”或者“我不喜歡的戲曲”的時候,也許并不意味著他真的喜歡或不喜歡戲曲藝術,而只是說明他喜歡或不喜歡接觸到的傳播方式。針對傳統的戲曲傳播,學者周華斌認為:“除了演員與觀眾以外,劇場和劇本是戲劇的空間載體和文字載體。”在電視劇中,除了文字和圖片之外,傳播方式就更多了。
傳播學理論的奠基人哈羅德·拉斯韋爾在1948年發表的《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構成傳播過程的五種基本要素,這就是“5W”理論。即:Who(誰)【控制分析】,says What(說什么)【內容分析】,in Which channel(通過什么渠道)【媒介分析】,to Whom(向誰說)【受眾分析】,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效果分析】。其實每一個環節都對現代觀眾是否接受戲曲、是否喜歡戲曲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為什么年輕觀眾看到電視轉播傳統京劇覺得陳舊,而看到電視劇《鬢邊不是海棠紅》的傳統京劇就喜歡呢?其實京劇沒有變,變的是渠道(in Which channel)。電視鏡頭后面是導演通過現代的鏡頭語言,講傳統京劇重新編碼、敘事、剪輯、創作,潛移默化地接通了現代人的審美接受水準,一個鳳冠、一件霞帔、一個云手、一段臺步在鏡頭下被賦予了精美古典又神秘的色彩,這份陌生感也讓京劇“出圈”。
高源:最近我也思考了很多,我有一些年輕的朋友提到游戲《原神》,因為我以前在上海京劇院工作多年,年輕的朋友來問我是否認識花旦演員楊揚,她是《原神》一個游戲人物的原型,我說當然認識。我特意去看了《原神》,游戲運作的過程確實很有意思,而傳播媒介確實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近年來還有個爆火的戲歌《武家坡》,也是貼合了現在傳播媒介的變化。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戲曲還是戲曲,但電視劇一直悄悄在改變,現在手機改變了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觀看方式從橫屏變成了豎屏,又造成了情緒上的傳播改變。《武家坡》這首歌傳達的也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但它帶來一系列不尋常的傳播效果,讓觀眾想象《武家坡》角色、人物、故事,全都可以腦補。
戲曲在電視中形成多種呈現,包括舞臺紀錄片、戲曲藝術片、戲曲電視劇等,戲曲故事作為經典IP在電視劇里不斷被改編,如《楊門女將》《包青天》等。電視劇題材的基因就是來自于戲曲,當然再往前追溯,還有文學的母本。新的傳播媒介給我們這些研究戲曲、創作戲曲、喜愛戲曲的人帶來新的挑戰,也考驗我們能不能把戲曲用恰到好處的傳播媒介傳遞給更廣大的觀眾。
魏睿:曾經戲曲經典是大IP,電視劇紛紛從中汲取資源,如今反過來,如果戲曲走IP改編之路,會是一條捷徑嗎?不一定,戲曲改編任何題材的難度不亞于原創的難度,有成功“出圈”的驚喜,也有得不償失的失敗。首先,動輒三四十集的電視劇內容體量大、人物多,除了主線外還有多條副線相互編織,而如今的戲曲舞臺劇僅有兩個多小時,除去唱腔之外時間更少,改編成戲曲必須刪繁就簡。其次,傳統戲曲與電視劇雖然都有虛實相生的美學特征,都有寫意性、綜合性的表演特征,但是畢竟藝術本體相去甚遠,戲曲演員在舞臺上的合理表演在鏡頭下就會不自然;高明的電視劇演員能用一個眼神或表情表達千言萬語,往往以無聲勝有聲。如果說出長篇大論的“我好悔啊我好恨”,就顯得突兀直白,觀眾會覺得膚淺,失去了豐富的想象空間。然而在戲曲舞臺上,觀眾不可能完全捕捉到演員的眼神和表情,戲曲的敘事和抒情還要依賴大段的唱腔,尤其是快要劇終的時候,主人公要回顧人生唱一段感慨或者道理,難免直白地表露內心的悲喜。
京劇《換人間》改編自53集電視劇《北平無戰事》,電視劇編劇劉和平采取了多維度的網狀敘事,有人稱其為“學者劇”。劇中有方孟敖調查走私賬目的線索,有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謝培東的潛伏線索,有蔣經國指揮曾可達的“孔雀東南飛”線索,有在國共兩黨做雙重間諜的梁經綸的線索……但是京劇《換人間》抽絲剝繭地選擇了一條線索——謝培東營救方孟敖并成功地迎接了北平和平解放,保留了原著的諜戰精髓,從開始就拋出了一個大懸念:誰是真正的共產黨?讓觀眾在兩個小時之內猜測。《換人間》還大膽地把電影、多媒體、舞蹈、交響樂、話劇等藝術拿來為己所用,呈現大片氣質,實則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海派京劇文化的淵源。
改編自電視劇的同名京劇《大宅門》大膽地從電視劇第一部40集的龐大情節中僅僅選取了“白景琦娶楊九紅”這條看似微不足道的線索,卻把這條線寫得飽滿,把人物之間的愛恨情仇纖毫畢現地描摹出來,從白景琦認識楊九紅起,到楊九紅被白母趕出家門為止,事件不多,恰好夠一臺戲曲的容量。劇本語言繼承了原著特色,京味兒十足,在極端的戲劇情景中隨時劍拔弩張,導演將戲曲程式化語言作為合理的載體,銜接戲劇節奏、人物塑造、劇情推進。在戲曲舞臺上,很少出現性格復雜、正邪相間的主人公,但是京劇《大宅門》的男主人公放蕩不羈,為人處事有些不正經,更要命的是個“媽寶男”,女主角則是個癡迷“高富帥”的煙花女子,社會閱歷豐富卻頭腦簡單,兩個人的性格缺點注定了愛情的悲劇結局,避開了京劇里司空見慣的臉譜化人物傾向,主人公不再是忠孝節義的道德標準化身,而是觀眾感同身受的真實的人,所以雖然不是《大宅門》電視劇的情節,但展現的是《大宅門》的氣韻。
還有像龍江劇《鮮兒》改編自電視連續劇《闖關東》,錫劇《裝臺》、京劇《青衣》也改編自同名小說,當然也因電視劇的影響而有了一定的傳播范圍。
三、怎樣融匯兩種藝術語言
和兩種表演體系
陳慧迪:我在2008年拍攝了越劇電視劇《何文秀》,電視劇版本跟舞臺版本的表演會有些不同,比如舞動長水袖容易擋鏡頭,導演會提出改動作,一些走動的場景不能復雜化。我們是實景拍攝,攝像機可以近距離拍攝演員一個眼神,有時將手、面部拍成特寫,展現當時人物的心情,這跟舞臺的呈現完全不一樣。
高源:你說到的話題涉及到戲曲本身是舞臺表演,是間離的效果,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觀眾這是假的。但是電視劇講究的是實景表演和拍攝,當戲曲改編電視劇、電視劇改編戲曲出現一些“水土不服”的情況,實際上是沒有解決兩個表演體系的矛盾。
李培:我是一個忠實的越劇本體語言的擁護者。當網絡、電視劇、越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電視劇可以提供鏡頭語言,越劇的語言本身是靈動的,什么是越劇的語言?越劇最擅長的就是表達心理語言,第一種是老一輩的藝術家創作的唱腔,如弦下腔和尺腔是為了感情的宣泄,第二種是表演藝術家塑造劇中人物的創造力。越劇語言可以進入鏡頭語言。演越劇電影《紅樓夢》,王文娟老師講,林黛玉要悄悄地走,悄悄地坐。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中,袁雪芬老師扮演祝英臺梳妝時,她說呂瑞英老師扮演的侍女插釵方式,拍電影和舞臺表演要有所不同。越劇在舞臺上是身體的語言,而鏡頭中可以轉化為表情的語言,鏡頭的切換、蒙太奇剪輯能夠適合越劇符號性的表達。
魏睿:劇種剛誕生時有很通俗的特征,但是隨著時間的增長,隨著文學性的積淀,隨著人們對它的敬重,劇種逐漸被捧為一種高雅的藝術,京劇、昆曲都有這樣的經歷,成為高雅藝術固然很好,融入了傳統文化的精髓。但是另一方面,這會不自覺地形成了某種束縛,繼承者的創作會受到質疑,面臨“是不是姓京、是不是姓昆、是不是姓越”的爭議。我很認可一種觀點,傳統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傳統是一道河流,每個人可以為它注入新的因素,成為一種新傳統。電視劇《甄嬛傳》和《步步驚心》之所以受觀眾喜愛,并不是因為宮斗和穿越,而是因為復雜的人性、異化的悲哀、姐妹之間的感情、絕境中的彼此溫暖,淋漓盡致地傳達給觀眾,才能引起共鳴。因此真正的好作品,既要有通俗性的一面,又要能觸動人最本真的一面。
(文稿整理/魏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