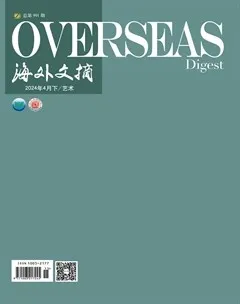關于阿瑟·韋利《詩經》情歌翻譯的思考
阿瑟·韋利對《詩經》的翻譯很特別,在20世紀他出版了1937年版和1996年版兩個版本的《詩經》(The book of songs),皆是對《詩經》的翻譯。他的翻譯經常結合英語詩歌形式反映《詩經》的結構和韻律,比如他使用自由詩歌來展現《詩經》中的節奏。他擅長捕捉《詩經》的情感和主題,特別對情歌進行創造性參與,這來自他對源文本的微妙理解。其《詩經》情歌翻譯通俗易懂又吸引人,同時不犧牲對原文的忠實呈現。其《詩經》翻譯對中國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是理解《詩經》豐富而持久的遺產。本文旨在探討阿瑟·韋利翻譯《詩經》在情歌翻譯方面的特色與成就。
1 阿瑟·韋利翻譯特點及其《詩經》翻譯價值
1.1 阿瑟·韋利翻譯特點
阿瑟·韋利是20世紀一位著名的英國漢學家,他的《詩經》翻譯體現他對原始文本的忠實程度、對文化細微差別的關注和文學品質。韋利翻譯不僅僅是語言上的轉換,而是經過精心創作的,以保持原始作品的詩歌本質和文化背景。具有以下特點。
1.1.1 忠實于原文意象
阿瑟·韋利高度重視原文的意象,他通過注釋的方式來解釋那些對英語讀者來說可能陌生的或需要額外背景知識的意象。例如,在翻譯《詩經》中的“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時,他不僅直譯了文本,而且在注釋中詳細解釋了“椒”象征著愛人的身材以及“椒聊”的含義,這樣既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又避免了文化誤解。
1.1.2 文化平衡處理原則
在處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元素時,韋利采取了一種平衡的策略,既進行了適當的文化轉換,又保留了原文的特色。例如,在翻譯“鳳凰”和“梧桐”這樣的具有特定中國文化象征意義的詞匯時,他選擇了“phoenix”和“dryandra”這樣在英語中能夠引起共鳴的詞匯,同時在注釋中解釋了原文的含義,這樣既保留了原詩的文化底蘊,又使其更容易被英語讀者接受。
1.1.3 注重詩歌的情感表達
阿瑟·韋利的翻譯注重傳達原詩的情感和氛圍,他在翻譯中努力捕捉原詩的情感色彩,并將其轉化為符合英語詩歌的表達方式。在處理《詩經》的“情歌”部分時,他特別強調了情感的表達,使得英譯本不僅傳達了原文的意思,還傳達了原文的情感和韻味。
1.1.4 語言的流暢性與詩性
阿瑟·韋利在翻譯《詩經》時,特別注重語言的流暢性和詩性,他在保留原詩結構和韻律的基礎上AZngSXQMMb9gHfYgOydJO7DYGJBh01au99VK+eniWrI=,進行了適當的調整,以適應英語的表達習慣。這種調整既保留了原詩的形式美,又增強了英譯本的可讀性和藝術性。綜上所述,阿瑟·韋利在翻譯《詩經》時,其翻譯策略是一種深入淺出、尊重源文本同時又兼顧目標語言文化的方法。
1.2 阿瑟·韋利對《詩經》的翻譯價值
阿瑟·韋利的翻譯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其翻譯不僅為《詩經》賦予了新的文化色彩,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跨文化交流和理解《詩經》的視角,使得英語讀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賞《詩經》的詩歌內涵,進而體會中國古代獨特的審美特色。第二,通過分析其《詩經》翻譯特點,可以深入理解翻譯家如何處理《詩經》中出現的意象、象征和情感等內容,這些是詩歌翻譯中的重要方面。第三,其《詩經》翻譯極為重視意象的傳達,他常常巧妙運用英語中類似的比喻和象征手段,力求在英語語境中再現原文的意境和情感,使英語讀者能夠體驗到原詩的美感和深度。
2 英譯《詩經》的興盛
自20世紀前期起,《詩經》在英國的翻譯與研究逐漸興盛起來。英國的漢學家開始紛紛翻譯《詩經》,其中,理雅各對《詩經》的翻譯是英譯的奠基之作。詹寧斯、阿連壁等相繼受到理雅各的影響,紛紛對《詩經》進行翻譯,他們的翻譯以有韻體為主[1]。阿瑟·韋利是繼理雅各之后對《詩經》翻譯影響深遠的一位漢學家。
3 阿瑟·韋利對《詩經》中情歌翻譯是一種創造性叛逆[2]
阿瑟·韋利翻譯《詩經》中的情歌簡單而易懂,意象的使用基本是一一對應,形容詞或副詞的使用新穎而充滿西方文化色彩。這一翻譯過程不僅打破了《詩經》原有的文化界限,還賦予了它新的審美維度。在筆者看來,阿瑟·韋利翻譯中的這一特色,在情歌的翻譯中尤為顯著,使得其《詩經》情歌翻譯成為了一個獨特而引人入勝的研究案例。他對《詩經》中情歌的gGDsZ2PlCd1NrUai82EFFcwDVFx7WScw5sTXesQSddU=翻譯多采用自由的直譯,他的詩多為自由體無韻詩。例如《桃夭》:
Peach-tree
Buxom is the peach-tree;
How its flowers blaze!
Our lady going home
Brings good to family and house.
Buxom is the peach-tree;
How its fruits swells!
Our lady going home
Brings good to family and house.
Buxom is the peach-tree;
How thick its leaves!
Our lady going home
Brings good to the people of her house.[3]
這里阿瑟·韋利用“Buxom”對應原詩中的“夭夭”,他將女性豐滿的身材比作桃樹碩果累累的狀態,這反映了兩種不同文化的世界觀:中國古代文人喜歡觀察和運用自然的特性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情感表達自然而含蓄,而西方人卻比較注重人本身的體態特征,情感表達直接而大膽。雖然此時這種自由的翻譯在詩體上失去了中文中的“韻味”,也和中國古代詩歌的傳情達意有一定差異,但這種中西文化碰撞產生了一種獨特的詩意,同時他將“桃夭”直譯成“peach-tree”是他重視“基本意象”的體現。再如《漢廣》的一段翻譯,他用四個動詞來詮釋“思”字所蘊含的復雜情感,這種簡單意義上的直譯方式,顯然是他努力保持原文韻味和意境的一種嘗試。他不僅僅是在字面上進行轉換,更是在情感層面上尋求共鳴。在阿瑟·韋利的書中,《漢廣》的翻譯之后,他又專門解釋了揚子江(即長江)和漢江的區別。很明顯,他對《漢廣》的翻譯并非僅僅停留在文字表面的簡單對應,而是基于對中國地理、文化的深刻理解之上進行的創造性轉化。雖然這段翻譯中直接運用的文化元素可能并不多,但是他巧妙運用英文的抒情方式,將《詩經》中蘊含的飽滿情感精準地傳達給西方讀者,使得翻譯作品既保持了原文的韻味,又賦予了新的生命力和閱讀體驗。
在《將仲子》的翻譯中,明顯存在一定的民俗文化詮釋,此時他的翻譯創造性更強。具體看一段翻譯:
I beg of you, Chung Tzu,
Do not climb into our homestead,
Do not break the willows we have planted.
Not that I mind about the willows,
But I am afraid of my father and mother.
Chung Tzu I dearly love;
But of what my father and mother say
Indeed I am afraid
I beg of you, Chung Tzu,
Do not climb over our wall,
Do not break the mulberry-trees we have planted.
Not that I mind about the mulberry-trees,
But I am afraid of my brothers.
Chung Tzu I dearly love;
But what my brother say
Indeed I am afraid.[4]
韋利在書中有一段評論很有意思:
This is a song of bridesmaids who suffered the indignity of being left behind when the bride removed to her husband's house. The image of a river dividing and joining again, as a symbol of temporary parting.
If people find a dead deer in the woods, they cover it piously with rush. But there are men who “kill” a gir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seduce her and then fail to “cover up” the damage by marrying her. Such is the burden of the next poem, its last three lines calling up elliptically the scene of seduction.
筆者把他解釋為:韋利認為,這是一首關于女儐相的詩,當女儐相短暫搬到丈夫家時遭受被遺棄的憤慨之歌。河流再次分合的意象,作為暫時分道揚鑣的象征。如果人們在樹林里發現了一只死去的鹿,wNmTZ9sdfzkmV0YLiYPDww==他們就會虔誠地用燈芯草蓋住它。但也有些男人引誘了女孩,卻無法通過和她結婚來“掩蓋”她所遭受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可能會“殺死”一個女孩。這就是下一段詩要表達的內容,它的最后三行隱晦地表達了誘惑女孩的場景。
這里阿瑟·韋利用他的理解介紹了詩中主人公的行為,他認為中國和歐洲一樣,在農村,男子常常在夜晚幽會情人,他提到許多英國民謠和民歌有類似的情景。他用英文I beg of you, Chung Tzu重復表達出原詩中女子欲愛不能、欲罷不忍的矛盾與無奈心理。這里的翻譯運用了中西民俗文化,同時在翻譯中沒有將中國家庭阻礙的根本原因翻譯出來,是他摒除了中國文化中經學義理。
綜合以上例子,筆者認為阿瑟·韋利《詩經》中情歌的翻譯特點可以用“創造性叛逆”來概括,具體創造性表現為使用直譯、保持基本意象、采用無韻自由體、運用民俗學等。 而李玉良在《<詩經>英譯研究》中也提到,他沒以任何形式翻譯《詩序》和經學義理。例如,《關雎》《葛覃》《卷耳》等篇原本都含有美刺的意義,但在他的翻譯中,這些詩歌的主題被單一化為求愛詩和婚姻詩。這是其翻譯《詩經》的叛逆性特點。
阿瑟·韋利翻譯時刪去經學義理的主張,既令筆者感到不解又充滿驚喜。“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種中式詩歌的審美價值,在他的翻譯下似乎以更加純凈和自然的方式體現出來,而“去美刺”的翻譯使得《詩經》的英譯本減少了很多內在的意蘊,也減少了經學中的倫理文化,只是一首單純的情歌。這表明,《詩經》的翻譯還需要后來的漢學家補充和拓展,盡可能完善《詩經》翻譯中的深層文化。將經學義理合理融于英譯中是一個大難題。
4 阿瑟·韋利《詩經》情歌翻譯的貢獻
阿瑟·韋利的情歌翻譯以其崇尚自然的特點而著稱于世,他善于通過意象的保留和中西文化的結合來自由翻譯詩歌,表達中不僅使其翻譯文學性加強,還沒有消減原詩中主要的中國文化意義。他的翻譯簡單易懂,適于在西方大眾中流傳,也易于傳播中國的文學與文化。同時他對《詩經》翻譯去除經學義理的部分體現了他獨特的翻譯風格,這不僅淡化了詩中政治教化的作用,拉近了讀者與詩的距離,同時他在翻譯《詩經》時所遵循的翻譯原則及取得的翻譯成果對以后的漢學家的翻譯有深遠的影響,也為中國學者更好地理解《詩經》提供了寶貴資料。
引用
[1] 李玉良.《<詩經>研究>》[M].濟南:齊魯出版社,2007.
[2] 袁旖鍶.創造性叛逆視角下《詩經》亞瑟·韋利英譯本的個案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14.
[3] Allen, Joseph R : The book of songs.[M]. 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 Edited with additional translations by Joseph R. Alle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6,p8.
[4] Arthur Waley : The book of songs. [M].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Museum Street,1937,p34.
作者簡介:王培勤(1991—),女,內蒙古包頭人,碩士,副教授,就職于北京經濟技術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