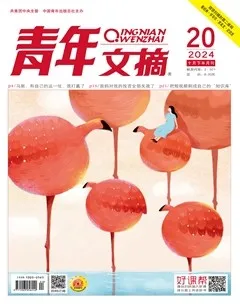意·林
自卑一定是壞事嗎
文/傾墨
自卑一定是壞事嗎?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一書中指出,自卑感及隨之產生的痛苦、焦慮,促使我們強烈地渴望擺脫缺失的狀態,我們通過努力追求一種具有超越性的目標來獲得自卑感的補償。
一種是積極補償。可以充分利用自卑感帶給自己的痛苦,使之成為自身成長的一種滋養,在戰勝自卑的道路上實現超越。在考試失利的灰暗日子里,痛苦與焦慮如影隨形,它們不僅僅是情緒的波動,更是內心深處自卑感的強烈投射。我們開始懷疑,自己的學習能力是否已然消失,自己的智力水平是否足以應對未來的挑戰。但正是這種深刻的自我懷疑,反而成了我們成長的轉折點。它迫使我們停下腳步,深入反思,審視自己的不足,也去尋找內心的力量。如何應對這份痛苦與焦慮,成為一場關于勇氣、自我發現、追求超越的旅程。
而消極補償則走向了反面:面對自卑感帶來的痛苦,采取消極的逃避方式,陷于“自卑情結”不能自拔。考試失利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陷入自我否定和沉淪。
(摘自《課堂內外·少年大學》2024年第8期)
最后轉身的草木
文/馮杰
在秋霜里,最后轉身的草木往往固執、堅韌。
柿葉,在做最后的堅持。我把一枚柿葉夾在書里,當作對整個秋天的懷念,宛如一個被壓縮過的秋天文件。
外祖父曾說柿有“七德”:一壽,二多蔭,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佳實可啖,七落葉肥大可臨書。
在鄉間我就在柿葉上寫過王維的詩。開始時,柿葉上的王維若隱若現,最后王維凝固了,在一枚柿葉上達到了永恒。
它像一個人一樣淡定,一枚葉子,在唐詩里。
(朵朵摘自《畫句子》,河南文藝出版社)
讀風景
文/[英]羅伯特·麥克法倫
我們對風景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也就是說,我們看風景時,看到的并非實際存在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認為存在的東西。
我們賦予風景一些并非它們所固有的特質——比如野蠻、荒涼,又依據這些特質來評價風景。換句話說,我們是在解讀風景,根據自身的經驗和記憶,以及共有的文化記憶來理解它們的形態。詩人威廉·布萊克確切地指出了這一道理,他寫道:“讓某些人喜悅得熱淚盈眶的樹木,在另一些人眼中不過是擋了路的綠色物體。”從歷史上看,山峰也一樣。
(豫之摘自《念念遠山》,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