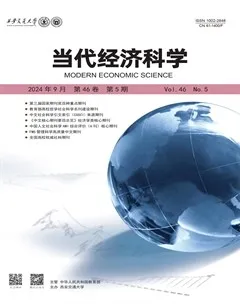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影響研究














摘要:隨著信息科技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推進,數字基礎設施為服務業的效率提升和轉型升級帶來更加突出的影響。基于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實際,驗證了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存在性,并采用2011—2019年中國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證明了數字基礎設施能夠有效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在利用工具變量回歸和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等穩健性檢驗后仍然成立。研究發現,規模經濟效應和結構優化效應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兩個重要渠道,其中生產性服務業的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是實現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受地區制度環境和地理區位等因素影響。在制度環境方面,市場化程度與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高、社會信任水平較高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更有利于促進服務業高效率增長、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在城市規模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于特大和大城市的服務業成本病具有顯著的緩解作用。據此提出政府應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推動服務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關鍵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服務業生產率;鮑莫爾成本病;規模經濟效應;結構優化效應;虛擬集聚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848-2024(05)-0032-15
一、問題提出
近年來,中國邁入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時代。2023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達到68.824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4.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2%①,服務業成為中國第一大產業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根據鮑莫爾富克斯假說②,盡管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通常滯后于制造業,但其穩定的市場需求確保了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持續存在。服務業持續吸納多余勞動力,導致服務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增加。然而,這種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可能會降低經濟增長速度[1],即隨著生產效率較低的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整體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緩,這種現象被稱為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長期滯后于制造業。而服務業生產率增長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服務生產和供給中的同步性與不可存儲性,這會造成規模經濟難以實現[2],以及低端服務占比增高[3],從而降低服務業質量和效率。因此,通過促進服務業生產率相對快速增長,“鮑莫爾成本病”的現象會得到有效改善。
根據現有研究,中國長期存在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本文采用程大中[4]的研究方法,使用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數據測度了2003—2019年中國整體服務業的需求價格彈性,如圖1所示。除2018年外,2003—2019各年份價格彈性絕對值均小于1,且歷年服務業需求價格彈性一直在0.8附近波動,平均值為0.821,說明中國長期以來服務業整體的需求價格彈性較低,這與2001年鮑莫爾提出的“服務業需求價格彈性穩定小于1”的結論相吻合。這表明當前中國服務業滿足“需求價格彈性較低”這一“鮑莫爾成本病”的前提條件。在滿足上述前提條件后,服務業相對于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滯后現象,便構成了“鮑莫爾成本病”產生的根本動因[5]。如圖2所示,2003—2019年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年度增長率呈波動下降趨勢,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年度增長率則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在2014年之后,兩種趨勢愈加明顯,意味著服務業滯后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程度逐漸提高。這表明當前中國服務業滿足“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對滯后”這一“鮑莫爾成本病”的根本動因。
在前提成因和根本動因的驅動下,隨著時間推移,制造業就業份額增長率為負且絕對值不斷增大,服務業就業份額增長率基本為正且絕對值不斷增加。這說明中國服務業已顯現出較為明顯的“鮑莫爾成本病”癥狀。綜合上述中國服務業需求價格彈性持續較低的現狀、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對滯后于制造業的本質特點,以及相關文獻[4-5]的研究結論,可以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確實存在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為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提供了新機遇。消費、投資、技術轉化和生產等多個方面賦能制造和服務業,優化產業結構布局,促進效率提升,為經濟帶來了新增長空間[6]。具體而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打破時間和空間的物理限制,促使服務生產和供給中的同步性與不可存儲性特征轉變為異步性和可存儲性[2],使得服務低成本生產和遠距離貿易成為可能,給服務產品的供需形態、貿易方式帶來顛覆性變化。因此,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和改善為服務業效率提升與轉型升級提供了重要契機,為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奠定了數字信息化基礎[7]。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通過強化規模經濟效應、優化服務業結構來改變中國服務業生產率增長長期滯后的局面。第一,在強化規模經濟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改變服務業生產和供給中的同步性與不可存儲性特征,使得服務業企業可以在使用相同的勞動力和邊際成本趨近于零的條件下服務更多的消費者,擴大全球范圍內潛在用戶規模,形成規模經濟優勢,從而對服務業生產效率產生促進作用。第二,在優化服務業結構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通過降低服務成本[2]、擴大市場潛力[7]、優化資源配置[8]等方式,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程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憑借其大規模、基礎性和普惠性特征,通過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發揮其低邊際成本的優勢,以降低服務的投入和擴散成本的方式吸引大量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進入,從而形成傳統空間集聚。另一方面,隨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數字技術的滲透性逐漸增強,產業發展由傳統空間集聚向以數據和信息實施交換為核心的網絡虛擬集聚新模式轉變[9],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生產性服務業的虛擬集聚提供強大底層技術支撐,實現了數字基礎設施視域下傳統空間集聚與虛擬集聚的協調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通過提高服務業內部“進步部門”占比[7]、促進結構的高端化[10]、推動其向產業鏈高端的延伸[3],提升服務質量與效率,緩解服務業整體發展滯后的局面,從而有效改善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但是,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發展對制度依賴度較高,良好的正式制度環境如市場化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和非正式制度環境如社會信任水平能夠實現服務領域的平等競爭,豐富服務產業內容,改善服務供給質量,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從而促進服務業高效率市場化改革與發展[11]。因此,數字基礎設施發展對服務業生產率增長的作用可能受當地制度環境影響較大。地區市場化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社會信任水平以及城市規模特征均會影響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作用效應。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從“鮑莫爾成本病”本質成因入手,研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如何緩解中國服務業發展過程中的“鮑莫爾成本病”這一現實問題,為服務業效率提升、彌合服務業與制造業效率增長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結合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大規模、基礎性和普惠性特點,從規模經濟效應與結構優化效應兩方面論證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作用機制,進一步厘清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賦能產業升級的路徑;第三,立足服務業對制度環境要求較高的特點,進一步檢驗了市場化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社會信任水平等因素對數字基礎設施賦能服務業的異質性影響,這為優化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普惠性和針對性效應提供了更為精準的證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產生是由于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技術經濟特征存在差異,導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滯后于制造業。作為支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數字基礎設施以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具有大規模、基礎性和普惠性特征[12],能夠有效打破信息、知識、產業和空間界限,從供給、需求和匹配等方面提升服務業生產效率,縮小服務業與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差距。第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提升服務供給質量。首先,在政務服務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數字政府建設,通過分析海量數據推動服務決策過程信息化、科學化,促進政府服務水平提高,提升服務供給效率[7]。其次,對于服務業企業而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服務業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和全鏈條數字化改造構建了重要底座。一方面,企業服務產品供給形態和傳播方式得以發生顛覆性改變,服務生產和供給中的同步性與不可存儲性特征轉變為異步性和可存儲性[2]。另一方面,在重塑服務業供應鏈的過程中,平臺經濟這一新商業模式以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支撐逐漸興起[13],企業圍繞平臺聚集,最大化地利用平臺效應,能夠以較低的交易、協調等成本推動服務供應鏈分工協作、優化服務供給方式。第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拓展服務業消費需求。一方面,數字技術激發服務業線上消費需求。服務業網絡消費方式不斷創新,服務場景逐漸豐富,網絡消費體驗隨之提升。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應用能滿足服務業線下消費新需求。在數字技術的引領下,傳統線下服務消費模式不斷轉型升級,以數字化賦能傳統消費為消費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多樣化消費選擇。第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加速推動服務供需優化并實現有效匹配,有利于服務資源高效配置,最終推動服務業效率顯著提升。而對于制造業企業,雖然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能夠通過促進分工水平、優化生產流程、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推動制造業生產效率提升,但與服務業相比,制造業產出與物質載體一一對應,生產流程和實物產出難以實現完全去物質化、擺脫時間和空間的物理限制,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制造業產品供給形態和傳播方式。因此,相比于制造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作用更為顯著。綜上,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提升服務業供給、需求和匹配效率,彌合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差距,為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提供基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1: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一)規模經濟效應
工業經濟時代,企業所追求的規模經濟,主要通過擴大生產規模以降低長期平均成本,進而實現收益最大化[14],因此制造企業能夠通過廣泛使用機器設備、標準化生產流程獲得規模經濟優勢,但對于具有差異化高、生產經營標準化低等特點的服務業產品而言,服務業企業較難形成規模經濟優勢。而數字經濟時代,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的普惠性特征,其普及與應用使得服務業企業打破時間和空間束縛,形成規模經濟優勢。規模效應的實現有利于服務生產流程、技術資金資源、組織管理實踐等各個要素之間有效匹配[15],促進服務低成本大規模遠距離提供,進而提高服務業生產率。以教育行業為例,相比于傳統課堂,網絡慕課(MOOC)能以較少的教師資源為更多的學生提供教育服務,且教育資源的存儲可以突破時空限制,在不同時間服務不同地域的學生。在數字經濟加持下,線上音樂和視頻等流媒體數字媒介通過互聯網傳播為觀眾提供遠程服務,這些消費新形態同樣擺脫了物理空間的限制,將服務轉化為數字商品,使流程工業化,降低宣傳傳播和運營維護成本,顯著提高服務效率[13]。相比于服務業,制造業雖然可借助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降低生產成本、擴大產出規模,但制造業產出多為有形商品,且制造業產品在使用時具有獨占性[11],大規模生產、遠距離運輸產生的成本可能會降低但無法消除,邊際成本難以趨近零。因此,由于制造業和服務業在產品供給形態、傳播方式等方面具有天然異質性,數字基礎設施發展通過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對服務業和制造業生產率增長存在差異化影響。對于所有可以在網絡空間提供的服務來說,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拓展了其市場范圍,使其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擺脫勞動生產率低的特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2: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強化規模經濟效應,緩解了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二)結構優化效應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能夠通過規模經濟效應縮小服務業與制造業生產率增速差距,還能夠通過促進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發展,實現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從而改善整體服務業經濟發展滯后局面。作為服務業的高端重要組成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的特征,但長期以來仍存在發展水平不高、結構不合理和“低端鎖定”等問題[3],對中國整體服務業生產率增速的貢獻有限。而伴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服務要素的可復制性與可流動性顯著提高,生產性服務業逐漸在地理空間上形成傳統產業集聚區,有助于服務業跨越“生產率門檻”,緩解相關領域的“鮑莫爾成本病”。相較于傳統空間集聚,虛擬集聚具備空間擴展無限性、信息實時共享性、平臺交易便捷性等特點和優勢[16],為生產性服務業傳統集聚空間格局賦予新特征和新機遇。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通過降低服務成本、擴大市場潛力、優化資源配置等方式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第一,降低服務成本。在傳統空間集聚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的地區能夠發揮其低邊際成本的優勢,吸引大量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形成地理空間集聚。在虛擬集聚方面,依托虛擬網絡空間,降低單獨建設成本,促使生產性服務業將更多資源用于虛擬集聚過程中的技術研發和服務創新[11],從而為服務業虛擬集聚提供動力。第二,擴大市場輻射。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弱化市場分割現象,為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搭建數字化平臺、優化信息交流,這有利于增強對外輻射能力,擴大對外服務半徑,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水平。在傳統空間集聚初期的良性競爭可以提高企業收益,但隨著一定空間內經濟主體逼近上限,固定地理集聚區域內競爭壓力不斷增加、資源獲取成本持續上升[9],服務業企業為了獲得本地市場規模優勢而靠近實體市場需求地的集聚動力減弱,逐漸向更具成本比較優勢的地區擴散,形成虛擬集聚。第三,優化資源配置。不同區域的勞動力和資本等資源要素稟賦存在差異,而數字基礎設施通過發揮普惠性作用,彌合區域數字鴻溝,改善區域要素豐裕程度,推動優質資源優化配置,為生產性服務業實現高質量集聚奠定基礎。以勞動要素資源為例,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越發達的地區,生活基礎設施往往越趨于完善[9],越能吸引勞動力空間集聚;另一方面,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能夠提高勞動力信息搜尋效率、降低搜尋崗位的成本并提高其流動性,提升勞動力市場匹配水平,促進勞動力市場不斷成熟[6],高素質勞動力匯集推動了高端服務業企業集聚區的形成。對于技術資源來說,得益于數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內部和產業間的技術交流邊界逐漸模糊[16],知識得以在網絡空間快速廣泛流動,形成技術溢出效應,促進要素資源向虛擬空間集聚,增強生產性服務業核心競爭力。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能夠促進服務業內部結構優化,提高企業專業化分工程度,提升服務業內部“進步部門”的比重,推動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做專做精做強[9]。作為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的大規模集聚有利于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產業鏈高端延伸[3],形成全生命周期的生產服務業價值鏈,提高服務業整體生產率。
綜上,在數字基礎設施的加持下,生產性服務業高效集聚能夠提高服務業整體生產率增速,有效降低服務業中技術進步緩慢的滯后部門占比,從而克服服務業企業“低端鎖定”問題,改善服務業發展水平不高、結構不合理的滯后局面。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說:
假說3: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優化服務業結構,從而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影響,本文設定了如下基本檢驗模型:
(二)變量測度和描述性統計
基于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2011—2019年中國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展開研究,形成了2 592個城市—年份的平衡面板數據。原始數據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所有變量均按照2011年的不變價格指數進行折算,為避免極端值干擾,對所有變量進行了前后1%的縮尾處理。
1.被解釋變量:鮑莫爾成本病(Bau)
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兩種方法測度“鮑莫爾成本病”。第一種方法是采用“技術滯后部門”商品的相對價格[2],但對于醫療保健、教育文化等服務業商品很難使用準確價格進行衡量[5]。第二種方法則是采用“技術滯后部門”工資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的差額[17-18],該方法無需價格信息就能將“鮑莫爾成本病”效應從不可觀測因素中識別出來。因此,本文參考第二種方法,利用城市層面的數據進行“鮑莫爾成本病”的測度。測度公式為:
2.解釋變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Din)
本文自變量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指標選取方面,本文借鑒范合君等[12]的做法,采用熵權法,以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人均電信業務總量、每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城鎮單位從業人員比重、數字中國指數共5項指標來衡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其中,互聯網寬帶是推動地區信息基礎設施發展的必要硬件載體,而信息基礎設施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核心[19]。人均電信業務總量與城市數字基礎設施供應量直接相關[20]。隨著移動電話普及率不斷提升,城市網絡信息化普及程度隨之提高,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奠定了重要網絡技術基礎[21]。此外,數字中國指數來源于騰訊研究院《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19)》。該指數綜合了各城市云計算、大數據儲存與計算能力、移動支付、數字產業、物聯網與數字政務等相關數據,能夠反映城市數字新基礎設施發展水平[22]。因此,上述5項指標涵蓋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新基建的主要方面,能比較準確地衡量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此外,需要說明的是,數字基礎設施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在后文所有回歸中,核心解釋變量作滯后一期處理。
3.機制變量
第一,規模經濟變量。參考馬述忠等[22]的做法,本文以服務業總產值反映總體市場規模(sca),檢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規模的正面影響是否有所強化。
第二,服務業結構優化變量。一是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指標。借鑒韓峰等[10]的衡量方法,本文以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作為衡量服務業結構優化效應的指標之一,城市i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規模PSi可表示為:
二是生產性服務業虛擬集聚指標。生產性服務業虛擬集聚同樣是表征服務業結構優化效應的重要指標。本文所研究的虛擬集聚是各類資源在網絡空間上的集聚,盡管虛擬集聚依托網絡平臺連結生產者和消費者,但對網絡平臺規模的測度存在一定難度,而作為虛擬集聚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線上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平臺規模和數據要素流動狀況[16],因此采用電子商務交易額衡量虛擬集聚。由于缺乏城市層面的細分服務業電子商務交易額數據,借鑒紀玉俊等[16]的思路,由省份層面數據加權到城市層面來測算。具體地,首先參照商務部《中國電子商務報告》的測算方法,采用電子商務采購額與電子商務銷售額之和的平均值計算各省份電子商務交易額,然后將其與各城市國內生產總值(GDP)占所在省份GDP的比重相乘以構造城市層面的電子商務交易額的代理指標。主要原因在于,城市GDP越高,說明其經濟發展水平越高,電子商務發展也相對更迅速[16]。參考張青等[9]的測度方式,采用區位熵方法衡量地區虛擬集聚程度:
4.控制變量
參考龐瑞芝等[5-6]的做法,本文還控制了可能影響城市“鮑莫爾成本病”的控制變量,具體如下:財政分權度(fis),用財政預算內收入比財政預算內支出表示;城市化水平(urb),用人口密度的對數表示;研發強度(rd),以科學技術支出占財政支出比值表示;人力資本水平(edu),采用教育支出與財政支出的比值表示。
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鮑莫爾成本病”的均值為0.043,標準差為0176,最小值為-0.322,最大值為0.413,表明不同城市“鮑莫爾成本病”的程度存在差異。各產業在城市的集聚水平差異較大,生產性服務業多集聚在東南部較發達城市,不同地級市在城市財政分權度、城市化水平、研發強度和人力資本水平等方面同樣存在差異:城市化水平的均值較大,表明目前中國城市化水平處于上升階段;與之相比,研發投入均值較低,這意味著研發投入強度不足,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優化投入結構。從傳統空間集聚指標(PS1、PS2)和虛擬集聚指標(vir)的均值來看,目前中國的服務業集聚水平較低,城市間集聚水平差異明顯且兩極化嚴重,原因在于現階段服務產業的地理集聚仍未跳出傳統空間集聚的發展規律,存在擠出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23],而虛擬集聚的發展存在逐漸加強的趨勢,但集聚效應仍有較大提升空間與潛力。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第(1)(2)列報告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影響“鮑莫爾成本病”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意味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有效緩解了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平均來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服務業成本病顯著降低0.891個單位。這意味著,按目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平均每年0.009個單位的增速,且維持就業份額(Lh/LT,2019年約為0.606)和城市總體實際工資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城市實際人均產值增長率每年平均增長0.481%。由此,假說H1得到驗證,即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此外,觀察控制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可知,財政分權度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財政分權水平過高不利于緩解城市服務業成本;城市化水平的系數和人力資本水平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城市化發展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能夠提高城市制造業和服務業績效,從而提升整個經濟系統的運行效率;研發強度的系數為正且不顯著,意味著研發強度提高在統計意義上還未能明顯緩解服務業成本病,這可能是因為現有研發支出在“精準投入”與“財盡其用”上還有改善空間。
(二)穩健性檢驗
1.控制固定效應
通過設定省份固定效應、省份與年份交互固定效應來控制隨城市和隨時間變化的諸多不可觀測且不可度量的因素,進而緩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能帶來的宏觀系統性環境的變化。單獨控制年份固定效應僅僅考慮了時間維度上的同質性經濟沖擊,但現實中的經濟沖擊將對不同省份中的城市產生異質性影響。為了控制住這些不可觀測的異質性沖擊因素,需要在回歸方程中引入交互固定效應。表2第(3)列結果表明,在考慮了宏觀因素之后,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2.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1)更換城市層面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測度方法。本文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測度方法由熵權法替換為主成分分析法(Dit),回歸結果見表2第(4)列,可以發現,在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鮑莫爾成本病”的結論依然成立。
(2)本文嘗試將城市層面的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多維度省份層面的核心解釋變量進行測度本文選擇將此指標用作穩健性檢驗有兩方面原因。第一,選題角度。要想從根本“祛除”“鮑莫爾成本病”,需要解決滯后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速長期偏低的問題,因此需要時間跨度較長、顆粒度較小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論證。同樣,數字基礎設施以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具備普惠性特征,發揮著促進經濟長期穩步高質量增長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希望借助2011—2019年共計9年的城市層面數據探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否會緩解“鮑莫爾成本病”。第二,數據可得性。關于與“數字”相關的變量,國家官方統計數據主要始于2013年,且基本集中于省份層面,這會導致可用數據較少,樣本顆粒度較大。綜合以上考量,本文選擇與研究內容更貼合、觀測樣本更多的城市層級數據進行基準回歸,將省份層級數據用于穩健性檢驗。。一方面,結合范合君等[12]的研究,并基于數據可得性,本文選取移動電話基站數量、寬帶接入端口數量、網頁數、域名數、IPv4地址數、光纜線路長度、軟件業務收入7個維度的指標數據,通過主成分分析法綜合測度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最終得到2013—2019年中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香港、澳門及臺灣)的相關研究數據。回歸結果見表2第(5)列。Inf的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在使用顆粒度更大的省份層級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后,回歸結果仍和基準結果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本文借鑒鈔小靜等[6]的方法,從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產值核算視角,采用各省份信息技術業分類下的通信及相關設備制造業、計算機及相關設備制造業等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相關行業的上市公司產值來衡量地區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Int)。由于城市層面數據缺失較為嚴重,因此以省份層面為標準進行統計,表2第(6)列的回歸結果表明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依然成立。
3.內生性處理
服務業發展過程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也有可能會進一步促進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建設,即本文基準回歸可能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為此,本文通過尋找合適的工具變量進一步解決內生性問題。借鑒趙奎等[24]的方法,本文嘗試采用份額移動法(shift-share design)構造合適的工具變量解決內生性問題。其基本思想是用分析單元初始的份額構成和總體的增長率來模擬歷年的估計值,該估計值與實際值高度相關,但與其他殘差項無關,滿足了工具變量的要求。本文的自變量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Dini,t0表示在初始t0年(2011年)城市i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Gt表示在t年的全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相對于初始t0年的增長率。一方面,初始年份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未來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核心解釋變量高度相關,符合工具變量的相關性要求;另一方面,初始年份全國層面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會明顯地受到某城市“鮑莫爾成本病”的影響,初始年份全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增長對具體城市“鮑莫爾成本病”而言是相對外生的,滿足外生性要求。因此,Bartik工具變量能夠作為本文的工具變量,解決內生性問題,并得到一致估計。具體地,份額移動法構造的自變量的工具變量IVi,t可以表示為:
五、機制檢驗與異質性分析
(一)影響機制檢驗
1.規模經濟效應
根據本文的理論機制分析,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使服務業企業可以使用相同的勞動力服務更多的消費者,不斷擴大市場用戶規模,進而形成規模經濟優勢。規模效應的出現有利于服務生產流程、技術資金資源、組織管理實踐等各個要素之間有效匹配[2],促進服務低成本大規模遠距離提供,進而提高服務業生產率,有效緩解“鮑莫爾成本病”。規模經濟影響機制的檢驗模型如下:
表4第(1)列展示了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規模經濟的影響。本文參考馬述忠等[22]的做法,選擇服務業總產值這一指標衡量總服務體市場規模,檢驗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規模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提高服務業規模經濟效應。盡管部分服務業產品具有差異化高、生產經營標準化低等特點,但是服務業企業借助信息技術可以突破地理距離限制,節約交易成本和交通成本,形成規模經濟效應[7]。特別是對于數字信息產品而言,其初始成本可能較高,但幾乎可以零成本復制,易形成規模經濟[14]。服務業企業間可以通過規模效應加強技術和資金等資源要素的整合與協調,達到成本最低、利潤最高的最優生產組合,實現提高服務業生產模式效率的目的,從而能改善服務業生產率增長長期滯后于制造業的現狀。
2.服務業結構優化效應
表4第(2)(3)列展示了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的影響,第(4)列展示了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生產性服務業虛擬集聚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均具有顯著促進效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基礎,從而改變了服務的不可分割、不可儲存等傳統特性,使得服務與生產分離成為現實,生產性服務業在數字基礎設施的推動下,通過降低服務成本、擴大市場潛力、優化資源配置等方式大規模集聚,提高服務業內部“進步部門”占比、促進服務業內部結構高端化、推動服務業向產業鏈高端延伸。首先,在企業“自我選擇”機制的影響下,生產效率較高的服務業企業繼續留在市場從事服務商品生產,提升了資源再分配效率[7];其次,專業化集聚有助于企業形成專業化網絡服務生產體系,降低企業間交易成本和進入壁壘,實現規模經濟[10];最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大規模集聚通過吸引關聯性企業進入,強化服務產業前后向聯系,形成循環累積效應,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產業鏈高端延伸,進一步擴大集聚優勢[3]。上述三條路徑有助于更好地推動服務產業結構升級,改善服務業滯后局面,從而有效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二)異質性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通過強化規模經濟和優化服務業結構提高服務業生產效率,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對于正處于轉型發展的中國來說,城市之間的規模、市場化環境等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這種緩解作用可能還會受到經濟環境和地理區位的影響。本文主要從市場化程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正式制度環境、社會信任水平這一非正式制度、城市規模等方面分析數字基礎設施發展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差異化影響。
1.市場化程度
本文以市場化總指數表征城市的市場化程度,數據來源于中國市場化指數數據庫。根據2011—2019年市場化程度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市場化程度高的城市和市場化程度低的城市兩組子樣本。表5第(1)(2)列表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有效緩解了市場化程度較高城市的“鮑莫爾成本病”。第一,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城市,新技術的進入與退出壁壘較低,這有利于服務業企業迅速調整組織結構、管理與決策模式,提高數據等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增強服務業企業應對市場和技術沖擊的能力,強化數字技術提升服務業生產率的效應。第二,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網絡信息平臺的發展。一方面,網絡市場增長逐漸弱化服務市場邊界,激發服務業貿易活力;另一方面,市場范圍擴展和市場規模擴大促使服務業形成規模經濟效應[15],規模經濟效應能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有效匹配,進而提高服務業生產率。因此,市場化水平越高,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生產效率的賦能效果越顯著,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也就越明顯。
2.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本文以地區知識產權綜合發展指數表征城市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指數越大反映該城市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越高。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11—2019年《全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報告》。根據各年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高的城市和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低的城市兩組子樣本。表5第(3)(4)列顯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于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在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更高的城市更具統計以及經濟意義上的顯著性。其原因在于:對于技術更迭慢、研發周期長的服務業企業而言,數字經濟下的侵權行為具有模仿速度快、取證復雜等特性;而知識產權保護的技術公開和權力獨占制度會降低創新技術被模仿的風險,激發企業新服務產品開發和服務創新的動力,最大化企業服務創新帶來的經濟價值。在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低的城市,侵權行為會抑制數字化企業開展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的創新活動,不利于企業服務化轉型。而對于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強的城市來說,服務業企業被侵權的風險降低,更加積極主動推進服務產品多元化發展,使服務業增長潛力得以有效發掘。因此,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越強,數字化發展對服務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
3.社會信任水平
作為溝通交流的重要體現,信任這一非正式制度被認為是決定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重要社會資本[25]。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技術可以通過增強社會信任水平推動服務業企業合作、降低服務成本[26]。因此,社會信任水平的差異會影響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借鑒現有研究,本文使用2000年中國企業家調查數據(CESS)的信任數據,這是目前涉及中國省際地區間信任水平的唯一數據來源[25]。本文根據社會信任水平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社會信任水平高的城市和社會信任水平低的城市兩組子樣本。從表5第(5)(6)列的結果可以看出,相比于社會信任水平較低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在社會信任水平較高城市中更明顯。主要是因為誠信規范、互惠合作的社會軟環境更有利于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經濟系統的有效運行[26]。在社會信任水平提高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互聯互通更容易構建服務業企業間網絡聯系,異地企業溝通交流更加順暢,交易過程中的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得到緩解,交易成本和監督成本大幅降低,這使得市場網絡交易關系更加穩固。因此,在社會信任水平較高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更有助于提升服務業生產效率,從而進一步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規模擴張產生的集聚效應、資源配置效應和競爭效應會造成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出現差異[27-28]。本文結合國務院2014年印發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中的城市規模等級劃分標準,將樣本合并整理后分為三個等級:超大和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和小城市,分組檢驗的回歸結果見表6第(1)~(3)列。從第(1)(2)列結果可以看出,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效應在超大、特大和大城市中較為顯著。可能原因在于:城市規模擴大吸引各類企業進入,集聚優質資源,有利于促進上下游關聯的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同時實現集聚經濟[27],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加快了各種信息、知識產品在城市關聯產業間的交流,從而提高城市產業生產效率。第(3)列結果表明,在中等和小城市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暫未顯現。這可能是因為中等和小城市缺乏數字技術人才、所需投入的資金和資源不足、服務產業相對傳統,這會導致數字基礎設施難以對服務業企業生產和消費提供直接技術支撐,尚未渡過數字轉型升級的“陣痛期”,難以形成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規模經濟和整個城市的集聚效益,使中小城市服務業企業無法擺脫生產低效率[28]。因此,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城市規模差異會對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作用產生影響,其中這種緩解作用在大城市中更為顯著。
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激發了服務業增長新動能,賦予服務業新的發展契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服務業時代是低增長時代”這一規律。本文采用2011—2019年中國28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重點分析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影響,并檢驗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強化規模經濟效應、優化服務業結構這兩條機制。研究結果發現: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有顯著的緩解作用;規模經濟效應和服務業結構優化效應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重要機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具有異質性,在市場化程度越高、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越強、社會信任水平越高、規模越大的城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服務業“鮑莫爾成本病”的緩解作用越明顯。本文的研究結論具有以下政策啟示:
第一,在數字基礎設施能改善服務業生產效率、驅動服務業轉型升級的現實背景下,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發揮數字網絡技術的普惠性特征。一方面,加快5G、千兆光纖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核心技術攻關,提升數字惠民水平、推進服務普惠均等;另一方面,重視傳統數字基礎設施改造升級,積極促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服務產業的融合發展,為提供優質高效的信息產品與服務奠定基礎,為整體產業效率的提升賦能。
79ca7e1ed9e33462e439f1fd07bbe4b5第二,利用數字新基建推動服務業獲得規模經濟優勢實現服務業產業結構的升級。由于任何專業化的生產和服務都需要有廣闊的市場才能獲得規模經濟,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有助于放大服務需求量和服務需求結構的多樣化,助推服務貿易量擴大和貿易模式多樣化。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優勢改變服務業可貿易程度較低的特點,做大服務市場,以此降低服務業的成本,提高服務業效率。
第三,完善地區數字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空間集聚和虛擬集聚,形成數字新基建視域下空間集聚與虛擬集聚功能互補、協同促進的新格局。一方面,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深度協作融合、與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合作聯盟,促進生產性服務業集群式發展,助力生產性服務業邁向高端,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實現服務業高質79ca7e1ed9e33462e439f1fd07bbe4b5量發展;另一方面,做大做強虛擬集聚,合理引導虛擬集聚有序發展,促進高端數據要素資源向虛擬空間集聚,形成地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相互協調的數字經濟發展格局,從而增強生產性服務業核心競爭力,拓寬服務業貿易邊界,賦能服務業高質量發展。
第四,從政府角度來看,應通過加快體制機制改革,為服務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一是提高市場化水平。通過打破市場封鎖和地方保護主義,消除服務業要素流動的體制性障礙,加快形成區域服務業經濟一體化市場,有利于服務業高質量發展。二是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能夠促進服務產品的多元化發展,從而推動服務業規模擴張、領域創新。三是提高社會信任水平。信息化時代容易產生數據安全等問題,誠信規范、互惠合作的社會軟環境更有利于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經濟系統的有效運行。四是實施動態化、差異化的數字技術發展戰略。由于數字技術的應用對不同地區服務業發展產生的積極影響具有差異性,因此需要加大對西北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技術、人才、資金等資源的傾斜,彌補西北地區在服務業發展基礎方面的劣勢,加快彌合數字鴻溝,進而推動西北地區服務業增長。五是實現數字基礎設施的普惠式發展,特別是中小城市應該有序推動人口和產業集聚,增加數字基礎設施供給,提高地區數字化可接入性,發揮數字信息技術帶來的外部溢出效應,降低中等和小城市陷入“數字化陷阱”的風險。
參考文獻:
[1]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3): 415-426.
[2]江小涓,羅立彬. 網絡時代的服務全球化:新引擎、加速度和大國競爭力[J]. 中國社會科學,2019(2):68-91.
[3]惠煒,韓先鋒.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促進了地區勞動生產率嗎?[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6(10):37-56.
[4]程大中. 中國服務業增長的特點、原因及影響:鮑莫爾-富克斯假說及其經驗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4(3):18-32.
[5]龐瑞芝,李帥娜. 數字經濟下的“服務業成本病”:中國的演繹邏輯[J]. 財貿研究,2022(1):1-13.
[6]鈔小靜,薛志欣,孫藝鳴. 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如何影響對外貿易升級:來自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經驗證據[J]. 經濟科學,2020(3):46-59.
[7]余東華,信婧. 信息技術擴散、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J]. 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12):63-76.
[8]曾藝,韓峰,劉俊峰.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提升城市經濟增長質量了嗎?[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5):83-100.
[9]張青, 茹少峰. 新型數字基礎設施促進現代服務業虛擬集聚的路徑研究[J]. 經濟問題探索, 2021(7): 123-135.
[10]韓峰,陽立高.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如何影響制造業結構升級:一個集聚經濟與熊彼特內生增長理論的綜合框架[J]. 管理世界,2020(2):72-94.
[11]王如玉, 梁琦, 李廣乾. 虛擬集聚: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空間組織新形態[J]. 管理世界, 2018(2): 13-21.
[12]范合君,吳婷. 新型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化能力與全要素生產率[J]. 經濟與管理研究,2022(1):3-22.
[13]李勇堅,夏杰長. 數字經濟背景下超級平臺雙輪壟斷的潛在風險與防范策略[J]. 改革,2020(8):58-67.
[14]裴長洪,倪江飛,李越. 數字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 財貿經濟,2018(9):5-22.
[15]紀玉俊,韋晨怡.數字經濟對我國服務業集聚空間格局的重塑:基于區域與行業異質性的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1):51-64.
[16]紀玉俊, 牛亞新. 數字經濟影響下的制造業集聚:新機制與新證據[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18): 137-147.
[17]HARTWIG J. What drives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Baumol’s model of “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8, 27(3):603-623.
[18]COLOMBIER C. Drivers of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does Baumol’s cost disease loom large?[R]. Finanz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institut an der Universitt zu Kln (FiFo Kln) Discussion Papers, 2012.
[19]張杰,白鎧瑞,畢鈺. 互聯網基礎設施、創新驅動與中國區域不平衡:從宏觀到微觀的證據鏈[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3(1):46-65.
[20]沈坤榮,林劍威,傅元海. 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信息可得性與企業創新邊界[J]. 中國工業經濟,2023(1):57-75.
[21]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 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J]. 經濟研究,2019(8):71-86.
[22]馬述忠,房超. 跨境電商與中國出口新增長:基于信息成本和規模經濟的雙重視角[J].經濟研究,2019(6):159-176.
[23]趙放, 李文婷, 馬婉瑩. 數字經濟視域下地理集聚與虛擬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關系[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24(1): 117-132.
[24]趙奎,后青松,李巍. 省會城市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基于工業企業數據的分析[J]. 經濟研究,2021(3):150-166.
[25]張維迎,柯榮住. 信任及其解釋:來自中國的跨省調查分析[J]. 經濟研究,2002(10):59-70.
[26]余典范,楊翹楚,陳磊. 互聯網聯系對地區間貿易成本的非對稱影響[J]. 財貿經濟,2022(8):150-167.
[27]柯善咨,趙曜. 產業結構、城市規模與中國城市生產率[J]. 經濟研究,2014(4):76-88.
[28]郭曉丹,張軍,吳利學. 城市規模、生產率優勢與資源配置[J]. 管理世界,2019(4):77-89.
編輯:鄭雅妮,高原Vol. 46No. 5Sep. 202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Baumol’s Cost Diseas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YANG Qiaochu YU Dianfan
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Summary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dominated by the service economy.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Baumol-Fox hypothesis,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service sector lags behind tha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ha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shift of labor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ervice-sector employment.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the service sector may slow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 phenomenon known as “Baumol’s cost diseas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ffers potential to mitigate these effects by enhancing both the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rough improvements i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optimiz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efficiency, and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economic growth.This article uses data from 28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19 to examine ho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can alleviate Baumol’s cost disease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Through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check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effectively counter this economic challenge.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re the key channels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itigat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Baumol’s cost disease. Specifically, both tradition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virtual agglomeration in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contribute to optimizing the service industry’s internal structure.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allevi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varies according to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cit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greater social trus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service-sector growth and mitigating Baumol’s cost disease. Additionally,large and very large cities have benefited more significantly from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howing marked improvements in service-sector efficiency.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main ways. First, it addresses a critical practical issue by investigating ho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an alleviate Baumol’s cost disease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providing new insights into improving service-sector efficiency and narrowing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Second, it highlights the dual role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this process, offering a clear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an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Finall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factors such as marketiz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social tru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ector development, providing evidence for more inclusive and targete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olicies.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offer valuable guidance for policymakers seeking to overcome Baumol’s cost disease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Keywords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ductivit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Baumol’s cost disease; economies of scal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virtual agglom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