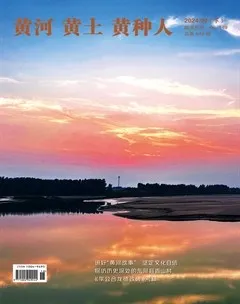《李公合龍德政碑》考釋


清同治七年(1868年)夏月,黃河巨浪自胡家屯涌至滎澤汛十堡(今鄭州市惠濟區馮莊村東),其勢洶涌,撼動天地。同治皇帝聞訊,特頒諭旨,令河南巡撫李鶴年與河督蘇廷魁共謀堵復之策。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西壩開工堵復,十一月四日東壩開工,至次年正月十五掛纜合龍,正月十八日閉氣。后世留有兩碑,一乃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為頌蘇廷魁之功德所立之《滎澤大工紀功碑》(現僅存拓本);另一石碑則是同治八年十月的《李公合龍德政碑》,乃鄭州京水沿堤百姓為歌頌河南巡撫李鶴年滎澤堵口之德政而立。
《李公合龍德政碑》原立于花園口將軍廟中,后經戰亂,將軍廟損毀,唯遺此碑。后在 1980年花園口涵閘改建時被發掘,存放于惠金黃河河務局防汛倉庫內,現陳設于惠金黃河河務局惠金黃河記憶展覽館院內。碑身高 211 厘米、寬 64厘米、厚 18厘米,碑額高 63厘米、寬66厘米、厚 19.5厘米,為對稱雙負屃云水紋,雕刻精美,中間題記方形。碑正面四周飾刻回龍紋圖案,中間豎行陰刻碑文,共計 15行,467字,殘缺10字,缺字以□標識。
《李公合龍德政碑》碑文
恭頌
欽加頭品頂戴河南巡撫部院兼提督軍門李大人 [1]合龍德政碑
中邦[ 2 ]為瀕河之州,撫臨斯土者,當春汛方漲,無不修陂障而嚴堤防。懿維撫提部院李大人蒞任以來,善政策不勝書 [3] 。奮戈南向,而群丑悉伏;旋旗北征,而逆徒盡滅。誠一方之保障,合四境所共為依賴者也。自去歲秋初,黃流飄蕩,由鄭滎 [4 ] 波及東南,郡邑各被其患。公具奏入告,圣天子 [5] 知人善任,即敕撫臣與共事僚屬協力辦理。故公于興工之先,舉凡兵民之統管,料材之轉輸,堤形與河流之長短深淺,無不事先預計 。 用財當何至于濫費,任人宜不得以曠功,以故縛埽負石, 木運土,無不踴躍直前,三逾月而告 焉。驚湍止為安 , 決居然順軌。仍于下流被浸之地,復令守令查明經理。其上計國事,下體民心, 平日撫蒞之善政, 如出一轍也。昔富鄭公 以青州察災,韓魏公 [6] [7]以廣惠勸耕,古大臣之經國,大抵類然。況以公封疆之內,有不動慈衷之軫念者乎?因想公自奉詔由汴[ 8 ]及滎[ 9 ],往復三百余里,皇皇焉不憚跋涉之瘁。然以視昔者,剿辦之日,內運機樞,外總軍務,其勞逸為何如也。迄今金堤永固,波浪不驚,遐邇翹首,咸思歌功而頌德。然此足以見公之治,而不足以盡公之治也。公之治跡,即連篇累牘,亦難悉數矣,豈紀頌之片言,所能罄其萬一哉?
鄭州北,京水寨 [1 0 ] 沿堤紳民叩。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陽月 上浣 [11] [12] ,榖旦。
注釋
[1]李大人:李鶴年(1827—1890),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清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六,由湖北巡撫調任河南巡撫。
[2]中邦:地名,代指河南。
[3]善政策不勝書:意為好事太多了,寫都寫不過來。
[4]鄭滎:地名,鄭州、滎澤兩地。
[5]圣天子:尊稱,此處指愛新覺羅·載淳(1856—1875),同治皇帝。
[6]富鄭公:富弼(1004—1083),北宋名相,封鄭國公。宋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決口,富弼時任青州知州,開倉賑災,安頓流民。
[7]韓魏公:韓琦(1008—1075),北宋名相,封魏國公。宋嘉祐二年(1057年),韓琦時任樞密使,奏請設置“天下廣惠倉”,實行均田。
[8]汴:地名,開封府。
[9]滎:地名,滎澤縣。
[10]京水寨:地名,鄭州直隸州京水寨,今鄭州市惠濟區花園口鎮京水村。
[11]陽月:農歷十月。
[12]上浣:上旬。
碑文所載
馮莊漫決事件始末
黃河在夏商周三代以前,自孟津奔騰過洛汭,直至大伾,一路東北直撲入海,那時的滎地尚未受到其害。到了明代萬歷年間,黃河從孟津、鞏、溫、汜水、河陰等地一路咆哮,抵達滎澤,給鄭州北郊帶來了無盡的災厄。
據張鵬翮所著《河防志略》記載,現今的鄭州段黃河堤始建于清康熙年間。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三十八年(1699年),人們不辭辛勞地創筑了從舊滎澤縣治(今鄭州市惠濟區單東村北一帶)至中牟楊橋全長 28.5千米的臨黃大堤。清雍正四年(1726年)更是向西續接筑至今鄭州市惠濟區西牛莊,彼時為土工秸料。
在清代,鄭州地區的黃河堤防由豫河營防守,該營隸屬管河兵備道管轄,其上還有河東河道總督。豫河營以下設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分防外委等職,統領步戰兵、守兵千余人。治黃的行政機構則是南河廳,亦屬管河兵備道管轄。乾嘉以后,河南全省黃河南岸增至上南、中南、下南、蘭儀、儀睢、睢寧、商虞、歸河 8廳,豫河營也相應分廳設營。滎澤、鄭州、陽武、中牟 4縣黃河南岸的防汛由上南廳和上南營負責,上南廳設同知1人,守備 1人;滎澤縣堤工長 6.177千米,設管河縣丞 1人,夫堡 12座、鄉夫23人;滎澤汛設分防 1人、兵堡 3座、汛兵 15人、丁 7人, 形成了嚴密的治河體系。
清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黃河頂沖胡家屯(今鄭州市惠濟區核桃園村東),此處壩埽毗連,防守得力,安然無虞。二十四日,大溜忽上堤至滎澤汛十堡,此處大堤久不著河,多年失修,因而舊工淤閉,堤身平矮,現如今驟然著溜,以致無工可守,使得河水坐彎淘刷,停積不消,堤根水位抬高數尺,幾與堤平。雖經河工集料下埽,拋石幫戧,但終因物料不濟,搶險無力,二十八日,邊溜旁趨漫溢成口。漫溢之水由李西河、常莊、東趙、青寨、大廟、京水而東,又經中牟、祥符、陳留、杞縣、尉氏、扶溝瀉注入淮。
同治帝在其上諭中,措辭嚴厲地明確了事故責任,大意為:在工地上負責防護的官員們疏忽大意,罪責難逃。南同知鄒梁,因辦理不善,隨堤落水喪命,已無法挽回。然而,對于其余在任的官員,如署河督所請的廳員等,僅僅革職議處,朕覺得處罰過輕。
特別是署上南守備王麟、滎澤汛縣丞龔國琨、署滎鄭汛把總朱永和,他們均被即刻革職,枷號河干,以此警示世人。開歸道紹 ,也被摘去頂戴,交部依例懲處。蘇廷魁,作為督辦河防的專責人員,未能事先預防,亦難辭其咎,朕決定摘去他的頂戴,革職留任,責令他戴罪立功,監督在工各員迅速堵筑決口,一刻不得延誤。足可見此次決口災難之大,清廷上下之重視。
為堵決口,滎澤設堵口工程局,計劃用銀 90萬兩。八月上旬戶部撥發庫銀 40萬兩,其余御準由兩淮鹽厘銀、閩海關洋稅及河南本年漕銀委解。在動工之前,李鶴年將一切計劃得周詳無遺。他統籌管理兵民,轉運材料,親自考察堤壩及河流的走勢、深淺。同時,他精打細算,任人唯賢,絕不讓人有空子可鉆。在李鶴年的有力主持下,方法得當、眾人一心,克服口門收窄、水位抬高、蟄塌不斷等施工不利影響,僅用 3個多月,便完成堵口。但是此處臨背高懸差 1.2米,背河潭坑水深 1米,堵后 3年還常出險。后滎澤汛兵增添至 30人、堡夫 24人,但仍然迭生巨險。據了解,20世紀50年代初,鄭郊沿堤背河尚有鐵牛大王廟(即滎工)潭坑、花園口潭坑、石橋潭坑,常年積水,沼澤一片,農田堿化,五谷不成。
新中國成立以來,這里先后經歷了放淤固堤、標準化堤防建設。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到鄭州視察黃河,在這里發出了“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偉大號召。如今,這里已經成為糧豐林茂、人水和諧的如畫盛景,游人絡繹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