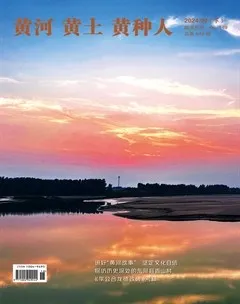明代青花瓷器外銷簡析

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已開始了海上對外貿易,南北朝時期已有瓷器外銷到朝鮮半島。青花瓷是中國傳統的名瓷,本文根據歷史社會背景對明代外銷青花瓷貿易進行梳理,結合國內考古發現,特別是香港竹篙灣遺址、廣東花碗平上川島遺址,及國外墓葬、窖藏和沉船考古發現,從多個角度闡述明代外銷青花瓷的情況。伴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無論是貿易目的地還是中轉地帶,其顯示的不僅是青花瓷單個瓷器品種的經濟交往,更是多個文化、文明交流的碰撞。
歷代海上對外交流
中國自古以來雖是一個以農業文明為主導的國家,但有著 18萬多千米的海岸線,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沿海地區的發展和貿易都很關注。最早開始嘗試開發海洋的地方政權是秦漢時期位于嶺南地區的南越國。20世紀 70年代,廣州象崗山發掘的南越王趙昧的陵墓,其墓中出土有越南東山文化的青銅提梁桶、非洲象牙、阿拉伯乳香、波斯銀盒,這些具有外來文化因素的出土文物,證明當時南越國與印度半島、阿拉伯地區、波斯灣地區有一定的經濟往來。
《漢書·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記載了54daa72fc5c6ba5e35fa96ef663719a7從今天廣東省、海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地出發前往海上諸國所需時日,各國進獻物品及風土人情。
東吳時期,西方的玻璃及制造技術傳入中國,《南州異物志》有記載相關的玻璃制造技藝。20世紀 50年代,湖北五里墩西晉墓出土的一些玻璃碎片,考古學家王仲殊認為應該是東吳時期從海路傳入長江流域的。
東晉時期,高僧法顯在《法顯傳》中詳細記載了他從斯里蘭卡回國時在外國商船上的所見所聞。 法顯的旅程為我們提供了關于當時中亞、印度等地區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等社會、經濟的寶貴信息。《法顯傳》是中國和印度之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也是中國古代關于中亞、印度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朝時期,對外交流貿易達到一個新的高峰,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中西方之間的交流不斷深入,長沙窯的執壺在西亞等地區出現了定制瓷款。
宋元時期,統治階級很重視對外貿易,在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泉州開設市舶司。宋皇室南遷后,導致大量北方地區處于金人的統治之下,為增加財政收入,宋代大力發展手工業,大幅度開放對外貿易。元代大一統后,也大力推行對外貿易,元代后期更是大規模開放私人的對外貿易。《諸藩志》《島夷略志》中有記載宋元時期與東南亞等國的貿易交換情況。
明代青花瓷器貿易
明洪武二年(1369年),景德鎮建立御窯廠,國家的大力投入使得景德鎮迅速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明朝初年,頒布了“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嚴禁百姓從事海外貿易,唯一合法的貿易方式是“朝貢貿易”,進行有時間、地點規定的官方貿易。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將朝貢貿易推向了頂峰,在沿途的滿剌加(今馬六甲)、印尼的蘇門答臘、孟加拉的吉大港、印度的古里(今科澤科德)和波斯灣沿岸的忽魯謨斯島(今伊朗霍爾木茲島)設置了“官廠”。
明朝時期,對朝貢貿易的原則是“厚往薄來”,往往以多于數倍的貨物與朝貢國進行貿易往來,以此來彰顯明代的國力和樹立國威。但隨著鄭和下西洋的結束,這樣的官方貿易也隨之土崩瓦解。然而國際市場對瓷器,特別是伊斯蘭國家君主對青花瓷的需求熱度依舊不減,自明代中期起,民間走私貿易逐漸興起。弘治年間,非洲好望角和美洲新大陸的一系列地理大發現,標志著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與此同時,景德鎮瓷器在歐洲逐漸形成消費市場,但這一時期景德鎮因為宦官壓榨百姓等造成御窯廠的多次停燒。《明史·食貨志》記載:“自弘治以來,燒造未完者三十余萬器。”可見停燒、減燒規模之大。在這一時期,東南沿海地區民間商團積極促使景德鎮瓷器外銷,甚至直接參與瓷器的設計,出現了許多定制燒造的青花瓷,如大扁壺、筆盒、抱月瓶、臥足碗、執壺等。“成、弘之際 ,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素以航海通番為生 ,其間豪右之家,往往藏匿無賴,私造巨舟,接濟器食,相倚為利”,從文獻中可知當時民間走私貿易的繁盛景象。
伴隨著地理大發現,人類開始進入大航海時代,歐洲與中國在海上直接建立貿易關系。葡萄牙、荷蘭及阿拉伯海商與中國不僅有著各種文化上的友好交流,同時還伴隨著沖突的產生。景德鎮外銷瓷器從東南沿海地區遠銷泛印度洋海域,通過歐洲船隊出現在歐洲上層階級的生活中。
明代晚期,一種新型外銷瓷器樣式克拉克瓷的出現,使得明代青花瓷器到達一個新的高峰。雖然學術界對克拉克瓷的定義存在著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克拉克瓷是伴隨葡萄牙、荷蘭等西方外貿而誕生的一種形式的瓷器。克拉克瓷器型主要是以盤、碗為主,有少量的瓶、壺等,紋飾主要有宗教類、人物、山水、花鳥,但畫面布局是在開光的框格之間用花卉樹枝作為分隔,此方式起源于歐洲,在歐洲一些國家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那里都有克拉克青花瓷器的實物收藏。
從考古資料看明代對外貿易
明代對外貿易的合法方式是朝貢貿易,同時史料和考古資料也證實了明代還存在大規模的民間走私貿易。廣州的提舉市舶司太監韋眷墓出土 3枚銀幣,據考古學家夏鼐考證,其中 1枚銀幣是威尼斯銀幣,另外 2枚是孟加拉銀幣。結合《明史》中對其身份和事跡的記載,“眷為廣東市舶太監,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可知在成華年間,提舉市舶司太監韋眷在廣州與中外商人勾結,營私舞弊,隨意侵尅外商,這 3枚銀幣可能是韋眷侵尅外商所得,也可以看出,當時威尼斯商人、阿拉伯海商和中國商人之間,在以間接接力的方式進行著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東南沿海的大規模走私始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私商貿易的興盛,促使出現了相對固定的私商港口碼頭,位于香港的竹篙灣遺址便是一例。竹篙灣遺址發現了大量的青花瓷殘片,經后期整理拼對,復原了 500余件青花瓷,器型以碗、盤為主,還有少量的杯、罐、器蓋等物品。出土的青花瓷器物外腹部、內底裝飾人物、龍鳳、山水、花草、獅子等圖案,大部分器物屬于明代中期民窯青花瓷,少數是檔次較高的成化窯青花瓷。
在廣東臺山上川島花碗平遺址發現了大量與葡萄牙人貿易往來的遺留,物品以青花瓷片和青花紅綠彩瓷片為主,器型仍以碗、盤為主,另有少量的瓶、杯、罐等。青花瓷片主要飾有十字交叉錦地紋、花卉紋和動物紋等。紅綠彩瓷片則多飾瓔珞紋、人物紋和花卉紋等,但多有菱形開光。青花瓷片上還裝飾有“長命富貴”“天下太平”“壽”等吉語,或“卐”“圣十字”等內容。根據學者推測,該遺址的年代應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間。
國內沉船大多集中在福建、廣東的沿海地帶,如廣東汕頭的“南澳Ⅰ號”、福建平潭九粱明代沉船、平潭牛屎礁明代沉船等。新發現的明代中期的南海西北陸坡的一號、二號沉船遺址,出土有青花瓷、紅綠彩、琺華彩瓷,還有搭載的原木,這些都可以反映出明代對外貿易情況。
國外的考古發現多數集中在東南亞、西亞和非洲地區的墓葬或沉船遺址,根據各個時代的宮殿收藏,可以更加直觀地說明明代的外銷情況。
1958年,菲律賓國家博物館在美國學者羅伯特·福克斯等人指導下,對菲律賓八打雁省的卡拉塔甘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共發掘500多座墓葬,出土青花瓷近 300件。菲律賓的馬尼拉圣安娜墓地 15座墓葬中出土的也有明代青花瓷。1948—1967年,馬來西亞多次在沙撈越地區開展考古工作,在發掘的15處遺址中,發現有約 16世紀早期的青花瓷。在文萊的盧穆特河流域和哥打巴圖遺址也發現了大量 16—17世紀的青花瓷。
在西亞地區,土耳其托普卡比宮收藏的元明清時期的青花瓷,數量豐富,器型精美,包含元明清時期外銷瓷的典型器型,如盤、壺、瓶、碗等。阿聯酋哈依馬角市政府聯合英國考古隊在佐爾法·努杜德港口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一批從南宋延續至明晚期的瓷片,其中包含了明弘治年間的青花瓷片。在東非,英國學者詹姆斯·柯克曼在肯尼亞等地開展考古工作,在格迪古城遺址出土有 16世紀的青花瓷;在蒙巴薩耶堡遺址出土有17世紀前的青花瓷;2010年,北京大學對格迪古城出土瓷器進行調研,發現了明中晚期的景德鎮青花瓷。在北非,20世紀 20年代至 80年代,來自英國和日本的學者分別對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進行發掘調查和研究,1998年,日本學者長谷部樂爾率領出光美術館、中近東文化交流中心對該遺址進行調查發掘,發現有15—17世紀的景德鎮青花瓷。
國外沉船遺址也多發現于東南亞、非洲沿海地區,沉船遺址數量較多,現列舉一些較為重要的沉船發現。東南亞海域的越南會安號、圣克魯茲號、圣迭戈號、潘達南號,馬來西亞皇家南海號,泰國西昌島Ⅲ號沉船等,非洲海域的南非圣本托號、幾內亞灣毛里求斯號等。國外海域沉船遺址的發現,不僅豐富了各類青花瓷器的資料,還對進一步研究明代海上貿易的發展狀況提供了翔實資料。
綜合各個時期的資料,我們可了解到,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就已經開始了海上的對外貿易,南北朝時期,已有瓷器外銷到朝鮮半島。唐代,對外瓷器貿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開展對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大大增加,從東亞、東南亞,遠到東非和北非沿岸,都能看到中國與各個國家的貿易商品。宋元時期,隨著造船技術的成熟,統治階級對開展海外貿易持積極態度,各類手工業得到發展,從各個方面促進了該時期的對外貿易,自由貿易市場空前繁榮。明初實行“海禁”政策,規定對外貿易的唯一合法途徑是朝貢貿易,這在很大程度上打壓了宋元時期的自由貿易市場,但海外市場需求量并沒有因此而減小,無形之中促進了民間走私貿易。尤其是近年來沿海地區及國外水下考古的不斷發現,使得我們對中國古代對外貿易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對外貿易不僅是經濟上的貿易往來,更是中外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并非為一國或單一人群所控制,而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相互協作發展的結果。
(作者單位 北京聯合大學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