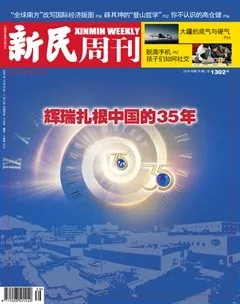有一個村子叫大鄭家

專欄作家
英倫新居民
朋友從上海來倫敦,捎來了老爸鄭重的新著《九十自述:我就是個鄉(xiāng)下人》。雖說是“自述”,但書中的主角是我們的老家大鄭村,一個偏遠(yuǎn)的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普通鄉(xiāng)村。老爸在前言中寫道:“1950年,我小學(xué)畢業(yè)后即負(fù)篋求學(xué),至今已經(jīng)七十年了,我也到得米望茶 之年,垂垂老矣。讀了幾本名家回憶錄以作消遣,那些大都是八十歲以后的晚年之作。我想,人到了晚年,才能品評青少年時代諸事的滋味。”
這部書的初稿開始于2009年。那年12月,父母前往南非探親,在約堡開普敦住了近三個月。閑暇時間多,孩子們總是問他們小時候如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那些時日,老爸除了每天記日記,也開始寫童年回憶。他在2010年2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翻閱寫的童年記憶,是如海瑤說的有粉紅色,只有歡樂,沒有苦難。其 實我寫了鄰居的挨餓、逃難,可能落筆簡單,沒有給她留下印象,我的童年的 確是在家庭溫馨中度過的,特別是門口荷塘,給我留下的是美的印象。現(xiàn)在 還很留戀它,可惜已經(jīng)干涸,完全消失了。 日前,要把它復(fù)印下來,因為是寫在豆豆寫毛筆的廢紙上,后面毛筆的 墨跡也復(fù)印出來,看不清楚,復(fù)印也無用了。只復(fù)印‘南非探親記’。”
兩年前的6月,《九十自述》精美插圖的作者筱江把這部童年回憶的打字稿發(fā)給了我,內(nèi)容豐富多了。我轉(zhuǎn)發(fā)給了哥哥海歌。因為父母兩地分居,我和哥哥從小就在老家跟著爺爺奶奶長大,所以,對老家的感情都非常之深。我倆贊嘆老爸記憶之好,我們的童年印象也被喚起了:麥稈扎成的草人掃天婆,掛在屋檐下,在雨中左右擺動;拉著掃把的叫魂聲,我們發(fā)燒生病時,衣服也這樣被搭在掃帚上,奶奶拉著滿村逛悠喊著我們的名字;小時候過年時才能吃到的山芋糖,糖稀裝在瓦罐里,可以用筷子插進(jìn)去攪一大坨出來,還有硬邦邦的糖瓜,用秤砣一敲就碎,哥哥也是進(jìn)門拿一塊,出門又拿一塊;正月十五蒸的面燈,蘆花編的毛甕 ,用黑黏土來摔響炮,鳳仙花染出的紅指甲……..還有各種風(fēng)物:關(guān)老陵、土地廟、砂礓地 、土簍褲子、各種石器工具……各類農(nóng)活:耕田犁地、收麥、打場脫粒、揚(yáng)場,推磨成面,舂米,苧麻剝皮搓繩,紡線織布…….
朋友從上海來倫敦,捎來了老爸鄭重的新著《九十自述:我就是個鄉(xiāng)下人》。雖說是“自述”,但書中的主角是我們的老家大鄭村,一個偏遠(yuǎn)的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普通鄉(xiāng)村。老爸在前言中寫道:“1950年,我小學(xué)畢業(yè)后即負(fù)篋求學(xué),至今已經(jīng)七十年了,我也到得米望茶 之年,垂垂老矣。讀了幾本名家回憶錄以作消遣,那些大都是八十歲以后的晚年之作。我想,人到了晚年,才能品評青少年時代諸事的滋味。”
這部書的初稿開始于2009年。那年12月,父母前往南非探親,在約堡開普敦住了近三個月。閑暇時間多,孩子們總是問他們小時候如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那些時日,老爸除了每天記日記,也開始寫童年回憶。他在2010年2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翻閱寫的童年記憶,是如海瑤說的有粉紅色,只有歡樂,沒有苦難。其 實我寫了鄰居的挨餓、逃難,可能落筆簡單,沒有給她留下印象,我的童年的 確是在家庭溫馨中度過的,特別是門口荷塘,給我留下的是美的印象。現(xiàn)在 還很留戀它,可惜已經(jīng)干涸,完全消失了。 日前,要把它復(fù)印下來,因為是寫在豆豆寫毛筆的廢紙上,后面毛筆的 墨跡也復(fù)印出來,看不清楚,復(fù)印也無用了。只復(fù)印‘南非探親記’。”
兩年前的6月,《九十自述》精美插圖的作者筱江把這部童年回憶的打字稿發(fā)給了我,內(nèi)容豐富多了。我轉(zhuǎn)發(fā)給了哥哥海歌。因為父母兩地分居,我和哥哥從小就在老家跟著爺爺奶奶長大,所以,對老家的感情都非常之深。我倆贊嘆老爸記憶之好,我們的童年印象也被喚起了:麥稈扎成的草人掃天婆,掛在屋檐下,在雨中左右擺動;拉著掃把的叫魂聲,我們發(fā)燒生病時,衣服也這樣被搭在掃帚上,奶奶拉著滿村逛悠喊著我們的名字;小時候過年時才能吃到的山芋糖,糖稀裝在瓦罐里,可以用筷子插進(jìn)去攪一大坨出來,還有硬邦邦的糖瓜,用秤砣一敲就碎,哥哥也是進(jìn)門拿一塊,出門又拿一塊;正月十五蒸的面燈,蘆花編的毛甕 ,用黑黏土來摔響炮,鳳仙花染出的紅指甲……..還有各種風(fēng)物:關(guān)老陵、土地廟、砂礓地 、土簍褲子、各種石器工具……各類農(nóng)活:耕田犁地、收麥、打場脫粒、揚(yáng)場,推磨成面,舂米,苧麻剝皮搓繩,紡線織布…….
家鄉(xiāng)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既無隱隱青山,又無長流的綠水”,是一片“無雨大旱、有雨大水的貧瘠土地”。放眼望去,是漫無邊際的莊稼地,有的田里會出現(xiàn)一兩個隆起的土包,成金字形,旁邊可能還會種棵樹,這是某家的祖墳。每隔二三里路,就能遠(yuǎn)遠(yuǎn)見到許多樹木環(huán)繞在一起,雖然看不見房子,但知道那是一個村子。
關(guān)于這個大平原,哥哥后來也寫過這么一段文字:“我們老家處在淮河和汴河之間,哪一條河發(fā)水,我們那里都會泛濫。反反復(fù)復(fù)的洪水泛濫,沖走了那片土地里所有的養(yǎng)分,橘子種在那片土地上,都會變成又苦又澀又硬的枸枳蛋。用土地貧瘠來描述,最是恰如其分。 貧瘠的土地,帶來的是貧窮的風(fēng)物。 我記得直到八十年代末書中寫的那個小村莊幾乎都沒怎么變。 所以父親書中寫到的四五十年代的風(fēng)俗物事, 我們在七十年代依然能體驗到很多, 黑乎乎的夜、磷磷的鬼火,門前的一汪荷花等等。 ”
當(dāng)然,最重要的,這個貧瘠的村子里,有爺爺奶奶。奶奶身形嬌小,喜歡管閑事,但敢作敢當(dāng),是村子里的良心。爺爺沉默少語,偶爾說一句話,也是擲地有聲的。正是因為他們,讓這個普通的大鄭家,成為拉動我們生命之線的起點。
正是因為他們,讓這個普通的大鄭家,成為拉動我們生命之線的起點。
家鄉(xiāng)是一馬平川的大平原,“既無隱隱青山,又無長流的綠水”,是一片“無雨大旱、有雨大水的貧瘠土地”。放眼望去,是漫無邊際的莊稼地,有的田里會出現(xiàn)一兩個隆起的土包,成金字形,旁邊可能還會種棵樹,這是某家的祖墳。每隔二三里路,就能遠(yuǎn)遠(yuǎn)見到許多樹木環(huán)繞在一起,雖然看不見房子,但知道那是一個村子。
關(guān)于這個大平原,哥哥后來也寫過這么一段文字:“我們老家處在淮河和汴河之間,哪一條河發(fā)水,我們那里都會泛濫。反反復(fù)復(fù)的洪水泛濫,沖走了那片土地里所有的養(yǎng)分,橘子種在那片土地上,都會變成又苦又澀又硬的枸枳蛋。用土地貧瘠來描述,最是恰如其分。 貧瘠的土地,帶來的是貧窮的風(fēng)物。 我記得直到八十年代末書中寫的那個小村莊幾乎都沒怎么變。 所以父親書中寫到的四五十年代的風(fēng)俗物事, 我們在七十年代依然能體驗到很多, 黑乎乎的夜、磷磷的鬼火,門前的一汪荷花等等。 ”
當(dāng)然,最重要的,這個貧瘠的村子里,有爺爺奶奶。奶奶身形嬌小,喜歡管閑事,但敢作敢當(dāng),是村子里的良心。爺爺沉默少語,偶爾說一句話,也是擲地有聲的。正是因為他們,讓這個普通的大鄭家,成為拉動我們生命之線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