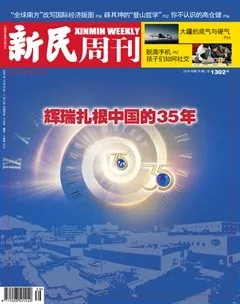閔行人讀《申江記》,老扎勁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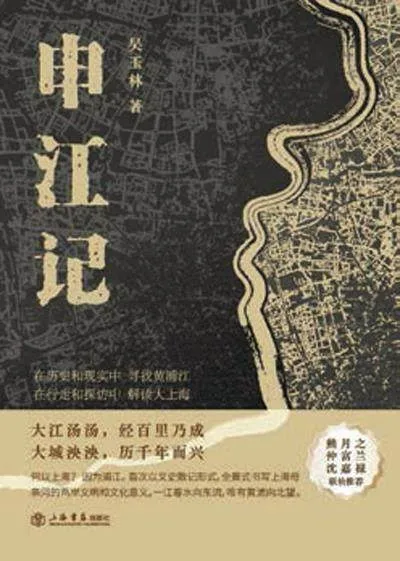
吳玉林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2024年8月
給閔行區(qū)政協(xié)委員、文史學者吳玉林的最新力作《申江記》寫書評,是需要莫大勇氣的。一方面,吳老師著作等身、交友廣泛,大半個上海的文史學家都在為他這本書叫好;另一方面,對于一個80后閔行人而言,自己對于黃浦江和上海歷史的了解實在太少太膚淺,捧起這本20萬字的書,大多時候與其說是在閱讀,不如說是在學習。
在誠惶誠恐之間,筆者利用剛剛過去的國慶假期,一口氣讀完了《申江記》,竟然一下子就打開了兒時的記憶閘門,第一次感到原來自己的成長史和黃浦江有著如此多的淵源,而這又在冥冥之中和上海的發(fā)展同頻共振起來。
如果單從松江石湖蕩東夏村黃浦江零公里處算起,到吳淞口,黃浦江干流段長89.91公里,流經了松江、奉賢、閔行、徐匯、黃浦、虹口、楊浦、寶山和浦東新區(qū)等地。而其中地域橫跨黃浦江的閔行,則坐擁著兩岸39公里的綿長岸線。這是閔行人的驕傲。
筆者出生在老閔行(閔行區(qū)江川路街道),4歲以前就住在黃浦江邊的閔行老街。聽長輩說,漲潮時分,從窗口把拖把伸到窗外再收回來就可以拖地了。
別說外地人,就連很多上海人都會發(fā)出這樣的疑問:閔行便是閔行,為什么還有一個“老閔行”呢?這是因為1992年9月,上海縣和原閔行區(qū)“撤二建一”,建立新的閔行區(qū),本地人為了以示區(qū)別,把江川路街道這塊原閔行區(qū)所屬區(qū)域,稱為“老閔行”。
作為“老閔行人”,是很值得自豪的。《申江記》里寫道:因為歷史上的“老閔行”地區(qū),古有秦皇馳道為水路要津,因地域之便,長期以來商貿發(fā)達,街市繁華、人文薈萃、群賢畢至,一度在江南地區(qū)城鎮(zhèn)中頗有影響力。從清乾隆中期開始,便被譽為上海縣首鎮(zhèn)。而此時這個上海縣的概念包括了如今的上海市區(qū)。隨著1958年1月,國務院將原屬江蘇省的上海縣、嘉定縣和寶山縣劃歸上海市管轄,閔行鎮(zhèn)一夜之間站在了時代的風口浪尖。
事實上,在通大橋之前,老閔行和黃浦江對岸的奉賢發(fā)展差距不小。《申江記》里有這樣一段記載:雖是一江之隔,但閔行和奉賢是“兩個世界”,一個天,一個地,一個繁華鬧猛一個是貧窮落鄉(xiāng)。擺渡到閔行就不一樣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閔行老街還沒拆掉前,大街小巷人流熙熙攘攘,農貿市場上的菜也是新鮮價廉……
如今,筆者住在老閔行和吳涇鎮(zhèn)的交界處,附近的浦江第一灣在《申江記》的筆下,就是黃浦江四大歷史時間節(jié)點(另三個為1843年上海開埠、1990年浦東開發(fā)開放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第一個——明永樂年間,“江浦合流”的治水措施,在如今閔行區(qū)吳涇鎮(zhèn)這里形成著名的“浦江第一灣”,迫使江水北折而去,黃浦江從而成為上海泄瀉入海主流,從根本上顛覆了前人狹隘保守的水利思想,也為上海數百年后成為“東方大港”奠定了基礎。而600年前“江浦河流”的方案,則由松江府上海縣魯家匯葉家行(今閔行區(qū)浦江鎮(zhèn))的一位書生葉宗行提出。
除了浦江第一灣,紫竹高新區(qū)、上海交大閔行校區(qū)、華東師大閔行校區(qū)、蘭香湖等在書中多有細述,既描繪了這片土地的自然生態(tài)景觀,又記錄了其生態(tài)、人文、科創(chuàng)的蝶變歷程。
讀完《申江記》,筆者不禁發(fā)出如此感嘆:何以上海,因為浦江。何以浦江,因為閔行!
書訊
《陌生的阿富汗》
一個雙肩包、一臺膠片相機、一份世界地圖、一顆充滿好奇與善意的心,這就是班卓的全部行囊。從喀布爾到巴米揚,再到坎大哈,她獨自漫游戰(zhàn)后阿富汗,直面風俗差異、性別冒犯、信仰摩擦,在陌生的土地上尋獲善意與希望。
作者班卓以女性特有的視角與經驗,將真誠和信任投向他者,記錄普通阿富汗人的喜怒哀樂:開書店的烏爾都語詩人、喀布爾旅館經理、曾是空手道冠軍的現(xiàn)役警察、為巴米揚繪圖的日本青年、坎大哈的八口之家……雖然災難仍未過去,人們依然渴望生活、熱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