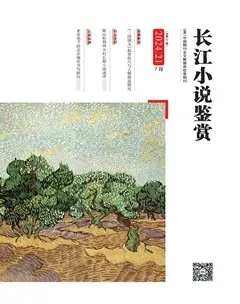從疏離到對話:蕭紅的離亂之感與抗戰前期小說創作
[摘 要] 在回憶學生時代的集會經歷的文章中,蕭紅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疏離,這一敘述姿態關聯著蕭紅獨特的戰爭理解。對戰時弱勢群體與日常生活的持續關注使得凝聚著個人感覺的“曠野”被重新激活,成為蕭紅在文學中追問個體與民族前途命運的重要意象。“曠野”背后是蕭紅主張作家貼近表現對象的戰時文藝觀。梳理《曠野的呼喊》集可以看到蕭紅與抗戰文藝主流的緊張關系,以及蕭紅的戰時書寫與文壇中心的對話價值,進而使得對小說集的評價方式從美學的、抗戰文藝的回歸到更貼近蕭紅創作脈絡的軌道中。
[關鍵詞] 蕭紅 《曠野的呼喊》 抗戰文學
[中圖分類號] I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1-0019-06
一、從“鐵路”記憶到戰時體驗
1937年12月,《七月》雜志刊載蕭紅的《一條鐵路的完成》,在這篇“救亡運動特寫”中,蕭紅回顧了自己在哈爾濱讀書時期參與學生運動的經歷。為了反對《滿蒙新五路協約》,保衛路權與主權,東北學生以及社會各界于1928年底發起游行示威活動。九年過去,為著抗日救亡的熱情,蕭紅寫下她在這次運動中的所見與感受,這篇小文中卻記載了一段并不算“熱情”的心理活動:
我只感到我的心臟在受著擁擠,好像我的腳跟并沒有離開地面而它自然就會移動似的。我的耳邊鬧著許多種聲音,那聲音并不大,也不遠,也不響亮,可覺得沉重,帶來了壓力,好像皮球被穿了一個小洞嘶嘶的在透著氣似的,我對我自己毫沒有把握。
“有決心沒有?”
“有決心!”
“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這還沒有反復完,我們就退下來了。因為是聽到了槍聲,起初是一兩聲,而后是接連著。大隊已經完全潰亂下來,只一秒鐘,我們旁邊那陰溝里,好像豬似的浮游著一些人。女同學被擁擠進去的最多,男同學在往岸上提著她們,被提的她們滿身帶著泡沫和氣味,她們那發瘋的樣子很可笑,用那掛著白沫和糟粕的戴著手套的手搔著頭發,還有的像已經癲癇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著:那被她擦過的人們,他們的衣服上就印著各種不同的花印。大隊又重新收拾起來,又發著號令,可是槍聲又響了,對于槍聲,人們像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么熱烈。至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完成吉敦路”這事情的本身已經被人們忘記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濱江縣政府。到后來連縣政府也忘記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這一場斗爭到后來我覺得比一開頭還有趣味。在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我相信我絕對沒有見過,但是警察我是見過的,于是我就嚷著:
“打倒警察,打倒警察!”[1]
“沒有把握”與“不怕死”之間的矛盾顯露出蕭紅對集會的復雜態度,作者反復書寫自己感到的壓力,并發現了行動目的在狂熱情緒中變得模糊不清。與“抗日救亡”熱情高漲的氛圍并不算融洽的這種敘述語調說明1937年的蕭紅已經覺察到了救亡運動所呈現的某種慌亂與幼稚的形式,以及運動中彌漫的讓人備感沉重的流血氛圍。
半個月后發表的《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中,蕭紅將抗日救亡運動的體驗與“中東路事件”期間政府主導的學生游行聯系起來。[2]雖然標題以“愚昧”區分了兩次學生運動的性質,但自發示威與政府主導游行的并列仍產生了運動目的兩相抵消、運動武力性質凸顯的客觀效果。沖突、暴力的一再彰顯說明蕭紅的緊張情緒正指向運動本身。在思考集會限度與反芻個人體驗的過程中,蕭紅確立了對學運與救亡的敘述姿態。
參與者蕭紅與回憶者蕭紅之間的張力為我們梳理抗戰前期蕭紅的戰爭感覺提供了闡釋空間。張力效果的來源可以追溯至蕭紅的戰時體驗:回顧學生運動經歷時流露的復雜情緒顯然與作者在上海、武漢戰時的個體感受相關。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寓居于上海的蕭紅在次日寫作《天空的點綴》,記錄平常生活因戰火顫動的時刻以及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觸,充斥著對戰事的疑問與不確定。結尾處蕭紅將目光放在短刀上,“對于它我看了又看,我相信我自己絕不是拿著這短刀而奔赴前線”。刀、匕首與武器的反復辨認透露出戰時環境下蕭紅對武力的絕對敏感。確認戰爭就是流血與暴力后,蕭紅難免感到沉重,隨之陷入“戰爭是要戰爭的,而槍聲是不可愛的”掙扎中。[3]而當著手抗戰救亡的宣傳寫作,蕭紅自然能夠發現學生游行與戰爭本身所共享的混亂形式,她開始剝離抗戰熱情中抽象、狂熱的成分,識別暴力本身對個體心靈和具體生活的傷害[3]。
由于“鐵路”事件帶來的動亂感受關聯著蕭紅的戰爭感覺,所以在這兩篇回憶文章中,作者選擇用“鐵路”事件引起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個人情感體驗為戰爭想象賦形。在抗戰前期,蕭紅對戰爭的理解存在著一種從“救亡”到“鐵路”記憶的展開方式。
一年后寫作的短篇小說《曠野的呼喊》里,“鐵路”記憶在蕭紅筆下重現。小說講述青年曲線抗戰,破壞日本人修建的鐵路最后被捕的故事,著重展示抗戰邊緣人物未知、迷茫與無助狀態。此時“鐵路”所代表的侵略、反抗與國別爭端成為背景,小人物面對戰爭切身的迷茫與悲痛擺上前臺。這顯示出蕭紅試圖對追溯“鐵路記憶”時產生的困惑與無助進行清理。她將回顧游行時的壓力與疑慮轉化為敘述動力,將抗戰救亡呼吁引起的反思推及日常生活層面,并把思考推進至更深刻的對戰爭中弱勢群體的關照上。故事鋪開的過程可視作蕭紅書寫被抗戰呼聲屏蔽了的個體經驗的過程,也是蕭紅在文學中疏解個人生活被戰爭擠占而產生的壓力的過程。類似關懷在蕭紅以北上臨汾的經歷為素材創作的《黃河》中也有體現,小說以八路軍與擺渡人的對談為主體內容,二人對話時反復出現“死人了還打仗”的聲音,涵括著以生老病死為代表的日常生活與戰爭對立的邏輯。可以看到蕭紅試圖從日常生活的正當性出發,譴責戰爭時期的暴力因素。
在同時期的書評《〈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中,蕭紅記錄了頗有意味的生活片段:因書中逃難經歷與女性處境書寫頗受觸動,蕭紅引起了男性作家的嘲笑,遂決定外出買菜逃離言語刺激,回家的路上她看見了一個衣不蔽體躺在草堆中的老人。面對赤裸裸的貧困慘象,蕭紅雖然以“抗戰”大環境為立足點進行了理性分析,對自己憎惡戰爭與流血的感性情緒予以否定,卻仍在語調中流露出傷感。“我憎惡打仗,我憎惡斷腿斷臂,等我看到了人和豬似的睡在墻根上,我就什么都不憎惡了,打吧!流血吧,不然這樣豬似的,不是活遭罪嗎?”流血的痛苦與戰亂的現實使蕭紅看到了被戰爭屏蔽的日常生活和更加悲慘的“偏僻人生”,戰時環境下的實際生活場景與對其深入的思考共同構成蕭紅戰爭感覺的主體部分[4]。
可以認為,蕭紅強調戰爭的異質性,她理解的戰爭是一種對個人生活的強硬介入的戰爭,也是一種將弱勢群體拉入更危險境地的戰爭。蕭紅是在民族情緒、日常經驗與人道主義的多重立場完成對于戰爭的批判。從這個層面上說,《一條鐵路的完成》具有超越了《七月》以“救亡運動特寫”為其命名時所期待的闡釋空間。
二、抗戰背景下的“曠野”更迭
作為短暫地出現于蕭紅三十年代后期寫作中的意象,“曠野”在不同文本中的意指有所區別。將“曠野”的更迭視作切口梳理此意象在各時期文本中的具體內涵,有助于進一步把握蕭紅如何將個人化的戰爭感覺訴諸文學寫作中。
《牛車上》是蕭紅于1936年8月完成的短篇,在這篇以兒童視角創作結構的小說中,“曠野”跟隨主人公悲慘命運的展開變換出不同面貌。小說開篇的“曠野”寬廣自由,生機勃勃,行走在“曠野”中的人也充滿活力。通過與蕭紅回憶“后花園”時頗為近似的詩性描寫可以發現,此時的“曠野”意象關聯著作者對自然的向往,對童年的追懷以及對無拘無束、自由生活的熱愛[4]。但伴隨五云嫂一家經歷的揭開,“曠野”很快就暴露出荒蕪的真實形態。遭受苦難命運的五云嫂朦朦朧朧地追問人生意義時,車夫無言地望向曠野,曠野也只是“昏昏黃黃的一片”。“曠野”之上的無常命運劫掠著生命,個體在“曠野”襯托下顯得格外渺小。小說結尾一行三人在沉重氛圍下走入人生的灰暗中,甚至這灰暗人生也無比漫長,“連道路也看不到盡頭”。“偏僻人生”究竟會走向何方?經歷多次冷眼、背叛和拋棄的蕭紅借“曠野”意象表達了自己對生命本相的洞察。蕭紅指出美好生活只是命運的面具,厄運到來之時,個體是如此脆弱的存在以至于無法改變命運的捉弄,只能選擇在苦難中接受自己的宿命[5]。
蕭紅常以詩作形式表達自己對愛情的感受,“曠野”意象也出現于其稍晚發表的詩作里,在1937年1月完成的《沙粒》中,蕭紅不止一次地發出“我心中所想望著的只是曠野”的感嘆,如其“海洋之大/天地之廣/卻恨各自的胸中狹小”,又如“世界那么廣大/而我卻把自己天地布置得這樣狹小”。對于習慣了東京生活,漸漸遠離感情苦惱的蕭紅而言,“曠野”是與圍困著她的小天地形成對照的另一重人生態度,此時的蕭紅已經不滿足于狹小的情感世界,她有意去以一種更廣袤的方式思考人生[6]。
通過梳理可以看到,“曠野”意象所指內容與蕭紅的個人經驗密切相關。寫作《牛車上》時蕭紅剛到東京,遠離熟悉的生活與社交空間本就使她常常感到寂寞,加之身體與精神狀態并不好,蕭紅形容自己“孤獨的和一張草葉似的”。充滿蒼涼之味的“曠野”也就成為作者獨居異國、無所憑依、充滿寂寥的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創作《沙粒》時蕭紅克服了東京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在異國環境下逐漸成長為擺脫依附狀態的主體。1937年底,在和蕭軍及友人的去信中,蕭紅對自己的生活和寫作提出諸多積極的計劃。[7]東京寓所的狹小也激發了她關于遼闊天地的想象,《沙粒》中廣袤的“曠野”象征著蕭紅在逼仄空間里外溢的主體建設欲望。因此,東京時期的“曠野”說明作者正剝離掉寫作中非個人化的部分,并試圖從貼近自我需求的立場出發作有關人生、命運的思考。
兩年過去,蕭紅于1939年初完成了《曠野的呼喊》的寫作。將《牛車上》對“曠野”的理解與此文串聯起來,就能發現陳公公在曠野中的呼號與車夫面向曠野的沉默有著近似之處:在命運的“曠野”上,人的質詢得不到回答,呼喊除了導致受傷流血外不會引起任何變化。兩篇小說中的“曠野”都指向底層人的心理狀態與生存環境。通過對陳公公、院落和村莊四周空曠環境的反復描述,蕭紅展示了抗爭者親屬迷茫而無所憑依的感覺,以及人無處躲藏、生存權利被剝奪、人生徹底陷入無解的極端境況。
與東京時期相比,蕭紅創作《曠野的呼喊》時的外部時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民族對日抗戰開始。思考個人與時代命運的蕭紅必須在文學中承接這一變動,《曠野的呼喊》中的“曠野”自然呈現出不同于此前的特點。首先可以發現小說中“風”的意象十分突出,開篇就寫風以野蠻的姿態席卷著一切。不只是曠野本身的荒蠻,無目的攻擊著人與生存資源的風沙也在考驗著陳公公一家。將視線放遠又能看到村頭廟堂前日本兵的大旗桿并不受風沙干擾,象征壓迫與奴役的旗桿挺直在讓陳公公頗為惱火的大風中,風沙與侵略戰爭共謀的本質由此揭示。“曠野”與“風”的雙重威脅表明了在侵略戰爭的炮火中,本就艱難維生的那部分人不得不面臨更加惡劣的生存環境。還需要注意“曠野”此時被“風”糾纏著,“而現在西方和東方一樣,南方和北方也都一樣,混混溶溶的,黃的色素遮迷過眼睛所能看到的曠野,除非有山或者有海會把這大風遮住,不然它就永遠要沒有止境地刮過去似的”[8]。曠野在風的席卷下變得模糊不清,曠野上的一切要素都被風沙遮蔽。這一自然環境描寫旨在表現“曠野”代表的無常命運在威脅人類生存的同時也是備受威脅的,說明蕭紅已經將對個體的關懷擴大至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進而在寫作中做到了對全民族命運的整體性把握。“曠野”既指向作者對單個人的不幸之憐憫,也暗含著蕭紅對抗戰前途的憂慮。從東京進入到戰時中國,“曠野”包含的范圍從個人孤立無援處境增擴至更宏大的戰時困境,此時的“曠野”不只是追問生命價值,揭示人生悲苦時的背景,還是蕭紅借以思考民族國家問題的核心意象,囊括著對個人、世界、侵略、抗爭、死亡等諸多問題的考量。
前面提及蕭紅的戰爭感覺本就源于日常生發出的敏銳感受。伴隨著戰事推進,蕭紅不斷深化對戰爭的理解,并自覺將充滿生活細節的個人感受納入《曠野的呼喊》寫作中。兒時記憶、留日經驗、戰時體驗均被調動起來組成“曠野”意象,成為銜接虛構文本與歷史現實的中間環節。蕭紅用“曠野”書寫陳公公、陳姑媽的恐懼與愚昧、貧窮與孤苦,書寫抗爭者家破人亡的凄涼命運,同時也思考著個體生命在戰爭環境下如何保存的問題。在調用凝聚著個人經驗的“曠野”的基礎上,作者對戰爭進行了抹去個體生命價值的批判,這一批判伴隨著全民族在戰爭大環境下應當何為的理性思考。“曠野”意象實現了從“展示底層人與悲慘命運的較量”到“思考個人與世界關系”再到“承接抗戰時期民族國家情感”的功能迭代。
“曠野”的更迭變換有跡可循。1938年1月,在《七月》社“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中,蕭紅回應作家在書寫戰時生活的困境時指出“我們并沒有和生活隔離。比如躲警報,這也就是戰時生活,不過我們抓不到罷了”[9]。蕭紅認為不必親自去往前線,只要生活在戰爭的大環境中,作家就擁有抗戰文學的素材,把握抗戰文藝的關鍵不在于緊貼戰事,而在于抓住戰時生活本身,并由此指出抗戰文藝存在“抓不住”戰時生活的問題。那么作家應該如何抓住戰時素材?同年4月“現時文藝活動與《七月》”座談會中蕭紅的一段發言可視作對此問題的解答:“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的,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那么為什么在抗戰之前寫了很多文章的人現在不寫呢?我的理解是:一個題材必須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來,或者跟作者起著一種思戀的情緒。但這多少是需要一點事件才能夠把握住的。”[10]蕭紅認為抗戰文學發揮動員功能的前提在于寫作的素材需要和作家的情感熟悉起來,寫作的內容不能是抽象的,而須是具體事件。也就是說,作家對自己要表現的內容應當具備熟悉的情感體驗與具體的個人經驗。
《曠野的呼喊》正是在這一文藝觀點下進行的寫作嘗試。在進入民族國家敘事時,蕭紅混入自身的歷史經驗,在行文中調用熟悉的“北中國”背景、“鐵路”記憶以及“曠野”意象。小說整合了作者的個人經驗與戰爭感覺,既有對于底層人民生活與精神困境的熟悉;亦有對戰爭時代中的日常生活被打亂的觀察;還注入了作家漂泊流浪無所依靠時的生命思索。這種貼近作家實際經歷的寫作使得陳公公在曠野上的呼喊具有可被闡釋的多重面向,蕭紅的戰爭文學展示出觸及靈魂的力量。
三、“勝利之問”與“從靈魂出發”的寫作
1938年年初,蕭紅與《七月》的一眾同伴響應建設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的號召去往臨汾,以此次北上經歷為素材寫成的散文《無題》中,蕭紅記錄下自己在同行人們謳歌北方風沙時產生的困惑。蕭紅不解于“他們”對野蠻風沙的盲目贊美,并發現“他們”無視具體的四季物候和侵略現實,指出有關北方風沙的感慨實際源自生疏引起的恐懼[11]。困惑與蕭紅認為文學表現內容須與作家情感經歷足夠熟悉的文藝主張相關。蕭紅期望在宏大戰爭里納入偏僻人生和日常細節。盡管《曠野的呼喊》存在個體與國家雙重關懷,但作者對兩者的理解有著層級關系,正是對個體的敏銳感受使得作者具備了把握民族國家命運的能力。所以蕭紅無法附和將具體經驗屏蔽的謳歌,并指出不足夠貼近表現對象的藝術傾向會導致作家無法分辨“力”與“野蠻”,進而在寫作時誤將殘忍的風沙指認為“偉大”。“他們”指一同北上的《七月》同人,雙方的分歧說明充滿細膩生活感覺的戰時文學觀念難以被整合進抽象的抗戰熱情和主流的文學表達。
帶著此種理解就能發現,《曠野的呼喊》開頭冗長的風物描寫有著蕭紅與《七月》作家群的對話意圖。形容庭院破敗時冷靜的敘述語調顯然不來自陳公公一家,而獨屬于以展示風沙對日常生活的具體摧殘來回應盲目“謳歌”的蕭紅。葛浩文認為《曠野的呼喊》是同名小說集中最差的一篇,他指出蕭紅常有妙筆的景物描寫與雜感筆法在這篇小說中成了“硬填、湊篇幅、拖泥帶水式的長篇大論”,這般足以稱作嚴厲批評的判斷正指向小說開篇的鋪陳[12]。從閱讀者立場看來,在主人公出場前大量的環境描寫確實引不起讀者的興趣。但如果將這段文字歸入蕭紅戰爭文學寫作的脈絡就能發現,堪稱瑣碎的風沙臨摹傳遞出作者與《七月》作者群在文學觀念層面存在分歧的信息,進而具有與文藝主流偏離的對話價值。
風沙描寫背后的對話意識于《曠野的呼喊》集收錄的其他文本中也存在著。《黃河》結尾,面對閻胡子“是不是中國這回打勝仗,老百姓就得日子過啦?”的困惑,蕭紅安排士兵給出必勝的答案,可隨后又著意刻畫的閻胡子被河灘沙粒淹沒的雙腳,暗示嚴峻自然環境并不受勝利預期的影響,將長久地威脅著人的生存[13]。《朦朧的期待》中寫李媽得知心上人去前方打仗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動,擔憂又不知所措的李媽只有在進入“勝利”的夢中才能暫時獲得精神放松,而“夢”的形式又隱喻著“勝利”的飄忽不定。借小說人物之口,蕭紅集中表達自己對“勝利”敘事的質疑。早在東京求學時,蕭紅寫給蕭軍的信就提到過“人盡靠著遠的和大的來生活是不行的,雖然生活是為著將來而不是為著現在”[14]。彼時蕭紅已經發現了“遠”和“大”的“將來”與“現在”人之間的矛盾。戰時環境下這一矛盾具體為“勝利”與真實生活的沖突。閻胡子和李媽的“勝利之問”正脫胎于此種沖突帶給蕭紅的危機感:洞悉人間悲苦的蕭紅明白戰爭不是導致小人物痛苦的唯一原因,戰爭的勝利也不會完完全全地化解他們人生的苦楚。可現實是,當抽象的勝利口號無可避免地進入了具體生活,蕭紅發現周邊存在著沒能被敘事主流覆蓋的角落,大環境對抗戰熱情強烈的認同將使這些角落中弱小生命在盲目歌頌野蠻的洪流中徹底迷失。接受新知識的知識分子何南生尚且會發出“抗戰勝利之后什么不都有了嗎!”的麻木感嘆,更何況閻胡子、李媽這般普通人[15]。
“勝利”敘事與戰爭熱情到底能多大程度上解決于人的具體困境?此種質疑進入到蕭紅的戰時書寫,推動著她偏離《七月》社文學中心。《無題》中的風沙引起蕭紅對于視“力”之強弱為評價好壞的文藝標準的思索,并由此展開對屠格涅夫的辯護。端木蕻良在刊登于1937年12月《七月》雜志上的《文學的寬度、廣度和深度》中對屠格涅夫作出“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里面可以找到類似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那樣整部的形式和內容來,可是你在屠氏的散文詩里絕對找不到《戰爭與和平》的整部的形式和內容來”的論斷,端木蕻良以此表達自己對精深宏大的文學主旨的追求,這一觀點也代表著《七月》作家群以及抗戰文藝整體較主流的看法[16]。《無題》中,常被指出創作“沒有中心”的蕭紅以無不惋惜的口吻回憶起自己被上述觀念裹挾時感到的失落時刻,進而指出對文學表現“力”的過分追求會帶來遠離作家靈魂的偏至,一味地鼓吹將使抗戰文學與現實隔膜而無法發出貼近人群的聲音,成為孤獨的寫作[17]。意識到蕭紅與戰時歷史環境和抗戰文壇中心的緊張關系,就能穿透“勝利之問”,看見蕭紅面對逐漸空洞化的抗戰文藝話語時,努力避免自己被卷入其中的焦慮。
在《曠野的呼喊》這一文學實踐下,蕭紅的焦慮被戰時個人化的經驗寫作化解,“勝利之問”從蕭紅的寫作中退場,弱勢群體在命運曠野上的呼喊聲代替了抽象口號。《蓮花池》中蕭紅不掩藏對為生存而不得已投靠日本人的祖孫二人的同情;《山下》作為敘述主體的林姑娘的悲劇也并非由戰爭直接導致。確立個人化寫作立場之后,蕭紅從自己熟悉的兒童視野和獨特體驗出發,關注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和無法把握的命運,盡管這些故事也放置在戰爭背景里,但人們在閱讀時獲得的大多是對于普遍且永久的親情、人性與生命的感悟。
從抗戰文學整體來看,《曠野的呼喊》集將偏僻人生的戰時體驗帶進了抗戰文藝視野;從蕭紅個人創作道路來看,小說集中收錄的文章展示出作者寫作時從焦慮走向沉靜和諧的過程。接下來的兩年間,蕭紅將在這種和諧狀態下創作出《呼蘭河傳》《馬伯樂》等動人作品,進入文學的又一高峰期。
四、結語
通過對蕭紅戰爭感覺與戰爭書寫的梳理可以看到,震顫心靈的動蕩促使蕭紅理解戰爭時納入個人經驗,并在對戰爭與抗戰文藝的反復辨認中漸漸偏離主流抗戰文藝話語,將炮火之下邊緣人生的進一步失落作為文學表現的主要目標。蕭紅在寫作時調動凝聚個人顛簸流浪體驗的“曠野”,以此意象表現戰時生活細節和窮苦群體的精神世界,將《曠野的呼喊》作為小說集名或許也隱含著作者的上述文學主張。
《曠野的呼喊》于1940年3月作為鄭伯奇主編的《每月文庫》叢書之一出版。鄭伯奇在總序言中感嘆自己未能上前線,希望收集的這些抗戰初期優秀作品能起到承擔精神動員的責任的作用。略帶遺憾的表述透露出《每月文庫》在出版過程中對戰爭以前線為中心,后方為補充的差序理解。在出版環節,看到了個體遮蔽困境并致力通過個人化寫作擺脫困境的蕭紅再一次面臨著被裹挾的命運。裹挾的再現,也更說明了蕭紅文藝觀點與戰爭書寫的獨特價值。
參考文獻
[1] 蕭紅.一條鐵路的誕生[J].七月,1937(4).
[2] 蕭紅.一九二九年底愚昧[J].七月,1937(5).
[3]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4]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5]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6]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7] 蕭紅著 蕭軍編著.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8]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9] 抗戰以后的文藝活動動態和展望——座談會紀錄[J].七月,1938(7).
[10] 現時文藝活動與——座談會記錄[J].七月,1938(15).
[11]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12] 葛浩文.蕭紅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13]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14] 蕭紅著 蕭軍編著.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15]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16] 端木蕻良:《文學的寬度、廣度和深度》《七月》,1937年12月第五期.
[17] 蕭紅著 林賢治編著.蕭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