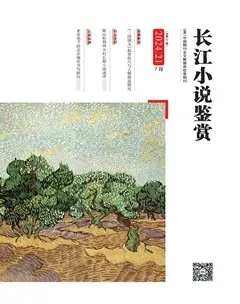水無常形——論《黑暗昭昭》中水的象征意義
[摘 要] 《黑暗昭昭》是20世紀英國著名小說家威廉·戈爾丁的一部小說,這部作品廣泛融入了神話原型、宗教文化以及象征主義,描繪了20世紀英國的社會生活以及人們的精神狀態。借助其豐富的象征意蘊,小說展現了人性的黑暗不僅存在于人的心靈內部,而且存在于外部的世界,同時表達了作者對人類未來的關切,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選取“水”這一在《黑暗昭昭》中頻繁出現且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分析其在小說中欲望與毀滅、救贖與自由的象征意義。
[關鍵詞] 《黑暗昭昭》 威廉·戈爾丁 象征 水
[中圖分類號] I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1-0041-04
威廉·戈爾丁(1911-1993)是英國著名作家、詩人。本文研究的小說《黑暗昭昭》出版于1979年,是戈爾丁的一部后期作品。它出版后便引起了批評界的關注,并廣受好評,獲得了“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威廉·戈爾丁在給唐·克朗普頓(Don Crompton)的信中寫道:“由于許多原因,《黑暗昭昭》是我拒絕談論的一本書。我越是被壓制,我的拒絕就變得越頑固。”[1]克朗普頓把戈爾丁的沉默歸結于小說晦澀難懂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也無法解釋[2]。由于戈爾丁的緘口不言,該作品一經出版便引起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與研究。
本文從象征主義的視角出發,選取“水”這一在《黑暗昭昭》中頻繁出現且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結合小說中的人物象征、意象象征以及環境象征,分析“水”在小說中的象征主義體現以及象征主義意蘊,從而幫助讀者從不同的角度解讀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發掘小說中的神秘主義氣息,以便更好地理解《黑暗昭昭》和戈爾丁其他作品的象征意義與深刻內涵。
一、戈爾丁與水的意象
象征在《黑暗昭昭》以及戈爾丁的其他作品中隨處可見,構成了作品情節結構的核心。在戈爾丁的作品中,水這一意象主要有這兩類象征意義。
第一,水的宗教色彩。作為一位具有濃厚基督教背景的作家,戈爾丁筆下的水往往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例如《教堂尖塔》中因暴風雨而傾倒的尖塔,和冒著風雨去觀察尖塔的情況,后被羅杰梅森打倒在一池污水中死去的教長喬斯林;《黑暗昭昭》中裸體走入池沼進行儀式的麥蒂,和喜愛在河邊玩耍,對電視中的海浪感到恐懼和熟悉的蘇菲等。以上這些事例都是水這一意象宗教色彩的體現。
第二,水的反面形象。在戈爾丁的作品中,火作為非常重要的意象出現,往往具有生命與希望的積極意義。正如在《黑暗昭昭》這部小說故事的開頭,作者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世界末日的圖景——被戰火襲擊的犬島、被炸彈炸毀的街區……然而,一位小男孩卻不可思議地從這末世的獄火中,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向絕望的人們。作為小說中“善”的代表,麥蒂從出生開始,他就與火結下了不解之緣。從火中誕生的麥蒂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也正為“火”這一意象,賦予了神圣與新生的象征意義。所以與之對立的水雖然有時也表現正面或中性意義,但大多數時候是作為反面意義出現的。書店水箱中的水是致使格林菲爾德小鎮付之一炬的間接原因,在議會廳門口進行儀式的麥蒂也由于自動噴水器的干擾而無法點燃火柴進而完成他的儀式。同時在《品徹馬丁》中,作者用了大量筆墨描寫馬丁為了求生與狡猾惡毒的海浪搏斗,且從一開始馬丁便身穿厚重的防水服。所有這些為水的出現蒙上了一層反面的、災難性的意味。
二、欲望與世俗之水
在《黑暗昭昭》中,人物的欲望,往往與口渴的生理狀態密切聯系在一起。在小說“麥蒂”篇中,作者提到了佩迪格里先生與麥蒂兩人口渴的狀態,它們都反映出小說中水具有代表欲望象征意義。
佩迪格里先生是格林菲爾德小鎮上孤兒學校的一名男教員,同時也是一位男同性戀者。他非常中意班上一位叫做亨德森的男孩子,并與其一直保持著“精神關系”。由于他對亨德森的癡迷,佩迪格里先生會頻繁地以補課的名義把亨德森叫到他的宿舍。久而久之,校長發現了他的補課行為,并禁止亨德森出入佩迪格里先生的宿舍。為了掩人耳目,佩迪格里先生暫時終止了與亨德森的來往,并不得不選擇他最為厭惡的麥蒂作為補課對象。“他說,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饑渴,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沙漠,人也有各種各樣的饑渴……佩迪格里先生癱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把臉埋在了雙手之間。‘我渴’。”這一段體現了佩迪格里先生無法見到亨德森時,內心的煎熬與渴望,也是對他同性戀欲望的初窺,是他后來受盡世人白眼和牢獄之災的根源所在。
與佩迪格里先生的經歷類似,麥蒂在遠走他鄉的旅途中也有過口渴的經歷。在這之前,麥蒂在弗蘭克里五金店的生活中,產生了對于性愛的追求與渴望。他為售貨亭里塑料花叢中艾倫小姐的美與芳香氣息感到震撼,在日常工作之時念念不忘的也是她“香水的味道,披散的長發”。在小說中也不乏對于麥蒂渴望性欲的表述,并且往往與“水”或“潮水”等意象相關聯。“由塑料花與散發出甜美光澤的褐色發浪所帶來的痛苦和特別的渴望,如潮水一般涌了回來”。由此可見,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水已經作為一種表示人們內心欲望的意象出現。
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麥蒂踏上了他前往澳大利亞的旅途。途中由于他對澳洲地理的無知以及識圖的失誤,他驅車駛離了主干大道,迷失在了荒蕪的小路上。他在尋找水源的途中,遇到了野蠻的土著。他只好向那個土著索要飲用水,但卻冒犯了他,并遭遇了閹割。但在他獲救之后,反而因此激發了他內心對自己使命的探索,讓自己在追求至善的路上更近了一步。“借助于從空中向他跳躍的土著人的釘上十字架的力量,這個問題又發生了變化,成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我的使命是什么?’”正是由于麥蒂被閹割,他更加堅定地將欲望與性欲徹底摒棄。此時麥蒂與水的關系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他不再是那個在澳洲的沙漠中苦苦尋求水源、欲望纏身的平凡旅人,而變成了一位試圖克服潮濕的環境,點燃圣火以警告世人的朝圣者與先知。這種巨大的反差使麥蒂更加靠近他“在烈火中被獻祭”的最終使命,也使麥蒂與水的關系從認同、渴求,變為了阻礙、對立。例如,在麥蒂的日記中,提到“一整天我看見了馬路兩旁下過暴雨,但是暴雨沒有下到我的附近。我認為這是一個信號,說明我的旅行是神圣的……”以及“我不常去盥洗室,因為我已經放棄了那么多的世俗生活”。這更加說明了對于現在摒棄欲望的麥蒂來說,水正是欲望的象征,是與神圣相悖的。
三、救贖與新生之水
在基督教文化中,諾亞方舟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舊約圣經》中有這樣的記載:“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的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于是引發了持續四十晝夜的大洪水,淹沒了骯臟丑陋的舊世界,而代之以潔凈明亮的新世界[3]。在此水具有雙重象征意義,不僅象征著巨大的、足以將世界毀滅的破壞力,同時也象征著潔凈靈魂、赦免罪孽,使人獲得希望和新生的神圣力量。
作為一位擁有基督教背景的小說家,戈爾丁在《黑暗昭昭》中為水賦予的象征意義與圣經故事中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作為威廉·戈爾丁的一部后期作品,《黑暗昭昭》在主題和其體現方式上與代表作《蠅王》具有顯而易見的相似性。但相比于《蠅王》中所表達的昭然若揭的嗜血渴望與野獸本性,《黑暗昭昭》不僅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戰爭的殘酷、人性的丑惡與潮水般的欲望,同時以更多的筆墨,著眼于對人性之善的描寫與歌頌。有學者認為,與水域相關的故事總是與主人公的冒險相關,人物往往需要水的引導來邁出成長的步伐[4]。誠然,小說中的許多人物也借由水的引導和幫助,提升了精神境界,凈滌了靈魂與身心。這里以麥蒂這一最能夠凸顯水這一象征主義意象的角色為例,每當麥蒂開啟一段新的人生經歷,或者更加明確自己的使命之時,大多都伴隨著與水的接觸。在這些決定命運的時刻,水的每一次出現,都代表著那個更加世俗的麥蒂的死亡,以及這個更加神圣、向善的麥蒂的新生。
在小說的前期,麥蒂因為愛慕自己的老師佩迪格里先生,出于嫉妒向深受佩迪格里先生喜愛的亨德森扔出了自己的體操鞋,間接導致了亨德森的慘死,并且害得無辜的佩迪格里先生鋃鐺入獄,從此他便一直背負著殺害同學、傷害老師的罪孽。退學后,麥蒂被安排在弗蘭克里五金店工作,并對那里的一位賣塑料花的女店員一見傾心,卻因為自己的罪惡之身而陷入了滿足欲望與禁欲贖罪的兩難窘境。在格林菲爾德小鎮散步時,面臨選擇的他在受到助理牧師無意間的一句“你是誰?你想要什么?”的質問后,他的思想發生了改變,他認為這兩句話“問得恰如其分,正是他心中所想”。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心中的塑料花與女孩的秀發被因罪孽而痛苦灼燒著他的火焰吞噬。他最終得出了結論,“他毫無吸引力的外表,會讓他跟這個姑娘的接觸變成鬧劇和羞辱。”這時窗外細雨蒙蒙,悲傷的他也在教堂為自己消失的未來哭泣,直到自己再也哭不出來。但此時麥蒂流干的不僅僅是他的眼淚,因為作者提到“隨著眼淚的流淌,他永遠也不知道身上的某些東西也隨之流干了”。凝視著自己流淌的眼淚,他也在這時做出了遠走他鄉的決定,放棄自己的欲望,毅然決然地踏上贖罪之路。這里窗外的細雨象征著麥蒂的世界觀正在經歷成長和變化,而麥蒂的眼淚代表著他為了獲得救贖與新生,最終決定離開小鎮了卻欲望、贖清罪孽的決心,也見證了麥蒂的成長,從一位擁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蛻變為一位禁欲而虔誠的朝圣者。此時麥蒂終于找到了那位助理牧師的問題的答案:“你傷害了你唯一的朋友;你必須貢獻出婚姻、性、愛。”
小說中類似這樣的表述還有多處,例如麥蒂在五金店工作期間,俯瞰運河的水流,認為能夠帶來裨益與治療之效;麥蒂從澳大利亞返回時,完好的眼睛中同樣淌出了淚水。麥蒂注視書店櫥窗內的玻璃球時,產生了自我的認同與覺醒,在小說中被描述為“泉水噴涌的感覺”。上文出現的種種例證都在反復證明,水在《黑暗昭昭》中被賦予了啟迪思想、凈滌欲望、帶來希望與新生的象征意義。
四、自由與脫俗之水
此外,水在小說中也象征著自由與脫俗。在希臘神話中,海神波塞冬的性格就是放蕩不羈的。海水之所以翻涌不息,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聲,正是因為海神波塞冬駕馭著烈馬金車馳騁于遼闊的海面。如同海神一樣,水也是自由奔放的,“它可以任意地流向各個地方,它沒有被束縛,更沒有被壓迫,它沒有外界的壓力,更沒有自身的壓力,它有的只是自由”[5]。在《黑暗昭昭》中,水同樣也代表著自由與脫離束縛的象征意義。
上文提到,麥蒂在澳大利亞的荒蕪小路上苦苦尋找水源之時,看到了在上空盤旋并譏笑他的天使。在麥蒂的眼中,天使“像潮水一般從空中離開”。并且后文提到“天使嘲笑他,是因為他不能飛翔。不過,他仍然能夠移動腳步,繼續艱難地前行”。此處如潮水一般在空中飛翔的天使與在地面上艱難前行的麥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潮水是自由而無羈的,它滾滾向前,不會因為任何理由而駐足停下,就像天使們那樣,他們超脫于世俗與欲望的束縛,可以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天界。反觀在荒蕪小路上行進的麥蒂,身上背負著間接殺死亨德森、使自己愛慕的佩迪格里先生鋃鐺入獄的罪孽,心中殘存著對滿足欲望的渴求與世俗的價值觀,自然是“不能飛翔”的。這里的“潮水一般”不只是描寫天使飛行的狀態,也象征著麥蒂對自由的渴望,以及希望摒棄欲望以贖罪的心理。
此外,水的自由與脫俗象征意義的體現也存在于麥蒂被禁止在議會廳門口縱火后,前往一處池塘進行的赤身裸體在水中穿行的古怪儀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儀式的過程中,麥蒂在腰部圍了一根懸掛著許多鋼圈的鏈條,便走入了水中。在他從水中出來后,他將鋼圈與鏈條收了起來放回汽車后備箱。在這一段描寫中,圍在腰間的鏈條與鋼圈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束縛”的概念。而當麥蒂完成了儀式,從水中走出并將鏈條解開后,麥蒂仿佛真正地獲得了自由,擺脫了束縛。他將小汽車送給了別人,徹底擺脫了他留在后備箱中的鎖鏈,同時“他現在可以輕松地在男人也可以在女人中間走動,可以正視別人,而不再被任何人所打動”。由此可見,麥蒂經過水的洗禮,脫去了世俗與欲望的束縛,變得更加自由與脫俗。
五、結語
《黑暗昭昭》不僅是麥蒂、蘇菲與小說中所表達的英國民眾象征主義角度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戈爾丁心目中人類社會的現狀。小說中的人們便是那些“不來就光”的人,麥蒂作為“光”降臨世間,人們卻肆意嘲笑麥蒂的古怪和丑陋,蘇菲作為“黑暗”的代表,人們卻紛紛夸贊其美麗光鮮的外表。這便是人們“愛黑暗”本質,也是小說人性之惡存在于外部世界這一主題的體現。
然而,“戈爾丁心目中的現代人畢竟不是彌爾頓筆下地獄中的撒旦,看不見一絲解放和希望之光”。就像小說中的水一樣,誠然,水象征著人們心中如潮水般翻涌的欲望,象征著小說結尾書店的爆炸中如病毒般席卷擴散的惡意和死亡;水催生了佩迪格里先生的饑渴,讓迷途的麥蒂感到痛苦,讓幼年的蘇菲感到恐懼,甚至在麥蒂的儀式中被視為阻礙,在結尾的災難中助漲了邪惡的火焰,讓舍身救人的麥蒂死于非命。但并非所有的水都是污濁而骯臟的。水象征著生命和新生,是佩迪格里的“生命節律”,也是蘊藏在《黑暗昭昭》中的救贖與希望。在異鄉迷途的麥蒂曾在天空中看到了潮水般歡快飛舞的天使以及“閃亮的水”,而戈爾丁也在這個充滿了污濁的世界里看到了依舊清澈純粹、向往自由與至善的麥蒂。盡管黑暗不僅存在于內心,也存在于外部的世界,但戈爾丁對一心向善并贖罪成功的麥蒂和雖受縛于欲望卻擁有美好內在的佩迪格里也同樣證明了,光仍然存在于這個黑暗的世界,希望與救贖的故事就在我們的身邊。
總體來說,《黑暗昭昭》中的水具有欲望與世俗、毀滅與死亡、救贖與新生、自由與無羈、神秘與魔幻等多重象征意義。本文對水這一意象的研究不僅是對作品藝術價值的賞析,而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戈爾丁小說所蘊藏的深刻內涵,解讀人物形象和主題,同時也為戈爾丁的其他作品以及英美文學作品中象征意義的研究提供了參考。
參考文獻
[1] Crawford, P.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William Golding: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M]. Columbi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153-154.
[2] 李曉青.《黑暗昭昭》中的善惡二元與圖形——背景轉換[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22(3).
[3] 李紅蕾.《他們眼望上蒼》中“水”的原型象征意義[J].英語廣場(學術研究),2013(7).
[4] 嚴曉馳.歐洲童話中的“水”意象研究[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20(4).
[5] 么春影,et al.葉芝早期詩歌中“水”意象探源——以The Stolen Child為例[J].才智,2014(9).
(特約編輯 范 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