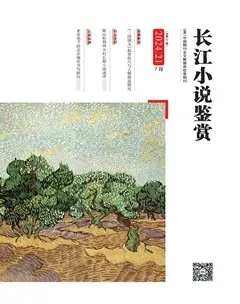丹尼爾·布萊克《到來》中的共同體構建與民族認同
[摘 要] 中間航道(The Middle Passage)的歷史記憶是非洲流散族群對于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集體記憶,為非裔作家展現民族共同體精神和促進民族身份認同提供了資源和精神動力。當代美國非裔作家丹尼爾·布萊克的小說《到來》以第一人稱復述“我們(we)”的集體視角,展現了中間航道上奴隸船共同體的凝聚和形成。非洲黑人遠離家園,在中間航道中,改進音樂、舞蹈等非洲傳統儀式,凝聚共同價值,彼此團結互助、傳遞情感支持,以集體聲音銘記集體記憶,形成了命運共享、情感共通、共同銘記集體記憶的奴隸船共同體。小說對中間航道奴隸船黑人共同體的書寫,表達了作者對共同體形成和歸屬的復雜情感和思考,也反映了作者引導當代黑人共同體發展構建的意圖。
[關鍵詞] 美國非裔文學 中間航道 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I10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1-0053-04
蓄奴貿易時期,白人沿一條呈三角狀的航線進行奴隸貿易,帶著貨物去非洲獲取奴隸,販賣到加勒比和美洲地區,換取物品返回歐洲,“中間”從非洲到加勒比和美洲的航線叫中間航道。數百萬被奴役的非洲人通過中間航道運往美洲,自此流落異鄉。中間航道歷史是非裔族群流散歷史原點,也是非裔文學的重要創作題材。當代美國非裔作家丹尼爾·布萊克的小說《到來》運用了集體敘事聲音,借助文學想象回看中間航道歷史中形成的黑人奴隸船共同體,以共同體的視角再現了奴隸船的重要意象及船上黑人受害者的悲慘遭遇,展現了奴隸船上的共同體的形成,描繪了黑人受害者堅強求存的共同體力量。作者對中間航道的書寫,體現了黑人受害者的物質困境和精神痛苦,也從積極的角度體現了他們熠熠生輝強大的精神力量,反映了其對美國非裔集體文化發展的作用,對非裔民族情感和精神凝聚的促進力量,以及作為非裔重要歷史文化記憶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對非裔自我和民族認同的重要作用。研究《到來》中的共同體是對美國非裔流散歷史中民族凝聚力的體現,小說對中間航道奴隸船共同體的描寫也反映了作者引導當代黑人共同體建設的意圖。
目前對于小說《到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于其主題、內容以及敘事聲音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方面有中間航道歷史、非裔流散、歸屬以及非裔身份構建上。以往的研究忽視了對小說中建立的共同體以及對共同體的書寫的研究。研究《到來》中的共同體可以幫助豐富和補充對這本小說的研究,從一個新的視角,以共同體的角度切入這篇小說由于集體聲音的塑造以及對黑人受害者的共同遭遇和抵抗的描寫來對這本書進行研究是有必要的:一方面,它能夠為作品主題的解讀提供新視角,另一方面,有助于體會流散黑人在流散歷史原點悲慘生活中的強大凝聚力和作者描寫共同體的意圖。在《到來》中,黑人受害者在奴隸船上逐漸建立一個具有凝聚力的團體,共同生活,由彼此共享的文化和經驗記憶、共同的奴隸命運、共通的情感形成了命運共享、情感共通、共同銘記集體記憶。因此,本文借用社會學中的“共同體”(community)概念,來探究《到來》中的共同體。
一、改進歌舞儀式與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
共同體是指由共同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和彼此間的關系構成的一個群體或團體,是一種歷史與文化的積淀形成的產物[1]。歌舞是奴隸船共同體共有的文化習俗基礎,在中間航道上,從傳統的非洲文化儀式,超越奴隸船黑人之間語言不通的境況,變成了黑人受害者們抵抗白人施暴者和寄托靈魂的生命儀式,也擔負了凝聚形成共同體的集體儀式的作用。
非洲有著和諧平衡的文化傳統,效仿自然和日常生活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歌舞文化。在白人到來之前,伴隨著鼓聲和樂曲,居民不分老幼自覺加入舞蹈。非洲居民們在婚葬、收獲、戰爭這些有關部落延續和交流聯系的關鍵時刻和休息時都會舞蹈。舞蹈在之前當地非洲居民的生活中承擔著儀式和娛樂的雙重作用。
在《到來》的中間航道上,舞蹈由黑人受害者演變和就地取材,成為團結彼此關系和延續共同體的手段和集體儀式。舞蹈將成員的軀體和靈魂聯系在一起,也將共同體的成員聯系在一起。舞蹈的動作和諧排布增加了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也促進著精神共同體的形成。
共同體依靠默認一致(consensus)與和睦團結達成一致[2]。在中間航道上,共同體在舞蹈的團結中形成。有時,黑人受害者被押上甲板在臨時制成的鼓的伴奏中表演跳舞。而“我們”中的一個,和愛人恰好在一艘船上。“我們”為他們遮掩分散白人注意力,讓他們有一些寶貴的時間聯系。這是第一次集體行動。黑人之間借舞蹈進行交流聯系,甚至交流組織叛亂。默契自發地遮掩舞蹈,增進了共同體的情感聯系,也成了共同體暫時的共同目標任務,發揮了團結和凝聚共同體的作用。
舞蹈,作為奴隸船共同體形成的儀式之一,從傳統非洲文化經過被俘黑人的因時制宜,成了共同體借以交流溝通的憑借和聯系凝聚共同體的習俗儀式,發揮作用的事件也成了共同體的共同經驗和共同記憶。同時,創造新的舞蹈也是奴隸船共同體延續的重要共同目標之一。
小說中“我們”對非洲故鄉的記憶充滿歌舞;音樂也在《到來》中無處不在,充滿和諧力量,為共同體的形成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音樂具有促進民族認同感的重要作用[3]。非裔民族的音樂作為集體的聲音,增強了奴隸船黑人的民族認同。在每個非洲村莊,多變的鼓聲無處不在,音樂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聲音。
合奏音樂的共同經驗發揮了團結合作的精神,促進了團體和諧和共同體的形成。為了對抗痛苦和焦慮,“我們”一起合奏,利用拳頭和腳大膽地敲擊節奏。成員之間音樂相合,這是共同體在形成過程中團結互助和共同協作中培養同伴情誼和和諧氛圍,同時共同的經驗促進了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
音樂也成了抵抗和延續成員生命的方式和共同目標之一。奴隸船上惡劣的生存環境、病痛折磨,白人的折磨、精神的崩潰使得生存分外艱難,放棄生命成了輕松的選項。“我們”有時哼唱整晚,同時回憶家人。“我們”用音樂抵抗痛苦,彼此鼓勵,振奮彼此的精神。
同時,音樂,作為一種特殊的語言,交流化解了奴隸船成員之間的矛盾,增進了受俘虜黑人之間的同伴情誼和交流。船艙里有來自不同部落的黑人,語言不通,很多部落以前相互敵對,許多非洲女人被放置在上層取樂。因此,一開始奴隸船的黑人之間的關系并不親密,且交流受限。然而以音樂作為語言交流,不僅聯系了奴隸船的黑人,也促進了共同體的團結和形成。
對歌舞等文化儀式的堅持,凝聚了中間航道奴隸船上來自不同部落的黑人受害者。共同的歌舞,是黑人受害者賴以生存的精神依托,也是奴隸船黑人集體彼此交流和培養同伴情誼的有效途徑,以不可替代的作用促進了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當然除了改進的歌舞儀式,在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中,奴隸船群體之間團結互助和精神上的共同支撐也是支撐和促進共同體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團結互助和共情治療與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
共同體的形成通常基于人們的歸屬感和互助意愿,成員之間共享相似的經驗和共同的目標。齊格蒙特·鮑曼認為共同體主觀上或客觀上具有共同特征,包括種族觀念、遭遇、任務、身份等[4]。丹尼爾·布萊克以奴隸船上黑人共同的奴隸命運為聯系,書寫了在共度痛苦時黑人受害者們凝聚形成共同體的過程,實現了對黑人民族精神力量的展現,塑造了一個具有高度象征意味和總結性的共同體。共同的命運和悲慘遭遇,反而讓“我們”通過團結互助和共情治療形成了一個超越部落、彼此扶持的奴隸船共同體,形成了集體認同。
共同體是通過血緣、鄰里和朋友關系建立起的人群組合[5]。奴隸船上的黑人們都是來自非洲大陸的同族,這本身就是一層無可分離的天然有機聯系。“我們”在狹窄的空間內相依為命,共同生活行動,建立堅定的朋友之誼。鮑曼在《共同體》中將共同體比作一個溫馨的能給人良好感覺的家,最重要的功能是為成員提供生活的某種確定性、歸屬感和安全感[6]。在共同命運中,“我們”在物質上變得互助,在精神上逐漸共通,形成了集體歸屬感和共同體之愛。
一方面,奴隸船黑人的團結互助和精神共情來源于非洲和諧傳統,認為一切生命互相聯系。村莊獵人會打下足夠全村人食用的魚,人們相信精神會彼此相遇,死后重逢。事情發生后,一開始黑人相互指責,但很快開始彼此關心。“我們”在關押的不同隔間,喊著愛人親屬的名字,等待回答,在沒有回答時再次哭泣。一次,一個父親的呼喚得到了回復,“我們”也哭了,為他獲得了神的恩典。
另一方面,在中間航道旅程上的共同命運和遭遇,促進了奴隸船成員的互相幫助,促使了共同體公共精神的形成。堅持公共精神意味著共同體成員在面臨整體利益和共同事務時,有義務尊重和服從共同體的價值規范[7]。奴隸貿易中,物資匱乏。一開始,對于白人給予的有限物資,例如淡水和食物,黑人們會彼此爭搶。雷蒙·威廉姆斯認為,如果存在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其特征應該包括平等成員之間的“寬容睦鄰”和“傳統互助”[8]。經過共同生活和共患難的共同經驗, 在旅程的后半段,即使物資依然匱乏,所剩的黑人之間卻堅持自覺分享物資,堅持民族傳統扶持互助的共同價值規范。
共同的遭遇形成了情感共通的命運共同體。滕尼斯認為成員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漸形成彼此的習慣,處于共生狀態,相互聯系和影響,相互理解和支持[9]。白人水手常以黑人取樂,施以性虐待。當還在船艙的黑人聽到尖叫,他們想到,這是我們的女兒、母親、姐妹、阿姨們的尖叫。由此可見,在共同生活中,血緣的宿命性促使他們彼此擔憂,彼此理解共情。
共同體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個體參與群體,分享共同的情感狀態[10]。對同伴的重視讓黑人俘虜們將點名變成了一種集體儀式。一陣沉默,就代表一條黑人的生命逝去。這時,集體以沉默予以悼念。集體悼念這種臨時的死亡儀式,在中間航道途中無法舉行葬禮的情況下,作為集體的情感活動,凝聚了共同體的情感,使得共同體的成員由血濃于水的親緣出發,在同一艘奴隸船的地緣上,形成了以情感為紐帶的共同體之愛。
三、集體記憶與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民族本質上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11]。人們通過共享的文化符號、歷史故事和共同語言來構建對共同體的認同。布萊克的《到來》運用了獨特的敘事角度,采用了第一人稱復數“我們(we)”的集體視角,用“我們”的集體聲音重述了奴隸船的集體故事,以集體聲音銘記集體記憶,促進了共同體的形成。“我們”并非是某個特殊個體,而是一艘不確指的象征性的奴隸船上的黑人,也是所有受到中間航道奴隸貿易影響的黑人。
在面向未來的維度時,“過去”的經驗是揮之不去的,“過去”也正意味著我們的認同之源[12],奴隸船黑人對集體記憶的銘記和自身文化的認可正始于他們對非洲故鄉的回憶。布萊克在與達娜·威廉姆斯的采訪中提及,“我們”在回憶中承認:如果在文化和精神上處于最好的狀態,“我們”可以避免沖擊。黑人受害者們重新審視了民族文化,更加認可尊重自身文化傳統。
奴隸船黑人共同體的形成也有賴于集體記憶的銘記,促進了共同體的認同和歸屬。黑人需要重新了解那段過去,化解壓抑在無意識深處的創傷情結,才能擁有更美好的未來。重塑奴隸船的集體記憶也是對共同體共同經驗的銘記和集體記憶的留存。這些記憶,大部分時間都以“我們(we)”的形式出現。小說主體分為三個部分,敘述了奴隸船黑人受害者們,即“我們”,在整個“到來”中的遭遇和記憶。這場到來包括白人的到來襲擊、黑人的被俘,大西洋上黑人的悲慘遭遇和艱難求生,也包括黑人在中間航道的終點——美國的圈禁和拍賣的場景。
小說講述在中間航道奴隸貿易期間,在一艘可以象征任何一艘奴隸船的奴隸船上,黑人受難者的遭遇。正如瑪塔·維班歐斯卡所評論的那樣,布萊克拒絕提供歷史細節,似乎將中間通道的整個旅程概念化為塑造現代非裔美國人集體意識的基本體驗。“我們”并不確指,船沒有名字,書也沒有具體時間信息,所以“我們”可以是所有與奴隸貿易奴隸船相關的黑人受害者。敘事聲音的不確指,方便了代入和體驗。
同時,奴隸船共同體的共同記憶也是由每個成員的記憶組成的,對個體的尊重和記憶加強了共同體的凝聚力。小說中,總共使用100多個名字,都有自己的含義,了解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名字,可以讓讀者更清楚了解他們是誰以及共同體對他們的期望。“我們”盡力記下身旁人的名字、含義和故事。叛亂中弄到了鎖鏈的鑰匙為我們解鎖被槍殺的Abeni(意為我們祈求她的到來,看那,她來了),“我們”在臨近拍賣前一起接生下來的小女孩Ayo(源自Ayodele,意為快樂回來了)……具體的記憶都構成了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個人的銘記強化了個體對共同體的認同。
四、結語
故事的最后,“我們”最后被拍賣,分散各處,但共同記憶凝聚聯系著所有人。縱觀整部小說,主視角“我們”講述了我們在中間航道航程中的生存故事。集體聲音訴說了族群共同的厄運,復數視角見證了無數逝者和少數生還者。民族國家通過出版書籍、建造博物館等方式凝聚共同體。小說中黑人受害者通過銘記彼此記憶,實際上建造了一座講述中間航道奴隸船的生存故事記憶館;丹尼爾·布萊克則通過對中間航道奴隸貿易歷史上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書寫,影響了其非裔讀者的民族認同。
小說《到來》,以集體敘事聲音第一人稱復數“我們”的聲音回看中間航道歷史,再現中間航道奴隸船這一重要意象和集體記憶符號。作者作為非裔美國人,進行了歷史回顧,借由這些受害者們的事跡,對歌舞等傳統非洲文化儀式的演進、物質情感上的團結互助以及對集體記憶的共同銘記,在抵抗白人施暴的同時,形成享有共同文化、情感溝通、集體記憶的奴隸船黑人共同體的歷史,促進美國非裔的民族認同和歸屬感。小說中對中間航道中奴隸船共同體的形成的書寫也反映了作者回顧和想象歷史以引導當代黑人共同體建設的意圖。
參考文獻
[1] 令小雄.人類命運共同體文化價值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22.
[2] 李榮山.共同體的命運——從赫爾德到當代的變局[J].社會學研究,2015(1).
[3] 殷企平.英國文學中的音樂與共同體形塑[J].外國文學研究,2016(5).
[4] Bauman Zygmunt.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5] T?nnies Ferdinand.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M]. Ed by Jose Ha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謝景慧.現代性語境下的共同體與社區共同體的當代想象[J].宜賓學院學報,2022(7).
[7] 陳飛.公共精神的哲學追問與共同體的當代重建[J].南京社會科學,2023,(11).
[8] Miller, J. Hillis. Communities in Fiction[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5.
[9] 寧子涵.《威尼斯商人》中共同體的缺失與重建[J].大眾文藝,2023(16).
[10] 劉斐.簡·奧斯丁《勸導》的共同體書寫[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23(5).
[11] Anderson Benedict.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Verso, 2006.
[12] 劉亞秋.記憶共同體何以可能:一個理論建構[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6).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