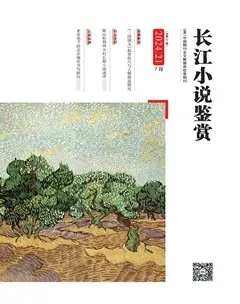論《金陵十三釵》的電影改編
[摘 要] 小說《金陵十三釵》因其獨特的題材、強烈的故事性以及嚴歌苓作品改編的成功經驗,被張藝謀選中并改編為同名電影。電影在保持原作核心沖突的同時,通過改變敘述視角、豐富戰爭場面以及強調英雄主義敘事,成功吸引了廣大觀眾,并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雙豐收。然而,改編過程中也展現出一定的市場和商業導向。盡管如此依然不失其作為經典故事的魅力與生命力。
[關鍵詞] 社會語境 敘述視角 故事情節 女性敘事 愛國情懷
[中圖分類號] I2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1-0085-04
小說《金陵十三釵》被著名導演張藝謀改編為同名電影,于2011年12月15日在全國上映。在編劇劉恒和嚴歌苓的加盟下,張藝謀將南京大屠殺那段動蕩歲月中的悲歡離合、家國情懷與人性光輝展現得淋漓盡致。該片上映期間,不僅迅速贏得了廣大觀眾的熱烈反響與高度評價,更在票房上大放異彩,獲得2011年度國產電影的票房冠軍。除了其商業性得到認可之外,其藝術性也贏得業界的贊譽。2012年《金陵十三釵》獲上海影評人獎年度十佳電影;2013年該片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故事片獎。電影《金陵十三釵》憑借高超的敘事藝術、深刻的愛國主義主題以及獨特的故事背景贏得受眾的喜愛。2014年12月1日,張黎導演將這部小說改編成了48集的電視劇《四十九日·祭》,在湖南衛視黃金時段首播。《金陵十三釵》的故事從小說到電影再到電視劇,說明了好的故事會不斷地被演繹和傳播,直至其成為經典。
一、改編的社會語境與文化背景
小說和電影屬于兩個系統,有自身的藝術體系和表達方式,但是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這個轉化的過程就是改編的過程。一部小說之所以被選中進行改編,說明小說本身就有無窮的魅力以及廣泛的受眾,《金陵十三釵》到底具有怎樣的魅力,使得張藝謀導演愿意進行改編呢?
第一,題材的獨特性。《金陵十三釵》的故事背景是南京大屠殺,關于這段歷史對于中國人而言是非常沉痛的,也是不可磨滅的慘痛記憶。所以這個故事的題材是非常珍貴的,而且電影史上表現南京大屠殺的題材并不是很多,除了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之外,電影史上再沒有此題材,但是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題材有很多,比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的名單》等,所以南京大屠殺的題材既敏感又稀缺。張藝謀導演選中這個題材的故事,一方面彌補了電影史在此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表現了一位中國導演記錄歷史的責任感。
第二,小說的故事性很強。故事不僅是小說的核心更是電影的核心。C2Pb+hBTsLxQye72p06O3w==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這證明了故事在當今時代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張藝謀導演非常看重小說的故事性。“我就想講一個好故事。”張藝謀在宣傳《金陵十三釵》時公開聲明。[1]《金陵十三釵》中最重要的敘事線索是日本人屠城,民眾進行反抗,這構成了故事的第一重沖突,即壓迫與被壓迫者之間的抗爭。當然在這個反抗日本人的體系中,有兩個特殊的群體是女學生和妓女群體。這兩個群體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階層,而且這兩個群體屬于女性群體身份象征中的兩端,即一個學生群體象征著純潔和未被踐踏,另一個群體——妓女卻象征著墮落和放蕩,這是女性群體中的兩端,所以故事的第二重沖突就來源于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相處,她們從相互充滿敵意、偏見、隔閡到最后惺惺相惜、和解,這個矛盾處理過程就是其故事發展的過程,也是兩個不同群體女性成長的過程。
第三,嚴歌苓的作品有改編成功的經歷。嚴歌苓作為著名作家與編劇,其多部作品被改編為電影。《少女小漁》《天浴》《小姨多鶴》《一個女人的史詩》以及后來的《芳華》《陸犯焉識》等都被改編為影視劇。嚴歌苓多是以跨文化的視角去表現人物的性格矛盾,故事的主人公多為女性。為什么導演喜歡嚴歌苓的故事或者說為什么嚴歌苓的小說有這么多被改編為影視劇?嚴歌苓解釋說:“我想許多導演喜歡我的故事,主要是因為我會把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全部放進去,所以畫面感比較強。”[2]正是因為嚴歌苓小說的這種畫面感或者說“上鏡頭性”,使得其小說有了更多改編為影視劇的可能。
第四,張藝謀導演對小說的偏愛。從導演早期的作品可以看出,張藝謀導演特別喜歡將小說改編為電影。比如其導演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紅高粱》等都是由小說改編成的電影,而且都很成功。把小說改編為電影,一是可以借助小說原來的讀者,另一方面一個被人熟知的故事更容易被受眾認可。
二、電影與原著的不同
1.敘述視角不同
在小說中,嚴歌苓采用的主要是兩種敘述視角,其一是全知全能的“我”的視角,即用“我”的視角來提醒讀者這更像一個回憶中的故事,也提醒受眾那個戰爭年代的殘酷,比如小說中對豆蔻的描寫不僅用了姨媽書娟的視角,也用了“我”的視角:“我在一九九四年,一次紀念‘南京大屠殺’的圖片展覽會上,看見了另一張豆蔻不堪入目的照片。這是從日本兵營的檔案中查獲的,照片中的女孩被捆綁在一把老式木椅上,兩腿撕開,正對著鏡頭,女孩的面孔模糊,大概是她不斷掙扎而使鏡頭無法聚焦。我認為那就是豆蔻。”[3]另一個視角是“我的姨媽”書娟的視角。小說的開場有這樣的描述:“我姨媽書娟是被自己的初潮驚醒的,而不是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外的炮火聲。她沿著昏暗的走廊往廁所跑去,以為那股濃渾的血腥氣都來自她十四歲的身體。”[4]小說這樣的開場,不僅提醒我們這是一個正在經歷青春期女孩的故事,戰爭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而且明顯地展現給受眾的是一個女性敘事的視角,用女性敘事來展現歷史,用戰爭中女孩的故事來控訴日本人的滔天罪行。
而電影中采用的則主要是第三人稱書娟的視角展開敘事。電影中這些妓女是如何走進教堂的,假神父約翰是如何成長為教堂的保護者,約翰與玉墨之間的愛情是如何產生以及戰火紛飛、槍林彈雨中的南京等,都在書娟的視角下展開。電影采用的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與小說中復雜的敘述視角相比,會使得電影的敘事線索更加清晰,也更符合兩個半小時左右電影的敘事時長。此外,電影把視角放在書娟身上,相當于展現的是女孩眼中的戰爭。因此小說和電影因為敘事視角的不同,展現出的主題就不同,小說更多的是講述女性成長的故事,電影借助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傳達給受眾的是一個英雄的故事,是軍人愛國的主題。
由此可見,小說和電影的立意點是不一樣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小說的作者嚴歌苓本身是女性,所以其注重女性敘事,注重在特殊環境中女性的成長,正如她自己所說“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總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終極戰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總是雙倍的。”[5]而張藝謀作為男性導演,其必然要考慮市場和受眾的要求,在他看來,女性敘事與當下主流敘事相比,主流敘事更容易引起大眾的共鳴,從而獲得更好的商業效果。此外,雖然張藝謀也側重于塑造兩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但是其塑造的視角仍然符合男性凝視的標準。“許多主流電影都是為‘男性凝視’(Male Gaze)而建構的,即敘事呈現的主要視角是男性的,電影的視覺快感(包括女性身體的奇觀)也是主要針對男性。”[6]
2.主要情節不同
小說中與電影中妓女出場時的處理方式不一樣。小說中妓女們的出場時間正好與書娟初潮的時間一致。即小說的開始就決定了這是一個關于女性成長的故事。以書娟為代表的女學生告別懵懂的少年時代迎來自己的青春期,并在經歷戰爭和目睹戰爭的殘酷之后最終成長事。以玉墨為代表的妓女們,她們在小說中的出場非常放蕩不羈。小說中這樣寫道妓女們的出場:“英格曼神父突然向圍墻跑去,書娟和七個同屋女孩這才看見兩個年輕女人騎坐在墻頭上,一個披狐皮披肩,一個穿粉紅緞袍,紐扣一個也不扣,任一層層春、夏、秋、冬的各色衣服乍瀉出來。”“阿顧捉住一個披頭散發的窯姐。窯姐突然白眼一翻,往阿顧懷里一倒,貂皮大衣滑散開來,露出里面凈光的身體。阿顧老實頭一個,嚇得‘啊呀’一聲嚎起來,以為她就此成了一具艷尸。”[3]從小說的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妓女們是翻墻進來的,而且使用了美人計趁機跳進教堂。而且這群妓女到來之后,與學生之間產生了一些矛盾,比如她們為了盛走一碗湯而產生矛盾。但就是這樣一群放蕩不羈的妓女們,最終完成了保護學生的使命,付出生命的代價贏回人性的尊嚴。
電影中這群妓女的出場則充分發揮了電影的視覺藝術效果,無論是在電影的構圖還是色彩上,張藝謀導演都非常考究。尤其是妓女們進入教堂的情節,影片中書娟透過五彩斑斕的玻璃窗,看到了風姿搖曳的妓女們,五彩斑斕的玻璃窗的顏色映照在書娟的臉上,時而泛紅時而泛黃,通過書娟的主觀鏡頭、學生們的近景鏡頭、窗戶的特寫鏡頭以及約翰的遠景鏡頭之間的反復切換,使得畫面具有一定的層次與節奏,這個五彩的玻璃窗不僅參與了敘事,而且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主要情節“圣誕夜事件”在小說和電影中的處理方式也不一樣。在小說中,玉墨是主動提出要替女學生去赴宴,而且沒有時間和女學生們告別的。日本人大佐帶領日本兵強行闖進教堂之后,阿多那多副神父和英格曼主神父請求大佐給予半小時的準備時間,在兩位神父惆悵絕望之際,是玉墨直接主動提出的要求替女學生去赴宴,之后便是紅菱和玉笙等人支持玉墨的做法。玉墨為什么能夠主動站出來替女學生去赴宴,小說鋪墊了很多玉墨與戴教官的愛情情節,并且戴教官為了保護女性而承認自己的軍人身份被日軍殺害時,玉墨目睹了全過程,這成為她要對抗日本人和替女學生去赴宴的強大動力。此外,小說中等妓女們全部打扮成女學生的樣子時,日本兵已經開始催促他們出發,所以在小說中妓女和女學生之間是沒有時間告別的。
在電影中,圣誕夜事件是被重點呈現的情節,與小說中有兩點不同:其一是在電影中,妓女們替女學生去赴宴這件事是被動發生的,或者說是為解決當時的燃眉之急而發生的,當時以書娟為代表的女學生們爬到樓頂想要跳樓,為了穩住學生們的情緒,玉墨情急之下說出替女學生去赴宴,所以在電影中妓女們替女學生們去赴宴這件事不是主動提出的,是在一定條件下迫于穩定學生情緒隨口說的。電影這樣的改編,雖然凸顯了戲劇沖突,但也削減了小說中的妓女們的主動性和為國獻身的勇氣;其二,在小說中,日本兵只給了半小時的時間,所以妓女和女學生來不及告別,但是電影中則是兩個不同的群體有告別的時間,他們彼此和解、認同,甚至惺惺相惜,電影中是一副大和解的局面。而且詳細展現了約翰為妓女們化妝、剪頭發的情節,所以電影中出現了那個經典的儀式化的場景:妓女們一字排開躺著,曾經給死人化妝的約翰的加入,不僅預示著這些女性身體的獻祭,也象征著她們有去無回的命運。
3.對戰爭場面的呈現不同
《金陵十三釵》的故事背景主要是南京大屠殺,因此嚴歌苓在小說中描寫了戰爭的殘酷,但是因其文字的書寫不如影視畫面更具渲染性,所以用筆不多,戰爭在小說中僅僅是故事發展的時代背景,不能成為故事發展的主角,甚至那些殘酷的日本人的燒殺搶掠在小說中,女學生沒有親眼所見,他們只是從神父那里聽說的,比如豆蔻的死,比如教堂之外正在經歷的屠殺。小說中寫道:“阿多那多把他從外面拍回的照片洗出來給女孩們看。女孩們都用手捂住眼睛,然后從指縫去看那橫尸遍野的江洲,燒成炭的尸群,毀成一片瓦礫的街區,一池鮮血的水田……”[3]
但電影作為一門視聽藝術形式,其感染力很強,為了突出戰爭的殘酷,且出于宏大主題的彰顯以及商業化的需要,所以戰爭在電影《金陵十三釵》中成為主要的表現對象。影中注重戰爭場面的渲染,傳達了英雄主義的精神。電影《金陵十三釵》兩個半小時的時長,有半個小時的時間在表現南京大屠殺。電影一開場便直接切入激烈的戰斗場景,硝煙彌漫,視線所及之處皆是戰爭的痕跡。日本侵略者暴行猖獗,他們無情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行為令人發指。在這絕望與混亂之中,一群女學生正奮力在戰火中奔逃,與小說中只看戰爭的照片相比,電影中的女學生一開始就直面了戰爭的殘酷。在電影開場的前16分鐘,導演用寫實的手法盡力還原那個戰亂的年代,同時表現了李教官及其戰友們的英勇抵抗。
三、結語
綜上所述,《金陵十三釵》作為一個成功的故事范本,嚴歌苓與張藝謀呈現出的是不同的面貌。嚴歌苓的小說以女性視角講述兩個不同身份階層的女性成長的故事,并控訴戰爭對人尤其是對女性的傷害。但張藝謀的電影則采用英雄主義敘事的模式,從不同的敘事視角、主要情節不同的側重點以及主題不同的呈現方式,不僅表現了假神父約翰從小人物成長為英雄的過程,而且展現了中國軍人英勇抗敵的愛國主義情懷。由此可見,小說與電影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各有其不同的敘述媒介與表達方式。
參考文獻
[1] 嚴歌苓.金陵十三釵[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
[2] 侯克明.女性主義背景的英雄主義敘事——《金陵十三釵》從小說到電影的文本轉移[J].電影藝術,2012(1).
[3] 萬信瓊,喻潤梅.近十年文學作品影視改編與傳播研究述評[J].電影評介,2011(8).
[4] 王乃芳,李田秀.改編與過度“詮釋”——試論張藝謀電影《金陵十三釵》[J].電影評介,2012(17).
[5] 滑喬佳.《金陵十三釵》電影改編藝術[J].戲劇之家,2021(18).
[6] 章簡寧.試論《金陵十三釵》電影改編之失[J].視聽,2020,(11).
(特約編輯 楊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