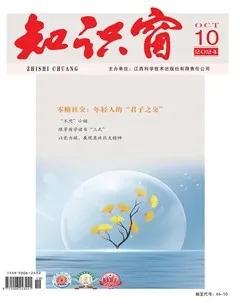聽月傳說
中秋將至,月亮像一個月餅,懸在小院的上空,照得我的心里焦急不已。
很久前,在西北做工的鄉人帶回稀罕的葡萄苗。從我有記憶以來,家家戶戶都移栽了葡萄苗,它們長得葳蕤一片,隨處可見攀出墻的寬大藤葉。而那個鄉人也講述了這樣一個傳說:“中秋夜坐在葡萄藤下,能聽見嫦娥、玉兔說話。”鄰里聽了哄笑道:“這才栽下葡萄苗,豈不是得等到我拄拐?”
等村子成了葡萄村,我想,我應該聽得到嫦娥和玉兔的交談了吧。
在我對傳說翹首以盼的日子里,鄉里的孩子卻專注于另一件事:賭誰家葡萄先熟。我并不在乎這個賭局的勝負,所以擔任裁判的角色。可村里的葡萄同根并茂,約定好似的,臨近中秋就一院一院爭相熟透,哪有勝負可以判斷。即使夜夜不睡,我也需化身千里眼方能捕捉一二差距,于是只好對著月亮禱告:“嫦娥,嫦娥,請告訴我,誰是贏家。”月亮笑而不語,仿佛在說時機還未到呢。
那是我幼時最虔誠的等待,一連半月,我總是早早合上作業本,便一頭鉆進葡萄架。此時,伙伴們已將注意力轉至月餅上。家鄉的蛋皮月餅遠近聞名,蛋皮極厚,吃起來滿嘴酥香,最合小孩子的口味,可蛋皮月餅的餡兒呢?聽聽年輕媽媽的控訴:“茶幾下、床頭后、沙發底……凡家里的犄角旮旯,總莫名生出月餅餡兒,碎成一塊塊,叫人既惱火又哭笑不得。”在啃光蛋皮后,剩下的餡兒或藏或丟給貓狗,是孩子們多年的秘密,甚至他們還相互攀比,比一比誰把餡兒藏得最久。最后,一口月餅都不愛吃的我反倒成了好孩子。有時,大人的標準就是這樣無理。
那時,我總是幻想著能用《借東西的小人》的主角阿莉埃蒂那樣靈動的姿態躲進葡萄架,用藤葉遮掩全身,獨留一雙幽亮的眸子藏匿在葡萄串陣里,然后陷入寂靜的暢想:我正在欣賞著一場月下的音樂會,往日聒噪異常的蟬鳴聲,此刻如交響樂一樣恢宏,嫦娥的聲音是清麗婉轉的,像小姨,她總是柔聲細語的,從不斥責小孩;玉兔的音色酷似稚童,不鬧騰……
我沉浸在美妙的暢想中。在不遠處的石階上,忙碌了一天的大人松松散散地落座,雖身心疲憊,嗓門卻十分響亮。我驚醒了,身上也漸漸覺察出被蚊蟲叮咬的癢意。我只好百般不愿地從葡萄架里鉆出來,躺到竹席上,緊貼著水泥地,像浮在輕柔的水里,涼透了也就不癢了。月亮緊隨著溜到眼前兒,星星怯怯地散落一兩顆。葡萄仍不開口,可我憋不住了,一串、兩串、三串……我興致勃勃地數起了葡萄串,把數記到肚子里是不易忘的,每數一串便吃上一顆,一會兒后吃撐了,也乏了,便回屋睡去了。
隔天一早,我被窗外彈來的一嗓子喚醒,“有雞啄葡萄了?怎么凈是葡萄架矮處、葡萄串屁股尖兒的葡萄粒少了?”我心虛地攏了攏被子,心中暗道今晚得站著摘葡萄,這次好賴在麻雀身上。
日歷一頁一頁地被撕去,我吃進數不清的葡萄,才把中秋夜盼來。大人的閑話總算嘮盡,忙里忙外開灶、支桌、上供,瓜果餅糖俱是圓咕隆咚的,溫乎的餅子也比平日肥而圓。小姨特意買了個足有鐵鍋蓋那么大的蛋糕,再沒有比這更團圓美滿的日子了。
那是我在葡萄藤下守過最久也是最短的一夜。直到公雞打鳴,我也沒聽見嫦娥和玉兔開口,我整晚都支棱起耳朵,急得快要譯出蚊子語了。當我醒來時天光大亮,屋檐下壞掉的風鈴無聲搖曳著,空氣寂寞得像剛送走一屋客人。母親說,我昨夜在葡萄架下睡得極香。這絕不可能。那時剛學習寫作,我便這樣記錄:“嫦娥攜玉兔同我講了一整晚悄悄話,天明又把所有記憶抹去。我不難過,反正嫦娥會記得,明年今日再問她真相。”
姥爺是在地里收獲后離世的,同蟬鳴一道,戛然終止在他最后的月夜。原來小院聒噪的交響樂是為姥爺奏的,僅短短一程。在那段日子里,每天只喝得下三兩口的雞湯、碩大的蛋糕、難以忘懷的團圓宴,竟都是姥爺告別的信號。可惜我長大了整整一輪,才徹底參透那些象征。小院翻一翻新,假裝日子仍滿是盼頭。只是一到中秋夜,我在院子里駐足久了,賞月都變得萬分苦澀。
老人去了,中秋就一年年來得急了,月光不比兒時的慷慨,也足夠指引匆匆的身影回到小院。最先入我眼簾的是葡萄枝,它枯而不死,根尚未爛透,硬挺挺地撐在墻角。各家的葡萄枝命數相似,可敬的是無一家拿去燒火,默契地給它功臣般的待遇,養在安靜一隅。
傳說依然美麗,因為我無法驗證。或許嫦娥和玉兔在等人先開口,托她的許諾,夢里雖無聲無息,但也熱熱鬧鬧的。
小孩子沒了葡萄可打賭,但也愛到處藏月餅餡兒。中秋拜長輩,送去蛋皮月餅,長輩會回贈一兩串葡萄,從前是現摘,現在得提前買了備好,若去得晚些,老人要折損不少呢。供桌上葡萄的顏色不勝往昔,好在年年依舊,敬獻給月上客和親人,告訴他們:“你們掛念的小白兔啊,一如從前——中秋一過便沒日沒夜在田間收獲的他們一樣,長成能擔當的模樣,奮力行走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