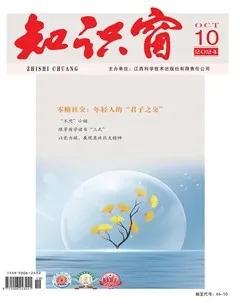梅嶺有清音
小暑至而盛夏始。在這個周末,我坐在沙發上看書,女兒踩著拖鞋跑來跑去,鞋子吱吱地響,女兒喳喳地叫,妻子臉上露出一絲不滿。在她發火前,我把書一合,決定與家人一同去南昌西郊的梅嶺走走。
六年前,我們住在梅嶺邊上。這些年雖然搬了家,但每年因采摘楊梅、桑葚、草莓來過梅嶺多趟。無論是怪石嶺、竹海明珠、月亮灣,還是銅源峽、太陽谷、老四坡……梅嶺的山野已“成竹在胸”,遠近的道路也老“簡”識途。
我們朝著大山出發,曠野漸深,空氣漸新,地勢漸高,猛然一瞧,已是竹葉婆娑、竹林深深。竹,四君子之一。關于竹的故事可不少,猖狂的阮籍和他的六個好友一得閑,便待在竹林喝酒縱歌;清人鄭板橋畫竹成癡,依竹而居;廢名的小說代表作,其主要情節也發生在一片竹林中。除了文人和名人,竹還有不少其他的“粉絲”。在我老家,幾乎家家后院都有一片竹林,種植竹子的原因沒有東坡先生“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浪漫,竹可用來制作桌椅板凳、籮筐筷箸。在鄉人眼中,竹的實用價值自然是列在文化價值前頭的。
在竹林中穿行,待進得洪崖丹井,一座巖紅的雕塑巍然而立,這便是樂祖伶倫。伶倫左手持五根長短不一的竹管,頭部昂揚向上,右手展開作拍擊狀。細看,他腹部收縮,嘴唇凸起,丹田中深藏一口氣息,待得此氣發酵千年,過肺腑穿竹管而出,激揚跌宕地、意志堅定地穿過歲月時序,在洪崖這一圣地散發而出,黃鐘大呂啊!這便是天地之聲。
倉頡造字,仿日月天地之形,字成則天雨粟、鬼夜哭;伶倫定樂,擬草木鳥獸之聲,樂成則鳳鳥鳴、韻律始。根據《漢書·律歷志》記載“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之后,伶倫便來到梅嶺隱居,在洪崖處鑿井五口,汲水煉丹,丹成,在此仙逝。
我時常想,人為什么會喜歡山,喜歡水,喜歡自然。從古說來,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回九江老家種豆南山下,伶倫到了人生后半段也選擇隱居山林。中國人骨子里喜歡深山,喜歡綠竹,喜歡漫無邊際的曠野。
天地飛鴻,綠野白駒。不妨聽一聽梅嶺的清音,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走在竹林下,我看見水激石,其聲嘩嘩然;我觸見風吹竹,其聲瀟瀟然;我聽見鳥獸鳴,其聲勃勃然。山石的縫隙有梅嶺的呼吸,泉水的脈動有梅嶺的韻律。天地間的各類聲音在梅嶺齊鳴,演奏者是伶倫,是天地,也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