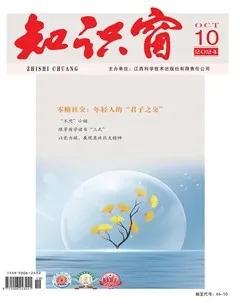文學(xué)里的蔬菜“大明星”
如果蔬菜有排名,那么有著怪味的芹菜、容易引發(fā)口氣的韭菜,以及奇苦無比的苦瓜肯定不算美食界的寵兒。但在古代文人的筆墨宣傳下,這些蔬菜成了詩詞里閃閃發(fā)光的“大明星”。
芹菜:學(xué)界“文曲星”
芹菜有多難吃呢?醫(yī)學(xué)家孫思邈在《千金食治》中寫道,芹菜味苦、酸、冷澀,真是比一般的藥材還難入口。對它的吃法,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shù)》中寫道,可以和大蒜、臭魚干一起炒著吃,這三種食材放在一起,可真是“怪味三菜”啊。
好在芹菜貌美,《呂氏春秋·本味》中記載:“菜之美者,有云夢之芹。”因而,它被善于發(fā)現(xiàn)美的文人稍加潤色,有了祈福之意。祈什么福?自然是像“文曲星”般文運亨通,譬如《詩經(jīng)·魯頌·泮水》中所記:“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這里的“泮水”是指古代學(xué)宮前的水池,學(xué)子在進京趕考前來此采芹祈愿,希望自己一舉奪魁。在《紅樓夢》第十七回中,賈寶玉說:“新漲綠添浣葛處,好云香護采芹人。”這“采芹人”就是指賈府的讀書人。
典故“獻芹之意”也和讀書人有關(guān),出自《列子·楊朱》中的故事。有人覺得芹菜好吃就送了人,朋友嘗后卻說:“太難吃了。”讀書人便用“獻芹”來謙言自己的見解淺薄,提前降低對方的期待值。如李白的“徒有獻芹心”,杜甫的“獻芹則小小”,都是此意。
韭菜:詩界“大明星”
韭菜不算難吃,韭菜餃子、韭菜炒雞蛋都是經(jīng)典搭配。但它有種刺激性氣味,吃完“口齒留臭”,久久不散,讓人十分尷尬。《清異錄》中記載,杜頤極愛韭菜,但別人實在受不了他的口氣,于是“候其仆市還,潛取棄之”,趁他不在家時把韭菜全都扔了。
詩人偏愛韭菜,因其代表盎然春意。比如,元好問吟詩道:“韭早春先綠,菘肥秋未黃。”能吃頭茬韭菜的時候,就說明春天到了。曹雪芹說:“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這描繪了一畦韭菜欣欣向榮地迎接春天的美好場景。宋代劉子翚筆下的“一畦春雨足,翠發(fā)剪還生”,更借韭菜的旺盛生命力道出了春天的蓬勃之美。
韭菜還是“春盤”的必備菜品。顧名思義,“春盤”是用一些能代表春天的蔬菜擺盤,一般選擇具有刺激臟氣功效的蔬菜。如晉代《風土記》中記載的“五辛盤”就是指盤中盛上蒜、韭菜、蕓苔、胡荽等“春菜”,有春氣蓬發(fā)之寓意。蘇東坡很中意韭菜,寫有“青蒿黃韭試春盤”“春盤得青韭,臘酒寄黃柑”“早韭欲爭春”等名句,表達他對暢意春日生活的向往。韭菜被詩人們一夸,轉(zhuǎn)瞬成了詩界的“大明星。”
苦瓜:教育界“大師”
886ce1e163cb782f60d4154ec3ad79f9苦瓜真苦,被稱為“苦味之冠”。清代學(xué)者屈大均卻說它是“君子菜”,曾在《廣東新語》中如此評價:“雜他物煮之,他物弗苦,自苦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其性屬火,以寒為體,以熱為用,其皮其籽皆益人,又有君子之功。”意思是說苦瓜即使與其他菜一起烹飪也不將苦味傳給其他菜,有君子“堅其志,苦其心”的品德;苦瓜雖苦,但全身上下都是寶,最能消暑滌熱、明目解毒,有君子無私奉獻的品格。
因此,苦不僅是一種味道,還象征敢于吃苦的美好品德。明末藝術(shù)大師石濤曾在《苦瓜和尚畫語錄》中寫道:“這個苦瓜老濤就吃了一生,風雨十日,香焚苦茗。”石濤自稱“苦瓜和尚”,在長達40年的游歷生涯中,他踏遍山河,不畏風雨,全身心投入藝術(shù)創(chuàng)作,用吃苦精神成就了自我。久而久之,苦瓜就有了教育意義,如清代汪森編輯的《粵西詩載》中有一首《食苦瓜》,告訴后人既要吃得苦中苦,又要明白先苦后甜的道理。
原來,這些蔬菜雖不是美食界的寵兒,但在其他領(lǐng)域發(fā)揮長處,成為文化界不可取代的“頂流”,豐富了我們的精神世界。我們也該學(xué)學(xué)芹菜、韭菜和苦瓜,不因短處自卑,而因長處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