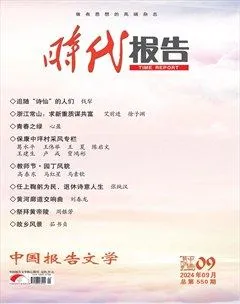一個山村的坐標
一
當一陣山風吹開太陽山麓鋪天蓋地的濃蔭,有一種境界是必然會出現的,這是一種人居山中、坐看云起的境界。
半個世紀前,有一首山歌這樣傳唱:“我家住湖北保康縣,馬橋公社靠西邊。西邊有座太陽山,山下瓦屋兩三間……”這山歌唱出了一個山村在時空中的坐標。相傳后羿射日,有一個太陽正好落在馬橋中坪的后山上,這山便叫太陽山,山下有一小片山中坪地,這就是中坪,一個山村就委委屈屈地趴在山谷里,被山風吹歪了的茅屋土房,東一間,西一間,一如山民身上襤褸的衣裳。那時這村里最好的房屋就是山歌里唱的兩三間黑瓦屋,那是中坪大隊部,也做過大集體的倉庫和食堂。一個被封存在大山深處的山村,像隱姓埋名一樣的存在,一看就知道,倘若沒有一條出路,這里就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山谷,這山谷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從村前流過的一條河——粉清河。
追尋一個山村的命運,其實就是追溯一條河流的命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養育的不止是生命,這大山的骨骼,這流淌的血脈,一直在塑造著這一方水土的人格或性格。你若要找一個性格最典型的中坪人,這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會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人,黃立杰。那是一個傳說中的老鐵匠,有人說那是個能人,有人說那是個狠人,有人說那是個“格球外”的人。“格球外”是這鄉下的土話,意思是很特別。
這樣一個老鐵匠,我還真要去見見他。在去見他的路上,我穿過一個鐵匠廣場。走進一間簡樸的辦公室,抬眼又看見一幅書法——鐵匠精神,這4個大字就跟鐵打的一樣,一筆一畫都閃爍著鐵一般的光澤。
這鐵匠情結未免也太濃烈了吧?我正站在一邊尋思,一個白眉老者不聲不響地走了進來。我打量著他,怎么看這就是一個平平淡淡的老人,神色安詳而又溫和。我還以為這是另一個人,一問卻偏偏就是他本人。我好奇地問他當過多少年鐵匠?他微微一笑,給我熱乎乎地端上了一杯茶,又遞上煙,便在一把農家的靠背椅上落座了。他不抽煙,不喝茶,守著一杯白開水,像個清教徒一樣默默坐著,嘴角始終帶著一絲淡淡的笑意。
這個傳說中的老鐵匠是共和國的同齡人,這輩子其實從未打過鐵,這鐵匠的名聲是在大集體時代練出來的。別看他個頭不高,但肩膀很寬,這是當年干農活、修水利練出的一副鐵肩膀。那年頭,一個總是搶著挑重擔的后生仔,18歲就當上了民兵排長,20歲入黨,隨后又當選為中坪八隊的生產隊長。那是中坪最大的一個生產隊,一隊之長管著500多號人,一個連胡子都沒有長黑的后生仔為什么能?在鄉親們看來,這后生仔既有能耐又特別能干,干起活來就像一個鐵打的漢子,為啥叫他鐵匠?打鐵還須本身硬。
黃立杰在當選隊長時就在鄉親們面前發下了一個誓愿,要讓大伙兒吃上白米飯。
這窮山溝里的山民做夢都想吃上一碗白米飯,但一看后邊那座山,這夢立馬就醒了,這不是白米飯,這是白日夢。看看吧,這山谷前邊是緊挨著粉清河谷的窘迫田地,后邊直抵山壁和石崖,“八山一水一分田”,無論你怎么辛勞地耕耘,收獲的只是世代的赤貧。為了多種幾棵養命的苞谷和土豆,他們只能攥緊鋤頭往崖邊上挖,往巖石縫隙里挖,你能到哪里去找一塊平整的水田?
當大伙兒都眼巴巴地仰望著后邊那座山時,這后生仔卻盯上了前邊這條河。遠遠看過去,一個像螞蟻一樣黑黝黝的身影,總是在粉清河邊尋尋覓覓,那亮閃閃的眼珠子圍繞著河流、河谷、河灘轉來轉去。
他在為這條河流尋找一條出路,為這山谷里的鄉親尋求一條活路。
這是從神龍架流來的一條季節性河流,她從冷峻逼仄的上游峽谷里一路奔涌而來,流到中坪,忽然蕩開一片寬敞的河谷,風吹拂著水面的波紋,散亂的水流在河床緩慢地流淌,一個人走到這里,連腳步也不知不覺地放輕了,放慢了。但你決不可小瞧了這條河,在某個季節乃至一夜之間,這條河就會變成一條泥沙俱下、縱橫決蕩的河流,頃刻間將這個山村沖得一貧如洗。當一場山洪席卷而去,緊接著地面就干了,從北岸河灘一直到后邊的山腳全是被洪水沖下來的亂石。
一個在這河邊生長的后生仔,從十幾歲就開始修水利,又懂水性,在反復觀察后他提出了一個設想,給這條水流散亂的河流開出一條暢通的出路,將大片亂石灘填平,改造成一片小平原。用現在的眼光看,這就是小流域綜合治理,而在當時,這個想法太大膽了,太超前了,在很多人看來這不是設想而是妄想。說來又非常幸運,黃立杰的這一設想經水利部門勘測論證后,還真是被上級采納了,隨后便付諸實施了。
那是一個全靠肩挑背扛的年代,當時的中坪大隊每年要出動上千勞動力,黃立杰帶領幾十個青壯年民兵組成了一支突擊隊,這些靠包谷糝和土豆養命的山民,為了吃上一口白米飯,先要把亂石灘上的石頭一塊一塊地背上岸,砌成一道新的河岸,再按100米長、50米寬把這亂石灘整成一塊塊田坯子,用石塊砌成田埂。接下來,還要用箢箕、背簍和獨輪車把山土搬運到這田坯子里來。那坎坷而沉重的腳步,在大山的陰影里一步一步地掙扎,這扁擔不知道挑斷了多少根,更不知壓爛了多少箢箕、背簍和獨輪車,但每一塊石頭、每一寸山土都知道,這條路走得有多么沉重而艱辛。這一走就是10多年,中坪大隊每年出動上千勞動力,那一個個像螞蟻一樣渺小的、黑黝黝的身影,像螞蟻啃骨頭一般在這亂石灘上填起了2000多畝的小平原,像袖珍版的江漢平原。在層巒疊嶂的大山區,這是唯一可以看見地平線的地方。
此時,正值芒種季節,一陣清風從粉清河的浪尖上掠過,帶著秧苗的清香吹到我的眼前,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倏忽而過,那恍惚的感覺忽又變得像眼前的秧苗一樣真切了,青蛙的吆喝聲一陣響過一陣,這秧田里還有泥鰍、蚯蚓拱出的一道道線條,這也是一條條生命的小徑,正在彌散的陽光和秧苗的影子伸向更隱秘的季節深處。
二
一個山村在大集體時代創造的奇跡,為一場劃時代的農村改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歷史進入一個轉折關頭,正當而立之年的黃立杰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1979年,中坪率先成為全縣第一個實現農村改革的試點村,那亂石灘上填起來的農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戶,那個效果就不用說了,鄉親們用一年的時間就打出了兩年的糧,把溫飽問題解決了。但又不能說,在分田到戶后許多問題也隨之而來,每到插秧季節,那些占據上壟的農戶往往就會搶占先機,攔截水渠,先澆灌自家的水田后,才把水放到中下壟去。這先機就是農時,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你在上壟把這個先機搶占了,那中下壟的農戶怎么辦,難道讓他們喝西北風去?
黃立杰一聽有人攔截水渠就趕過去了,這個農戶不是別人,是他嫡親的姐夫哥。他先是一口一聲地叫哥:“哥啊,這是集體的水渠,你不能只顧自己一家人,別的人家也要活啊!”
姐夫哥卻把眼珠子一瞪說:“如今分田到戶了,各家只能各顧各,我要不把這田種好,誰來管我的死活?”
黃立杰的臉眼看著就變得鐵青了,這個人從來是對事不對人,認理不認親,當年他當生產隊長時,連親爺老子遲到了他也要扣工分,你這親姐夫不講理,他又怎么認你這個親?既然你軟話不聽,他就把手硬生生地一揮,指著姐夫手里的鐵鍬說:“這水渠原來是什么樣的,你就給我恢復成什么樣,否則中下壟的損失你就要全部賠償!”
這話說得像鐵一樣硬,一個“鐵匠書記”名聲變得更響亮了。
如果這個人只有鐵面無私的一面,那還真是從門縫里瞅他。在他看來,這件事不是個別的事,這樣的人也不是個別的人,若從個人利益出發,誰都只顧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尤其是姐夫那句話,更是深深刺痛了他,這村里人難免有個三長兩短,若種不好田,吃不上飯,誰來管他們的死活?這村里以前再窮還有集體做靠山,隨著田地、農具、牲口分散到各家各戶,這集體形還在,神已散,只有大隊部留下的幾間空蕩蕩的黑瓦屋,這集體沒有經濟做支撐,成了一副空架子,有的人甚至想把這幾間黑瓦屋也拆光分光,那這個集體就真是一無所有了。
這不是一個山村的問題,這是農村改革中必然會遭遇的問題。在那大包干的熱潮中,一個最基層的農村黨支部書記已開始冷靜思考,如何讓鄉親們把自家的小日子過好,又能讓大伙兒把集體的大日子過好?他思來想去,這田地可以分,但集體不能散,這集體不是空的,必須以集體經濟做支撐,才能帶領鄉親們走出一條更寬廣、更踏實的路。
這條路黃立杰當時還沒找到,這是他認準的一個方向,也可以說是一次重新確認。
一個黑黝黝的身影,又開始在這山水間尋尋覓覓了,那亮閃閃的眼珠子又盯上了流經中坪的另一條河——蘇溪河。這河說是河,卻似一條溪,但一年四季不斷流,又加之地勢高,落差大,那落差產生的激流又催生了他的一個想法,這里能不能建一個小水電站?
這又是一個大膽設想。這個人真是太有想象力了,那時這山谷里的鄉親們還是靠松明子和煤油燈照明,何年何月才能用上電燈,很多人連想都還不敢想,而這個人不想就不想,一想就要在這山村里建一座水電站,簡直是異想天開!但對這個人的想法你又不能不信,看著那亂石灘上改造出來的小平原,吃著這香噴噴的白米飯,不都是從一個設想開始嗎,你能不信嗎?這也是黃立杰的底氣和信心,他對鄉親們又發下了第二個誓愿:“只要大伙兒像改造亂石灘一樣,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個小水電站一定能修起來,我們就再也不用燒松明子、點煤油燈啦。”
這個誓愿而今早已不是懸念,為了追尋黃立杰當年的足跡,我也走向了這條河,但我卻走不到他在40多年前抵達的那個高度,只能站在山腳下仰望。當我一眼看見那突兀而猙獰的危巖,腿肚子就連連打顫。莫說人類,這懸崖和深淵連猿猴也不敢走。而在當年,黃立杰帶著中坪村那些剽悍而又敏捷的漢子,在大山威嚴的注視下,一個個用繩子把自己吊在半山腰,有的仰頭朝崖壁上打炮眼,一錘子掄起來飛濺出一串熱汗,一錘子砸下去就迸射出一片炫目的火花,那手掌上磨出的血泡和虎口震出的鮮血,連同汗水一同流淌。他們一邊流血流汗還一邊相互招呼,“小心,小心啊!”一不小心,那腳下的懸崖與深淵就決定了你最終的命運。
中坪人就是以這種誰也不堪回首的方式再次改寫了一個山村的命運,他們幾乎在絕地上修建了一座蘇溪河水電站,接下來又建起了一座裝機容量更大的低茨河水電站。當一個被漫漫長夜籠罩的山村剎那間被明晃晃的電燈照亮,這里的山民第一次在夜晚看清了這個祖祖輩輩居住的山村,第一次在夜晚看清了自己的模樣,連影子看上去也是那樣清晰。
這小水電站不僅給鄉親們帶來了恒久的光明,也給一個山村從傳統農耕走向現代化新農村注入了強勁的能量。這是中坪村集體經濟第一個支點。有人說這是他們掘到的第一桶金,我覺得不是,小水電站給中坪村帶來了可持續性的集體經濟收入,這發電量除了以優惠價格供應村民和村里的企業,還有多余的電量輸入國家電網,每年為村集體盈利30多萬元。
誰都知道,水電站的裝機容量取決于流量,山溪型小河流的流量是有限的,但一個“鐵匠書記”從來不會在局限前止步。若就此止步,這一個村辦企業就像一輛獨輪車,又怎能帶動一個山村的4000多名鄉親一起奔小康?黃立杰那亮閃閃的眼珠子在山上轉來轉去,想為中坪尋找更能掙錢的門路。忽然想到縣里在馬橋鎮周邊先后已經開采了幾個磷礦,我們中坪的山上有沒有磷石呢?根據已發現磷礦的山脈推斷礦脈的走向,黃立杰判斷這山上應該是有礦的。一想到有礦,黃立杰心里就開始盤算了,一個村莊有了一座礦山,這村集體經濟就有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柱,但是怎樣才能確定這山上有沒有磷石?若要請勘探隊進山勘測,需要一大筆資金,找到礦了還好說,找不到礦一大筆錢就打了水漂。他心想中坪只有這么大,自己從小就上山放過牛、砍過柴,這山山嶺嶺、溝溝岔岔他都走熟了,何不先去找找看?這個人一旦有了想法立馬就會變成實干。他不動聲色跑去周邊的磷礦考察了一番,搞清楚了磷礦石長成什么模樣,還撿了一塊回來做樣品,然后便背著一把尖嘴鎬頭,一趟趟上山去尋找。這山上九溝十八岔,他也不知翻了多少道嶺,鉆了多少條溝,當他搜尋到翟家溝一帶,扒開一堆刺蓬,眼里驀地閃爍出一種奇異的光澤,那是一塊金黃色的石頭,很像磷礦石。他挖了幾塊石頭,背到襄陽市一家磷肥廠進行化驗,還真是磷礦石,而且是含磷量很高的磷礦石。
這消息在村里一下傳開了,當大伙兒奔走相告時,黃立杰卻在望著一座山長久地出神。
山上有磷這山就是一座寶山,但怎么才能開采出來呢?要說也簡單,別的村大多是采取大包干的方式,將礦山包給礦業公司或礦老板,村里從中拿提成。中坪人一開始也覺得這種方式最干脆,幾乎是坐享其成,可你跟人家一談價,才發現沒那么干脆簡單,一家礦業公司開出了價,每開采一噸礦石給中坪村提成一元錢。黃立杰一開始就知道對方會壓低價格,沒想到他們會把價格壓得這么低。
他瞟了對方一眼說:“你們沒有搞錯吧?我們賣石碴也不止這幾個價。”
對方沖他微微一笑說:“好商量,好商量。”
黃立杰一聽那話里有話,也微微一笑說:“那好,我先得跟咱們村民商量商量。”
黃立杰是村里的一把手,但他從來不是一個人拍板,更不會為那話里的話而出賣村集體的利益,這村里的大事都是交給村民們來商議和決策。村民們一聽人家開出這么低的價,一個個連肺都給氣炸了,大伙兒一致決定,這礦山決不能包給別人開,要開就自己開。這也正中黃立杰的下懷,只有把開采經營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村集體手里,才能進一步壯大集體經濟,讓每一個村民分享到礦山帶來的福利。
你要掌握這個主動權,那就要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苦和累。這開礦先要打通一條通向礦山的路,為了不耽誤開礦,黃立杰還提出了一個兩不誤的方案,一邊修路,一邊從外邊請開礦師傅來勘測礦脈打礦洞。這路還沒有修通,機械設備上不了山,黃立杰又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把機械設備一塊一塊拆卸下來編上號,搬到山上后重新組裝。這是個笨辦法,可黃立杰說:“我們山里人除了力氣還有什么呢?”他當時正感冒發燒,大伙兒都勸他在一邊歇著,他搖搖腦袋說沒事,出一身透汗就好了。只見他把頭一埋,背一拱,兩腿往后猛地一蹬,一塊鐵板就上了背。村民們心里贊嘆,真是個名不虛傳的鐵匠書記!在爬山時,那身體一直保持30度角的姿態。黃立杰肩膀上扛著拖拉機拆下的一個大件,渾身直冒汗,口里還喊著號子,那號子是鼓勵他自己的,千萬別被壓趴下。那粗獷的號子聲帶著金屬的余響在大山的上空回蕩。可這肩背上的鐵家伙一落地,他一下就虛脫了,差點一頭栽了下去。幾個村民趕緊把他扶住了,要送他下山去休息,他搖搖頭,又和大伙兒一起按照編號組裝機器。一個“鐵匠書記”就是以這種鋼鐵般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演繹和詮釋著中坪村的傳奇,其實這人間又有誰是真正鐵打的漢子,每個人都是血肉之軀,但無論苦難和堅強,血與汗,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磨礪,黃立杰還真是像淬火后的鋼鐵一樣冷靜而淡定了,用他的話說,人是五谷蟲,越做越英雄,天天做就習慣了。
為了開礦,中坪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而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卻未迎來輝煌。這礦辦起來后,鄉親們都指望這個“鐵匠書記”來管理,但按當時的政策,村支部書記不能在企業兼職,黃立杰也希望有個懂業務又有管理經驗的人來當礦長,讓企業按企業管理模式獨立經營。誰知這個村集體企業開了一年又一年,原以為種下的是一棵搖錢樹,結果卻挖了一個大窟窿,不但未給村集體交一分錢,還倒虧了400多萬元。那些背得起石頭和鐵塊的中坪人,為了這背不起的冤枉債一下炸了鍋。在群情激昂之下,一個“鐵匠書記”被推上了中坪磷礦第一責任人的位置。
黃立杰接手磷礦后,先對賬目進行清理,在清理的過程中他也越來越清醒了,那前任礦長不是不懂經營管理,而是不為村里經營,是為他們自己和親朋好友關系戶經營,這些人把錢拿到礦上來投資,卻不是按利潤分成,都是按20%的利率掙高息,利息轉本,本又生息,越滾越多,那賣礦的錢還不夠支付高息,這又怎能不虧損?黃立杰隨即通知那些在礦上掙高息的人趕緊把錢拿走,過期不再計息。這一個漏洞被堵住了,黃立杰接管后的村磷礦只用了一年多時間就把400多萬元的窟窿給填平了,第二年就開始給村集體上繳盈利了,而接下來那錢一年比一年交得多,這礦山真的成了一棵搖錢樹。
誰知幾年過后,又刮起了一陣風,當時不少地方借企業改制之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要求把村辦企業一次性全部賣掉,一些集體企業的管理者也趁機把出賣集體資產變成了牟取暴利的機會。誰都知道,這礦山誰買去誰發財,黃立杰若是從一己私利出發,他也可以乘機把這個集體磷礦賣掉,作為負責人還可以搶占先機,優先集資購買。磷礦上的會計說,如果黃書記順應了那潮流帶頭買下礦,那現在他個人名下的資產已經不止3個億。可是黃立杰說:“我要那么多錢做什么?”他自己和少數幾個人發了財,那幾千村民怎么辦?這村里公共事業建設的錢從哪里來?為此,他一直頂著壓力堅決不賣。有人說“不換思想就換人”,他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可以換人,但這個思想不能換,你們必須找出根據來,在黨章和憲法里,哪條規定說發展集體經濟犯法?”
村人說,這是“鐵匠書記”最鐵的時候,如果沒有這樣的鐵心,沒有這種鐵打的公心,中坪磷礦早已改頭換面,現在都不知道姓什么了。在黃立杰的堅持下,如今,這個村辦企業已形成集開采、加工、運輸、銷售于一體的產業鏈,為中坪及周邊村民提供就業崗位500余個,每年為村集體盈利8000多萬元,還要為國家納稅8000多萬元,多年來一直是保康縣名列前茅的納稅大戶之一。
這是一棵已長得根深葉茂的搖錢樹,但黃立杰心里十分清楚,本村的礦產資源比起鄰村是最少的,終歸有一天要開采殆盡,這也迫使他提前謀劃新的出路,那就是逐步走出資源依賴性,向綠色生態經濟的發展方向轉化。滿山遍野的葛根吸引了他的目光。
葛根是一種在南方山區天生地長的雙子葉植物,這是治病的良藥,卻不苦口,那味道挺好,還有一股特別香醇的滋味兒。我小時候頭痛發熱,出麻疹,拉肚子,母親就把挖回來的葛根搗成汁液給我喝。我父親在勞累一天后肩酸背痛,回來喝上一杯葛根茶,那身子骨慢慢就變得舒坦了。這雖說是好東西,但在我家鄉從來沒有把葛根做成一種產業,在走進中坪之前我也從未見過這種產業。這一次,我是眼睜睜地見到了。從中坪礦業走進中坪葛業,一股源自山野的植物香味撲鼻而來,這是葛根特有的香味。
透過封閉式的玻璃櫥窗,那無塵車間里安裝了一條條自動化生產線。展廳里擺放著琳瑯滿目的各種葛根食品。這眼睜睜看見的和我想象的反差太大,我原想那粗壯的、土得掉渣的葛根,只是在土作坊里加工,沒想到一個山村竟然建起了這樣一個現代化食品加工企業。
一個反差接著一個反差,這車間隔壁的展覽室里有一個直播演示平臺,在我的印象中,直播帶貨的都是很潮的年輕人,這平臺背后卻坐著一位60歲出頭的大姐。這讓我感到有些對不上號,這個我對不上號的人就是中坪葛業的創始人趙禮敏。
這是一個勤勞熱心、腦子活絡的女能人,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別的村民都把眼光盯著那剛剛分到手的一畝三分地,這個農家婦女就開始進行各種嘗試,她在自己的農家小院里試種巨峰葡萄,在家里的菜園子試種植冬暖式大棚蔬菜,還養過南疆黃羊。這每一個嘗試,她都是在中坪村邁出的第一步,而她的第二步就是想在嘗試成功后帶動鄉親們一起致富。這些嘗試都沒有失敗,卻一直難以形成一個產業鏈,她也一直邁不出第二步。在摸爬滾打十幾年后,趙禮敏捕捉到一個商機,她發現葛根粉在市場上銷路不錯,這野生葛根在中坪山上就有,只要人勤快就能挖下來,但如何加工提煉葛粉呢?這個難不倒她,她到處拜師學藝,那些能用土法提煉葛粉的老師傅往往都藏在深山里,這一趟山路就要走十幾里,有的甚至是幾十里。她不知吃過了多少次閉門羹,但終于感動了一個荊門的師傅,那是個留過學的企業家,他向這位誠心學藝的農村中年婦女傳授了葛根提取技術。
這加工得有生產場地啊,她看上了村里的幾間黑瓦屋。這早先是中坪大隊部,也做過大集體的食堂和倉庫,趙禮敏又在這里開起了一個土法上馬的小工廠,全廠職工最早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她自己,一個是丈夫宦忠清。這樣的小本經營和小農經濟一樣,就像“一滴露水養活一棵草”,單憑一家一戶的打拼既難以完成產業升級,更無法形成一條產業鏈,只能被擠壓在產業鏈最低端,掙幾個微薄的辛苦錢。
這是小農經濟天生的局限,趙禮敏一直想要邁出的第二步還是遲遲邁不開。
這個局限被早已有心發展葛根加工的黃立杰看在眼里,他對趙禮敏說,這不是一個人一家子能夠干的,一家做只能是小打小鬧。他鼓勵趙禮敏加入村集體經濟陣營,鼓勵她依靠集體力量帶領大伙兒一起干。中坪村集體經濟能夠健康發展做大做強靠的是黃立杰為代表的黨組織,村里的黨員共有90多名,設立了村黨委,下設3個黨支部。趙禮敏就成了村黨委重點培養對象,而她在這么多年的左沖右突中,對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局限也有了越來越深切的體驗,她創業的初衷就是想帶動鄉親們一起致富。由于她悉心鉆研技術,村里也不斷加大扶持力度,修建廠房,添置設備,一家個體小作坊就發生了質的變化。或者說是一種從作坊到現代企業的升華。2008年1月,中坪村黨委將葛根加工定為村集體經濟的朝陽產業,成立了湖北中坪葛業開發有限公司,注冊了“汾清河”產品商標,趙禮敏被任命為公司總經理。在追夢路上,她邁出了新的一步。
隨著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葛根資源的需求量也越來越大。以前,這加工廠的原材料都是村民到山上去挖,那野生葛根長在犬牙交錯的山巖中,東一根,西一根,你要把它從巖石的縫隙里挖出來,既艱難又會損害生態植被,有的山區已封山育林,禁止山民上山開采。這個問題黃立杰其實已提前看到了,中坪葛業若要真正走向規模化經營,就必須先走出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對野生葛根進行人工栽培。為此,他們與湖北省農科院農產品加工與核農技術研究所簽訂研究開發葛根新食品的技術合作合同。在專家指導下,趙禮敏經過幾年試種,終于將野生葛根在農田培育種植成功,這為“公司+農戶”的產業鏈打通了第一環,中坪葛業免費為農戶提供葛根種苗和種植技術,村里還專門調劑土地建立葛根種植基地,以保底價回收農戶在山坡、山地種植的葛根。他們還帶動周邊6個鄉鎮及神農架、房縣等地的農戶種植葛根,這一帶是葛根生長的黃金地帶,現已建成葛根種植基地1萬余畝,培養造就了一批新型農民,葛根種植戶年均增收在萬元以上。
這產業鏈的第一環已經完全打通了,趙禮敏又瞄準了第二環,把粗加工推向深加工。趙禮敏每邁出關鍵的一步都是借助科技的力量,那腦子里冒出了一個什么念頭,或是遇到了什么難題,她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向專家求教。此前,他們用傳統方法生產的葛根粉只能用開水沖泡,而現在的生活節奏很快,她在市場調查中發現,那些年輕的消費者希望用冷水也能快速沖飲。在專家的指點下,趙禮敏和廠里的技術人員通過一次次試驗,終于攻克了這個技術難點,生產出了冷水速溶葛粉,現已成為中坪葛業的主打產品。隨后,他們又生產出了400目超微葛根粉,把葛根從粗加工推向了細致入微的深加工。這兩項研發技術都獲得了國家發明專利,給中坪葛業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其產品品質和特色在行業中已遙遙領先。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坪葛業又于2021年投資1600多萬元擴建生產車間,裝配了全自動化生產線,從單一的葛根粉加工發展到葛片茶系列產品、橡子粉加工、紅薯粉加工,還開發出了琳瑯滿目的休閑小食品,已形成了種植基地—加工生產—多渠道營銷的全產業鏈,銷售額從最初的幾萬元躍升到如今的2000萬元,這條綠色生態產業鏈條還在不斷延伸。
眼下,趙禮敏從總經理的崗位上退居二線,而她還在一心一意輔佐新上任的年輕總經理,為拓展市場、培訓直播銷售人才,她又變身主播,帶領直播間的觀眾走近葛根、認識葛根:“北有人參,南有葛根。人參是那樣小巧,葛根卻是這樣粗壯。我們中坪山川秀美、生態良好,這得天獨厚的環境為葛根培育創造了優良的生長條件。野生葛根一般需要十幾年的生長周期,有的甚至要長幾百年,大家看,這就是一根生長了幾百年的葛根,這么粗壯的枝干,我一只手都圈不住,你別看它土得掉渣,卻有著豐富的營養和保健價值……”她一邊講述,一邊示范如何沖泡葛根粉:“我們先用冷水沖開,再一邊倒入開水一邊攪拌,這樣一杯綿密香糯的葛根粉就沖泡好了。”
中坪葛業是村集體經濟的第三個支點,中坪村在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還從浙江千島湖鱘龍科技有限公司引進了生態鱘魚養殖項目,總投資3億多元,分兩期建設。我來到這里時,一期項目已建成投產,這里養殖的第一批鱘魚共有100多尾,最大的已長到二三百斤。鱘魚渾身都是寶,尤其是魚子,被譽為“軟黃金”,一斤價值上萬元。魚子的重量一般為魚體重的十分之一,一條二三百斤重的鱘魚取魚子做成魚子醬就能賣幾萬元,據估計這一批鱘魚的總價值就超過2000萬元。鱘魚對生態環境特別挑剔,一個能養鱘魚的地方,那環境和水質就不用說了。這魚池里的水是從粉清河引來的,從太陽山照過來的陽光,反射著粉清河的水浪,一條條大魚攪動著水池,忽而下潛,忽而上浮,一閃眼,我看見一條鱘魚翹起的尾巴,一轉眼,又看見了一條鱘魚露出的腦袋,不知還是不是剛才那一條。
三
中坪,這一小片燦爛的土地,原本是一個窮鄉僻壤的山村,遙想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在改革之初的那條思路,40多年來經過一步一步的探尋、一步一步的驗證,從貧困走向溫飽,又從溫飽走向小康,如今中坪人已過上了平淡富足的生活。現在可以確認,這是一條以集體經濟做支撐的共同富裕之路。
如今中坪的產業從一輛獨輪車已形成4個輪子一起轉的良性循環,而這集體經濟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坪磷化。走進中坪磷化的辦公樓,我腦子里又一次出現了強烈的反差,這座老舊的辦公樓自從蓋起來后就沒變過,門還是那個門,院還是那座院。隨著歲月的色澤一層一層地加深,那灰白色的墻壁不知不覺變成了暗黃色,風吹雨打與烈日炙烤的痕跡相互滲透又各有層面,在蔓延的苔蘚中呈現出堅韌的紋理。此刻,太陽很大,一座老建筑投在地上的陰影比建筑本身更清晰。這陰影掩蓋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過往,也許只有通過過來人的回憶中,才能追溯一個山村數十年來的塑形過程。
一個平平淡淡的老人,一個傳說中的“鐵匠書記”,此刻就坐在這里,坐在那把農家靠背椅上,一坐就是幾十年,這個人,這把椅子,還是那樣簡樸而又牢實。10年前,黃立杰就從村黨委書記的位置上退居二線,大伙兒現在都叫他老書記。而在創業職工們的挽留下,他仍擔任中坪磷化公司董事長。這是一個沉默寡言的老人,我不問話,他不開口,而一旦開口,這個看似平凡的老人,那眼神里便透出一股不平凡的光澤。這眼光不像一個鐵匠那樣銳利,卻像粉清河一樣明澈。這讓我暗自驚訝,一個活到了70多歲的老人,竟然還有一雙明澈透亮的眼睛。但凝神一想又不覺得驚訝了,一個人經歷了漫長而坎坷的人生,就像一條河流穿越了重巖疊嶂、幽谷險灘,才會變得如此明澈而透亮,仿佛可以把世間的一切看透。
當我問這個董事長的年薪是多少,他的回答又讓我吃了一驚:“10萬元。”
我扳著指頭一算,他的月薪只有8000多元錢,其他的公司高管都跟他差不多。那些中低層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跟這些高管的工資也差不多,在礦上務工的村84411420d6d00d1e961851bfc5ab39e2民年收入也在8萬元以上。無論8萬以上還是10萬元,這收入在農村均已達到富裕的程度,而這村里最富裕的就是村集體,一個4000余人口的山村,擁有5億多元的固定資產,從村集體到村辦企業沒有一分錢的負債,他們也不用舉債,每年都留足了流動資金。這么多錢怎么用?有人說,老書記在任時把村里的每一分錢都攥得出汗,但一撒手就是大手筆。現在換了新書記、新班子,在用錢上也跟老書記一樣。那么這些錢撒在哪里了?這是我很關心的,更是村民們最關心的。
老書記喝了一口白開水,對我豎起一個指頭,這擺在第一位的就是民生福利。
山村里建起水電站后,他又發下了一個誓愿,要讓中坪的鄉親們像城里人一樣喝上自來水。這大山里其實不缺水,走進山野,到處都能聽見清亮的流水聲,但一口水隔著一座山,山里人只能背著水桶去山澗里汲水,走兩三里路去粉清河里挑水。為了讓村里人喝上干凈的山泉水,村集體投入200多萬元,將蘇溪河水從十幾里外引入1000多戶村民家里,整個工程不要村民出一分錢,只要每家買一塊水表。自己買的水表,自己放心,自己負責把水表管理好就行。水價像城里一樣實行階梯式水價,但價格只有城里的十分之一,每月人平均5方水,每方只要5毛錢。水,還是原來的山泉水,只是換了一種流向,而山里人也換了一種活法,只要擰開家里的水龍頭,就能喝上清甜的山泉水。
一個難題解決了,緊接著又有一個老難題,中坪雖說是一塊山中坪地,但山上還有3個村民小組,當一縷一縷的炊煙在白云深處飄出來,你才發現那深山老林里還有人煙。這些散居深山的村民和獨居戶,被高山深壑重重阻隔,形單影只地活在寂寞人間,沒有電,沒有水,沒有路,很多人一輩子打光棍。為了把這3個村民小組搬遷到山下來,村集體又投入了大筆資金,把一戶戶村民從傾斜的土屋里搬進了嶄新的家園。讓他們走出深山,是人類對自然的讓步,這深山里原本就是不適合人類居住和種莊453c24918fbfef036c046094933e09e8稼的地方,過度開墾必然會加劇水土流失、泥石流和山洪暴發等自然災害,在加害自然的同時又加害自己。讓他們走出深山,是人類文明的進步,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交通、飲水、用電、通訊、就醫、上學等種種難題,這是為山里人開辟的一條重生之路。
隨著中坪村集體經濟逐年壯大,中坪村也面臨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歲月不饒人啊,在逝水流年中黃立杰的頭發不知不覺就白了一多半,當年那些跟他一起背石頭、扛鐵塊的青壯年,一個個都是白發參差、滿臉褶皺。黃立杰看著這正和自己一樣慢慢變老的一代人,又對鄉親們發下了一個誓愿,用中坪磷化的利潤為村民購買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讓年滿60歲的村民也能像城市職工一樣享受養老退休金。這在農村可真是一個新鮮事,這大山里的人從沒聽說農民還能退休,一個農民一輩子到頭都是農民,只要還有一口氣,那手里就攥著一把鋤頭。當黃立杰提出要給村民買社保,鄉親們一開始都覺得有些不靠譜。此前,縣社保局曾征求兩個富裕村的意見,問他們愿不愿意買,結果都不愿買。既然人家不愿買,咱們中坪村為什么要買?有的人把社保當成了那些到處拉客戶的商業保險,還有人建議干脆把錢給分了,飯到嘴里才是飯,錢到口袋里才是錢,免得把錢投給別人卻打水漂。
這山村的農民都是實在人,只是“鐵匠書記”更實在,他一邊扳著指頭給村民算實賬,又一連發出三問:“這錢攤到每個人手上又能分到幾個錢?分了又能用多久?咱們農民為什么就不能退休?以前這村里窮,咱們有想法也沒辦法,現在有了集體經濟做支持,就應該讓村民享受到和企業職工一樣的退休待遇。別的村不愿干,咱們干,我就不相信國家會虧待咱們!”
中坪村的鄉親們算了小賬,又算大賬,大伙兒算來算去心里不踏實,黃立杰這回破天荒地搞了一言堂:“買!大家再信我一回!”從2007年開始,中坪磷化每年為村民購買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給6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健康補貼,一年就要投入700多萬元,而讓村民們驚喜的是男人一到60歲、女人一到55歲,社保局的錢就打到個人賬戶上了!如今已有1100多位村民辦了退休手續,開始領退休養老錢了。據磷化公司財務總監褚應強粗略算了算,按年人均15000元收入算,僅退休金一項每年就有1700萬元流進中坪村村民的錢袋子。現在4個村民就有一個60歲以上的老人,若不是提前繳了社保,他們又怎能安度晚年?
為了探個究竟,我隨意走進一戶農家,那瘦高的老漢叫宦成俊,現年62歲,已拿了兩年退休金。老伴周昌菊,比他大1歲,也比他多拿了一年退休金。老兩口一年的退休金加起來就有4萬多元,每年還在遞增。他們還種著一畝三分水稻田和苞谷地,還有自家菜園,一年的收成加起來也有1萬多元,自家種的糧食和蔬菜瓜果也吃不完,每年還要蒸幾百斤苞谷酒、殺一頭兩三百斤重的大年豬。老兩口有一兒一女,兒子考上大學時,村里還獎勵了一筆錢,如今在襄陽市工作;女兒嫁到了粉清河那邊的河南坪,過著自己的小日子,不用父母操心,而父母有了退休金,也不用兒女多操心。
宦成俊一家的日子就是中坪村每戶普通農家的日子,老兩口過得很愜意,很自豪:“這日子比我兒子在城里還過得好咧,可惜他把戶口遷走了,想回也回不來了。以前那是養兒防老,如今有了退休金,我們也不指望兒女給我們養老了,等老到走不動了,我們就住到醫養中心去……”
老兩口說的醫養中心,是中坪村的一座地標性建筑,在走進這個村之前,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這座背靠太陽山的大樓。在我的印象中,一個鄉鎮有一座衛生院,一個村里有個“一村一醫”的衛生室,那就算農村醫療的標配了。而中坪村在2015年就建成了全市首家村級綜合性醫院,2022年又興建了中坪醫養中心。這哪像一個村級醫院啊,總投資超過5000萬元,占地5000多平方米,共11層。這比一般縣級醫院的設備還好,開設有1UFvt3S5q+TAtAoSBlzJgA==急診科、內科、外科、婦科、口腔科、中醫科、康復科、理療科等10多個臨床科室,配置了四維彩超(CT)、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等現代化診療設備和標準化供應室和手術室,一個個穿著白大褂的醫師和護士,正給來看病的村民治療,這其中有副主任醫師、主治醫師、執業護士。在這里,骨科手術、腹部手術都可以做。若有治不了的病,這里與城里的大醫院直接聯網,可以邀請專家前來會診,也可以用救護車直接送往大醫院,患者回村后,這里可以提供后續康復治療,不用患者來回奔波。村辦醫院不僅解決了中坪村村民的就醫難題,也給馬橋鎮周邊和神農架的群眾帶來了方便。
醫養中心還有一個重要功能,為村民提供一站式康復養老服務。不僅解決了那些空巢老人的生活難題,也為在外創業的年輕人解除了后顧之憂,除了中坪村村民,還有周邊的村民來這里治病或養老。一個從鄰村來的老人,患有肺源性心臟病,這種慢性病原來需要常年進城求醫,一個往返在路上就要奔波四五個小時,由于子女在外打拼,老人無人陪伴,治療很不方便,更要命的是這種慢性病隨時都有猝發的生命危險,許多患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只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撒手人寰。自中坪醫養中心建成后,這位老人的難題在家門口就解決了,他在樓下治療,樓上康養,一旦有什么危險在第一時間就可以搶救,這就是集醫養于一體的最大好處。難怪宦成俊和周昌菊老兩口想要住到醫養中心來,看了設備齊全、服務周到的養老公寓,連我都萌生了在這里養老的念頭。
這些空巢老人都是有兒女的老人,而這人間最不幸的還是孤寡老人,他們的命運說來又各有各的不幸,但在中坪村都享受到了同樣幸福的晚年生活。中坪村有個小微社區叫幸福坊里,是中坪第一批五保戶的集中安置小區。宦廷樹老人是中坪四組的一位五保戶,他年輕時上山砍柴,被樹砸傷了手臂,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沒有得到及時救治,從此落下了終身殘疾。那年頭,一個窮山溝里的殘疾人連自己都養不活自己,更別說娶妻生子,他感覺不是一只手臂殘廢了,而是這輩子都廢了。眼看年歲漸老,一想到那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老年生活,他就充滿了絕望。而在他絕望之際,村里給他買了養老保險,這讓他感覺又有了依靠和活下去的希望。當他年滿60歲,他不但能領到退休金,還比別的村民多了一筆五保金,村里又把他安置到這幸福坊里。他的房間是一居一室,后邊是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室內還裝了空調和有線電視,小飯桌上擺著火鍋,正燉著一條魚。這70多歲的老漢越活越精神,看上去只有60多歲,他喝著20多元錢一斤的酒,抽著20多元錢一包的煙,又是給我端酒,又是給我遞煙,那感覺不是一個五保戶,而是一家之主,那真是一種主人的感覺。這當家作主也是要有底氣的,這底氣就來自墻壁上貼著一張收入明白卡,他每年的退休金、五保金加起來有33488元,村里每年還給他另繳380元的醫保資金。我查了一下,2023年全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691元,一個中坪村的五保戶不但沒有掉在平均值后面,反而遠遠超過這個平均值。這些賬目一筆一筆都在一張明白卡上,貼在進門那道被陽光最早照亮的墻壁上。當年,他在分田到戶時按下了一個鮮紅的手印,在這張明白卡上,他又按下了一個鮮紅的手印。
在幸福坊里,我見到的每一個五保戶什么都不缺,別的村民家里有的東西,他們都有,他們唯一缺少的就是兒女,但他們并不缺少人間的溫情與關愛,這村里的干部、黨員、團員、鄉親們和中坪小學的孩子們時常像家人、兒女和孫兒孫女一樣來看望他們,這些無兒無女的老人也享受到了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在他們眼里,我也算是一個遠道而來的老親戚吧,當我同他們揮手告別時,這些老人站在太陽山投射過來的陽光里,揚著笑臉說:“常來走走啊!”
告別幸福坊里,我又走進中坪小學。在一個偏遠的山村,孩子們邁開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上學難,黃立杰一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上過學,而文化的缺失讓他對文化知識愈加渴望,在教育上他一直是大手筆投入。這是一座山村小學,也是一所從幼兒園至六年級的寄宿制完全小學,設置了9個教學班,全校設施按照城市示范小學的標準建設配置,教學質量一直名列全縣同級同類學校前列,并入選襄陽市首屆文明校園。校園里有一棵高過屋脊的香樟樹,一棵樹就撐起滿院綠蔭,地上的濃陰如樹冠一樣漫開。這棵樹,是一所學校的標志,也是一個山村的標志,我圍著它轉了一圈又一圈,仿佛無限循環的小數……
四
我在中坪轉悠了3天,這是保康縣最大的行政村,而一個山村又有多大呢?我從東走到西只有7公里,從北到南只有兩三公里,這就是一個山村的境界,全村面積還不到18平方公里。中國很大,中坪太小,但若仔細一想,你又覺得這個山村不小了。鄉村,就是鄉土上的中國。我已走過無數山村,大山深處,這樣的山村無處不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振興,終歸取決于鄉村振興。中國的每一個鄉村,都深深介入了中國的歷史,在一定程度決定著甚至改變了中國命運的走向。
中坪,這一小片燦爛的土地,原本是一個窮鄉僻壤的山村,40多年來從貧困走向溫飽,又從溫飽走向小康,如今已過上了平淡富足的生活。這個山村不但探索出了一條以集體經濟做支撐的共同富裕之路,還創造出了一種可推廣的鄉村治理模式。
鄉村怎么治?關鍵要看誰來治,而關鍵少數往往是推動發展的關鍵因素。在中坪村的發展史上,一個“鐵匠書記”就扮演著這樣一個關鍵角色。他是這村里公認的第一號能人,說話從來是鐵板釘釘,干事那是斬釘截鐵,那鐵的紀律、鐵的信仰、鐵的責任、鐵的執行,在一個山村就集中體現在一個“鐵匠書記”身上,這就是“鐵匠精神”。這也得罪了不少人,有的還是他的親人。這里的民風既有淳樸的一面,也有強悍的一面,有人點燃過他家的柴垛,有人甚至拿著火藥闖進了他家里。對此,黃立杰一向無所畏懼,卻也逼著他往更深處思考。這樣一個4000多人口的山村,若要長治久安,僅靠“能人治村”或“鐵腕治村”是行不通的,只能用依靠法律和制度來治理,這最大的法律是憲法,最小的制度則是村規民約,而村民自治是憲法確立的一項基本社會制度。早在1991年,中坪村就制訂了第一個村規民約,其后又經過多次的修改和完善,現在的村規民約包括總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農業生產及農田管理、山林管理、村莊規劃、戶口管理等12章。這每一條、每一款都是中坪村的鄉親們一條一條商議出來的,具有很強的操作性,經村民大會表決通過后,就成為了中坪村全體村民的行為準則。這是中坪在村民自治上邁出的第一步,也是一個山村在鄉村治理模式上的一次關鍵轉型,從“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和村民自治。
對此,中坪人說得更簡單:“鄉村怎么治?事情怎么辦?村民說了算!”
這里就以中坪村的村容村貌和環境整治為例吧。如今很多人都在懷念那種古樸的、原生態的自然山村,或許只有驀然回首,你才能猛然看清它的本質。在整治之前,中坪和許多農村一樣,廁所都是用石塊和磚頭砌成一圈的露天茅廁,房前屋后不是牛欄就是豬圈,鄉親們吃飯的時候,那些亂哄哄的綠頭蒼蠅從糞坑里直接飛到了鍋邊上、飯碗里。一到雨天,糞坑里污水漫溢出來,流到哪里,哪里的水就變得又黑又臭。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坪村以環境整治為突破口,聘請專業規劃設計團隊編制修訂村莊建設規劃,又到每個村民小組去聽取鄉親們的意見。這一個村民小組就是一個自然村,每一個自然村都有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的提出要打通一些還沒有通組到戶的斷頭路,修通全村的公路循環線,有的提出要對老化而雜亂的電線、網線、通信線纜進行統一規劃和提質改造,而村民們反應最強烈的環境污染問題,當務之急是要修通全村的污水管網。這9個村民小組,一共提出了10個具體建設項目,但要將這10個項目一下子全面鋪開,資金有限,施工場地也有限,最多只能開工5個。這又是一道選擇題,這個選擇權交給了村民,由各組村民推選出61名代表,進行投票表決。在投票之前,設計方現將一幅環境整治效果圖攤開,對每一個項目逐一講解,對村民提出的每一個疑問都耐心地予以解答。村民代表在仔細看過、聽過、問過、討論過后,然后現場投票、唱票,村“兩委”班子成員、村民組長和駐村干部在現場監票,按得票多少選出了生活污水管網改造、公路循環線和通戶道路建設等5個優先開工的項目,全程都有現場錄像,一切都是在陽光下公開的,像粉清河一樣透明。
這是中坪村實施鄉村治理和村民自治的一個經典案例,也是一種可推廣模式,2018年,中坪村被司法部、全國普法辦授予“全國民主法治示范村”榮譽稱號。
只有讓村民參與共謀村級治理,老百姓有了當家作主的感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活他們的主動性和內生動力。那規劃就像一幅最美最新的圖畫,這些工程不用村民們掏一分錢,也不要他們投工投勞,一切由專業施工隊負責施工,這村里,誰都希望一幅最美最新的圖畫化作美好的環境和幸福生活。可中坪村卻不是一張白紙,在施工的過程中,難免會占用一些農家的菜園、屋坪,還有一些打在紅線之外的圍墻要往后縮,那些閑置多年的老舊雜屋也要按規劃拆除,這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牽涉到老百姓實實在在的利益,這也是施工隊最擔心的,生怕與村民發生沖突或出現阻工現象。他們還真是想多了,這些由村民說了算的事情就是不一樣,他們在施工過程中從頭到尾沒有一個村民阻工,有的村民提前就按照紅線扒了自家的老舊雜屋、拆了自家的圍墻,給工程讓路,有的村民還主動到工地上來幫忙,村民王綿福還將自家的挖機開進了改造污水管網的施工現場,連人帶機器一起干,這是白干,不要一分錢。施工隊不想讓他白干,要給他開工資,這個豁達又風趣的漢子笑呵呵地說:“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啊,我們應該來幫下忙,但可不能幫倒忙。”
眼下,我正在走的這一條條路,早先是灰撲撲的泥土路,然后是3米多寬的水泥路,現在是一條通組到戶的道路,連接著高速公路的循環線,一路上凌霄綻放、花果飄香,連飛出花叢的蜜蜂、蝴蝶、蜻蜓,都散發出迷人的香味。這個季節,葡萄還沒熟透,在掛滿露珠的枝葉間水靈靈地閃動,桃樹低著頭,那白里透紅的桃子已長得有些忘形,看著就想呷一口。
第一次走進這個山村,我還以為走進了一個生態旅游度假村,一幢幢錯落有致的民居背靠青山,坐擁碧水,這村里是見縫插綠,見空造景,村在園中,房在花中,人在景中,如天人合一般融為一體,那清澈透亮的波光映襯著一個個活動廣場、休閑平臺、鄉村舞臺、風雨廊橋、荷花塘、運動噴泉,這不只是風景的點綴,這就是中坪人的生活。這山谷里的鄉親們如今已過上了城里人應有盡有的生活,這個山村卻還保持著一派濃郁的鄉村風情。
一個山村的面貌,往往就是村民的精神面貌。這個山村給我最清晰的印象就是特別干凈,打心眼里覺得,這里人的心里也特別干凈。人的心靈越干凈,做人的境界就越高,如王國維先生所云,有境界自有高格。而在一個山村,這樣的追求又深深地植根于鄉土,那世代相傳的家訓和家風就是鄉土中國內在的精神紐帶,傳承著人世間的良善與德行。“道德去彌遠,山河勢不窮”,中坪村在依法治村、村民自治的同時,將傳統美德與新時代鄉村治理實踐相結合,讓無形之德浸潤在靈魂里,體現在細微處。曾幾何時,在村民的腦袋和口袋同樣貧困的年代,有的人為了搶先澆灌自家的水田而挖斷村里的水渠,有些鄰居為了一塊宅基地或菜園的分界而拿著尺子量來量去,那真是寸土必爭,搞不好就會打得頭破血流,而現在這樣的爭吵幾乎絕跡,每個人心里都有了另一種尺碼,那是一把道德的尺子。這村里的“十星文明戶”“五好家庭”“好公婆”“好媳婦”,都是由村民按心中的道德尺碼評選出來的,也是他們為自己立起的標桿。這些鄉村道德模范做人做事說來都平平淡淡,只要你像他們一樣孝敬老人、愛護孩童,把夫妻關系、父子關系、婆媳關系、鄰里關系處好了,把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凈凈,你也會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
大山無言,這大山里的人一直默默地追求著自己想要做的人,想要做的事,從不張揚自己做了什么,一個山村的文明之光卻沒有被大山遮蔽,中坪村連續三屆被評選為全國文明村,這意味著中坪人不但走出了一條最適合自己的路,還打開了一個很大的世界。
對于一個山村的變化,若用日新月異來形容未免太簡單了,你很難在短時段里窺見其實質性的變化,這是在潛移默化中的嬗變,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發生的。我沒有看見中坪的昨天,只看見了中坪的今天,若是一個40年多前從這山谷里走出去的人,在暌違多年后重返故鄉,他也許已經找不到回家的路,但那條粉清河依然在陽光下流淌,她跟明鏡兒似的,映照著一個山村的流逝歲月,照亮了一方水土如今的現實。這條河也是一個山村的坐標,可以讓一個歸來的游子重新確認自己。而“鐵匠書記”就是在一次次重新確認中,對中坪村的鄉親們做出了一個個莊嚴的承諾,這每一個承諾的兌現,其實就是一個共產黨人對自身使命的一次重新確認。
老書記黃立杰在與我的交談中說得最多的就是自己的使命,當我問他在村里發揮出了哪些關鍵作用時,他喝了一口白開水,清清嗓子說:“中坪村能有今天,不是哪一個人干出來的,這是咱們全村的鄉親們一起干出來的。”
這一句簡樸而又干練的話,讓我腦子里迸出了一個詞“共同締造”,一起干出來的就是共同締造,這美好環境與幸福生活就是中坪村的鄉親們共同締造出來的,從一個鄉村到一個國家,只有共同締造,才能從生活到精神上走向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本質就是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統一。
在告別中坪的那個午后,我和現任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黃森林有一次暢談。這個正當盛年的漢子,也有一雙明澈得近乎透徹的眼睛。他原本是馬橋二級水電站的正式員工,后因國企改制下崗,他在商海打拼多年后,一個機遇降臨了,湖北省實施“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旨在為農村培養留得住、用得上、懂技術、善經營的復合型、應用型人才。這一培養方向正是黃森林追求的方向,他隨即報名應試,考入了華中農業大學大專班。他的初衷原本是多學UoUBI6l8SDtdmjXp4q7Qug==一點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帶領中坪村的鄉親們進一步開拓新型產業,沒想到中坪村的鄉親們對他寄予了深情厚望,在2014年村“兩委”班子換屆時,老書記退居二線,他以高票當選村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這一屆新班子肩負著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歷史使命,他們在村集體經濟打下的基礎上確立了自己的雙重使命,一是要守住村集體經濟現有的基本盤,一是要進一步拓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產業鏈。在這一屆班子的主持下,村集體先是投資1600多萬元對中坪葛業進行了改造升級,建起了中坪醫養中心,從浙江千島湖鱘龍科技公司引進了鱘魚養殖項目。而現在,中坪村又瞄準了未來的發展方向,那就是打造一個集觀光、休閑、采摘于一體的農旅融合特色產業區。
他在描述,我在想象,想象未來的中坪村又將是怎樣的一個境界。在他那一臉風平浪靜的外表下,我隱隱聽見了一種聲音,像是血脈里的流淌聲,又像是粉清河滔滔不絕的流淌聲,水滋養著風,風生水起,一個山村未來的境界在我的想象中變得愈加生動而鮮明了。
責任編輯/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