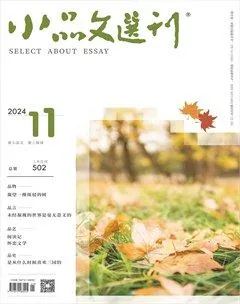懷戀文學(xué)
要說與文學(xué)結(jié)緣,還得追溯到我的童年。幼時我即喜愛作文課。每逢老師繪聲繪色地朗誦,我總是激動不已。小學(xué)四年級時,老師總把我的作文作范文讓同學(xué)們評閱。于是我的幼小的自尊在老師的褒獎呵護(hù)下更是不斷膨脹,于是便有了習(xí)文之癖。有一次作文,記得是記一次有意義的勞動,我便生澀地創(chuàng)造了“分不容等”這樣的別詞,后來知道了原本就有“刻不容緩”這個成語。
再后來,“文革”了,學(xué)校不再上課,學(xué)生也無須讀書。我便從學(xué)校混亂的圖書室借閱了幾本較厚的小說:《紅日》、《鋼鐵巨人》、《烈火金鋼》以及《魯迅雜文》等。在許多時日里,我輪番著讀這幾本書。再后來,圖書室關(guān)閉了,無奈,我便從鄰居同學(xué)家借了高年級的語文課本去讀。
突然有一天,學(xué)校通知學(xué)生復(fù)課。匆匆到校,便見校園里堆了蒙古包那樣規(guī)模的書堆。旁邊一字排開的是我昔日尊敬的語文老師,當(dāng)時他們的統(tǒng)稱是“牛鬼蛇神”。
同學(xué)們集合齊了,校造反派領(lǐng)導(dǎo)宣布:點火燒書。片刻,滾滾濃煙把圖書室乃至這些語文老師的藏書都化作灰燼。此時,我感覺,我的文學(xué)夢都破滅了。
燒書的火勢絕不似點燃別的燃物那樣旺盛,而只是一個勁沖散著、噴放著濃烈的黑與白的煙,我趁著煙的掩護(hù),從火里搶出了幾冊那個年代反映文學(xué)動態(tài)與文學(xué)理論的《文藝報》,趁著混亂,裝在衣襟下。
那次離校,我就與學(xué)校徹底告別了,當(dāng)年底,也就是1967年的12月,我便懷揣幾冊《文藝報》與瑪拉沁夫的《春的喜歌》踏上了漫長的軍旅生涯。
緣由幾冊《文藝報》的導(dǎo)引,我的生命歷程埋下了文學(xué)的火種。那時節(jié),在軍營里,除了訓(xùn)練、施工,然后就是“天天讀”(領(lǐng)讀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當(dāng)新兵時,我?guī)讉€早上就背誦完了《老三篇》(《為人民服務(wù)》、《愚公移山》、《紀(jì)念白求恩》),剩余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反復(fù)翻閱那幾冊《文藝報》和瑪拉沁夫的《春的喜歌》以及僅有的小說《紅巖》……這種空泛但疏淡的閱讀依然重新點燃了我的文學(xué)激情。我還是不斷地練筆,做寫生式的日記,或者寫點當(dāng)時時髦的“紅太陽”詩。
后來,我居然做了師政治部的新聞文化干事,好像可以堂而皇之地做文學(xué)了。然而這種喜悅沒有維持多長時間就又夭折了。事情是這樣的:當(dāng)時我作為師級機(jī)關(guān)文學(xué)創(chuàng)作員,參加了某軍區(qū)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班,當(dāng)時適逢要求寫軍內(nèi)“走資派”;面臨這個陌生而苦澀的主題,我實在是提不起一點激情來,反倒覺得文學(xué)不那么可愛了。于是我一門心思寫新聞,寫人物通訊,做官樣文章。沒想到至此丟棄文學(xué),便開始了苦澀而漫長的寫作官樣文章的歷程。
轉(zhuǎn)業(yè)地方后,對文學(xué)的酷愛還沒有泯滅,我依然循著“文”的方位,尋找自己的生存環(huán)境。然而現(xiàn)實卻又一次擊碎了我的文學(xué)夢。地方機(jī)關(guān)要求的不是你能吟花作月,寫出什么優(yōu)美的散文,做出什么小說詩歌之類,而是要你能夠駕馭機(jī)關(guān)公文、領(lǐng)導(dǎo)講話或是理論研究的文體,為存計,還是棄文從政吧!這種選擇與文學(xué)竟隔絕了近20年。寫了20年官樣文章,盡管取得了一些浮名躁績,但我的感覺是麻木與懊喪。審視我數(shù)百萬字的陳舊文稿,更深刻地感覺是寫了一堆廢紙,消磨了大半個生命!
想起文學(xué),心頭依然隱隱作痛。特別是步入中年后、歲月遲暮的時候,我清晰地感到:人生最終留給我、陪伴我走向生命盡頭的依然是曾經(jīng)給予我激情與夢想的文學(xué)。文學(xué)對于我就是全部,我會在遲暮之年重新尋找文學(xué),培植激情去涵養(yǎng)生命。我會在文學(xué)的感動中,在文學(xué)的陪伴下,度過以后那些難于激動但依然充滿希望的歲月。
選自《山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