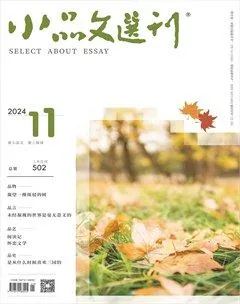誤入葦塘深處
久在北京城里生活,城里眾多的公園和綠地總給人能工巧匠精心設計的秩序感,處處凝結著人為的美學智慧。暑假,我從北京返回故鄉,早上五點多鐘,出去跑步,小時候常來捉魚摸蝦的那條大河展現在我眼前的,卻是另一番質樸、純真的天地。南朝梁代鐘嶸曾經在《詩品》里引湯惠休語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如果說城市園林是一種錯彩鏤金的美,那此刻呈現在我眼前的則是一種出水芙蓉般灑脫、自然之美。《二十四詩品》中有“沖淡”一品,其曰:“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想必眼前的景象恰恰符合這“沖淡之美”吧。
河水在這里放緩了腳步,停滯成好大一片葦塘。靠近水邊時,整個人變得非常清爽。微波粼粼的水面十分寬闊,水邊茂盛地生長著蘆葦、菖蒲、柳樹等,不遠處的水面上竟然還有亭亭玉立的荷花。河岸邊,有悠閑的朋友在專注垂釣,那場景像極了明代畫家吳鎮筆下的《漁父圖》。經過他們身邊時,我突然想起那首廣為流傳的小詩:“路人借問遙招手,怕得魚驚不應人。”于是我的腳步變得小心翼翼,生怕發出的一丁點兒聲音會驚擾到他們的魚兒。
遠處岸邊,高大的柳樹搖曳著婀娜的枝條,像妙齡少女秀發飄逸。柳樹枝頭,棲息著一只體形較大的白色鳥兒。我定睛一看,是只白鷺。年少時,我好像從未在家鄉的河道中見過白鷺。平日里多在宣紙上描繪優雅的白鷺,此時的邂逅可謂平添一分驚喜。不遠處的水中,還有數只白鷺在嬉戲,有的在梳理羽毛,有的在水中覓食。才女李清照當年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寫出“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的名句。沒想到,數百年后的今天,我于村外的一處葦塘,竟得以欣賞到與之極其相似的場景。
水畔簇擁著一叢一叢的菖蒲和蘆葦。菖蒲的頂端,已經長出了赭紅色的蒲棒,藍色、綠色、紅色、黃色的蜻蜓在毛茸茸的蒲棒間翻飛起舞。我又想起喜歡的一位畫家——河口濕地畫派創始人石建f4362b3e15e1f119ca9ddb5ca8e53d1774c8ad5d0d517309712e9be13f4ad406勛老師擅長的濕地美景圖。他曾畫過一幅以蒲棒和紅蜻蜓為主體的作品。畫面中,密密麻麻的菖蒲交織,數十只紅蜻蜓在菖蒲上飛舞,身姿輕盈,姿態各異。我正想,石老師一定是見過類似的場景,才會創作出這韻味十足的意境佳作吧。突然,水面上有魚兒翻跳,恰如李賀那句“老魚跳波瘦蛟舞”,但凝神看去,又不見了魚兒的蹤影,只在一小截荷梗上,見到一只長嘴短尾的藍色小鳥臨水而立。我躡手躡腳地走近,生怕它被我驚飛。嗬!竟然是只美麗的翠鳥。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觀察一只翠鳥,它的艷麗色彩讓人著迷。我不禁感嘆,此處葦塘真是寶地。
此時,清晨的太陽已經升起,氣溫逐漸升高。我只好戀戀不舍地離開這片濕地,原路返回村莊。今日跑步,竟誤入葦塘,邂逅白鷺、翠鳥、荷花、蘆葦、菖蒲……真如陶淵明誤入桃花源那般美好。
選自《羊城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