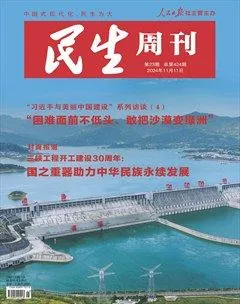為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農村留守未成年人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當前階段出現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黨和國家對此高度重視。早在2016年,國務院就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公共服務不均等、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問題的深刻反映,提出要積極開展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關文件也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預防作出了法律規范,提供了明確遵循。
近年來,農村留守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多發頻發,個別案例成為社會熱點,證明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在執行層面還需要不斷加強,需要持續完善留守兒童法治關愛與保護的社會治理機制,積極做好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預防工作。
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形勢比較嚴峻
前不久,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今年3月發生在河北邯鄲的初中生被害案涉及的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核準追訴。
核準追訴,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已過訴訟時效的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行使的特殊職權,目的在于讓有罪者受到嚴厲懲罰。
然而,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核準追訴的程序性流程和已過訴訟時效的案件的相關規定無二,沒有更多特殊的規定。在對成年人的刑罰當中更多強調“行為”,即客觀行為中的“危害行為”這一構成要件,但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更多關注“人”的因素。
課題組在結合廣東省科技廳“百千萬工程”農村科技特派員第二輪重點派駐項目“科技多元化賦能鄉村振興示范與推廣”和廣東省委教育工委高校“雙帶頭人”教師黨支部書記工作室建設項目推進中,調查相關數據顯示,2023年批捕、起訴未成年人犯罪總體上升,農村留守兒童違法犯罪形勢依然嚴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審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處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在最高人民檢察院2024年5月31日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3)》中顯示,2023年共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6855人,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8954人,同比分別上升73.7%、40.7%。通知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52194人次,對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落實犯罪記錄封存49524人,同比分別上升0.46%、49.98%。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中三大問題尤為值得關注:侵害婦女兒童犯罪行為呈上升趨勢,涉網絡犯罪問題突出,家庭監護缺失問題突出。

圖為云陽縣人民法院干警和孩子們在一起。(圖/CFP)
2021年至2023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為留守兒童的案件共1835件,占比22.94%;被告人為單親家庭的案件共556件,占比6.95%;被告人為再婚家庭的案件共223件,占比2.79%;被告人為孤兒的案件共19件,占比0.24%,許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關愛和教育。
從這三大問題中不難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比之大。
那么,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分析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應該如何預防、有效減少農村留守兒童的犯罪?如何建立農村留守兒童法治保障對策?
農村留守兒童犯罪主要有四個方面原因
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社會大環境的影響。低學歷、低經濟決定了大部分家庭的父母為了改善生活條件、增加家庭收入外出務工,使正需要父母教育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父母缺乏陪伴,使得社會不良風氣極易蔓延到農村留守兒童這一整片區域。
其二,家庭、學校對農村留守兒童教育不到位,甚至缺失。未成年人的法治觀念需要通過學習習得,犯罪低齡化證明了法治觀念習得的不及時、缺失。
厭學、失管且無業的青少年是犯罪的主要群體,其中侵財類犯罪尤為突出。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多方面原因的綜合作用。由于對學校生活產生抵觸,厭學、失管的青少年選擇逃課或輟學,從而脫離了正規教育的軌道。
其三,留守兒童心理問題可能導致在行為上缺乏自我約束,更容易作出沖動的決定,從而走上犯罪道路。主觀上的厭學加上學校、家庭管理的不到位,使得這些兒童更加放縱、游手好閑。
而正由于教育的缺失、管理的缺少和經濟上的拮據,使得這些兒童的人生觀、價值觀扭曲。他們遠離學校生活,往往缺乏社會所需的學歷和基本工作技能,這使得他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由于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和明確的未來職業規劃,他們可能變得閑散,缺乏動力去積極面對生活。這種困境使得他們更容易陷入邊緣化的狀態,與社會主流逐漸脫離。
其四,犯罪主體不懂法不畏法。部分農村留守兒童心智不成熟,情感強烈不穩定,易激動,亟須學校和家庭教育引導。部分留守兒童由于認識水平低,不懂法或者沒有守法意識,很容易實施一些違法犯罪行為。等到逆反心理發展嚴重時,他們就會抗拒社會道德和法律,從而形成不畏法的無所謂的態度,甚至有意做出違反法律的動作。
進一步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機制
在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預防和治理工作中,不僅要做到依法懲治,形成高壓嚴打態勢,更要做好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預防,建立協同治理制度、完善核準追訴制度、加強監護制度,構建社會、學校、家庭、立法、執法等多元化聯動體系,改進完善和發展普法模式,進一步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機制。
—應建立協同治理制度,構建多元化教育主體體系。不服法、不懂法類青少年兒童往往是校園里的“燙手山芋”,利用社區資源可以協助學校開展該類青少年兒童的普法活動,從不同角度切入,讓青少年兒童更容易接受普法教育。
與法律工作者的合作還能夠幫助學生與同輩少年建立聯系,在法律工作者的引導下,學生可以參與到各種法治教育活動中,如模擬法庭、法律辯論等。這些活動不僅能夠提高學生的法律素養和實踐能力,還能夠讓他們結識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起更加緊密的同輩關系。
改進家庭教育引導機制至關重要。在留守兒童家庭中,父母教育的缺失、父母法律思維的不完善等對青少年犯罪來說是不可忽視的誘因。
—應完善核準追訴制度。刑罰作為懲罰犯罪的手段,只有在不得已時施用,本身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不追究刑事責任,有可能不足以防止社會危害性,因此需要完善低齡未成年人核準追訴制度。
—應加強監護制度。改進家庭教育引導機制至關重要。家庭教育的缺失對青少年犯罪來說是不可忽視的誘因,然而規制家庭教育行為,不能僅靠家長的自覺性,更需要政法機關的強制性和約束力。
前期調查評估實際上是開展工作的前提,只有對犯罪家庭進行正確的、準確的評估,才能因人而異制定具體的督促監護令,確保督促監護令的可行性;后期的回訪工作可以動態調整,節約司法資源,若改造效果未達預期的,則可以視情況延長督促期限或者變更督促項目等。
—應加強普法隊伍建設。定期開展普法教學主體交流學習工作,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建設高素質青少年法治專門隊伍。
一是要加強思想政治建設,結合留守兒童犯罪特點,做到對癥下藥,把理想信念教育擺在隊伍建設第一位;二是普法隊伍需嚴于紀律,維護社會正義,做到遵法守法,盡職盡責;三是要加強理論學習,只有不斷夯實理論基礎,從理論學習中持續汲取營養,才能切實打造“信念堅定、勇于擔當、紀律嚴明”的法治專門隊伍;四是提高自身覺悟和職業操守,根據社會的需要,培養出高素質的普法法治專門人才。
—在數字時代,應開發利用好互聯網線上普法模式。目前普法模式在線上的應用僅有微信宣傳等少數手段,線上普法可進一步拓寬渠道,加大應用投入,完善青少年普法產品,搭建短視頻、微電影、網絡短劇、AR、VR等產品平臺,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實現青少年法治教育多元化。
(作者潘星容為廣東金融學院法學院副院長、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廣東省法學會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通訊作者陳蘋蘋為廣東金融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