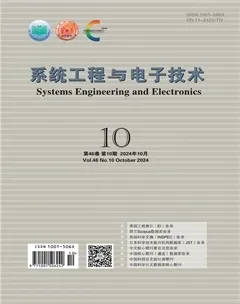組織戰略匹配管理中的語義建模方法研究綜述








摘 要:戰略匹配是戰略規劃的一個子內容,側重于檢查戰略規劃與戰略行動的一致性。通過戰略匹配,組織的項目、計劃或個人的計劃與組織的長期業務目標保持一致。主要從語義建模角度闡述了這一領域的最新發展。為了引出這一關鍵技術領域對于組織戰略匹配的重要性,首先討論戰略匹配的基本概念及其發展,特別是通過核心要素分析軍事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特征,有助于理解大型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復雜性。然后,分析現有語義建模的主要方法,受限于當時的技術發展水平,這些方法仍有許多缺陷和不足,當前的語義技術應用也有一大部分是為解決這些遺留問題而產生。最后,總結戰略匹配管理中的語義技術應用,希望為該領域技術的后續發展提供參考。
關鍵詞: 戰略匹配; 組織; 企業架構; 概念建模; 語義建模; 本體
中圖分類號: E 92 文獻標志碼: A""" DOI:10.12305/j.issn.1001-506X.2024.10.16
Review of semantic modeling methods of enterprise strategic
alignment management
WANG Tao LIN Mu1, LI Xiaobo ZHU Zhi ZHU Yifan WANG Weiping1
(1. College of Systems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2. Unit 92941 of the PLA, Huludao 12500 China)
Abstract: Strategic alignment is a sub-domain within the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that ensures consistency betwee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 organization’s projects, programs, and individual plans align with its long-term business goals by achieving strategic alignmen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antic modeling.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critical technical field to organizational strategic alignment,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evolution of strategic alignment i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ategic maching problem is analyzed in military organizations through core elements, which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strategic alignmen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Moreover," the existing main semantic modeling methods are analyzed, which still have many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in technic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As a solution to these remaining problem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urrent semantic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has been developed.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semantic technology in strategic alignment management is summarized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is area.
Keywords: strategic alignment; organization;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concept modeling; semantic modeling; ontology
0 引 言
確保項目交付能力與組織戰略規劃保持一致,一直是組織戰略管理領域的重點關注問題。管理人員在基于項目進行規劃時,經常面臨項目最終交付能力與戰略規劃目標錯位的困擾。隨著項目數量的增加和項目間依賴性的提高,發現規劃項目群內部的不一致和冗余也變得愈加困難。尤其在國防建設領域,軍事能力的形成高度依賴于集成的中長期過程,而軍事能力的運用則高度依賴于標準化的流程。國防組織是一種典型的統一型組織[1],具有高度標準化、集成化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其能力的形成特別依賴于內部成員的協調,以及組織戰略規劃與執行的協調和匹配。為了保證戰略規劃與執行的協調一致,國防組織通常需要做出兩個方面的決策:規劃決策與評估決策。規劃決策旨在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確定優先發展項目,以實現組織的戰略意圖;評估決策則通過檢查項目交付的能力,確定其是否達到預期的戰略目標。對于統一型組織而言,規劃、建設、評估和執行通常由特定的細分組織(利益相關方)負責。考慮到大型組織的復雜性,項目的最終交付能力與戰略規劃目標之間容易產生偏差。因此,大型組織,尤其是統一型組織,需要一種建模和分析方法,以確保項目的交付能力與組織戰略規劃的一致性,并在組織內形成對戰略意圖的共同理解,從而提高內部協作和集成的效率。這類問題通常被稱為戰略匹配問題。
戰略匹配在現代管理學領域的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重點在對組織內部的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體系進行規劃和管理,并使其適應組織的內外部環境。該概念最早由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Venkatraman等[2]提出,其中的“匹配”指的是組織的業務戰略與IT基礎設施在戰略和功能兩個維度上的一致性[35]。相關研究集中在戰略匹配建模及以此為基礎的企業評估,包括戰略匹配度、企業績效及其關聯關系的實證研究[615]。需要指出的是,也有研究使用“業務與IT匹配(business-IT alignment, BITA)”表述相類似的概念[1617],特別是國內的相關研究[1823]。近年來,對于戰略匹配問題的研究已經擴展到了組織的其他方面[2431],如項目管理、人力資源、質量控制、企業數字化等,而不再局限于IT體系的規劃和管理。
隨著戰略匹配研究的逐步深入,知識在戰略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實際上,早在1996年,Saint-Onge[32]就指出,隱性知識對戰略匹配至關重要,這些隱性知識主要涉及組織內部人員的價值觀和整體文化,在“數據信息知識智慧”的轉化過程中占據核心地位。此外,有研究發現,高層決策者的知識儲備對戰略匹配的成功實施具有重大影響[33],共享語言、共享領域知識和知識系統則是推動戰略匹配的關鍵因素[34]。
語義建模是一種將自然語言文本轉化為計算機可理解的形式的方法,是實現共享語言、共享領域知識和知識系統的有效手段,在相關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各領域規劃人員發現,企業架構作為戰略匹配知識建模工具擁有巨大的潛在優勢。因此,自1987年Zachman框架[35]提出以來,各類架構建模框架,如開放組體系架構框架(the open group architecture framework, TOGAF)、美國國防部體系結構框架(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 DoDAF)、統一體系架構框架(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 UAF)便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于戰略匹配研究。相關文獻探討了以企業架構作為工具研究戰略匹配問題的方法[18,3638],架構建模框架被視作一種實現工具并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架構建模框架的諸多限制使其在具體實踐方面受到諸多詬病。例如,一項關于架構建模工具的調研指出,TOGAF的主要缺點是“描述過于冗長,大約有800頁(目前縮減為500多頁),對于大部分使用者來說都太復雜了”[39]。Kotusev[4041]指出,現有的架構建模框架所定義的概念起源于非經驗來源,缺乏成功實施的證明示例,并且在多個重要方面偏離了組織中的實際應用。
除了企業架構,語義網[42]也是被廣泛地用作語義建模的工具。語義網的概念由互聯網之父Berners-Lee在1998年首次提出,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個包含7層技術內涵的體系結構,其中本體層采用了資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的擴展語言RDF集構(RDF schema, RDFS)和網絡本體語言(web ontology language, OWL),這些技術可以幫助專業領域的用戶構建機器可讀的概念模型。由于互聯網的廣泛應用,語義網技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大量的開源工具和資源為其提供了支持,同時也引起了架構建模語言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近年來,結合語義網技術和架構建模語言來研究戰略匹配問題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例如,Hinkelmann等[43]結合企業架構建模和企業本體,提出一種使用語義元建模方法解決戰略匹配問題的思路,該方法用RDFS取代統一建模語言(unified model language, UML)作為架構的元建模語言。Roach[44]認為,現有的架構建模語言在信息系統的行為和治理方面存在不足,因此選擇使用RDF來設計戰略匹配的元模型以解決這個問題。Fuchs-Kittowski等[45]基于語義網的概念設計開發架構建模的語義協作工具,用于支持企業架構的協同開發。在國防和軍事領域,Hoyland[46]提出一種方法,將語義網技術應用到基于系統理論的架構建模中,用于解決美軍聯合條令的可重用性評估問題。Das[47]介紹了一項基于語義網技術與美國國防部能力使命柵格(capability mission lattice, CML)相結合的概念演示研究,用于從裝備論證的早期方案中識別可能的設計缺陷。
過去,人們習慣于使用企業架構框架對戰略匹配問題進行描述,但是近年來的研究已經證明語義網技術作為企業架構框架的替代工具具有巨大的可擴展性,對于解決現有架構建模框架在戰略匹配問題研究中的諸多限制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以國防組織的戰略匹配問題為研究對象,在介紹戰略匹配基本概念的基礎上,分析目前常用的語義化知識建模方法及其語義建模技術的相關拓展應用,期望從語義建模的角度重新審視戰略匹配問題,為戰略匹配中的知識管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1 戰略匹配概述
通常情況下,戰略是使用自然語言來進行闡釋的。決策者借助戰略規劃[48]這一過程,將戰略決策內容具體化為統籌安排的戰略行動,并將這些行動轉化為具有指導性的文本。戰略規劃的主要內容包括形勢研判、指導思想、目標任務、總體布局、資源保障、關鍵步驟及落實舉措。一般情況下,這些內容構成了戰略規劃作為一個綱領性文件的核心描述。
戰略匹配可以被視為戰略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側重于檢查戰略規劃與戰略行動之間的一致性。通過戰略匹配,組織能夠確保其項目、計劃或個人的計劃與組織的長期業務目標保持一致。戰略匹配模型(strategy alignment model, SAM)是該研究的基礎,如圖1所示。這里,“匹配”或“對齊”這一術語強調了一致性在實現組織戰略中的關鍵作用。
通過查閱相關研究資料,總結出以下幾種戰略匹配的定義。
(1) 戰略匹配的早期定義是業務與IT的匹配[2,5]。其涉及戰略契合與功能集成兩個方面問題,涵蓋4個組成部分:戰略契合是保持組織外部定位和內部安排的一致性,由業務戰略和IT戰略組成;功能集成是保持業務要素和功能要素的一致性,由組織結構流程及IT結構流程組成。相關研究還特別強調組織作為一個整體與外部環境的匹配。
(2) 基于項目的戰略匹配[4953]。這種定義認為在組織中實施項目組合管理可以提高戰略實施和項目交付的成功率,從而縮小戰略制定與戰略實施之間的差距[52]。組織通過項目投資組合管理實現資源分配與戰略的一致性,并通過項目組合對整體戰略的支持程度來評估戰略匹配的程度[53]。
(3) 基于能力的戰略匹配[5456]。強調通過管理具有適應性的能力[54]實現組織的戰略匹配,通過管理一組能力,使組織具備“在多種環境和條件下部署和使用能力而不調整其性質”的特性[55],能力被視為連接業務和IT的媒介[5657]。
(4) 跨領域的戰略匹配[58]。文獻[58] 認為戰略匹配超出了業務與IT匹配的范疇,是通過戰略、結構、技術、文化、環境等多種因素之間的匹配實現的組織績效指標。強調結合運用戰略管理、企業架構、基于能力的規劃和投資組合管理4個領域的概念和方法來實現戰略匹配。
從上述戰略匹配的定義中可以看到,戰略匹配已經不再僅僅關注組織結構、流程和IT之間的匹配。現代組織利用IT來支持運營和管理已非常普遍。對于那些在IT應用方面已經取得顯著成就的組織來說,僅僅強調IT對組織戰略規劃的重要性是不夠的。因此,綜合考慮多種要素及其匹配問題,是確保現代組織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保持戰略規劃與目標一致性的必要手段。同時,數據和知識作為大型組織戰略管理中的一種特殊資源,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IT迅速發展的今天,信息將更多地作為底層資源出現,而“數據信息知識智慧”這一邏輯將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并成為推動組織戰略匹配的基本路徑。
2 戰略匹配核心要素軍事特征剖析
國防組織的戰略匹配問題在相關研究中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國防組織作為典型的復雜巨系統,因具備特殊的使命性質,其戰略內涵更為豐富。即便只從戰略規劃與執行的層面考慮戰略匹配,其復雜性也遠超過一般的商業組織。因此,本文選取國防組織的戰略匹配作為研究對象,深入剖析戰略匹配的特點和復雜性。
項目和能力已被確認為戰略匹配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國防組織在戰略匹配上的領域獨特性。但對于國防組織來說,其還包括一些自身領域獨有的概念。鑒于此,考慮將更多元素納入戰略匹配的核心要素中,并將知識視為連接這些要素的關鍵資源,從而構建戰略匹配的基礎概念,戰略匹配過程如圖2所示。
2.1 以能力為核心的匹配
以能力為核心的戰略匹配在軍事組織中最為常見,且應用廣泛。選擇能力作為核心過渡要素,基于以下3個主要原因。首先,能力描繪了組織“在多種環境和條件下部署和使用能力而不需調整其本質”的特性[54],這種特性在研究復雜多變環境下的戰略匹配問題時非常有價值。其次,軍事能力既是戰略目標的一種體現,也可作為衡量組織戰略目標實現程度的指標,這通常是其他要素所無法比擬的。最后,能力提供了與其他要素相互關聯的機會,可以通過多種要素的組合方式來定義,這使得能力在戰略匹配研究方面天生具有語義上的優勢。因此,能力作為核心過渡要素,起到了連接組織戰略需求和技術背景的關鍵作用,幫助組織確定關鍵技術和發展優先級,制定戰略發展路徑和規劃路線圖,從而成功完成戰略任務。
基于能力的規劃被廣泛運用于軍事組織的發展規劃中。能力作為核心要素,可以自下而上地被定義為5個層次[59]。
(1) 能力的基礎輸入:包括裝備、人員、培訓、基礎設施、后勤支持等方面。
(2) 能力:執行某項行動的能力。
(3) 能力域:達成某項使命的能力。
(4) 軍事組織能力:某一兵種或領域的能力。
(5) 國防組織能力:支持與國家政治和經濟利益相一致的戰略能力。
這5個層次的能力是相互關聯和支持的,每一層為上一層提供基礎和支持,從而實現從戰略目標到底層資源的匹配。例如,美國國防部在2018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其總的戰略目標是“建立一支更具殺傷力的聯合部隊”。為此,定義了包括核力量、空間賽博領域、導彈防御、聯合作戰在內的共8項軍事組織能力。再向下分解,由美軍的聯合能力域(joint capability area, JCA)定義,由9項能力域和上百項能力組成。最終,通過基于能力的規劃方法,使用這些相互關聯的能力對軍種需求論證工作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包括能力評估、戰略制定、投資決策、能力組合管理、基于能力的部隊建設和作戰規劃。這些明確的能力需求促進了各軍種聯合作戰能力的生成,有效避免了軍種各自為戰、重復建設而導致的能力冗余和經費浪費問題。
2.2 以流程為核心的匹配
以流程為核心的戰略匹配是從運行角度研究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一種方式。流程匹配是軍事組織保持良好運行的必要條件,同時以流程作為核心過渡要素可以很好地彌補以能力為核心進行匹配時的不足。從語義角度來看,能力作為核心過渡要素可能需要大量的語義解釋。對于第2.1節給出的5個層次的能力來說,隨著能力層次的提高,能力的描述也更加宏觀,對其進行語義解釋也越困難。例如,當提及“聯合能力”時,其內涵和組成是相當模糊和不明確的。相比而言,“攔截能力”是一種更容易被人理解的概念,人們可以輕易地聯想到使用“攔截成功率”來衡量,進而給出一個符合普遍認知的定義。因此,對于頂層能力來說,在組織內部形成統一的認知并非易事。
相較于能力,流程更易于在組織內部形成統一的認知。流程具有明確的組織邊界,涉及該流程的相關組織成員在與處于同一組織的成員進行交流時,對流程的理解不會產生太大的分歧。因此,將能力匹配到流程上是一種很好的解釋方式。此外,流程為戰略匹配的跨域重疊問題提供了一種解耦能力。能力與能力之間無法清晰地界定,當提及“防空反導能力”和“攔截能力”時,并不知道其嚴格的邏輯關系,也就是說能力間經常存在重疊的問題。因此,通過將能力映射到流程,再通過流程檢查能力的冗余和差距是一種常用的方法。
另一方面,從組織結構的角度來看,以流程為核心的戰略匹配可以更好地適應組織結構的變化。在國防組織中,由于任務和戰略的變化,組織結構經常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流程為核心的戰略匹配可以根據任務和戰略的變化靈活地調整流程,從而更好地適應組織結構的變化。
綜上所述,以流程為核心的戰略匹配可以更好地解決國防組織考慮流程管理中的匹配性問題,雖然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對流程的界定和劃分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模糊性,但仍然是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可以更好地理解國防組織的戰略匹配問題。
2.3 以作戰概念為核心的匹配
出于對組織未來長期目標進行定義的需要,組織還需要一種能夠綜合多種要素的概念,描述組織在未來所應該具有的能力和運用這種能力的流程和方法。在商業組織規劃中,這通常被稱為“愿景”,而在國防組織中,這一概念通常被作戰概念所取代。當然,一些大型非商業組織也有使用作戰概念進行規劃的實際例子,因此這一概念也并非國防組織所獨有。例如,美國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60]將作戰概念定義為描述如何使用系統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期望或最終系統作用的整體高級概念。因此,對于國防組織來說,作戰概念需要進一步細化。美國國防部早期使用聯合作戰概念(joint operations concept, JOpsC)定義了一系列不同細節層次的作戰概念[61],并在2021年版《美國國防部軍事術語詞典》中給出了其作戰概念的明確定義:一種口頭或圖形的陳述,清晰簡明地表達了指揮官意圖完成什么目標及如何利用現有資源來完成。美軍作戰概念的發展歷經多次變更,產生了多種解釋,但根據相關文獻的總結[62],作戰概念一般包括以下4個層次。
(1) 頂層作戰概念:在戰略層面概括描述作戰環境、作戰類型等關鍵特征的作戰概念。
(2) 作戰運用概念:描述體現某種作戰運用理念的相對較為寬泛的作戰概念。
(3) 功能概念:某一類型軍事行動的一般性作戰概念。
(4) 集成概念:特定軍事行動(尤其是聯合的情況)相關的作戰概念。
例如,美軍在2000年發布的《聯合愿景 2020》[63]中,定義了“全譜優勢”的作戰運用概念,即美國部隊具備單方面或與多國和跨機構伙伴聯合行動,在所有軍事行動中擊敗任何對手并控制任何局勢的能力。這一作戰概念所蘊含的作戰運用理念是作戰力量應具備顯著的信息優勢和機動特性。由此,確定了若干功能概念,如優勢機動、精確打擊、集中后勤和全方位保護。其中,優勢機動功能概念確保美軍能快速識別、選擇和鎖定目標,找出對方防線的薄弱點,并在需要時通過精確打擊的方式,將信息作戰與空間、空中、海上和陸地行動緊密結合。
2.4 戰略匹配的復雜性
根據上述關于核心要素的討論,國防組織的戰略匹配問題涉及多個方面:組織的戰略需要分解到層次化的能力中;組織的業務流程需要不斷地與服務匹配,以適應能力需求的變化;體系的組成部分需要集成以提供相應的服務;項目需要明確所交付的系統和技術具備何種能力。這些內容反映了國防組織戰略匹配的不同維度。若將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視為函數,戰略匹配的主要目標則是建立這些要素之間的關聯、組成及語義邏輯關系。這些復雜的邏輯關系構成了戰略規劃過程中的“迷霧”,是戰略管理人員面臨的主要挑戰。盡管從函數的復雜性角度來看,語義邏輯關系可能并不復雜,但實際上,戰略匹配的復雜性遠不止于此,因為國防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組織的分工協作和規劃執行的動態循環過程。具體來說,有以下兩個特點。
(1) 戰略的有效執行依賴于良好的分工協作,這體現了戰略匹配的多組織特性。為確保各組織間分工協作的順暢,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和重復投資,戰略匹配是多個組織共同參與的過程。
(2) 戰略匹配需應對持續動態變化的組織環境,這體現了戰略匹配的多時態特性。組織的外部環境會隨時間推移而發生改變,因此需要在組織的不同發展階段建立各要素間的關系。這類問題通常被稱為“戰略轉型”問題。在此背景下,需要根據外部競爭環境、技術進步等因素的變化,對規劃進行動態調整和優化,以確保戰略匹配的實現。
為全面實現有效的戰略匹配,上述兩個特點需緊密結合。為此,應借助先進的知識管理方法和工具,加強并優化組織的分工協作和規劃執行,進而推動戰略匹配水平的全面提升。
3 戰略匹配的語義建模方法
隨著IT的持續發展,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出現及其與組織戰略管理的深度融合,知識對戰略匹配的積極促進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可。這一支持過程依賴于知識的共享和有效管理[6471]。通常,在一個組織內部,知識的共享和應用包括兩個階段,分別是概念化和操作化[72]。概念化是對所關心問題相關概念的清晰描述,將背景概念轉化為系統化概念;操作化是將系統化概念轉化為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標的過程,這些指標用來進行后續的定性定量計算。通過上述兩階段過程,知識得以轉化為可重復利用的資源,從而為戰略匹配管理提供支持。
通常,組織內部的知識以兩種形式存在:個體知識和組織知識庫。這兩者通過特定的媒介進行交互,以促進知識的流動。按照知識的表達形式,組織內部的共享知識可以分為3種類型:自然語言知識、半形式化知識和形式化知識。
(1) 自然語言知識
自然語言知識是使用文字、圖片或自定義的圖形符號來描述的知識。基于文字的描述方式可以準確地表達組織對于知識內容的定義,但由于語言本身的二義性,具有不同領域知識和經驗的個體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基于文字的知識通常需要借助非文本形式的手段(如圖片、表格)或具有一定半形式化特征的手段(如戰略地圖、發展路線圖)來幫助個體理解文字背后的知識信息。
(2) 半形式化知識
半形式化知識也被稱為圖形化知識,在系統工程領域中,這些圖形被賦予了規范化的約束和定義,被稱為基于模型的系統工程(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 MBSE)。這類方法使用規范的、具有特定輸入輸出的圖形符號來表示知識內容之間的關系。為便于相關人員的理解和交流,所用的圖形符號通常是國際或業界公認的標準規范,或者是約定俗成的、不會引起歧義的表現形式。半形式化知識的優點是具有較強的描述能力和較好的可讀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推理驗證功能;缺點是會帶來額外的學習成本,具有較高的使用門檻,而且其推理形式只能是基于簡單邏輯的,如描述邏輯、一階謂詞邏輯等,推理復雜問題的能力有限。
(3) 形式化知識
形式化知識是使用具有嚴格數學語義的符號集來描述的知識。本體、描述邏輯等都是典型的常用形式化描述方法。形式化知識的優點是在定義符號系統的基礎上,嚴格限定了符號的語義和邏輯關系,具有良好的定義,可以精確地表達問題;缺點是描述形式不夠自由和豐富,推理能力也僅限于所采用的邏輯推理范圍。
上述3種知識描述方法各有優缺點,通常在戰略匹配管理中,需要針對問題需求結合使用,以滿足相應的問題需求。從知識共享的角度分析,半形式化和形式化知識更便于存儲和管理,尤其是考慮到知識的更新問題,使用自然語言方法描述的知識需要對大量的文檔進行管理,不利于組織內部知識的動態管理。從推理能力拓展的角度分析,上述方法的推理能力都有局限,但形式化方法由于具有嚴格的數學表示形式,為引入現代自然語言處理和深度學習技術提供了可能性,其推理能力的拓展更容易實現。因此,通過語義化建模手段建立組織內部共享知識的知識庫可以為后續應用提供極大的便利。
在戰略匹配問題的語義建模方面,已經有很多較為成熟的方法,包括但不局限于:基于元模型的方法、基于本體的方法和基于參考架構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解決戰略匹配問題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支持。
3.1 基于元模型的語義建模
MBSE運用建模語言、結構定義、建模過程和表示框架,對現實中的靜態和動態要素進行建模。MBSE通常通過元模型對概念進行形式化。元模型是特定語言的應用模型表達空間的陳述集,即元模型是模型的模型,是指導組織如何建立模型、對模型的語義或模型之間如何集成和互操作等信息的描述。在MBSE中,元模型被用來對建模進行規范和指導,從而確保組織范圍內各個子系統的一致性。本節將介紹目前主流企業架構框架中對于戰略匹配問題的語義化知識建模方法。
(1) DoDAF
DoDAF聲稱其支持美國國防部的核心決策過程,包括需求管理、采辦、系統工程、項目管理及能力組合管理[73],這些過程均與戰略匹配問題息息相關。DoDAF使用元模型來規范和定義語義建模,稱為DM2(DoDAF meta model)。DM2定義了架構數據元素,為架構描述內部或之間的語義一致性建立了基礎。采用這種方式,DM2支持組織內部和多組織間的信息交換和復用。DM2包括3個層次:概念數據模型、邏輯數據模型和物理交換模式,分別對應于不同組織人員對概念建模的需求。
DM2的定義遵循國際國防企業架構規范(International Defence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Specification, IDEAS),該規范用于協調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國防部的架構框架,主要內容是定義了基于UML的頂層概念,如圖3所示。其中包括:① 事物(任何個體或個體的集合);② 個體(具有時空性質的事物);③ 類型(事物的集合);④ 元組(事物之間的有序關系,諸如關系數據庫表中的行結構、“主謂賓”形式的三元組關系等)。
DM2的概念數據模型從IDEAS定義的本體中繼承了上述屬性,在此基礎上定義邏輯數據模型和物理交換規范,如圖4所示。建模人員可以在其規范框架下進行定制化的領域建模工作。除了用于DoDAF以外,其還被用于現在新的UAF架構框架。
(2) UAF
不同MBSE工具之間的差異使得其很難一對一地匹配元模型,導致使用不同框架的架構師之間溝通不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相關組織開始研究開發新的架構框架,即UAF。
UAF使用UML類模型創建了其語義模型,稱為領域元模型(domain meta model, DMM)。DMM是一個公共的參考框架,將不同框架中的概念統一和整合到這個模型中。即使使用不同的架構框架,架構建模人員也可以在這個公共的DMM上進行建模。盡管使用UML作為建模語言,但UAF的DMM為非UML/系統建模語言(system modeling language, SysML)使用者使用。UAF使用了兩個主要的文檔[74]來規范這一過程。
1) UAF DMM:描述了UAF定義的DMM和視點,定義不考慮建模工具情況下的DMM描述形式。
2) UAF概要文件:指定使用UML/SysML情況下如何實現UAF。
在視圖定義方面,UAF主要參考了“視圖矩陣”概念。這個矩陣以矩陣形式在建模對象和視圖類型兩個維度上規定了其所涵蓋的視圖。目前,UAF已經被廣泛應用于體系開發[7578]、人因分析[7980]、安全風險建模[81]等問題。此外,也有相關研究使用UAF的戰略視圖執行SWOT(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es,threats)分析[82]、投資組合管理[83]等與戰略匹配緊密相關的問題。
(3) TOGAF
TOGAF是由開放組織于1995年定義的企業架構框架,其基礎是美國國防部開發的信息管理技術架構。與DoDAF和UAF主要面向軍事組織領域建模的需求不同,TOGAF的內容元模型更關注組織的IT管理方面的建模。因此,其在商業組織的戰略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且可能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架構建模框架。
TOGAF定義了核心內容和擴展內容兩類元模型,如圖5所示,提供可裁剪的元模型來減輕學習負擔。核心元模型提供了一組最小的架構內容,并保證這些架構內容的可追溯性,如參與者、業務能力、業務服務、行動方針等的可追溯。其他更具體或更深入的建模被包含在擴展元模型中,包括在組織治理、服務、流程、數據、基礎設施整合、動機方面的擴展。TOGAF的官方指定建模工具是ArchiMate建模語言,從業務、應用和技術3個層次對組織內部的主體、客體和行為進行建模。
以上3種企業架構框架都支持對戰略匹配問題進行語義建模。相對而言,DoDAF和UAF在國防領域的研究更為常見,TOGAF則主要在非國防領域的研究中使用[36, 84],也有少量研究考慮通過建立TOGAF、DoDAF等架構的聯系來解決國防領域問題[85]。
3.2 基于參考架構的語義建模
參考架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比架構更具一般性,是對架構的高級抽象。參考架構的典型代表是聯邦企業架構(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 FEAF)。根據文獻[86]的闡述,當組織內部的多樣性達到某種臨界值時,組織會產生一種需求,需要使用比架構更抽象的方法來支持組織全生命周期過程。滿足這種需求的第一步是通過將架構中的概念分離出來,進一步抽象得到一種架構模式。因此,架構模式比架構更具一般性,可以指導組織對架構進行調整,以適應不同的應用環境。第二步是在架構模式的基礎上,結合組織的多樣性需求設計出一種能夠涵蓋所有這些需求的參考架構,用于規范未來不同架構的建模需求。建立參考架構包括以下兩方面基本原則:① 參考架構是組織對使命、愿景和戰略的詳細闡述,有助于在多個產品、組織和流程之間形成共同理解;② 參考架構基于實踐中得到驗證的概念而建立。
因此,參考架構是一種“架構的架構”,從這個意義而言,DoDAF、TOGAF等架構框架都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參考架構,因為其本身提供了對自定義架構的支持,具有一定的架構模式屬性。但是從建模的角度來看,參考架構內的概念并不要求具有很強的語義聯系,也不做建模語言的要求。相反,參考架構要求涵蓋更廣的領域,從而保證能夠反映組織內部的多樣性。
(1) FEAF
FEAF是最有代表性的參考架構之一,由美國政府支持,為政府機構各部門(包括國防部)的架構建模提供參考。在FEAF出現之前,美國政府的許多機構已經開始了架構的建設。為了協調這些架構的管理和互操作,FEAF被設計為采用“片段式結構”,將整個架構劃分為若干片段,每個片段對應某個特定的業務領域,并采用架構描述方法對各個業務領域進行架構描述。
FEAF使用參考模型來實現統一的語義建模。參考模型之間具有一定的弱語義聯系,但在參考模型內部往往只提供分類術語表,不提供語義聯系,體現了作為參考架構的抽象特性。在第二版FEAF中,FEAF的參考模型擴展到6個,包括績效參考模型、業務參考模型、數據參考模型、應用參考模型、基礎設施參考模型和安全參考模型,如圖6所示。
此外,FEAF為美國國防部提供了相應的接口,劃定了專門用于建模國防部相關概念的使命域,包括作戰使命域、業務使命域、情報使命域和信息環境體系使命域4個子領域。每個子領域下包含若干個與國防部相關的業務參考模型,進一步按照業務和服務進行逐級細分。
(2) CML
2013年,美國國防部在新的聯合能力與集成開發系統中引入了“目標手段方法”的描述框架,稱為CML[47,87],如圖7所示。該框架同時也是使命工程方法的一部分,與聯合使命線程、系統架構、功能接口描述以及集成試驗與評估共同構成了使命工程的一種工程實現流程。
CML目前仍是一個基礎框架,為美國國防部的戰略指南、使命任務和其他部門的活動提供可追溯性[88]。盡管尚未公開更多具體內容,但顯然CML并非一個新的架構框架,而是一個描述組織使命、愿景和戰略的參考框架,其中涵蓋了組織的技術架構、業務架構和用戶環境,充分體現了參考架構的基本特征。
3.3 基于RDFS/OWL本體的語義建模
現有的架構建模方法通常基于UML/SysML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關系,如DoDAF、UAF。這是因為SysML等建模語言能夠支持對系統行為的建模。然而,對于語義建模問題來說,基于UML/SysML的方法不夠簡潔,并且通常依賴特定的專用程序。自語義網概念在1999年誕生后,萬維網聯盟逐步建立并完善了標準語義網技術棧的標準體系。特別是使用RDF和OWL建立的標準化信息交換機制很快得到廣泛的應用,成為目前語義建模的主流方法。
語義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很快引起戰略匹配研究人員的興趣。研究人員開始使用語義網技術來解決戰略匹配中的數據訪問、語義推理、概念重用等問題[89]。首先,語義網技術使用鏈接數據這種圖模式的方式實現對數據資源的定義。這種方式以三元組作為基本形式,通過對資源進行簡單陳述,使機器可以理解數據之間的關系,三元組也成為知識圖譜技術的基本數據結構。簡單地說,鏈接數據以最為簡潔的形式定義了一種與工具無關的數據表示形式,這為海量數據的管理提供了技術基礎。其次,語義網技術提供了滿足不同應用需求的本體建模標準,包括RDFS和OWL的幾種擴展版本,提供了表達能力遞增、計算效率遞減的子語言,用戶可以根據對推理的需求選擇使用最合適的本體建模語言。此外,標準語義網技術還定義了規則互換格式和語義網推理語言,來輔助本體進行推理。研究人員對本體作為語義建模的使用有著廣泛的研究興趣,語言學、計算機科學、系統科學,乃至目前快速發展的人工智能領域,對本體的研究熱度一直很高,圍繞本體構建和本體匹配的大量研究為戰略匹配中的概念重用和數據集成提供了足夠的方法資源。
受到語義網技術快速發展的影響,許多基于UML/SysML的架構框架也開始提供對語義網技術的支持。對象管理組織在2005年就發布了其本體定義元模型標準,擴展了UML語言對RDF和OWL的支持[90]。DoDAF在2.03更新中也提供了視圖到OWL格式的轉換支持。目前,使用基于語義網技術的本體修飾已有概念建模框架的技術方法已經非常成熟。許多過去沒有使用語義網技術的建模框架也陸續引入本體作為建模的基礎[9195]。基于本體的語義數據還將在使命工程中發揮重要作用[96],成為運用人工智能技術促進組織內部知識共享的基礎。
表1總結了使用上述語義建模方法來解決國防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相關文獻。通過深入分析這些研究可以發現,近年來該領域的研究主要以基于RDFS/OWL本體的語義建模技術和基于UAF的語義建模技術為主,代表了該領域未來研究和發展的趨勢。基于RDFS/OWL本體的語義建模技術是新一代網絡IT的產物,隨著海量知識的不斷產生,使用這項技術支持知識管理的需求將不斷提高,網絡IT在海量數據處理方面的優勢將更加凸顯。這種技術利用RDFS和OWL的強大功能,能夠有效地描述和定義領域內的概念、實體及其之間的關系,從而為領域知識的表達和共享提供有效的手段。而UAF作為一種統一的架構框架,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可擴展性,可以適應不同領域的需求。未來,UAF可能會進一步整合各種語義建模方法,形成更加全面和高效的語義建模體系。這種靈活性使得UAF能夠更好地應對領域內復雜多變的問題,并可以根據不同的需求和場景,選擇最適合的語義建模方法。兩種建模方法將繼續發揮其優勢,并相互補充,為未來的語義建模研究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支持。
4 語義建模技術拓展應用
前文介紹了目前在戰略匹配管理領域研究中語義建模的主流方法,本節主要介紹這些技術在解決戰略匹配問題中三方面的拓展應用。
4.1 知識庫集成
對于大型組織來說,在構建知識庫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存在大量的現成知識庫,組織需要的往往是將這些現成知識庫整合為一個規模更大的知識庫,而不是重復地再造。在語義技術出現以前,整合這些數據庫非常困難,而且用戶通常不了解這些數據庫的細節。語義技術的出現為這類需求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解決手段,基于本體的數據訪問(ontology-based data access, OBDA)[9899]技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
OBDA也被稱為虛擬知識圖譜[100],是一種利用本體實現在不同抽象層次上訪問數據的技術。例如,用戶需要訪問存儲在關系型數據庫中的數據,但是又不清楚數據庫的表模式時,OBDA可以幫助用戶在不需要知道數據源細節的情況下,通過概念域模型的查詢來表達其信息需求。
OBDA的使用場景一般是已有大量的數據存放在數據庫中,或者多個數據庫中。雖然可以通過預設查詢庫提供預定義查詢,但當出現新的需求時,必須重新定義新的查詢語句,這一過程費時費力。OBDA通過本體和映射實現對用戶查詢需求的多次轉換,通常這些映射是基于描述邏輯的,有很多開源工具可以實現這部分功能。OBDA的另一個優點是其在多種查詢語言進行轉換時,查詢效率所受影響很小。在最差的情況下,也不比傳統的關系型數據庫的查詢應答效率差[101]。借助OBDA技術,諸如目標、使命、業務流程等高級抽象概念可以從較低抽象層次的實時數據中提取信息[102]。此外,OBDA可以幫助組織實現對知識庫的動態擴展,特別是基于現在的知識圖譜技術[103]。
4.2 多語言建模
語義技術的另一個典型應用場景是大型組織在處理復雜問題建模時,可能需要使用多種建模工具,此類問題又稱為多語言建模或多范式組合建模[104105]。一般出于對整體層面的考慮,此類場景中需要額外建立跨語言、跨工具間仿真模型的聯系。通過語義建模方法,可以使用語義標注[106]技術為此類問題提供一種易于實現的解決方案。
語義標注是利用語義技術進行注釋或解釋的一種技術。相較于其他形式的注釋類型,語義標注通常通過本體進行注釋[107109],因此語義標注是機器可讀的[110]。作為語義技術的一種具體應用,語義標注廣泛用于對文本、圖像、視頻、網絡服務等對象進行注釋[111116]。雖然架構建模語言一般會提供一套用于規范概念定義的本體和數據標準,但使用語義標注來增強架構建模語言的機器可讀性仍然有必要。使用語義標注可能有多種原因,例如當使用架構建模工具處理現存數據時,數據本身可能已經存在一個定義過的本體,需要在架構語言和已有本體之間建立聯系;又或者,當架構建模語言自身的本體和數據標準無法滿足數據的語義關系時,可能希望通過自定義的本體來建立數據的語義,然后再通過語義標注技術將自定義本體鏈接到架構建模語言。
考慮戰略匹配的語義建模問題,現有的架構建模語言(如DoDAF、TOGAF等)所提供的概念模式在語義上仍然存在很多沖突。例如,DoDAF中的能力是一種屬性,而不是類。而在UAF的概念定義中,能力被定義為類,并且具有一個抽象的父類——能力要素。顯然,在這兩種架構語言中,能力的內涵存在差異。使用UAF進行建模的人可能會發現,DoDAF所定義的能力無法直接映射到UAF的概念中,這種語義上的差異會給建模人員帶來理解上的困難,這與架構建模語言聲稱能夠保持理解上的一致性是相悖的。
一些較早的研究采用模型裝飾[114]等事后擴展技術解決架構語言建模的兼容性和擴展性問題。這類方法的主要優點是不需要額外的工具支持,缺點是新的注釋污染了原始的元模型,可能會產生不必要的副作用。有些特定的架構建模語言提供了模型的事先擴展機制,如UAF。為了支持DoDAF及其他已有架構的集成,UAF提供了語言擴展機制,這是通過允許定制UAF元模型的概要文件來完成的,允許術語、符號的變化,或者向類中添加新的語義。但是,這種擴展機制增加了架構建模語言的復雜性,對于建模人員來說帶來了額外的學習成本。
語義標注技術可以通過額外的本體層和映射機制解決上述問題[116],Fill[117]詳細介紹了這種方法的原理。通過增加額外的本體層,架構建模語言和語義數據可以通過特定映射機制實現相互轉換而互不影響,由架構模型到本體的對應關系將由映射機制進行解釋,這給建模人員帶來了極大的靈活性。當集成兩種不同架構語言定義的模型時,本體層作為中間件,可以用于實現實例間的靈活轉換。此外,如果存在外部知識庫,語義標注技術還提供了對知識庫的靈活訪問,這種技術方法在風險辨識[118]、醫療衛生[119120]、知識管理[121]等問題中得到了應用。
4.3 語義分析與推理
架構分析[122123]是指通過架構模型生成用于組織評估、組織轉型、組織重構等相關信息的方法。架構分析服務于組織戰略管理過程,所能提供的服務有助于解決組織的戰略匹配問題。例如,架構分析可以實現多種功能[124],考慮戰略匹配問題,其可能的應用包括如下3個方面:① 依賴性分析。分析組織內部要素的依賴性關系,分析組織戰略目標實現與規劃項目的依賴性關系;② 覆蓋性分析。發現組織戰略規劃的冗余和缺口,分析缺失部分的影響及其替代解決方案;③ 異質性分析。發現戰略規劃要素之間的差異性,確定其是否需要重新分解和組合,從而保證整個體系設計的一致性。
利用架構分析能力規劃冗余和重復具有很強的應用價值,然而手動評估和識別大型信息系統中的冗余元素是一項繁瑣、容易出錯且耗時的任務。Antunes等[125]結合描述邏輯和RDF查詢語言,探索了使用本體推理和查詢技術實現架構分析的方法。Osenberg等[126]認為可以通過分析架構模型變更產生的影響來實現架構分析功能,并且基于形式化的架構模型定義來保證嚴格的本體推理。文獻[127]使用本體和描述邏輯提出了一種用于分析業務功能與服務匹配的方法,該方法通過機器可讀的邏輯規則實現了自動推理,有效地避免了大量的人工成本。上述研究的主要思想是通過從架構模型到本體的轉換,利用本體匹配工具來推斷概念之間的對應關系,為架構分析提供了一種自動化手段。
使用本體的推理技術屬于符號化方法,一般只能使用邏輯方法進行推理,如描述邏輯、謂詞邏輯等。這些推理方法對于知識的挖掘程度有限。隨著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術的快速發展,特別是知識圖譜相關技術的發展,語義推理技術逐漸擺脫了符號邏輯推理的限制,有可能成為新的探索方向。Valiyev等[128]介紹了使用NLP技術管理北約戰略和政策文件的一項研究,通過文本相似性技術從語義和句法角度發現文檔及文檔各部分之間的關系。Kang等[129]就NLP在組織管理領域的研究進行綜述,認為目前在戰略管理方面,NLP主要被用于概念相似性測算。Huang等[130]使用NLP的分詞技術和基于詞典的方法,提出了一種基于語義分析、自動建立業務模型關聯的新方法。
5 結 論
本文分析了大型組織,尤其是國防組織在戰略管理中的戰略匹配問題。戰略匹配問題涉及多個領域的內部概念及其之間的語義聯系,通過網絡IT增強組織戰略匹配的一致性,是一個不斷迭代的螺旋上升式過程。語義技術和方法已經成為現代組織戰略管理過程中戰略匹配不可或缺的重要應用技術。從早期的模型驅動組織,到數字化組織,再到當前企業轉型中常提到的數智化轉型,可以預見,現代化組織對語義技術的使用需求將持續增長。
本文主要從語義建模方法的角度闡述了這一領域的新發展。首先,討論了戰略匹配的基本概念及其發展,特別是通過核心要素分析了軍事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特征,這有助于理解大型組織戰略匹配問題的復雜性。然后,分析了傳統語義建模的主要方法,由于當時的技術發展水平限制,這些方法仍存在許多缺陷和不足。當前的語義技術應用有一部分是為了解決這些遺留問題而產生的。最后,總結了語義技術的拓展應用,希望能為該領域技術的后續發展提供參考。
總之,語義建模技術仍在不斷發展演進。作為一種經過實踐驗證的技術方法,其理論和方法內涵將繼續深化和發展。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近年來,知識圖譜、預訓練語言模型和大語言模型技術正持續涌現,并不斷顛覆傳統技術和方法。這正說明戰略匹配的語義建模問題需要在未來投入更多的關注和研究。本文為該領域研究提供了一個初步的框架和參考,希望有更多的研究關注這一領域問題的研究和發展,從而推動戰略管理理論、方法在全局規劃管理和頂層籌劃設計中的深入研究和廣泛應用。
參考文獻
[1] ROSS J W, WEILL P, ROBERTSON D.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s strategy: creating a foundation for business execution[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6.
[2] VENKATRAMAN N, HENDERSON J C, OLDACH S. Continuous strategic alignment: exploi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for competitive success[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993, 11(2): 139149.
[3] CHAN Y E, HUFF S L, BARCLAY D W, et al. Business strategic orien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alignment[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7, 8(2): 125150.
[4] CIBORRA C U. De profundis? Deconstructing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alignment[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1997, 9(1): 6782.
[5] HENDERSON J C, VENKATRAMAN H. Strategic alignment: levera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transforming organizations[J]. IBM Systems Journal, 1993, 32(1): 472484.
[6] BROADBENT M, WEILL P, BRIEN T, et al. Firm context and patterns of IT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y[C]∥Proc.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Sciences, 1996.
[7] BURN J M, SZETO C. A comparison of the views of business and IT management on success factors for strategic alignment[J]. Information amp; Management, 2000, 37(4): 197216.
[8] LUO Y, PARK S H.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performance of market-seeking MNCs in China[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 22(2): 141155.
[9] BERGERON F, RAYMOND L, RIVARD S. Ideal patterns of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J]. Information amp; Management, 2004, 41(8): 10031020.
[10] AVISON D, JONES J, POWELL P, et al. Using and validating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model[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4, 13(3): 223246.
[11] CHENHALL R H. Integrative strategic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strategic alignment of manufacturing, learning and strategic outcomes: an exploratory study[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5, 30(5): 395422.
[12] CAMPBELL B, KAY R, AVISON D. Strategic alignment: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05, 18(6): 653664.
[13] CUI T, YE H J, TEO H H, et 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pen innovation: a strategic alignment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amp; Management, 2015, 52(3): 348358.
[14] LI W, LIU K, BELITSKI M, et al. E-leadership through strategic align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6, 31(2): 185206.
[15] ILMUDEEN A, BAO Y, ALHARBI I M. How does business-IT strategic alignment dimension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s[J].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9, 32(3): 457476.
[16] ULLAH A, LAI R.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ignment[J]. ACM Transactions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3, 4(1): 76105.
[17] REICH B H, BENBASAT I.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alignment betwee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bjectives[J]. MIS Quarterly, 2000, 24(1): 81113.
[18] 張萌萌. 面向體系架構的軍事信息系統業務與技術匹配關鍵技術研究[D]. 長沙: 國防科技大學, 2019.
ZHANG M M. Research on key techniques of business-it alignment in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architecture[M].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19.
[19] 陳洪輝. 基于體系架構的指揮信息系統業務與技術匹配現狀[J]. 指揮信息系統與技術, 2019, 10(2): 17.
CHEN H H. Current situation of business-IT alignment of command and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architecture[J].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2019, 10(2): 17.
[20] ZHANG M M, CHEN H H, LYYTINEN K.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al co-evolution of business and IT: a complexity perspective[C]∥Proc.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
[21] ZHANG M M, CHEN H H, LUO A 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business-IT alignment research with enterprise architecture[J]. IEEE Access, 2018, 6: 1893318944.
[22] 張延林, 肖靜華, 謝康. 信息系統與業務戰略匹配研究述評[J]. 管理評論, 2014, 26(4): 154165.
ZHANG Y L, XIAO J H, XIE K. An overall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J]. Management Review, 2014, 26(4): 154165.
[23] 宋立夫, 張健, 陳萍. 企業管理系統與信息系統匹配原理及方法研究[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7, 7(2): 5154.
SONG L F, ZHANG J, CHEN P. Matching theory and methods between management system and information system of enterprise[J]. Journal of Northwest Aamp;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7, 7(2): 5154.
[24] GLAISTER A J, KARACAY G, DEMIRBAG M, et al. HRM and performance-the role of talent management as a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an emerging market context[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28(1): 148166.
[25] GURBAXANI V, DUNKLE D. Gearing up for successful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2019, 18(3): 209220.
[26] MCADAM R, MILLER K, MCSORLEY C. Towards a contingency theory perspective of quality management in enabling strategic alig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9, 207: 195209.
[27]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A strategic alignment framework for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2 29(2): 285309.
[28] HANIFF A P, GALLOWAY L. Modeling strategic alignment in project netwo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2 40(5): 517530.
[29] BASTIDAS V, REYCHAV I, HELFERT M. Design principles for strategic alignment in smart city enterprise architectures (SCEA)[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23, 219: 848855.
[30] GHONIM M A, KHASHABA N M, AL-NAJAAR H M, et al.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its impact on decision effectiveness: a comprehensive mod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202 17(1): 198218.
[31] ARAUJO M, STOROPOLI J, RABECHINI R.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ategic alig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 18(8): 2150042.
[32] SAINT-ONGE H. Tacit knowledge the key to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intellectual capital[J]. Planning Review, 1996, 24(2): 1016.
[33] KEARNS G S, SABHERWAL R. Strategic alignment betwee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knowledge-based view of behaviors, outcome,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6, 23(3): 129162.
[34] PRESTON D S, KARAHANNA E. Antecedents of IS strategic alignment: a nomological network[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9, 20(2): 159179.
[35] ZACHMAN J A. A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architecture[J]. IBM Systems Journal, 1987, 26(3): 276292.
[36] BHATTACHARYA P. Modelling strategic alignment of business and IT through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ugmenting archimate with BMM[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7, 121: 8088.
[37] BHATTACHARYA P. Aligning enterprise systems capabilities with business strategy: an extension of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model (SAM) using enterprise architecture[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8, 138: 655662.
[38] HINKELMANN K, PASQUINI A. Supporting business and IT alignment by modeling business and IT strategy and its relations to enterprise architecture[C]∥Proc.of the Enterprise Systems Conference, 2014: 149154.
[39] BUCKL S, ERNST A M, LANKES J, et al. State of the art in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management[R]. Munich: Software Engineering for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2009.
[40] KOTUSEV S.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 reconceptualization is needed[J]. Pacific Asi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 10(4): 136.
[41] KOTUSEV S. TOGAF-based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practice: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 43(1): 321359.
[42] BERNERS-LEE T, HENDLER J, LASSILA O. The semantic web[J]. Scientific American, 200 284(5): 3443.
[43] HINKELMANN K, GERBER A, KARAGIANNIS D, et al. A new paradigm for the continuous alignment of business and IT: combining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modelling and enterprise ontology[J]. Computers in Industry, 2016, 79: 7786.
[44] ROACH T. CAPSICUM-a semantic framework for strategically aligned business architecture[D]. Sydney: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11.
[45] FUCHS-KITTOWSKI F, FAUST D. The semantic architecture tool (SemAT) for collaborative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C]∥Proc. the of 1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roupwar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Use, 2008: 151163.
[46] HOYLAND C A. RQ-Tech, a strategic-level approach for conceptualizing enterprise architectures[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 12: 3742.
[47] DAS A. Capability requirements portfolio managemen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using semantic data lake as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proof-of-concept experiments[D]. Bost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8.
[48] 王文榮. 戰略學[M]. 北京: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9.
WANG W R. Science of strategy[M]. Beijing: Chin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 SRIVANNABOON S, MILOSEVIC D Z. A two-way influence between business strategy and project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6, 24(6): 493505.
[50] MESKENDAHL S. 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strategy on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and its success-a conceptual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0, 28(8): 807817.
[51] BUYS A J, STANDER M J. Linking projects to business stra-tegy through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2010, 21(1): 5968.
[52] KAISER M G, EL-ARBI F, AHLEMANN F. Successful project portfolio management beyond project selection techniques: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tructural align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5, 33(1): 126139.
[53] SOLTANI E. Business and project strategy alignment: ICT project success in Iran[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0, 63: 101404.
[54] DANESH M H, YU E. Analyzing IT flexibility to enable dynamic capabilities[C]∥Proc.of the Advance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Workshops, 2015: 5365.
[55] COMBS J G, KETCHEN D J, IRELAND R D, et al. The role of resource flexibility in leveraging strategic resour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 48(5): 10981125.
[56] STIRNA J, GRABIS J, HENKEL M, et al. Capability driven development-an approach to support evolving organizations[C]∥Proc.of the IFIP Working Conference on the Practice of Enterprise Modeling, 2012: 117131.
[57] MIKLOS J. A meta-model for the spatial capability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 43(2): 301305.
[58] ALDEA A. Enterprise strategic alignment method: a cross-disciplinary capability-driven approach[D]. Enschede: University of Twente, 2017.
[59] GOROD A, WHITE B E, IRELAND V, et al. Case studies in system of systems, enterprise systems, and complex systems engineering[M].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4.
[60] KAPURCH S J. NASA systems engineering handbook[M]. Philadelphia: Diane Publishing, 2010.
[61] 齊嘉興, 楊繼坤. 美軍作戰概念發展及其邏輯[J]. 戰術導彈技術, 2022(1): 97105.
QI J X, YANG J K. The development and logic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 concepts[J]. Tactical Missile Technology, 2022(1): 97105.
[62] RATIU A. The relevance of the operating concepts in the defense planning process[J]. Defense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2017, 12(12): 416426.
[63] Joint Chiesf of Staff. Joint vision 2020 “America’s military: preparing for tomorrow”[EB/OL]. [20231011]. http:∥pentagonus.ru/doc/JV2020.pdf.
[64] SHANNAK R O. Intermediary effect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J].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 24(24): 112128.
[65] CHOE J. The 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s through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J].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4, 22(1): 115.
[66] AL-AMMARY J. The strategic alignment betwee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strategy: the impact of contextual and cultural factor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mp;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4, 13(1): 1450006.
[67] OBEIDAT B Y, AL-DMOUR R H, TARHINI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between IT business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firm performance[J]. European Scientific Journal, 2015, 11(7): 344368.
[68] COSTA R G G, REZENDE J F C. Strategic alignmen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value creation: implications on to an oil and gas corporation[J]. RAUSP Management Journal, 2018, 53(2): 241252.
[69] DABIC M, KIESSLING T. The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alignment of MNC subsidiaries[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9, 23(8): 14771501.
[70] YOSHIKUNI A C, ALBERTIN A L. Leveraging firm performance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ategic align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an empirical study of IT business valu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GRANTHAALAYAH, 2020, 8(10): 304318.
[71] ABUEZHAYEH S W, RUDDOCK L, SHEHABAT I. Integration betwee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a case study of Jordan[J]. Construction Innovation, 202 22(4): 9871010.
[72] ADCOCK R, COLLIER D. 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 95(3): 529546.
[73] BOCAST A, MCDANIEL D. The DoD architecture framework, volume 1: overview and concepts, version 2.0 change 1[M]. BOCAST A. Arlington Count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5.
[74] ABHAYA L. UAF (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 based MBSE (UBM) method to build a system of systems model[J]. INCO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2 31(1): 227241.
[75] EICHMANN O C, MELZER S, GOD R. Model-based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of systems using 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 (UAF): a case study[C]∥Proc.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Systems Conference, 2019.
[76] 劉婧婷, 郭繼坤. 基于UAF元模型的戰區聯合作戰精確保障體系構建方法[J]. 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 2020, 42(6): 13241331.
LIU J T, GUO J K.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t support system for joint operations in theater command based on DMM of UAF[J].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2020, 42(6): 13241331.
[77] TIRONE L, GUIDOLOTTI E, FORNARO L. A tailoring of the 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s meta-model for the modeling of systems-of-systems[J]. INCO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8, 28(1): 16911705.
[78] BANKAUSKAITE J. 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based trade study method for system architectures in model-based 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D]. Kaunas: Kauno Technologijos Universitetas, 2023.
[79] CARLSON O, HOHENSTEIN S, BUI J, et al. Human factors in the 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 applied to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C]∥Proc.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Systems Conference, 2019.
[80] HAUSE M, WILSON M. Integrated human factors views in the unified architecture framework[J]. INCO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7, 27(1): 10541069.
[81] GARCA J J L, PEREIRA D P. Analyzing system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concept phase using UAF domains[J]. INSIGHT, 202 25(2): 5660.
[82] TORKJAZI M, DAVILA-ANDINO A J, ALGHAMDI A, et al. UA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enterprises[J]. IEEE Access, 202 10: 123549123559.
[83] MARTIN J N. Extending UAF for model-based capability planning and enterprise portfolio management[J]. INCOS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2 32(1): 1535.
[84] RIWANTO R E, ANDRY J F. Enterprise architectures enable of business strategy and IS/IT alignment in manufacturing using TOGAF ADM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2019, 1(2). DOI:10.2426/ijiteb.122019.
[85] JRGENSEN H D, LILAND T, SKOGVOLD S. Aligning TOGAF and NAF-experiences from the Norwegian armed forces[C]∥Proc.of the 4th IFIP WG 8.1 Working Conference on the Practice of Enterprise Modeling, 2011: 131146.
[86] CLOUTIER R, MULLER G, VERMA D, et al. The concept of reference architectures[J]. Systems Engineering, 2010, 13(1): 1427.
[87] LEE M N. Information capture during early front end analysis in the joint capabilities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JCIDS): a formative study of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 (DoDAF)[D]. Bost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6.
[88] AHMED L N. Improving trade visibility and fidelity in defense requirements portfolio management[D]. Bost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4.
[89] VERES C, SAMPSON J, BLEISTEIN S J, et al. Using semantic technologies to enhance a requirements engineering approach for alignment of it with business strategy[C]∥Proc.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lex, Intelligent and Software Intensive Systems, 2009: 469474.
[90] GASEVIC D, DJURIC D, DEVEDZIC V. 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 and ontology development[M]. Berlin: Springer, 2006.
[91] SHEEHAN J H, DEITZ P H, BRAY B E, et al. The military missions and means framework[C]∥Proc.of the Interservice/Industry Training, Simulation and Education Conference, 2003: 655663.
[92] 葉國青, 舒宇, 葛冰峰, 等. 基于使命和方法框架的武器裝備體系結構建模[J]. 火力與指揮控制, 201 37(7): 15.
YE G Q, SHU Y, GE B F, et al. Stracture modeling of weapon equipment system of systems based on missions and means framework[J]. Fire Control & Command Control, 201 37(7): 15.
[93] 金叢鎮. 基于MMF-OODA的海軍裝備體系貢獻度評估方法研究[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學, 2017.
JIN C Z. Research on evaluation method of naval equipment’s contribution degree to system warfighting based on MMF-OODA[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mp; Technology, 2017.
[94] DEITZ P H, MICHAELIS J R, BRAY B E, et al. The missions amp; means framework (MMF) ontology: matching military assets to mission objectives[C]∥Proc.of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ymposium, 2016.
[95] DEITZ P H, BRAY B E, MICHAELIS J R. The missions and means framework as an ontology[C]∥Proc.of the Conference on Ground/Air Multisensor Interoperability, Integration, and Networking for Persistent ISR VII, 2016: 4556.
[96] MAHER M, ORLANDO R. Reduce the warfighters’ cognitive burden[C]∥Proc.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Computing, 2019: 143152.
[97] LEE J, PARK Y. A study on the abstracted meta model of DoDAF 2.0 for CBA methodology execution[C]∥Proc.of the 10th AC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Networking and Parallel/Distributed Computing, 2009: 364369.
[98] POGGI A, LEMBO D, CALVANESE D, et al. Linking data to ontologies[EB/OL]. [20231011].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0461267_Linking_Data_to_Ontologies.
[99] XIAO G, CALVANESE D, KONTCHAKOV R, et al. Onto-logy-based data access: a survey[C]∥Proc.of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8.
[100] XIAO G H, DING L F, COGREL B, et al. Virtual know-ledge graphs: an overview of systems and use cases[J]. Data Intelligence, 2019, 1(3): 201223.
[101] 張宇軒. 一種基于本體的數據訪問與集成系統的設計與實現[D]. 杭州: 浙江大學, 2018.
ZHANG Y X.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ontology-based data access and integrated system[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8.
[102] CARDOSO E, MONTALI M.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d compliance monitoring[C]∥Proc.of the IEEE 23rd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Distributed Object Computing Workshop, 2019: 7584.
[103] POMP A, LIPP J, MEISEN T. You are missing a concept! enhancing ontology-based data access with evolving ontologies[C]∥Proc.of the IEE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mantic Computing, 2019: 98105.
[104] 李小波. 基于DSM的效能仿真多范式組合建模方法研究[D]. 長沙: 國防科學技術大學, 2013.
LI X B. A DSM-based multi-paradigm composable modeling method for effectiveness simulation[D].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13.
[105] 朱智. 模型驅動的裝備仿真模型語義工程化建模技術研究[D]. 長沙: 國防科技大學, 2018.
ZHU Z. Model-driven semantic engineering techniques for equipment simulation modeling[D].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18.
[106] LIAO Y, LEZOCHE M, PANETTO H, et al. Semantic annotation for knowledge explicitation in a 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context: a survey[J]. Computers in Industry, 2015, 71: 2434.
[107] TALANTIKITE H N, AISSANI D, BOUDJLIDA N. Semantic annotations for web services discovery and composition[J]. Computer Standards amp; Interfaces, 2009, 31(6): 11081117.
[108] LIN Y. Semantic annotation for process models: facilitating process knowledge management via semantic interoperability[D]. Trondheim: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109] KIRYAKOV A, POPOV B, TERZIEV I, et al. Semantic annotation, indexing, and retrieval[J]. Journal of Web Semantics, 2004, 2(1): 4979.
[110] OREN E, MOLLER K, SCERRI S, et al. What are semantic annotations?[EB/OL]. [20231011]. http:∥www.siegfried-handschuh.net/pub/2006/whatissemannot2006.pdf.
[111] REEVE L, HAN H. Survey of semantic annotation platforms[C]∥Proc.of the ACM Symposium on Applied Computing, 2005: 16341638.
[112] DASIOPOULOU S, GIANNAKIDOU E, LITOS G, et al. A survey of semantic image and video annotation tools[M]∥Knowledge-Driven Multimedia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Ontology Evolution: Bridging the Semantic Gap.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11: 196239.
[113] 牛麗慧, 歐石燕. 科學論文語義標注框架的設計與應用[J]. 情報理論與實踐, 2020, 43(3): 120132.
NIU L H, OU S Y.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emantic annotation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articles[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amp; Application, 2020, 43(3): 120132.
[114] 郭少友, 竇暢, 常楨. 網頁語義標注研究綜述[J]. 情報雜志, 2015, 34(4): 169175.
GUO S Y, DOU C, CHANG Z. Review on semantic annotations of web page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5, 34(4): 169175.
[115] KOLOVOS D S, ROSE L M, DRIVALOS M N, et al. Constructing and navigating non-invasive model decorations[C]∥Proc.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l Transformations, 2010: 138152.
[116] FILL H G. Semantic annotations of enterprise models for supporting the evolution of model-driven organizations[J]. Enterprise Modell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rchitectures, 2018, 13(5). DOI:10.18417/emisa.13.5.
[117] FILL H G.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modeling language for semantic model annotations[C]∥Proc.of the Advance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Workshop, 2011: 134148.
[118] FILL H G. An approach for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risks on business processes using semantic annotations[C]∥Proc.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2012.
[119] FILL H G, REISCHL I. Stepwise semantic enrichment in health-related public management by using semantic information models[M]∥Semantic Technologies for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SMOLNIK S, TEUTEBERG F, THOMAS O, ed. Hershey: IGI Global, 2012: 195212.
[120] AHMAD M, ODEH M, GREEN S. Derivation of a semantic cancer car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from RIVA-based business process architecture using the bpaontoeia framework[C]∥Proc.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cer Care Informatics, 2018: 152164.
[121] MALIK S K, PRAKASH N, RIZVI S A M. Semantic annotation framework for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 using KIM architec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b amp; Semantic Technology, 2010, 1(4): 1226.
[122] BUCHER T, FISCHER R, KURPJUWEIT S, et 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an exploratory study[J]. Journal of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2007, 3(3): 3343.
[123] JOHNSON P, LAGERSTROM R, NARMAN P, et 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nalysis with extended influence diagrams[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07, 9(2): 163180.
[124] NIEMANN K D. From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to IT governance[M]. Heidelberg: Springer Fachmedien, 2006.
[125] ANTUNES G, BORBINHA J, CAETANO A. An application of semantic techniques to 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models[C]∥/Proc.of the 49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16: 45364545.
[126] OSENBERG M, LANGERMEIER M, BAUER B. Using semantic web technologies for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nalysis[C]∥Proc.of the 12th European Semantic Web Conference on the Semantic Web. Latest Advances and New Domains, 2015, 9088: 668682.
[127] SOSA-SNCHEZ E, CLEMENTE P J, PRIETO E, et al. Aligning business processes with the services layer using a semantic approach[J]. IEEE Access, 2018, 7: 29042927.
[128] VALIYEV G, PIRAINO M, KOK A, et al. Initial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on nato strategy and policies[J]. Information amp; Security, 2020, 47(2): 187202.
[129] KANG Y, CAI Z, TAN C W, et a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alytics, 2020, 7(2): 139172.
[130] HUANG L, REN G J, JIANG S, et al. Toward dynamic model association through semantic analytics: approach and evaluation[C]∥Proc.of the IEEE 21st Conference on Business Informatics, 2019: 130137.
作者簡介
王 濤(1976—),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戰略規劃評估、體系工程與體系仿真。
林 木(1983—),男,工程師,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戰略規劃評估、體系工程與體系仿真。
李小波(1983—),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戰略規劃評估、體系工程與體系仿真。
朱 智(1989—),男,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裝備體系論證與仿真評估。
朱一凡(1963—),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裝備體系論證與仿真評估。
王維平(1963—),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戰略規劃評估、體系工程與體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