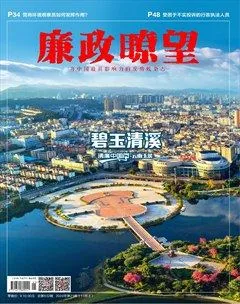玉溪:清流如玉的文化底蘊

玉溪之名,得于水。在夾雄山—祭天山山脈的深林溪谷中,一條大河流淌而出,與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共同孕育出了玉溪這座高原水鄉。這條河,在《水經注》中其名為“橋水”,到了清代康熙年間,始有“玉溪”之名。《新興州志》記載,“大溪河,一名玉溪河。在州北五里”。“其水縈帶,蒼碧如玉”,“玉溪”之意即為溪水清凈透亮,如玉帶潺潺流淌。
作為地名,“玉溪”是年輕的,而這片土地卻是古老而厚重的。“這里擁有悠久的歷史,澄江帽天山化石群揭示了5.3億年前生命的起源,玉溪先輩創造出了標志古滇文明的青銅文化;這里擁有靈動的山水,有撫仙湖、星云湖、杞麓湖交相輝映,紅塔山、秀山、哀牢山等山秀甲滇中,形成了獨特的山水風光、田園村寨;這里擁有深厚的底蘊,辛亥革命‘將軍群’、云南白藥創始人曲煥章都是從玉溪走出的名人,人民音樂家聶耳為國而歌、奏響了‘前進,前進,前進進’的時代最強音。”玉溪市委書記王力表示,“接下來,我們將持續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用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厚植廉潔奉公的文化基礎,夯實清正廉潔的思想根基,積極構建廉潔文化建設矩陣,扎實推進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取得實效。”
“禮樂名邦”的文化積淀
1984年7月1日,古生物學家侯先光再一次登上了玉溪市澄江縣境內的帽天山,繼續進行艱苦細致的化石采集工作。不知敲開了多少塊石頭后,忽然,一枚栩栩如生的納羅蟲化石出現在他眼前。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遺產管理委員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金宏森介紹,這枚小小的化石以及隨后發現的大量保存軟軀體的化石標本,為全面、系統研究澄江生物化石群奠定了堅實基礎,向人類揭開沉睡了5.3億年的寒武紀早期世界,生動再現了地球生命大爆發的奇觀。
澄江動物化石群的發現,解釋了生命從何而來,也讓玉溪有了“生命起源地”之美譽。那么,生命又將如何豐富、向何處去?這是新的問題。
文明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寒武紀離我們太過遙遠,不妨先順著人類歷史的足跡尋找文明的回響。
玉溪有三湖,撫仙湖湛藍明凈,鑲嵌于群山之間,有“琉璃萬頃”之稱;星云湖如群星閃爍,落入湖中;而杞麓湖畔,一座名為通海的城市屹立千年。“通海”意為通達大海,地處云南腹地,這座城市為何有著如此廣闊寓意的名字?據介紹,通海之名形成于唐代。唐玄宗天寶年間,唐朝與南詔國之間的天寶戰爭爆發,經過五年的激烈戰爭,天寶十四年(755年)唐軍大敗,南詔國由此崛起。取得巨大軍事勝利的南詔國王志得意滿,并在新開辟的領土上設置了通海郡,寄托了他“開疆拓土、通江達海”的勃勃雄心。
不過在坊間,熱衷故事的人們也會把通海的得名與一個治水傳說聯系起來。相傳,古時杞麓湖洪水泛濫,百姓苦不堪言,一名俗姓李的僧人畔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登上湖畔的秀山,勘看水脈,最后在湖東用錫杖擊穿地表,形成落水洞,將杞麓湖無法承載的洪水引入大海,露出大量良田。通海百姓由此感恩畔富,把他看作神僧。畔富治水的故事在通海一帶流傳,如今人們還能在秀山上探訪畔富祠,體會通海地名背后寄托的百姓安居樂業的愿景。
杞麓湖畔的秀山,垂直高度只有200米左右,卻被列為云南四大名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承載的文脈。秀山歷史文化公園工作人員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記者介紹,秀山這座看似小小的山上有200多塊匾、聯、碑、刻,可謂“無額不匾,無楣不聯”。這與通海的地理位置有關,《通海縣志》記載,“通海最扼咽喉”,作為交通要道,南來北往的人們路過通海,登高秀山,見湖山美景難免留下墨寶,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此盛況,是中原文化與云南地方文化的結合,是通海文化、玉溪文化的縮影。匾山聯海記載著無數文人的筆墨與文思,秀山腳下還有一座氣勢恢宏的建筑,也見證了通海文脈的繁盛。
始建于元代的通海文廟,經明、清多次修繕擴建,如今依然屹立。文廟主體建筑依山就勢,循中軸線順勢疊升,共分四進三大院落,建造規格較高。值得一提的是,通海文廟宮墻北面墻壁上鐫刻著“禮樂名邦”四個大字。相傳,這是清代乾隆年間通海知縣朱陽所題。他到通海上任后,幾個月都沒有受理過一起案件,感到十分奇怪。經過四處打聽,他得知通海百姓之間幾乎沒有什么紛爭,哪怕有一些小矛盾,也能通過當地有威望的老者調解。朱陽深感當地民風淳樸,便題寫了“禮樂名邦”贊揚此地的文明程度。
玉溪境內的文廟不少,除通海文廟外,還有江川文廟、澄江文廟、玉溪文廟。這些文廟濃縮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書寫了云南科舉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據《新纂云南通志》記載,明代永樂癸未科(1403年)應天府鄉試中,華寧人張文禮、王遴考中舉人,這是玉溪士子第一次在科舉中嶄露頭角。次年會試中,張文禮考取進士,“臨安甲科自文禮始”,玉溪歷史上第一個進士由此誕生。清代玉溪第一個進士則是澄江人趙士麟,他參加了康熙甲辰科(1664年)會試,也是清代云南進士第一人。明清兩代,玉溪約有進士、舉人共1192人,其中進士109人、舉人1083人。
如今,文廟早已不復以往文化中樞的地位,但其蘊含的文脈,仍生生不息地浸潤著一代又一代的玉溪人民。
敢為人先的擔當精神
“似春雷天崩地裂,摸胡須似鋼針,猶如鐵釘……”在澄江市小屯村,有一種流存范圍極窄的古老儺戲——關索戲,用以驅鬼辟邪、祈求風調雨順。關索戲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是唯一以人名命名的戲種。
關索,相傳是關羽的第三個兒子。羅貫中在《三國演義》第87回中寫有“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諸葛亮命關索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關索來到云南,駐兵于小屯村,故小屯村原名“先鋒營”,這也是傳說中關索戲的起源。關索戲的劇本主要是圍繞三國故事,尤其是蜀國展開。
然而,關索其人,正史中不見記載。是否真有關索,關索到底是關羽的親生兒子還是義子,都一直有爭論。不過,關羽的親家李恢倒是澄江人,關羽的女兒關銀屏是由諸葛亮做媒嫁給李恢的兒子李蔚。關銀屏與李蔚的合葬墓,如今就坐落在澄江市舊城村的金蓮山上。作為當地人,李恢也是關索戲中一些劇目的主角,如《李恢說合馬超》。
李恢是建寧郡俞元縣(今澄江市)人,被玉溪當地學者認為是“玉溪入正史第一人”。他出身當地大姓,學識膽識俱佳。公元213年,劉備攻下綿竹,與劉璋在雒城對壘相持時,李恢來到劉備麾下,并成功說服馬超歸順劉備,助力劉備攻取益州。
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后不久,負責管理南中軍政事務的庲降都督一職空缺。劉備有意讓李恢這個本地人接任,試探著問李恢有沒有推薦的人選。李恢用西漢名將趙充國“莫若老臣”的故事自比,主動請纓擔當重任,出鎮南中。李恢沒有辜負劉備的期望。在劉備去世、蜀漢政權交接的國力虛弱階段,南中豪強紛紛反叛,李恢苦苦支撐,并在配合諸葛亮平定南中的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被封為漢興亭侯。
關鍵時刻,李恢敢于擔當,才干卓異,在歷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筆。這樣敢為人先的精神,也頻頻閃現在后世玉溪大地養育出的歷史人物身上。
清朝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通海人朱嶟考中進士,從邊陲小城來到京城入仕為官,前后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朝,曾擔任江南道監察御史、禮部尚書、太和殿軍機處行走等職,后官至內閣大學士。

道光年間,當清廷還沉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時,世界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英國殖民者開始向中國民間大量販賣鴉片,不僅致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百姓的精神和體質也受到極大摧殘。道光十六年(1836年),身為內閣大學士兼禮部侍郎的朱嶟上《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旗幟鮮明地提出嚴禁鴉片的主張。朱嶟禁煙主張的提出,比林則徐早了兩年,且見解更為深刻。
朱嶟深刻地意識到了鴉片泛濫的嚴重危害,也看清了英國殖民者利用鴉片實現侵略的險惡用心,他駁斥了“弛禁”派主張準許外商將鴉片納稅,實際是將吸食、販賣鴉片合法化的觀點,大聲疾呼:“中華若不盡早根除鴉片之禍,國人危矣;國人既危,中華更危矣!”
作為禁煙先驅,朱嶟心系民族危亡,忠于職守,病逝于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賜封謚號“文端”,在皇陵之地劃出一塊地予以厚葬,并在他的家鄉通海立了“皇清敕封忠信朱文端公嶟故里碑”用以紀念。
清正廉潔的為官之道
在玉溪市區東南郊,沿秀山路盤山而上,經上靈秀村繼續前行,抵達下靈秀村,在一片干凈整潔的民房之中,可以看到一座稍顯不同的建筑,門口端坐著兩尊石獅子。拾級而上,抬頭便可看到一塊匾額寫著“陳公祠”三個大字,門楣兩邊的對聯則寫著“岳河鐘瑞兄弟聯芳,鑿山導水利濟悠長”。
陳公祠紀念的是有“鐵面御史”之稱的明代官員陳表。他于明朝弘治三年(1490年)出生在新興州(今玉溪市紅塔區)北古城,自幼聰慧過人。不過,陳表的科舉之路并不順遂,在28歲參加會試落第后,考慮到家境貧寒,陳表暫時放棄了科舉入仕之路,到四川南溪縣任教諭,解決生計。南溪任教六年,陳表“課士有方”,當地人對他十分推崇,贊揚他“講文學必根道學,做經師不愧人師”。
陳表并不甘心安于一隅,嘉靖二年(1523年),他再次參加科舉,并考中進士,由此踏入仕途。嘉靖十一年(1532年),政績突出的陳表升任浙江道監察御史,次年又任欽差大臣,巡按直隸淮安、揚州等地。據陳表后人介紹,彼時淮安知府是權傾朝野的夏言的侄子,他倚仗夏言的權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堪言。當地官員也懼怕夏言,選擇明哲保身,對其侄子的惡行熟視無睹。陳表見不得如此行徑,盡管有好友和同僚勸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卻態度堅決地表示:“吾今代天巡狩,詎可容私!”他還說:“非種不除,如其生靈涂炭何!吾職寧休,民害必除。”陳表雷厲風行地懲治了淮安知府,卻也如他自己“預言”的那樣,因不畏權貴、堅守正義而為當權者所不容。很快,陳表就因“忠直見忤”而被削職。

嘉靖十七年(1538年),陳表“自楚歸滇”,歸途中,他多寫詩抒發心境。《興福寺少憩次陳尹子》一詩,就以“塵苦當于何處謝,歸來蓮社領青山”句,暗指官場的骯臟,表達對故鄉的思念與熱愛。
回到家鄉的陳表并未消沉,而是積極投身建設家鄉。他見家鄉沒有官學,學子只能跋山涉水到外地應試,便聯合父老鄉紳,向朝廷陳請設立州學。最終朝廷批準了陳表的呈請,從此結束了新興州沒有官學的歷史,促進了當地教育的發展。他見家鄉水系分布不均,決心興修水利,并帶頭捐資千金,在靈照山下開鑿涵洞,修筑撒喇溝,解決了沿溝農田的灌溉難題。至今,撒喇溝水仍對當地農業生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是陳公祠大門對聯上“鑿山導水”的由來。
陳表第17代后人陳家榮對記者感慨道:“‘代天巡狩’是陳表仕途的頂峰,也是他仕宦生涯的終點,他對家鄉的貢獻是深遠綿長的。我們一直以陳表清正廉潔的高尚情操而自豪,也堅持傳承‘勤儉治生’‘清屬爾心’的家風。”
在陳表之后,玉溪歷史上另一位杰出的清官廉吏也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就是王元翰。
王元翰是寧州(今玉溪市華寧縣)人,在明朝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考中進士。王元翰宦海沉浮,官職最高也不過是刑部主事,從職位來說不值一提。不過,王元翰雖官微言輕,行事卻剛正不阿,是明朝有名的諫官、廉吏。
從王元翰入仕的細節來看,他本應有著大好的前途。他考中進士時,考官為首輔沈一貫。沈一貫認為王元翰“筆舌互用,腕有鬼工”,有意將他作為自己的門生。這是旁人求之不得的,王元翰卻避之不及,表示:“知己之恩,同于再生,生何敢忘!然而人臣無私交,使相君而開誠布公,生請北面精謹以事之。”王元翰表達了對沈一貫知遇之恩的感謝,同時拒絕與其有私人關系,實際上是在抵制“寧負朝廷,不負舉主”的官場潛規則。初入官場就有如此勇氣,充分彰顯了他潔身自好的秉性。
后來,王元翰堅持原則,屢次彈劾結黨營私的腐敗官員,惹怒大批權貴。最終,王元翰反被誣為貪官。為自證清白,王元翰甚至將家中財物悉數搬出,擺放在城門下,可惜仍免不了被罷官。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王元翰帶著污名回到家鄉,在撫仙湖畔閑居,留下大量詩作,用以表明心志,其中《泛撫仙湖詣孤山用壁間韻》一詩,用“閑賦滄浪間濯纓,湖山蕭瑟趁秋晴。山當孤處群松伴,湖以仙名一鶴橫”的詩句,借山與湖之景,表達了自己清正廉潔之志。
好在,歷史給了王元翰公正。《明史·王元翰傳》評價他稱“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銳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畏其口”。
往事如煙,消散在云嶺之間,唯有氤氳綿延的文化與精神長留。5.3億年前的納羅蟲化石與撫仙、星云、杞麓三湖見證了時光流轉,從入正史第一人到后世無數的清官能吏,玉溪這片美麗的土地上擁有太多的故事,足以吟唱成歌。深厚的文化底蘊,余韻無窮,當歷史的車輪行至近現代,玉溪厚積而薄發,在新的時期,繼續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