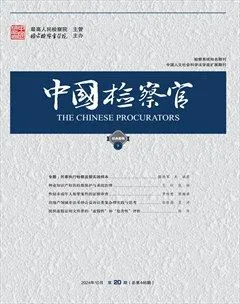公立醫院護士長耗材申領權的公務認定
摘 要:公立醫院護士長利用申領耗材的職務便利收受賄賂的案件,在構成要件身份認定上存在爭議,應對“公務論”進行宣言解釋,實質性界分公務與勞務。對護士長耗材申領權能的性質辨析,應審慎衡量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法益觀念,引入剝離權源及實損利益的解釋基準,明確耗材申領權對公務性采購權的支配性影響。辦理此類案件時,司法人員應樹立法益保護為先的觀念,將“從事公務”作為認定構成要件身份的唯一標準。
關鍵詞:護士長 耗材申領 公務認定 宣言解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同有關單位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中強調,要重點查處醫療領域行賄問題。[1]醫藥領域受賄案件,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是界定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關鍵構成要件要素。“兩高”《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已明確區分“醫療機構國家工作人員采購行為”與“醫務人員開處方行為”,司法實踐中對于傳統的兼具醫生處方權和科室行政管理職權身份的案件已形成較為一致的司法裁判觀點,即認定為公務行為,以受賄罪論處。然而,在同時具備護理和管理職責的護士長利用申領醫用耗材的職務便利,收受耗材銷售人員回扣的案件中,能否將護士長耗材申領行為視為公務,成為司法認定難點。
一、公立醫院護士長耗材申領權的“公務”認定爭議
[基本案情]黃某系X市兒童醫院心血管內科護士長,負責本科室醫用耗材的領取、使用,同時負責向醫院設備供應科提出使用、更換醫用耗材的品牌、型號,醫院設備供應科從設備庫房中供應相應的醫用耗材產品。黃某利用上述職務便利,為R公司、B公司等醫用耗材銷售企業提供幫助,按照留置針每個2元、霧化吸入器每個3元等標準,收受R公司、B公司業務員馬某、費某等人給予的回扣款現金共計24.2萬元,用于個人消費。法院認為,黃某身為公立醫院護士長,對耗材有保管、申領等管理職能,從事的工作具有公務性質,屬醫療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2]
筆者認為,案例中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意見》第4條第1款規定的采購活動,仍以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為前置要件,第2款規定了非國家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正是由于耗材申領行為可能不屬于公務行為。[3]上述認定思路沒有進一步回答,護士長申領耗材的行為是屬于形式上的采購行為,還是實質上的處方行為?護士長實施的與采購相關的申領行為是否等同于醫療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負責采購的行為?究其原因,當處于護士長身份判定這一具體語境下,現有司法解釋與理論觀點均未對“公務論”開展具體解釋,能否將護士長耗材申領行為視為公務具有一定爭議。
二、“公務論”的宣言解釋
所謂“公務論”,是指依照《刑法》第93條之規定,基于“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文義,強調在規范層面從事具有公共性質事務的實質內涵,但并未進一步指出如何區分公務與勞務。“當文本含義適用于具體語境不明確或存在爭議時,解釋者通過論理分析、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等,主體性地確定不明確法文的含義,或者選擇與以往不同的更為妥當的含義,或者對以往解釋進行修正。”[4]在體系地進行文本解釋修正時,既不能囿于固有概念,又不能忽視文本用語的相對性,對護士長身份資格的認定,傳統“公務論”仍具有借鑒意義。
(一)司法運用中的公務論
以形式說為代表的身份論、血統論等,早已被理論和實踐所拋棄。理論通說從事務內容角度實質厘定公務的范圍,認為公務僅指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帶有行政性質的事務,其本質特征是管理性、職權性。[5]司法實踐現所采納的公務論,在解釋規范上體現為“管理性”“公共性”“職權性”特征,是區別于勞務的重要特征,具體認定思路是根據行為人的身份及其職責綜合判斷。解釋思路以階層式思維,遞進式判定從事公務的范圍,認為公務具有法律性特征,這種特征必然體現在行為人所代表的身份上,于是以行為人的法律身份為基礎,從事關系到多數人或者不特定人的利益,并同時具有裁量、判斷、決定性質的事務。[6]該論借鑒域外公務論,從更為實質的角度界定公務范圍,將與職權相關的公共事務納入公務性質衡量,較之理論通說更為明確。
(二)現有公務論的運用困境
在實然狀態下,護士長職責中必然包含了上述管理職責,部分公立醫院職責文件中明確規定了護士長具有護理管理、耗材領用管理、病房管理等帶有行政管理性質的職責內容。依照通說觀點,可以直接得出護士長在領用耗材時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結論。即使采用更為實質的觀點,護士長具備事業單位編制身份,申領耗材行為具有一定的判斷性、決定性,所申領耗材作用于不特定的病患對象,其申領行為兼具職權性和公共事務性質,仍可得出從事公務的結論。然而,實踐中不少案件的裁判結果表明,較之護士長職務更高的分管護理工作的醫院院長助理、護理部主任或科室主任,利用負責領用骨科材料等醫用材料的職務便利,按照銷售數額收受醫用材料公司給予的回扣款,法院認定被告人未直接參與采購活動,而是利用處方權的醫療行為,從而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論處。依照現有公務論,同樣是領用醫用耗材,由于護士長不具備醫生的處方權,其本身的職權具備管理性質,只能認定為受賄罪。
(三)公務與勞務的實質性界分
針對現有“公務論”在認定醫療受賄領域案件時缺乏顯性的界限要素,有論者指出:“對醫療機構人員的工作性質進行辨析,區分公務與勞務、技術等內涵。從事公務的‘務’是組織、管理職務,而不是一般的技術職務,醫療行政人員普通的財務、技術、統計職能也不能算是公務行為。”[7]另有觀點認為:“國有醫院從事醫療數據統計、傳輸、維護等信息管理工作的信息管理員,無論屬于在編人員,還是非在編人員,因其工作兼具技術性和管理性雙重屬性,具有公務性質,故都以國家工作人員論。”[8]上述觀點雖然存在差異,但均以區分“技術”和“管理”為論證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筆者認為,具體到上位概念“依照法律從事公務”,“依照法律”屬于表面的構成要件要素,不為違法性程度提供依據,在具體認定時無須特別關注,對于“從事公務”應當統籌界限要素“勞務”,將“公務論”再定義為“行為人實施的具有一定裁量性,影響不特定或多數人或公共機構權益的職權性管理事項,但純粹提供體力或智力成果轉化的一般性勞作的事項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勞務”具體可以細化為“普通勞務”“技術性勞務”“技術性管理勞務”。“普通勞務”是指既不具備支配性管理性質,也不具備智力成果轉化的一般性勞作;“技術性勞務”是指具備一定智力成果的純粹性知識判斷事務;“技術性管理勞務”是指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權益實施的兼具管理和一定智力成果的事務,例如具有行政管理職權的科室主任醫生以處方形式推薦藥品的行為就兼具技術性與管理性特征。顯然,前兩種勞務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務”,第三種勞務性質可能存在一定爭議,需要在案件事實與規范對應的過程中結合法益保護的“質”與“量”綜合判定。
三、法益衡量視閾下護士長耗材申領權之識別
在解釋規范時應從實質出發,行為所侵犯或體現的法益務必成為規范構成要件要素的解釋理由。護士長申領耗材行為的公務性質認定,應從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法益中衡量。
(一)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法益衡量
當前有學說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為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以及公民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屬國家法益范疇。[9]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尚未形成一致觀點,理論上有廉潔性說、不可收買性說、公正性說、競爭秩序說、背信說等形色觀點,該罪的法益必然與社會法益觀念下的市場經濟秩序、公司企業管理秩序密切相關,鑒于司法實踐中已使用商業賄賂概念,生活事實所包含的市場經濟關系中也體現出商事關系的信賴特征,筆者更傾向于本罪法益以背信為實質,來源于公司對員工履行忠實義務的合理信賴,限定于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委托關系。二罪所保護法益的實質區分源于權源之間的差異,受賄罪法益背后是國家機器的滲透,權力尋租的權源以國家力量賦予,體現職權行為源頭的國家性、公共性,權力的尋租直接或間接侵害了國家利益,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法益乃透過經濟秩序被市場利益賦予尋租空間的非公共性權源,侵害的是不涉及狹義的國家利益的純粹市場秩序。“公共事務必須體現國家性的面向,其核心特征在于,處理相應事務的權限根源于主權者的權力,行為人是受主權者的委托而代為處理相應的事務。”[10]上述“技術性管理勞務”的公務性辨析,應透過此種法益觀的衡量,剝離權源和受損利益性質加以判定。申言之,經過法益觀衡量,判斷特定行為在賄賂犯罪體系中的公務性,需明確權力來源及受損法益的性質,這也是準確識別護士長耗材申領權性質的關鍵。
(二)護士長耗材申領權能的性質交織
公立醫院護士長對所申領耗材、藥品的品牌、型號具有決定權,所領用耗材、藥品作用于不特定多數病患,似乎屬于公務范疇。然而,生活經驗表明某類型醫用耗材、醫療器械的選用可能并非純粹的管理性事務。例如,哪個品牌的留置針在減少患兒打針恐懼感時效果最優以及在避免藥物之間的反應時功效最佳,何種型號的霧化面罩對霧化吸入療法最有幫助,哪種醫用冷敷貼對緩解皮膚過敏、痤瘡等更具效果,該類事務的判定恐早已超出絕大多數一般人的認知能力,屬于專業人員的專屬領域,需要特定智力成果的轉化,必然同時交織著管理性和技術性判定,這與醫生處方行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應屬上述所論“技術性管理勞務”。
有反對者認為,即使認為護士長申領耗材行為類似于“醫生處方權”,但從形式上看卻不存在適用空間。《處方管理辦法》第2條第1款明確規定“本辦法所稱處方,是指由注冊的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在診療活動中為患者開具的、由取得藥學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的藥學專業技術人員審核、調配、核對,并作為患者用藥憑證的醫療文書”,第8條第1款也規定“經注冊的執業醫師在執業地點取得相應的處方權”。因此從規范上看,處方限定為藥物,而不包括器械耗材,護士長也不具備處方權資格,無法評價為“處方行為”。然而,“臨床上除了處方藥,也有許多非處方藥物的治療方法,護士處方權一定要和醫生一樣嗎?還是一個包含了藥物和非藥物的‘大處方’概念?”[11]顯然,該問題不僅是刑法問題,更是社會問題。筆者認為,從事實上看護士長耗材申領權雖無法等同“處方行為”,但不排除特定情形下具有與處方行為的高度疊合性,需進一步明晰。
(三)護士長耗材申領權能的性質辨析
作為“技術性管理勞務”的耗材申領行為之性質,應根據前述所論權源和受損利益的法益衡量觀,結合不同情狀構建體系性識別機制。毫無疑問,公立醫院采購評標委員會成員或參與采購結算具有一定決策權能的人員所行使的醫用耗材采購和結算權限源于國家權能賦予的公權力,且直接關乎公立醫院利益(背后是國家利益),該采購權應當認定為公務。據此,公務性質取決于耗材申領權是否對采購權發揮決定性作用。
第一,當護士長的耗材申領權支配或決定了采購權,其權源路徑已具備覆蓋采購權的高度蓋然性,在性質上等同于采購權時,應當認定為公務行為。有論者指出:“凡是醫療機構藥庫未庫存的藥品,臨床科室主任利用職權提交用藥申請,產生了對應采購單、指導藥企供貨并收取回扣,都可以認定為受賄罪。”[12]同理,對于護士長申領耗材,也應當通過單一耗材申請權與采購權之間的關系判定行為性質。例如,某公立醫院護士長所申領耗材的品牌型號醫院設備庫房中并不存在,在無需經過規定的審批流程或審批流程流于形式的情況下,醫院相關人員根據護士長的申領要求即采購了上述耗材進入設備庫房,用于該科室領用的,該護士長的領用行為已覆蓋采購權,應當認定為公務。
第二,當護士長的耗材申領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采購權,其權源路徑同時具備申領的內部秩序性與采購的公共事務性時,應當認定為公務行為。例如,某公立醫院護士長的耗材申領權限同時具有即領用即結算的功能,或醫院定期根據所申領耗材型號數量與供應商進行結算的,表明該申領權已將權源擴展至采購活動,在行為性質上發生競合,同時具備了勞務性和公務性,此時在解釋論上面臨抉擇。此種情形中的“技術性管理勞務”已并非純粹的技術性勞務行為,而是兼顧技術性判斷和管理性抉擇之行為,發生了勞務與公務間的性質競合,應認定為公務行為。
第三,當護士長的耗材申領權獨立于采購權或并不對采購權造成支配性影響,其權源路徑僅來源于醫院內部秩序管理,不應當認定為公務行為。前述案例中護士長所申領的耗材器械均系已經過采購流程進入醫院設備庫房,無論如何更換、申領甚至管理相關耗材,其行為方式均未超出醫院內部管理范疇,更類似于醫生處方行為,在“技術性管理勞務”領域內其管理職能的權源已終結于醫院采購機制內部,單純以護士長申領權不可能對背后所征表的國家性利益造成損害,宜認定為技術性勞務行為。
四、類案司法認定之修正
該類案件的司法認定大前提源于《刑法》第93條“國家工作人員范圍”、《意見》第4條“采購活動和處方行為”以及《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中關于“從事公務”的解釋。當有權解釋的精準度無法定位紛繁的案件事實時,當諸多混亂的概念纏繞于案件事實時,爭議必然產生,筆者認為,司法實踐對類案的認定思路應作如下修正。
(一)規范概念歧義時應樹立“法益保護為先”的觀念
當“從事公務”“采購活動”“開處方職務便利”“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等規范意旨及有權解釋從不同的維度、上下位概念、涵攝區間等預設案件事實時,司法人員應剝離概念迷霧,剔除先入為主的固有認定觀念,價值中立地以預適用罪名間的法益衡量為解釋理由,比較此罪與彼罪間的法益區別,并以此介入規范概念之中。在認定護士長耗材申領行為性質時,針對案件事實與抽象規范概念間難以對應的法律適用困境,務必審慎結合案件事實比較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間的法益保護差異,剝離出二者權源及受損利益的實質區別,合理界分公務與技術性勞務、技術性管理勞務,對應出耗材申領權與采購權限間的支配性影響及權源性質異同,從而準確識別規范解釋之旨趣。換言之,當前述規范概念出現歧義時,司法人員應當首先確立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法益間的顯著區別,結合特定案件事實,準確判定護士長耗材申領行為權源性質的管理性、技術性,并結合對采購權的實質作用,做出準確認定。
(二)將“從事公務”作為認定構成要件身份的唯一標準
當前司法實踐中,之所以形成遞進式認定思路,即以形式上的編制身份加之以實質上的代表公職行使公務為綜合基準,具有證據法上的因素。因為用以證明編制身份的書證之取證難度遠低于實質的公務事實的取證,后者甚至事先無法設想證據種類、證據鏈組成內容,其證明力亦時常存有異議。誠然,司法標準并非唯編制身份論,但該思路使得監察人員、司法人員在綜合判定時,對編制身份形成“先前的固有印象”,再對公務的實質標準加以斷定之時,極易簡化裁量理由,甚至出現表面上論證公務性質,而實際上直接以編制身份推定公務性質的現象。例如,有監察理論研究者認為:“從事公務之行為具備公務行為的組織性、公益性、民主性,參與公務活動,實際承擔公務職能的非政府組織、企業(包括私營企業)和公民個人,但凡存在侵犯公務之廉潔性、公共性和安全性之行為,均屬于監察對象之范圍。”[13]這表明當前“公務論”存在監察與司法銜接之困境,這對于絕大多數傳統的國家機關公職人員案件不存異議,但對于類似于護士長申領耗材收受賄賂之行為卻存在不同觀點。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案件時,應明確將“從事公務”作為認定構成要件身份的唯一標準,按照前述權源與受損利益的實質標準引導調查取證。法院在適用法律時,運用現有“公務論”同時應更為精準的辨析被告人所從事活動的勞務與公務性質,從而做出準確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