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們的小說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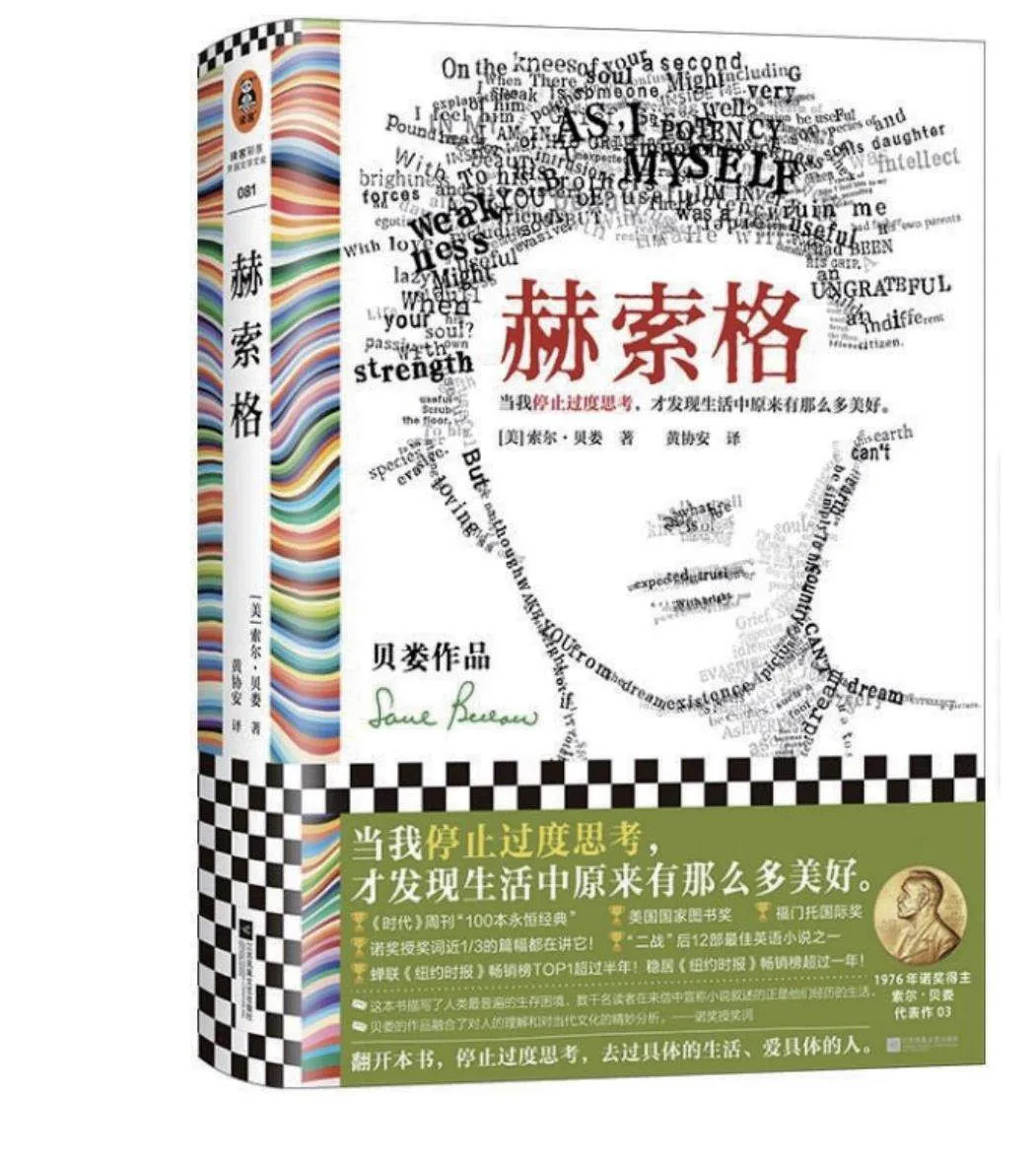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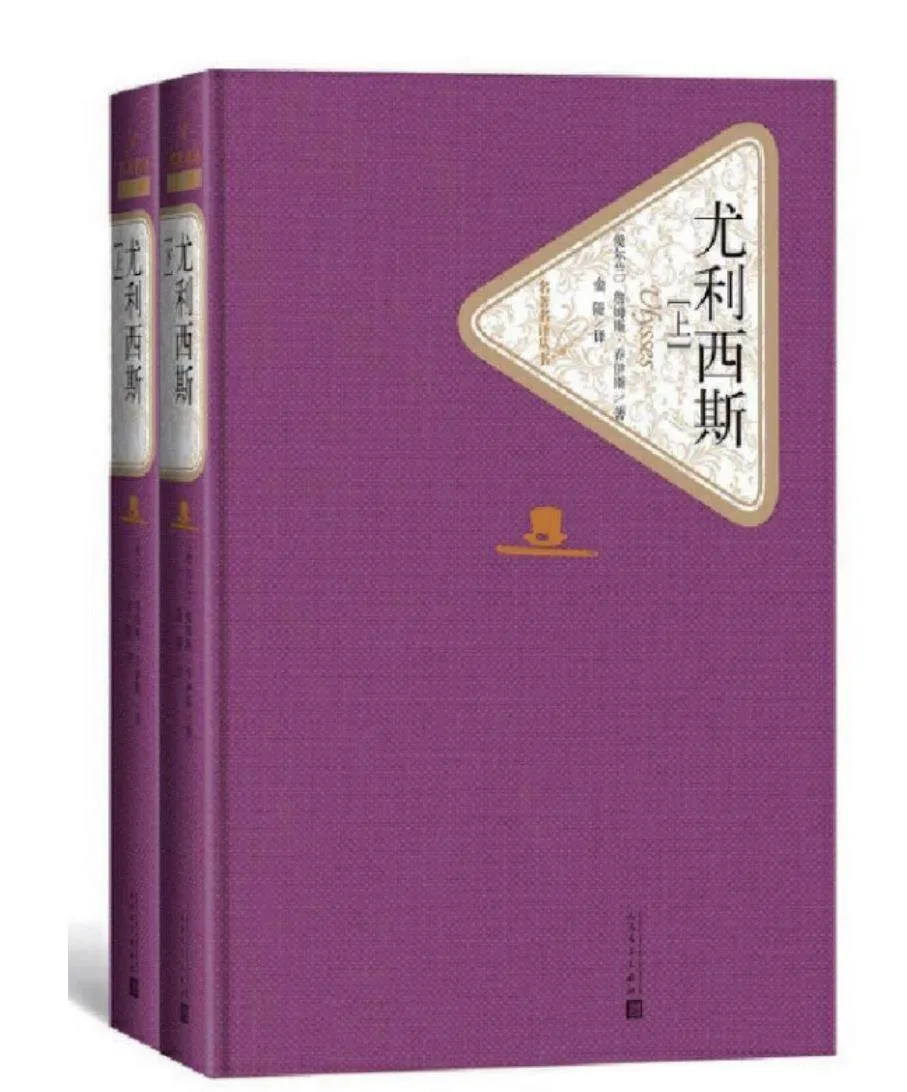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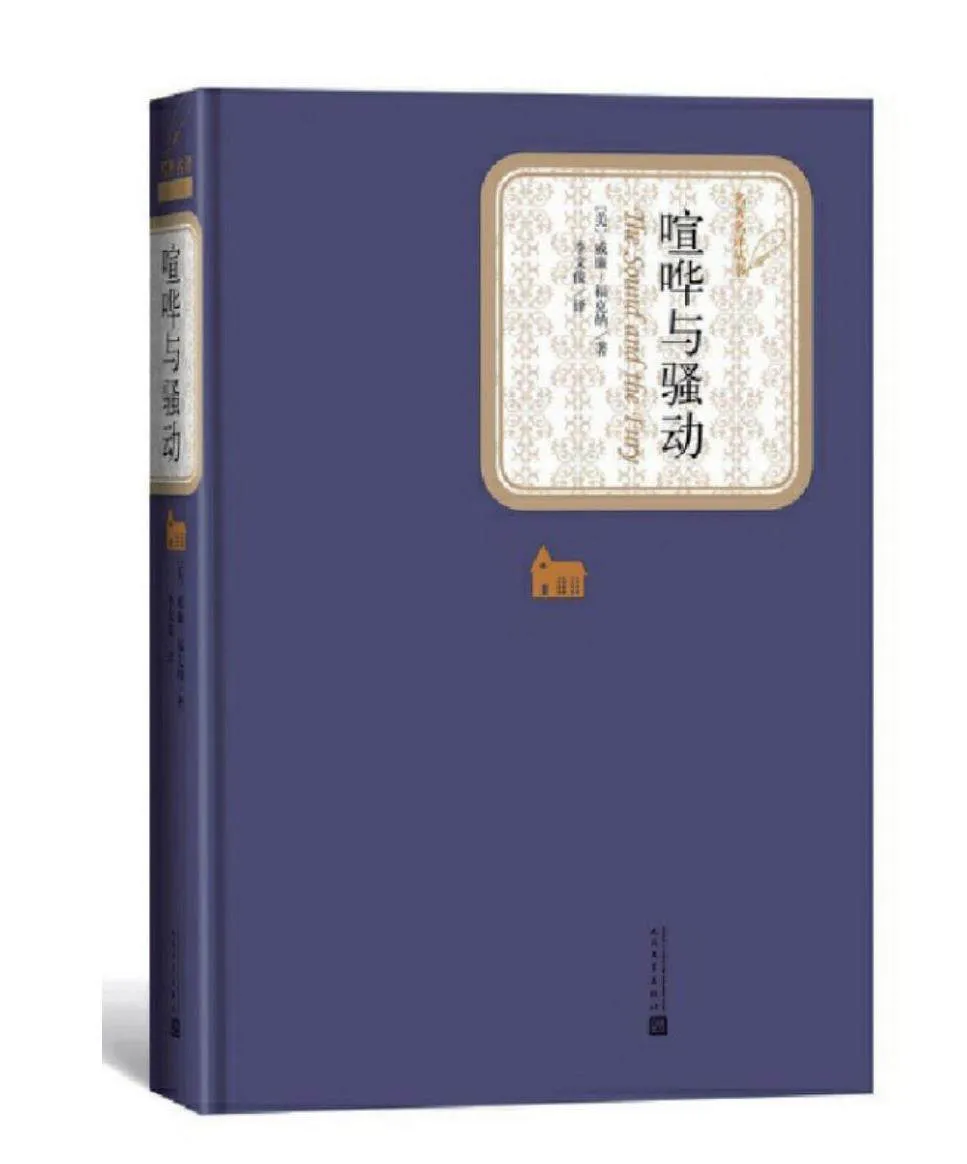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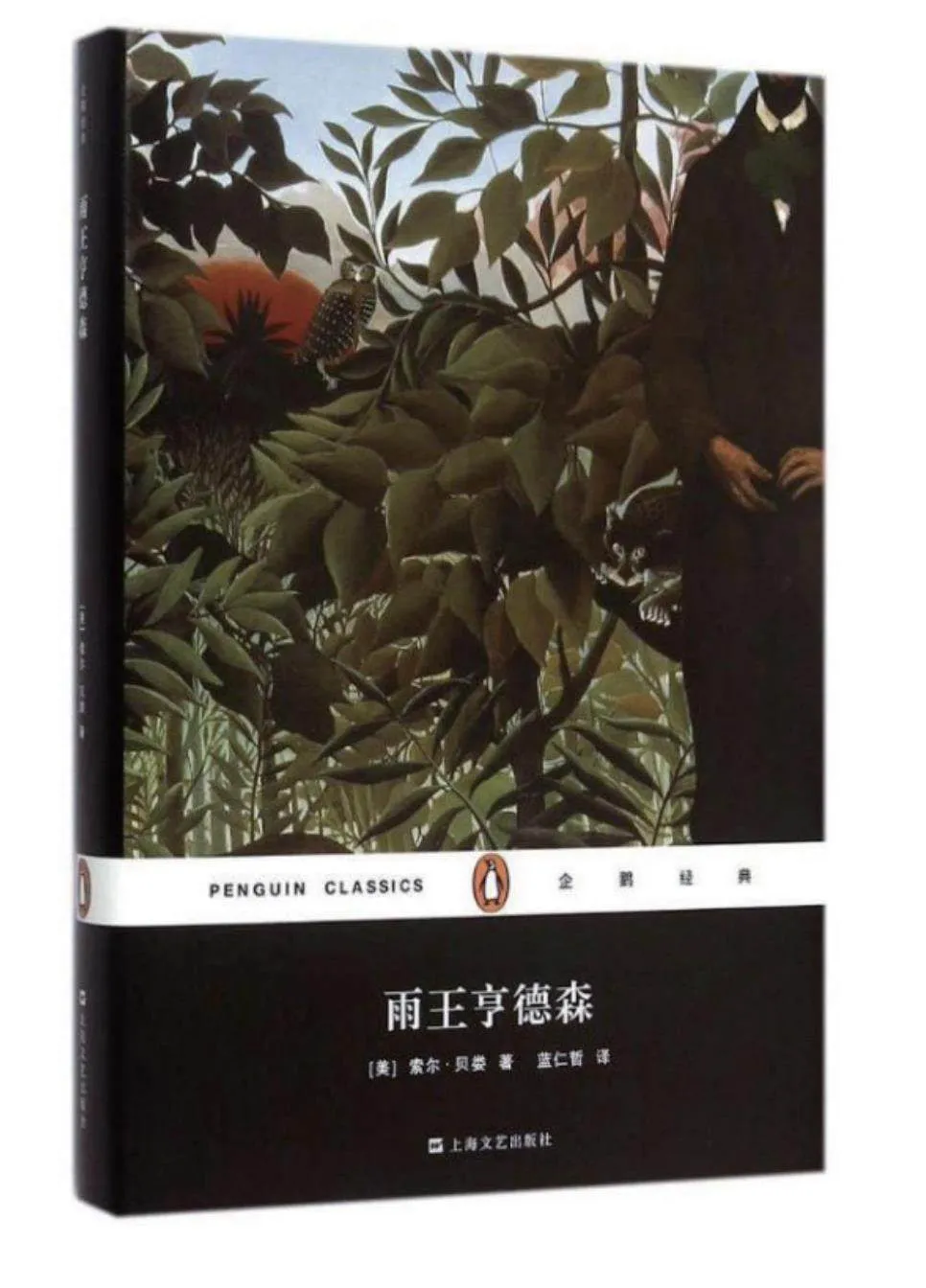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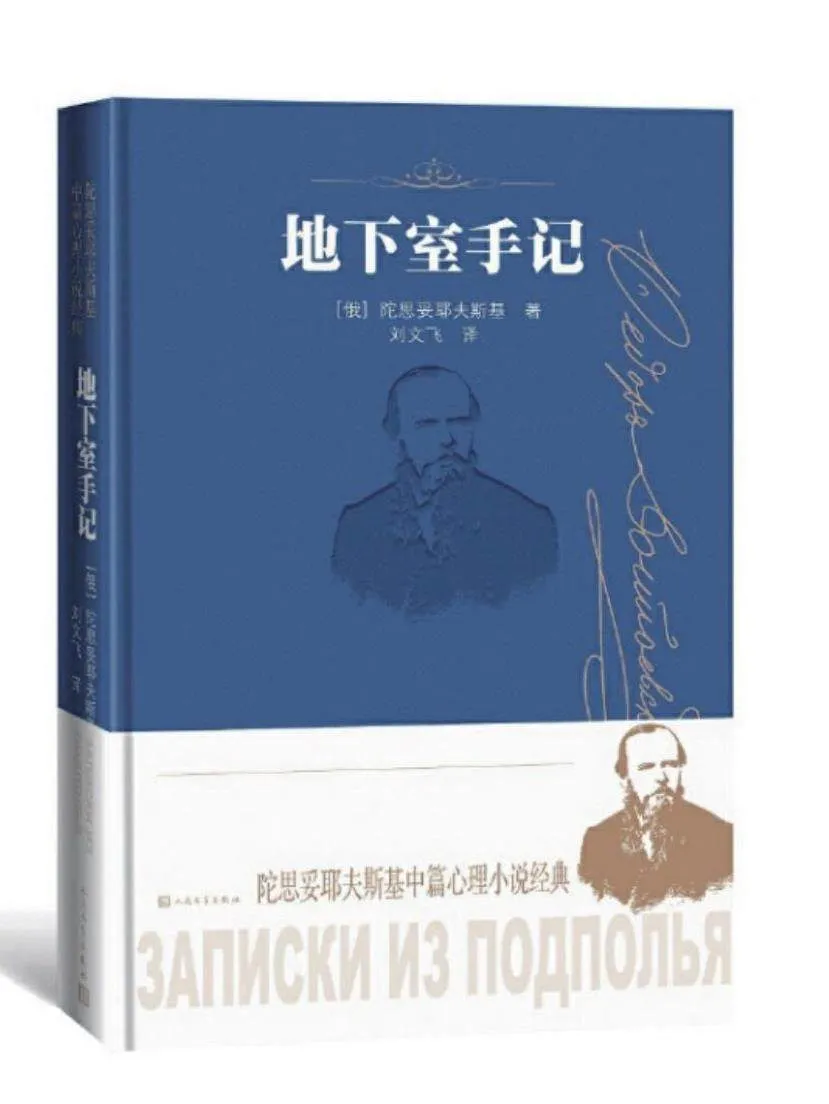
第一章 美國作家福克納:
把意識流融入人物的內心世界
作者按:本章主要以李文俊的中譯本為依據。對非英語、非西方文化背景的讀者來說, 看這個譯本比看英文原著更易于掌握,因為譯者在注釋方面下了許多功夫,除了向讀者解釋一些背景資料外,還在意識流敘事中為讀者說明時空轉換的關系。本章小說引文出自福克納: 《喧嘩與騷動》,李文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4。此外,本章引述的評論和作者自述皆出自《福克納評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0。
在介紹外國經典文學作品的計劃中,遲遲沒有寫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 1962)的《喧嘩與騷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一直在名單中,中國臺灣譯作《聲音與憤怒》,是我最早看的志文出版社譯本),是因為他的這本小說過于復雜,怕在有限的篇幅內不能詳細介紹其精粹。近年由于教寫作課的關系,我都會以這部小說為意識流技巧的模板。 雖然我知道學生不一定會看完整本小說,但能讓他們涉獵這樣一本技巧高超的名著,對其小說技法的學習不無幫助。
今天之所以介紹《喧嘩與騷動》,是因為最近重讀福克納的傳記和作品,興起了寫小說的念頭,順便想通過對這部小說寫作技藝的分析,探討一下小說寫作的藝術。
討論福克納的作品,總是難免牽涉現代小說的技法和藝術。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和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意識流技巧,讓福克納由寫實主義進入現代主義創作之林。年輕時一直醉心于文學寫作的福克納,由筆記、散文、 詩歌到小說,都在努力嘗試找出一種福克納風格。不同于海明威的簡潔明快,福克納通過不同人物的內心世界刻意地展示文學語言的藝術 (兩人的敵對風格也造成了兩派讀者的對立)。
福克納是美國南方文學的代表人物,在后面介紹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以描寫黑人內心世界為主的莫里森,就被稱為福克納的繼承者。福克納在美國南方密西西比州一個沒落的莊園出生和成長,高中沒讀完便輟學。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服過兵役,復員后常常以此為自豪,整日穿著軍服穿街過巷,四處宣揚自己在戰役中受過傷,有時甚至用走路一拐一拐來證明。但事實上他從沒上過戰場,由此可見他當時的虛榮心。雖然高中沒畢業,但他于 1919年以退伍軍人的身份進了密歇根大學,后來因為覺得無聊而中途輟學。他希望當一個專業作家,于是一面打工,一面寫作投稿。
愛好文學的福克納在大學一年級時便不時在校刊發表詩歌與短篇小說,后來休學了,仍有作品在校刊發表。雖然能賺點稿費,但這離他專業寫作的理想還遠。福克納的工作經歷可說是劣跡斑斑,他從沒有認真做好過一份工作, 總是被辭退,他曾在家鄉的郵局工作過一段時間(由他一人管理整個郵局,南方小鎮郵局只是一個小站),但整天只是讀書寫作,對應該由他處理的郵件愛理不理,惹來不少投訴,最后被辭退。不過,那段時期他的閱讀量驚人, 通過郵局郵遞的文學雜志總是由他先看,他更是在上班時間讀完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
當時的福克納已開始專注于小說創作, 但他的作品時常遭文學雜志退稿。他最后認識了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兩人成了忘年之交,他通過安德森認識了一些雜志編輯和出版商,作品和讀者見面的機會才多起來。(兩人后來卻不相往來,因為福克納在一篇隨筆中諷刺了安德森。)福克納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軍餉》(Soldier's Pay)也是通過安德森向出版社推介才得以出版。之后他拿了版稅去歐洲游歷,期望感受一下當時最前衛的文學風貌。
《喧嘩與騷動》是福克納寫于1928年的作品(初版是在1929年),之前他出版過兩部小說:《軍餉》(1925)和《蚊群》(Mosquitoes)(1927),其中《軍餉》的寫作手法接近現實主義,《蚊群》以蚊子比喻病態的美國藝術家,中間用了一些意識流技巧。可是,兩部作品都沒有獲得文評界關注,這讓他十分氣餒。由于他已經讀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其他歐洲前衛文學作品,十分醉心于對寫作技巧的運用, 于是他決心不理市場,開始創作一部他認為在技巧和風格上都能獨樹一幟的作品—這就是后來為他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喧嘩與騷動》。 這部小說也是福克納在藝術上最成熟的小說創作,他不止一次地說,這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一部作品。
《喧嘩與騷動》的書名出自莎士比亞悲劇 《麥克白》第五幕第五場麥克白的著名臺詞:“人生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福克納鐘愛《喧嘩與騷動》,是因為這部小說是他“最華麗的敗筆”(most splendid failure)。由于不再擔心是否能得到批評家和讀者的喜愛,他以自己想寫的方式去敘說美國南方一個白人家族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康普生一家的四個兒女身上,由大哥昆丁、三弟賈森以及智障的小兒子班吉輪流出場敘述。而三兄弟講的故事,卻是圍繞著二姊凱蒂。福克納后來表示,他想講的是凱蒂的故事,但他又覺得三兄弟的敘述仍不足以說清楚,于是又加了保姆迪爾西做總結式的敘述。因而全書共分四章, 分別從四個人物的視角去述說發生在康普生家的故事,其中凱蒂則是整個小說的靈魂。
即使在90多年后的今天看來,福克納的敘事手法仍是頗為復雜的。通過四個人物的不同視角,福克納讓讀者知道了康普生一家最反叛的女兒凱蒂半生的遭遇。這里先綜述一下整個故事的大概。
《喧嘩與騷動》的敘事時間點是1910年和1928年,而故事時間的跨度則從1898年至 1928年。康普生一家曾經是當地的望族,家中原有頗多田地和黑奴,后來破敗得只剩下一幢大宅、黑人保姆迪爾西和她的小外孫勒斯特。一家之主的康普生雖說是律師,但很少接洽業務,更是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最后病逝于1912 年。康普生太太是一個自私冷酷的女人,有事無事都嘮嘮叨叨。由于她的這個性格,家里的孩子都難以獲得溫情和母愛,其中女兒凱蒂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變得反叛和浪蕩。凱蒂企圖從淑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結果釀成了悲劇。她10多歲就與男性交往,懷了身孕后不得已跟另一名男子結婚,但婚后男方發現真相, 于是棄她而去,而她只有把私生女寄養在母親家,自己離家出走。
故事中的大哥昆丁深愛著妹妹凱蒂,甚至愛得超越了兄妹之情。兩兄妹也非常友好,但凱蒂的叛逆性格使得她在家里成了一個離經叛道的人物。她濫交,男女關系混亂,并因此造成悲劇。她離家出走后把私生女小昆丁遺留在家里,脆弱而多愁善感的昆丁愛她甚深,看到她的墮落,自己也變得瘋狂,最后于1910年投河自盡。昆丁自小和凱蒂感情要好,但性格多愁善感,更因家族沒落而精神萎靡。他對妹妹的鐘愛已到了癡戀的地步,甚至向父親述說虛構的亂倫故事。妹妹的未婚先孕,使他立即失去了精神平衡。
賈森排行第三,是凱蒂的大弟弟,也是一家雜貨鋪的小伙計。他是一個典型的功利主義者,只看重金錢利益;他記仇,為了報復,做起事來往往不顧后果。和昆丁相反,他對凱蒂充滿怨恨,因為他以為是凱蒂的私生活和壞名聲令他失去了本來應該得到的工作。他甚至把怨恨延伸至凱蒂的私生女小昆丁以及關心凱蒂母女的黑人女傭迪爾西。福克納說過:“對我來說,賈森純粹是惡的代表。依我看,從我的想象里產生出來的形象中,他是最最邪惡的一個。”
班吉是康普生家的小兒子,他天生是個智障者。故事由他揭開序幕。那是1928年的一天, 他已經33歲,但是智力還停留在三歲的階段。 姐姐凱蒂自小就很照顧他,他也十分喜歡凱蒂, 甚至片刻也不想離開她。當凱蒂離家出走后,他時常通過氣味和對其他對象的聯想,回憶他們相處的時光。
上述的故事不是線性敘事,而是通過班吉、 昆丁和賈森三個人物的回憶和獨白并成的,再加上家中女傭迪爾西以全知觀點講述和補充前面三人的故事。可是,小說出版后有不少讀者感到難以整理出故事內容。15年之后,福克納在《袖珍本福克納文集》中補寫了兩篇附錄, 詳細地交代了康普生家族的故事。(見中譯本附錄。福克納常常說,他把《喧嘩與騷動》的故事寫了五遍。)
福克納利用班吉這個人物的先天缺陷展開敘事,其間以意識流技法穿插了近30年的回憶片段。班吉沒有邏輯思維能力,只能憑感覺和腦海中遺留下的印象將事件重組,因此很容易把過去的事與當前的事混淆在一起。對作者而言,這是最能施展意識流技法的一個人物。通過理解他腦海中過去和現在重疊的意象,讀者要十分細心才能整理出一個故事大概:最鐘愛他和最照顧他的姐姐凱蒂于1911年即他14歲那年離家出走后,他整個生活失去了重心。每次看到和感覺到與凱蒂有關聯的聲音、畫面或氣味時,他腦子里都會出現兩人相處的一些片段。在這一章里面,福克納十分著意經營意識流技法—當時最前衛的小說創作手法。福克納把這一章形容為“一個白癡講的故事”,所以他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班吉的意識流動交代故事脈絡。在這一章中,他告訴了讀者正走向沒落的康普生家族里面各個人物的特征,以及他們和班吉的關系。有批評家指出,這一章是 “一種賦格曲式的排列與組合,由所見、所聽、 所嗅到的與行動組成,它們有許多本身沒有意義但是拼在一起就成了某種十字花刺繡般的圖形”。而福克納正是通過人物的意識流動,編織成時間與空間的重疊意象,從而構成了一個時空交錯的故事。
第二章由康普生家中長子昆丁以內心獨白的形式敘事。福克納在這里用的語言與前一章不同。昆丁是哈佛大學的高才生,他的語言邏輯性強,說理多,但大都是自言自語,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中的內心獨白。 福克納在這里強調的是時間,他通過意識流的敘事手法,把時間和空間重疊在一起,讓讀者感受到敘事者當時的心理混亂狀態。關于時間, 薩特在評論這部小說時指出,福克納的哲學是時間的哲學:“……一個人是他的不幸的總和。 有一天你會覺得不幸是會厭倦的,然而時間是你的不幸……”(見第二章《昆丁的自白》)薩特認為那是這部小說真正的主題,他看出福克納采用的寫作方法似乎是對時間的否定。(昆丁自白中那只手表是被弄壞了的。)通過這一章,我們發現《喧嘩與騷動》其中的一個敘事原則是打破時間的順序,并同時重置空間的位置。(班吉由一個現實中的空間維度穿越了空間和時間。)昆丁對著手表獨白:“……經常對一個武斷的圓盤上那機械的指針位置進行思考,那是心理活動一個征象。父親說的,就像出汗是排泄。” 昆丁嘗試探究時間之謎,他認為要理解真正的時間,必須拋棄這些計時的手段,“……凡是被小小的齒輪滴答滴答滴掉的時間都是死了的; 只有時鐘停下,時間才活了”。所以根據薩特的看法,“昆丁毀掉他的手表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它迫使我們在鐘表的幫助下看到時間。白癡班吉的時間也不是用鐘表計算的,因為他不識鐘表”。
在這一章中,昆丁的獨白有點語無倫次。 一路讀下去,我們知道,當時由于他鐘愛的妹妹凱蒂未婚先孕,并跟另一個男子結婚,他感到十分失望。當時他正在考慮自殺。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一個人在語無倫次地獨白,另一方面又明白他的語無倫次有跡可循。在昆丁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他為人善良,是父親的崇拜者,甚至繼承了父親的傳統道德觀念。當他知道凱蒂失去童貞時,甚至打算跟那個男人決斗。凱蒂的貞潔對他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內心對妹妹有著戀人的感覺;他甚至對父親虛構和妹妹有亂倫關系。
第三個出場敘事的是賈森。他在康普生家族中是一個行事魯莽的人。他沒有智障,也沒有哥哥的多愁善感,但他為人現實、功利,從另一方面看,他像是一個瘋子—貪婪、自私自利、無情無義。福克納在這一章賦予賈森的語言是直接而粗鄙的,對讀者來說,讀來易懂得多。賈森的敘述主要交代當前(1928年)的事情,是沒有時空交錯轉折的線性敘事。例如開頭第一句便十分直接,“Once a bitch always a bitch”,簡單的一句便盡顯他的粗鄙性格。這一章的敘事風格直接而簡單,因而補充了前兩章模糊不清和抽象的敘述。尤其對于弟弟班吉被閹割的原因、昆丁的自殺以及凱蒂的離婚, 這一章都給了讀者一個較清晰的印象。通過賈森的敘述,我們又知道,他是康普生太太最疼愛的兒子,大哥昆丁自殺后,他成了家中的經濟支柱。因此,他內心對哥哥和妹妹都充滿怨恨, 在字里行間對他們百般挖苦,語言粗俗,口氣輕佻。
黑人女傭迪爾西是最后一個敘事者—福克納賦予她一種圣母瑪利亞般的性格。(小說與 《圣經》有很強的連帶關系,后面補充。)福克納說過:“迪爾西是我自己最喜愛的人物之一, 因為她勇敢、大膽、豪爽、溫厚、誠實。”她對康普生一家照顧有加,面對一個破敗和沒落的家族,她寄予無限的同情。她尤其同情班吉和凱蒂的遭遇,并且處處保護他們。在冰冷的康普生家族中,她可說是各人的精神支柱。她忠心和慈愛,比近乎病態的其他敘事者更能看清現實。對福克納來說,迪爾西是“人性的復活” 的理想—這在福克納有意把迪爾西的敘事放在復活節這一天可以看得出來。(譯者李文俊指出,根據《路加福音》,耶穌復活那天,彼得到耶穌的墳墓那里,“只見細麻布在那里”,耶穌的遺體已經不見了。在《喧嘩與騷動》里, 1928年復活節這一天,康普生家的人發現,小昆丁的臥室里,除了她匆忙逃走時留下的一些雜亂衣物外,也是空無一物。在《圣經》里, 耶穌復活了。但是在《喧嘩與騷動》里,如果說有復活的人,也不體現在康普生家后裔的身上。福克納經常在他的作品里運用象征手法, 這里用的是“逆轉式”的象征手法。)
在《喧嘩與騷動》中,最具有象征意義的一個場景是童年時期三兄弟望著凱蒂爬在樹上窺探屋內正在舉行的喪禮。三個男孩子仰頭望, 看到的是凱蒂沾了泥巴的內褲。福克納以此象征凱蒂的不貞,也象征康普生家族的衰落。從凱蒂童年時期的反叛,可以看出她的出格和大膽,她的行為舉止和這個推崇傳統價值觀的南方家庭格格不入。對比她的兩個兄長,他們連爬上樹的勇氣都沒有。福克納曾經表示,凱蒂這個角色實在太美麗,令他十分著迷,所以整個小說都是圍繞著凱蒂的遭遇展開。
像《喧嘩與騷動》這樣一部在當時來說敘事手法大膽、語言和結構看似散亂的小說,出版后并沒有得到多大回響,尤其在美國本土, 許多讀者都看不懂這部小說。但是在歐洲,這部小說逐漸得到出版商和作家的留意,深入的評論尤其是探討這部小說寫作技巧的文章陸續出現,使得福克納在歐洲漸漸被人注意。幾年之后,《喧嘩與騷動》成了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其意識流手法堪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 媲美,二者并列為20世紀的杰作。
第二章 美國作家貝婁:
通過象征探討人生意義
作者按:本章小說引文皆由筆者譯自英文原著。
最近由于編輯舊作的關系,找到了一篇寫于1977年的書評《貝羅的超人—雨王韓德信》,原著目前一般的通行譯法是《雨王亨德森》,作者是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重看自己的文章,驚覺歲月催人老,也驚覺當時所介紹的這部小說仍然那樣富有現實意義。
《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以夸張和漫畫化的黑色喜劇創作手法,描寫了一個在美國從事養豬業的百萬富翁因為找不到活著的意義,特意走到非洲去,希望找到人生真義的故事。說這部寫于60多年前的小說具有現實意義,是因為我們今天仍有不少人在想著同一個問題,人到中年,像書中主人公亨德森一樣50多歲的人,回首半生,有時不禁自問: 我這一生難道就這樣過了嗎?可不可以改變? 怎樣改變?
1998年,紐約公共圖書館選出的20世紀 100部英文小說中,就有貝婁這部小說。《雨王亨德森》之所以成為經典,除了作者認為這是他寫得最好的一部小說外,還因為里面的主題像是回應今天耽于消費逸樂的社會。1977年我在《大拇指》中這樣介紹小說的內容:
小說的開頭,韓德信正處于一種絕望的狀態;他苦感于過去的生活毫無意義,內心深處有一個聲SSe7T1FLa5iwHT/CHz9PXw==音不停地響著:“我要!我要!我要!”要什么呢?他像是知道,但因為得不著,卻又仿佛不知道。
重讀寫于40多年前的書評,亨德森那種“我要!我要!”的聲音,仿佛又回到我的腦海里。 記得那時候我是貝婁的“粉絲”,他還沒有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我就已十分喜歡他的小說。 由《晃來晃去的人》《受害者》《奧吉 ·瑪琪歷險記》《雨王亨德森》,到《赫索格》《賽姆勒先生的行星》等,我在美國圖書館把英文原著一本一本地借回家看,再加上部分中文譯本, 例如劉紹銘先生翻譯的《何索》(《赫索格》),總算生吞活剝地看了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后來分析,喜歡貝婁,除了跟我一向喜歡的哲學思考甚有關系外,還因為我仿佛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中的主人公,扮成當代美國知識分子,混進了貝婁的小說中。我不知道這是否和我那時的“地下室”性格有關,但顯然他的小說十分符合我當時的口味。而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我那時也是一個尼采迷,對《雨王亨德森》中的超人主題自然十分著迷。
重讀多年前自己寫的這篇書評,我發覺原來這幾十年來我一直都在響應亨德森“我要!我要!”的呼喊。
下面我再借那篇書評講述一下亨德森的故事:
“是什么令我走到非洲去的?”他解釋說,就是心里面的那個聲音。他是百萬富翁,今年55歲,現在的太太是第二任。他養豬,是因為對于生活感到失望,對于同時代的人感到失望……他學拉小提琴,是想借此和逝去的父親互通信息。他的生活只有過去:“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女朋友,我的孩子,我的動物,我的習慣,我的金錢,我的音樂課,我的偏見,我的酗酒,我的獸欲,我的牙痛,我的臉孔,我的靈魂,我要高聲喊叫:‘不!不!走開。我詛咒你,滾開!’但怎樣叫它滾開?它們是屬于我的,是我自己的。”對于將來,或是現在,他均處于一種彷徨的境況。
一天早晨,他因為和太太吵架,竟嚇斃了送早餐進來的老婦人,這使他體驗了死之可怖:“噢,真羞人!真羞人!我們怎可以呢?我們為什么由著自己這個樣子?我們在做什么?我最后安身的,齷齪沒窗的框框正等著我們啊!所以,看在上帝的分上,行動起來吧,韓德信,有朝一日,你也會像這個樣子死去的。死亡會使你消失了,除了一團腐肉,什么也沒有剩下來。因為你一事無成,所以一無所剩。趁現在還有時間—現在!行動起來吧!”
就是這樣,他被內心的那個聲音驅使著,走往非洲去。首先,他碰到了阿紐威族人,從他們的女族長處,他學到了“人是要活下去的”(Grun-Tu-Monlani)。在韓德信心目中這個女族長是個充滿智慧的女人:她是靜的,是快樂(Bittah)的代表。在她心里面沒有痛苦這回事:她不會為了焦慮而做出激烈的行動。她的族人因為有青蛙走進了水池,而不敢讓牛只喝水,以致它們活活地渴死。當全族人沉浸在這種悲哀的空氣里時,這個女族長卻微笑地接受了這種無可奈何的處境。這點,韓德信實在看不過眼;他為了拯救他們的牛,乃主動請纓要將青蛙趕掉。可是,他自制的炸彈卻把水池也炸毀了,他眼巴巴地看著池水流掉。
他從阿紐威族學到的“人是要活下去的”這個事實,使他更加迫切地尋求“怎樣活下去”的方法。他不能像阿紐威族一樣,只知生活,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不謀解決之道。他離開了。這次,他遇上了華威威族。他們的族長達夫(Dahfu)是一個哲學家,他和韓德信很快便成為朋友。在一次祈雨儀式中,韓德信以健壯的身軀捧起了他們的云神木像,于是他們封他為“雨王”。
達夫養了一頭母獅,它“會使意識發亮,會使你沸騰起來……”他要求韓德信模仿那頭母獅的動作,以期將他改變過來。面對母獅的時候,韓德信又再次面對他那不敢承認的事實—對死亡的恐懼。達夫看出,他是一個逃避者。他說,如果他能夠面對母獅而不露恐懼的神色,那他便能夠接受宇宙間最殘酷的事實—死亡了。
“它是絕不逃避的……而這正是你需要的,因為你是一個逃避者。”對韓德信來說,不但要面對它,而且要模仿它—死亡。他學它一般作爬行俯伏、吼叫。“學這頭野獸吧!”達夫告訴他,“以后你便會從中發現人性了。”和達夫相處,韓德信悟出了很多生存的道理:“我們這一代,單只是重復恐懼和絕望,而不圖改變嗎?”“一個勇敢的人會使罪惡停止不前。我不是在預言,但我覺得這個世界將由高尚的情操來駕馭。”
依照族例,族長是要捉回先王放生的雄獅的,達夫也不例外。可是,他因為被族中不滿他的祭司陷害,被那頭雄獅咬死了。達夫的死亡,使韓德信看透了生命。和雄獅比起來,困在地窖里的那頭母獅,只不過是真實的副本,是受擺布的真實,在面對死亡的一剎那,他才真正地面對那兇猛殘酷的真實。現在,他知道以前所找尋的真實,是一種虛偽的真實。他雖然高喊:“我要!我要!”而心靈卻還是沉睡著,便是這個道理。根據族例,作為“雨王”的韓德信是要繼承達夫的地位當族長的,但他已經不能再忍受那種虛偽的真實,他要逃出來,回應心里的那個聲音,找尋真實,面對死亡。他偷了代表達夫靈魂的幼獅,逃回美國去,在55歲這一年,開始讀醫科。
《雨王亨德森》是在1959年出版的,當時的貝婁已經是成名小說家,他之前出版的長篇小說《奧吉·瑪琪歷險記》為他奠定了當代杰出小說家的聲譽。不過,在那個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當道的年代,他的作品被部分批評者視為不夠前衛,他們認為他屬于維護美國傳統價值的保守派。他們指責他墨守成規、大男子主義,又批評他有種族歧視觀念并推崇精英意識。而貝婁則以小說《賽姆勒先生的行星》反駁這些指控,并且嘲諷美國社會中那種嬉皮士作風是淺薄和無聊的。他對社會問題的一些看法也讓人覺得他的思想屬于保守派,而他在 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上發表演講時說:“現今的社會,提及私生活,混亂或者幾近瘋狂;說到家庭,丈夫、妻子、家長、孩子,都困惑而迷亂;再看看社會風氣、人際交往以及性行為,更是世風日下。個人混亂了,政府也暈頭轉向了。道德的淪喪和生活的潦倒是我們長久的夢魘,我們困在這騷動的世界里,被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困擾。”
熟悉貝婁作品的人,都看出他向往美好社會的思想源自維護美國傳統價值觀的愛默生和惠特曼。而那時候,我因為常泡美國圖書館,早已看了不少這兩個人的作品。惠特曼的《草葉集》所散發的自由主義和個人價值的意識,以及愛默生所提倡的脫離歐洲影響的美國獨立精神,都曾經影響過我,而貝婁的這兩個精神導師帶給他的,是他通過小說人物對當時消費主義開始出現、功利主義盛行、國人精神受“污染”等現狀的不滿而表現出的憤世嫉俗。在《雨王亨德森》中,他試圖用他的兩個精神導師的教誨來拯救這個世界—他眼中的美國。無論他的思想有多保守,這種想法即使在今天的美國,以及受美國物質主義影響的所謂現代化都市,也十分必要。后來雖然我的思想越來越“左傾”,仍然覺得貝婁的這些看法有其可取之處。
從形式上看,貝婁的小說作品也被視為保守的。一些現代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批評家認為,他的創作風格仍然屬于寫實主義傳統,雖然里面有不少意識流或個人獨白,但他沒有像一些自封為先鋒派的作家一樣,把內容做拼貼式的處理,把人物的言行描寫得像夢游一樣,而是實實在在地描寫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以及他與他所處的世界之間的關系。貝婁也寫文章批評過當時的先鋒派作品,認為他們故作艱深。就在出版《雨王亨德森》之前,他還寫過文章譏諷那些專門在小說里面找尋象征意義的讀者,指出他們想在雞蛋里發現生命奧秘的閱讀方式,離深刻的閱讀理解太遠,已經成為一種對文學的威脅。
貝婁這些話當然是有感而發的。當時的美國批評界仍然是現代主義當道,形式主義批評充斥學院,大家關注的不是故事,而是能夠從故事中發現多少象征的東西。因此,即使故事蒼白無味也無所謂,只要里面含有“豐富”的象征意義—而這些所謂“象征意義”得由批評家來“點化”讀者。這種情形在今天的美國已經沒有那么普遍,因為各家爭鳴的批評方法使讀者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是在一些地方,例如香港地區,這種唯形式論的現代主義批評方法仍有市場,甚至影響了創作者。劉紹銘說近年來看到的香港小說是“無愛”的,我認為主要的原因也許跟這種批評和創作方法有點關系。
不過,在《雨王亨德森》這部小說中,貝婁卻跟他的讀者開了一個玩笑。正當他義正詞嚴地要求讀者不要鉆牛角尖,從雞蛋里找尋生命的奧秘時,他自己卻通過亨德森這樣一個夸張式的喜劇人物,以黑色喜劇的方式把一篇充滿象征意味的小說送到了讀者眼前。也許,貝婁是想示范一下:要寫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說,得來看我的!
在《雨王亨德森》中,豐富的象征就像一個猜謎的旅程,貝婁在人物和事物中,都賦予了十分強烈的象征意味。亨德森就如希臘神話中的奧德賽般在冒險旅程中悟出了人生真諦。雖然貝婁在大學讀的是人類學,但小說中的非洲是一個他不曾到過的地方,而現實中這樣的非洲也不存在—它只是貝婁用來象征原始生命力的一個場景。在《雨王亨德森》中的非洲發生的一些故事,有不少可以在《圣經》中找到根源,而從象征死亡和恐懼的獅子,甚至達夫這個名字(“Dahfu”與“Death”幾近同音)中,都可以看出貝婁的苦心經營。
我在那篇書評中,引述貝婁在一篇文章中對亨德森的評論:“韓德信所要找尋的,是對死亡的焦慮的治療法。”我還說:
在經歷了老婦死亡后,韓德信開始重新發掘自己的生存價值,他不但要知道“人是要活下去的”,而且還要知道怎樣活下去。“我要!我要!”這個聲音不斷地敲打著他的心。要什么?很明顯,他是要活下去。怎樣活下去?在去非洲之前,他不知道,經歷了非洲的冒險回到美國后,他知道了—他需要真實的生活,敢于面對死亡,超越死亡,懷著萬古柔腸的愛心,打倒一切虛偽的生活。
重讀這段書評時,我覺得自己當時在年輕的理想主義影響下也許有點說過了頭,然而,當我重看《雨王亨德森》后,書評中這種感覺又強烈地涌現了出來。為什么會那樣呢?寫完那篇書評后,我已又體驗了幾十年的生活歷練,對人生的歡樂憂愁,人世間的愛和恨,應該體會更深刻了吧,應該不會那樣慷慨激昂了吧?但我仍然為小說中那種對生命的關愛、熱切期待新生活和愛情的想法所深深觸動。也許,《雨王亨德森》的感染力就是整部小說所散發出來的對生存價值的熱烈追求。這里面又出現了另一個我十分喜歡的人物—尼采。尼采的超人哲學,不但感染了年輕時的我,即使今天,他仍是我愛讀的一個哲學家。在《雨王亨德森》中,尼采的超人意識可說無處不在。美國當代文學批評家托尼·坦納(Tony Tanner)在討論貝婁這部小說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亨德森,就如貝婁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樣,想找出一個人怎樣可以在屈服于現實的同時……而又能撇開所有的限制而超越(transcend)他自己……有很多尼采的聲音,事實上,里面不斷出現的哲學箴言……可以用查拉圖斯特拉的一句話概括,即人是被超越的動物。”
“雨王”亨德森和尼采的超人,都是要超越當今世界已經頹廢敗壞的人類。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說,“我教你們超人的道理。人是一樣應該超過的東西”,又說“人是一根繩索,系于禽獸與超人之間,凌駕于深淵之上”。亨德森,或尼采的超人,都是比現世人類更高級的物種,在尼采看來,現世的人類可以通過自我超越而創造出超人,而人類實踐的目標就是使這個理想實現—成為真正的人,即超人,這也是全人類的目的。尼采的超人理論是在上帝已死的前提下出現的。超人,源自擺脫長期統治西方社會的基督教倫理,和從頹廢中覺醒的“最后的人”。尼采稱這種“最后的人”是“較高級的人”,但還不是超人。因為在他們的身上,仍然有不少塵世間的回憶,還不能完全擺脫基督教倫理觀和人類的頹廢生活,仍然需要偶像崇拜。這種最后的人,正是亨德森所見到的達夫,而亨德森最后超越了他,成了超人。正如查拉圖斯特拉對這些最后的人說的:“你們只不過是橋梁而已,唯愿更高超的人在你們身上渡過去吧!你們代表接替,然則不應怨怒那超過你們而達到高處的人吧!”貝婁以他的小說回應了尼采:超人要從“最后的人”的后人中產生出來。
在小說的最后部分,亨德森在返回美國的飛機上,哼著亨德爾的《彌賽亞》,這首表示感恩上帝的樂曲,混合著悲哀、快樂、憤怒和激情,同時讓人感受到優美而崇高的寧靜境界。他又叫空中小姐把飛機上一個波斯(Persian)的孤兒的座位換到他旁邊,把小獅子給他抱著玩。他看著孩子那雙散發著好奇光芒的大眼睛,發覺這雙眼睛充滿著新的生命,而這種新的生命,仿佛含著一種古老的力量。貝婁通過亨德森體驗到個人的自救來自對人性的體認和接受—惠特曼的“我”歌唱自我,認為探索自我就能探索到人類的靈魂,而非來自現代社會中那些尋求人類解脫的各種理論。多年前我在前面那篇書評提到的—現代(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美國社會是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當前的美國文化是面臨崩潰的文化,現代人存在于這樣一個社會,應該回歸到原始文化中去學習,從原始和野性中學習一種純樸無私的人間之愛,以融和當前充滿戾氣的社會—在今天竟然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選自《大師們的小說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