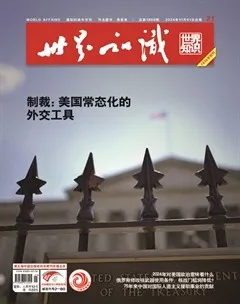歐日試圖聯手搶占全球氫能發展先機
近年來,氫能發展越來越受到各國重視,尤其歐洲和日本,是最看重氫能的兩大行為體。近期,歐盟和日本簽署氫能合作備忘錄,雙方表示將在氫能業務、技術開發和安全規則等方面進行合作,以建立有彈性、可持續的氫能供應鏈。根據國際能源署資料,目前全球尚未確立與氫能合作相關的明確國際標準,歐盟和日本利用技術領先優勢,率先建立氫能規則,試圖搶占市場開發主導權和國際貿易規則話語權。這在促進氫能投資和需求、推動國際氫能合作的同時,也可能引發新一輪能源政治競爭和供應鏈混亂。
歐盟和日本氫能戰略較為完善
一個經濟體的氫能產業發展不僅受市場需求、有效利用等現狀影響,還包括一國政府的氫能戰略、政策規劃以及資金支持力度和規模。當前,歐盟和日本都制定了完善而宏大的氫能戰略,但市場方向較為模糊。日本早在2017年就制定了氫能基本戰略,還提出兩個關鍵的戰略組成部分,一是“氫能產業戰略”,目標是提高日本產業在氫能市場的競爭力;二是“氫能安全戰略”,意在保障氫能的安全應用。日本政府計劃提供20萬億日元的前期投資,以吸引公共和私營部門進行綠色轉型相關投資,并在未來十年內實現150萬億日元或更多投資。日本國內氫、氨供應鏈和基礎設施建設也正在推動氫能從技術開發階段轉向商業化階段,試圖建設一個完善的國內氫氣市場和“氫基”社會。
2020年,歐盟委員會發布了《歐盟氫能戰略》,并于2022年啟動了歐洲氫能銀行作為融資工具,以加速在歐建立完整的氫能價值鏈。歐盟與地中海國家的綠色氫能合作伙伴關系將促進其從非歐盟國家進口可再生氫,目標是到2030年進口1000萬噸低碳氫。歐洲還計劃到2040年修建起約4萬公里的氫氣輸送管道,為歐洲大陸利用氫能解決氣候問題提供基礎設施支持。
在氫能開發和清潔利用新技術領域,歐盟和日本處于領先地位。例如,在甲烷化過程中,二氧化碳通過催化劑與綠色氫氣反應生成合成甲烷,從而被捕獲和回收。這一技術已經被歐盟和日本掌握并應用到氫能生產中,降低了氫能的碳排放量,所生產的氫能基本達到了歐盟低碳氫的標準。日本在2023年更新其氫能源戰略時,概述了氫作為聯合發電燃料、燃料電池、熱電聯產系統熱源以及合成燃料和電子甲烷等回收碳產品原材料的潛在用途。
然而,全球氫能應用仍然主要集中在能源產業和煉化領域,只有不到0.1%的需求量產生于重工業、交通和電力生產領域。此外,氫能是資本高度密集型產業,氫能供應鏈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大規模投資。在歐洲,氫能大規模開發和部署依賴已有天然氣管道的改造和擴建等基礎設施項目,然而,烏克蘭危機后的天然氣供應中斷影響了管道設施建設和氫能項目的實施。同時,液化天然氣基礎設施建成后滿足了歐洲部分天然氣需求,管道氣和管道改造、擴建反而不是那么急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歐洲氫能的開發和部署。在日本,當下的通貨膨脹是氫能投資不足和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用可再生電力生產的氫能。成本上升導致政府承諾的投資項目被擱置或延遲實施,投資風險升高。
氫能國際合作中的地緣政治因素
氫能作為清潔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正在成為實現全球能源轉型和氣候目標的關鍵戰略資源。鑒于各國在氫能生產、貿易、投資和創新等領域的合作需求,制定氫能供應鏈國際標準、構建良性的氫能產業競爭環境尤其重要。歐盟布局氫能國際合作戰略背后有深刻的地緣政治考慮。烏克蘭危機以來,歐盟多個成員國面臨能源供應中斷危機,不得不出臺緊急計劃應對能源短缺和電力價格上漲。能源資源豐富且靠近歐洲大陸的北非國家、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和中亞國家等成為歐洲越來越重要的能源供應方。得益于歐洲能源市場的刺激,這些國家正在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以期成為歐洲主要的清潔電力供應國。
歐盟在亞太地區選擇日本作為氫能合作伙伴也主要出于地緣政治考慮,它把日本視為其在“印太”地區最為重要的戰略盟友。6月3日,歐盟和日本發表聯合聲明稱,將共同制定清潔氫氣供需相關政策,并在推進新燃料開發技術方面開展合作。不過,面對綠色經濟、氣候變化和網絡安全等全球性挑戰,中國是歐盟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尤其在亞太地區,中國在經貿和基礎設施領域的重要地位是該地區其他任何國家都難以比擬的。但是,在與中國接觸與合作的過程中,歐盟希望在該地區有更多平衡中國的力量加入,而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戰略”的亞洲國家,歐盟可以依托與日本的氫能合作將自身影響力延伸到亞太地區的經貿、跨國基礎設施和技術投資領域,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競爭。
烏克蘭危機一方面給歐洲制造了能源危機,另一方面也給其他國家提供了新的能源市場,尤其是天然氣和氫能等較清潔能源。然而,在國際氫能貿易領域尚缺乏清潔氫能的統一標準和證書的相互認可,市場的互聯互通也因此較難實現。當前,歐盟和日本政府部門和私營企業正在制定計劃推動資本流入氫能領域,但由于缺乏統一而清晰的跨國政策、規則和機制,政府對低碳氫能需求側的支持不足。沒有強勁的需求,生產商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來保障大規模投資,氫能的生產和整個產業難以持續。

中歐合作前景廣闊
盡管各國對于可再生能源制氫的稱謂存在差異,如中國稱為“綠氫”,而歐洲稱為“低碳氫”,但可再生能源電力與電解水制氫的耦合是符合全球氣候目標的唯一氫能發展方向。在這一共識基礎上,中歐氫能合作前景廣闊,機遇前所未有。
首先,中歐氫能合作可以為全球能源轉型另辟蹊徑。中國和歐洲目前都面臨化石燃料不足的問題,短期內也不可能實現可再生能源和氫能的大規模替代和轉型。在全球氣候危機下,各國降低碳排放的任務較為迫切,中歐需要另辟蹊徑,尋找一條更具可行性的減排路線。例如,未來在實現凈零排放目標下,煉油、鋼鐵等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減排任務艱巨,如果以氫能取代化石燃料供能,可以幫助這些產業加快實現低碳綠色轉型。去年,鋼鐵制造產生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7%左右,德國鋼鐵產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其全國工業總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可以說,鋼鐵產業是碳排放大戶,而該產業的綠色轉型取決于低碳氫能否足夠低價和規模化生產。低碳氫在煉油廠的擴大應用也可以為燃料替代的能源轉型之路提供方案,即通過低碳氫在提煉環節的燃料“加持”來延長石油這一化石燃料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主導地位。國際能源署預計,到2030年,低碳氫在煉油廠的消費占比將達到15%。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實現,將有助于推動煉油產業的低碳綠色轉型。
其次,中歐氫能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歐洲在氫能開發應用技術領域占據優勢,但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較高。中國氫能產量較高,但綠氫占比較低,在應用場景、液氫儲存和遠距離運輸領域尚存在瓶頸。中歐各自都存在氫能開發應用的短板和長處,但都具有發展氫能的強烈愿望,雙方可以通過合作投資實現優勢互補。例如,中國可以引進更先進的歐盟電解技術擴大綠氫生產規模,以綠氫替代灰氫,為全球溫室氣體減排作出更大貢獻。德國等歐盟國家則可以利用技術、市場和規則較為成熟的優勢,在中國投資綠氫項目,用中國本土生產的低價可再生電力擴大綠氫生產規模。這不僅可以直接降低綠氫成本,生產規模的擴大也可以獲取更高利潤,應用場景擴大帶來的穩定市場規模還有助于更好地規避市場風險。如果中歐聯合進行第三方投資,則可以整合全球氫能資源,幫助“全球南方”國家實現從化石燃料到氫能的跨越式發展,盡早統一國際氫能標準,完善氫能產業鏈和貿易鏈,為實現全球能源轉型提供更大保障。
最后,中歐氫能合作需避免一些可能出現的挑戰。能源作為戰略資源已被過度安全化、政治化,甚至武器化,能源供應安全極易受到外交關系、經濟制裁和沖突戰爭等政治事件影響。隨著氫能消費量和貿易量上升,其戰略地位將很可能超過石油和天然氣,形成“氫能政治”。中歐作為世界重要氫能開發經濟體,如果各自制定的相關法規和證書差異性較大,可能會導致市場割裂和碎片化。各國搶占市場先機和話語權,將造成供應鏈風險上升。為了避免更大的無序和混亂,歐洲方面需強化氫能的環境氣候和經濟屬性,淡化其政治屬性,盡快構建可以與中國溝通的氫能合作平臺、融資機構和金融支持。中國則需要提早規劃氫能國際合作戰略,以市場推動氫能發展,防止氫能過度政治化。中歐在氫能國際合作中可以采取更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來加強協調談判,在制造技術、需求創造和供應鏈建設等方面統一認識,合作制定新的氫能法規,共同促進低碳綠色氫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