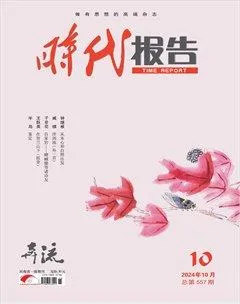從本心和自然出發

王冉的詩,總是注入美學的力量、生命的氣息,以略帶傷感又看見光亮的心,去深入觀察事物,在低聲輕吟中寫出細微中的遼遠,生存中的哲思,很好地將“及物”與“及心”融合在一起。《秋日隨想(組詩)》傳達出了主體的生命體驗,把心投放到客體,絲毫不懼將最真實的內心世界展現出來,既有“來不可遏,去不可止”的酣暢,又在舉重若輕的飄逸和深邃中隱藏,同時她拋去了哲學思考的沉重肉身,唯有身心體悟,不露聲色地與自然同呼吸。
一、找到自我即找到世界
秋天,總能讓人產生精微觸感。詩人善于抓住秋的微涼,秋的雨聲,秋的多彩,秋的荒涼,從實到虛,從物象到表象,并一一指認,啟迪人去找到自我、找到世界。比如《私語》中“蔥蘢,枯萎/只消一夜無聲的雨”,這里的“雨”,是實在的雨,也是虛無的生活。事物、自我和群體變為了同一性,引發人代入其中看清現實,掂量人生的背后,終究是“一場雪后/悄然白了頭”。但就算看透了一切,詩人在《八月焰火》里,依然有勇氣面對,她從“有近乎荒蕪的美”看到了“天空清澈”,充滿矛盾的句子卻寫出了或從容或優雅的自我。也許歷經的風雨只是磨礪,盡管“月光還在來的路上”,也能讓靈魂抵近安寧。因為她如《九月的黃昏》一樣堅信著“秋天的饋贈就在眼前”。是的,每一個人提到秋季,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收獲,也許“我的眼淚先于葉子落下”,但在《秋日午后》“那一架的薔薇又開了”,只要去努力,去發現,去偽存真,總有美好的事物呈現在面前。
湯顯祖在《玉茗堂文之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提到:“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饑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臥可以興。鄙者欲艷,頑者欲靈。”無論秋天多么蕭瑟,無論生活給了多少磨難,通過認識論中有限的感官經驗去把握對象,將不可能變為可能,當在煙火人間找到了自我,“可以翱而以翔”,世界也就廣闊、敞亮了。
二、漫步方式去撿拾詩意
無論是《私語》《九月的黃昏》,還是《秋日午后》《秋思》,所有靈感,都來源于真實生活的軌跡,以漫步方式,在不經意間不斷撿拾正能量的詩意,透露出輕微反思的自覺,并且不被直接的感覺形式所迷惑,而是跳出來,接受智慧的光芒。好像每個地方她都在場,又好像都不在場,天地間只剩自然本身,只剩一片純粹。
《私語》一句“我們看花時/沉醉于春光浩蕩,以回憶的方式進入秋天的現場,卻“不知秋天已經啟程”,身在此山中時,一動不動,怕一動,就會一劍封喉,瞬間白頭,及此,詩意已盡出。其實春天已是昨天,不必過多眷戀,就讓傷感悄然消失,靜靜地“走遍曠野”,讓“萬物內部開始瓦解”,或許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但糾結過去是沒有意義的,放下一些,遺忘一些,既是救贖,也是治愈。正如《八月焰火》:“我推開窗/剛好看到你/笑得那么明朗”,盡管曇花總是一現、盡管眼中總是荒蕪,盡管是平平淡淡的夜晚我推開窗,但看到的卻是曇花從不傷感,永遠是明朗的笑。曇花也只是靈魂的客觀對應物,剔除了現代性的斷裂、頹廢,以積極心態去擁抱生活,擁抱一種自然、舒適的狀態。《九月的黃昏》大致基于下班路上,看到“每一粒葡萄都很飽滿”,也看到“葉子落下”,這就是秋天的特色,有收獲也有失去,但“我相信回頭就能相遇”,詩人以敏銳的視覺,精準抓住意象,表達出自己的情感,正應了那句“情至不能已,氤氳化作詩”,很重的眼淚,很輕的筆觸,讓時間從心頭穿行而過。《秋思》也許是在窗前沉思,也許是在門口倚門而望,在雨后,在月亮升起,在山楂樹捧出燦爛果實的時候,想過往,想毫不相干又休戚相關的事。《秋日午后》的題目就更像是在漫步,用及物的手法寫出“最后一顆絲瓜蕩在藤蔓上”極具畫面感,“那棵大樹失去了鳥鳴/開始慢慢交出體內的色彩”,一個“交出”之詞作陌生化處理,想象無限,詩意縱橫,張力盡顯。
三、瑣碎時間中無聲靜聆
人生匆匆,現代人的腳步更是沒有片刻停留,錯過了許多風景。詩人王冉卻反其道而行之,她在平常生活的瑣碎時間如“在這荒涼的午后”“在路燈下轉身”等,慢慢地走,去傾聽自然的私語,去靜聆一場無聲的雨,去觀察一根絲瓜蕩在藤蔓上,去凝視“門口那棵山楂樹”,甚至在深夜去看一次曇花盛開,從某種角度來看,詩人都是用一些樸素的意象作為掩體,并點到為止。詩人是敏感的,也許眼中有淚;又是內斂的,有淚也只是無聲滑落,就像天邊一股狂風,看得見正吹過來,卻始終沒有到達。生活中總會遇到這樣的場景,淚流滿面卻無抽泣之聲,有些是毫無端由,有些是痛到極致,但與命運抗爭過程中,我們從來不說一句話,因為生活就是生活,必須在視線模糊中,自己默默站起來,清醒地去尋找解鎖的鑰匙,否則將被禁錮其中不得動彈。整組詩里詩人閉口不言,只是靜靜地、默默地看著一切,身在其中卻置身事外,朦朧得像霧像雨又像風,又清晰得完全可以辨別,保留了獨立的個體生命意識,又與自然融為無形,達成和解后直通神性。
四、矛盾交織又符合邏輯
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奎因在《真之追求》中斷言:“誰都知道‘真’陷于悖論,達到十足的自相矛盾的程度”,《私語》里春光與秋天,蔥蘢與枯萎;《八月焰火》里曇花與勇氣,繁茂與荒蕪;《九月的黃昏》里喧囂與黃昏,凋零與擦亮;《秋日午后》里荒涼與溫暖,熱烈與清冷;《秋思》里黑夜與月色,嫩芽與老了,無不是矛盾的詞語,場景剎那轉換,在強烈的對比下,給人造成肆無忌憚的沖擊波。仿佛格格不入,又仿佛先天一體,很多事,放在兩者之間或小范圍內,是不可調和的,是必須承受的,但從更多維度、更遠視角看,又是正常的、可放下的,這也正是生活混沌之所在,也是精神的出口。
如何去解構生活,去建構人生,抵御看不見的傷口和疼痛,正是讓人思考的問題,要從中挖掘出自我的身份和存在的意義,需要去探索去追尋,然而,詩人用“思無邪”式的輕柔,細膩記錄了生活,以及情感波動,在空間和時間拼成的圖景里,顯得真誠坦率,又不斷走向縱深,做了徹底分解后,告訴讀者一切都符合邏輯,并給了一束光之后悄然退場,讓讀者去思考,去反思,如何重塑內心世界,如何建構生活,這正是這組詩的意義所在。
鐘嶸提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認為抒情是詩歌的本質,詩是情感激蕩的產物,而寓情于景是經典手法。狄德羅在《文藝理論譯叢》中指出只有情感才能打動人心:“沒有情感這個品質,任何筆調都不能打動人心。”王冉的詩從本心和自然出發,用及物的具象和及心的意象,將一切情感悄然融入其中。盡管詩人對日常事物是感性的,但又超越了日常,讓鳥鳴、星光、果實的氣息吹進心靈深處,不斷糾偏、扶正,摒去雜念,從而在內斂的感性中去對理性把脈,見自己,更見眾生。
作者簡介:
鐘繼根,70后,內江資中人,現居綿陽。綿陽市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作品發表于《星星》《奔流》《散文詩》《劍南文學》《三角洲》等刊物,出版詩集《來自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