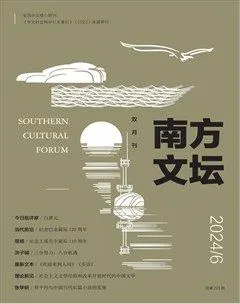經與權:“人民文藝”的曲折與轉進
一、“人民文藝”的經與權
“人民文藝”是個歷史性的概念,它自身包含著根本目標與現實策略之間的張力,即經與權的矛盾與統(tǒng)一。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文稱《講話》)等經典文獻中,毛澤東深刻把握了這種哲學關系。
據胡喬木回憶,關于《講話》,毛澤東最認可郭沫若的評價,并引為知音之論。按郭沫若的說法,《講話》的要害在于“有經有權”,既有“經常的道理”,又有“權宜之計”①。對此,陳晉做了更具體的解釋:“一個是當時揚‘普及’而抑‘提高’,這里‘權’的成分是很顯的;一個是文藝從屬于政治并為政治服務,也是‘權’的成分多一些。”②
但是,這個問題,遠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簡單。在我看來,《講話》所表達的“人民文藝”的經與權,并不僅表現在內容的層面,還表現在形式的層面,即《講話》本身的修辭方式。毛澤東發(fā)表《講話》時,深刻地意識到了經與權、原則與策略、根本目標與現實任務之間的緊張,因而不得不采取隱微的講法。真正的“人民文藝”或它的理想狀態(tài),遠景與目標,并不適合講,講多了反倒有礙于它的達成,只能把現實任務當成目標來講,把最終目標的當前環(huán)節(jié)當成目標本身來把握,才能打通走向最終目標的道路。因而,作為歷史展開的內在環(huán)節(jié),《講話》對“人民文藝”現實任務的表達,既有強烈的自我肯定,又充滿了自我否定。在這個意義上,《講話》是真正的哲學表達,是毛澤東式歷史辯證法和矛盾論的出色運用。《講話》的修辭本身就體現著“權”,有些話,從根本目標上來看是錯的,但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講就是對的,可以促使目標的達成。反之亦然,從根本原則上講,有些話毫無疑問是對的,但放在特定語境中卻是錯的,恰恰違反了“經”的本義。只有權,才合乎經,這大概正是《講話》一再強調的所謂“革命的功利主義”的真義吧。
對于《講話》,僅從字面上去理解,是膠柱鼓瑟,緣木求魚,是教條主義或“形而上學”。很多人看似表面上對《講話》或“人民文藝”尊崇備至,無比擁護,其實卻違背了真“經”,這大概讓毛澤東備感孤獨和寂寞吧。只有郭沫若初步摸到了正確的門徑,大體符合“辯證法”,雖說也未盡其義,畢竟已是難能可貴,所以受到毛澤東贊賞。但也僅止于私下的贊賞罷了。因為,經與權的張力與矛盾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說到底,并不存在某種固定的可被清晰表述的實質性的原則,原則性本身也要在動態(tài)變化的時勢中加以把握,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并具有新的內容。不過,它的總體精神和方向是穩(wěn)定的。
什么是“人民文藝”的經與權?“經”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方向,權是特定時期的具體的歷史任務,一個個有待不斷克服的具體環(huán)節(jié)。從深層的辯證法來看,“權”是在歷史約束中的具體策略,它并不必然表現為對終極目標的持續(xù)而無間斷地逼近,有時,它甚至可能表現為后撤和迂回。革命黨的政策,是內在于這個歷史展開的邏輯的,當然,它同時也是作用于這一過程的能動性力量。因而,領袖代表政黨所做的《講話》只能表達有限的真理,這就是“權”。《講話》本身是政治性的修辭,不是學術性的真理陳述。
遺憾的是,這種未被清晰表達,也不宜被清晰表達的“經”的內容,越來越被忽略了。隨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權”的內容被固化了,逐漸轉化為至高無上的“經”。此后的建設時期,并沒有像革命者樂觀估計的那樣快速切入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緊迫的任務一直壓迫著革命黨進行現實的選擇,這種持續(xù)的張力使新中國仍保留了延安時期的“經與權”的緊張感。現實并沒有為邁向社會主義的新文化準備好充足條件,相反,政治和經濟建設,或者說社會主義的物質建設,反倒要求著文化繼續(xù)扮演它催生物質性條件的先鋒角色。這種狀況也使毛澤東本人非常無奈,他經常表達對文化建設的批評(批評的指向是雙重的,一是文化所發(fā)揮的效用不如人意,二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本身遲緩,尤其在“人民性”上存在欠缺)。據陳晉的說法,在1960年代,毛澤東曾表達過對《講話》的不滿,并說過“對這篇東西很不滿意,自己沒有興趣看它”③。這或許顯示了他對始終無法擺脫“權”的糾纏的焦躁情緒。
李潔非、楊劼的解讀是符合實際的:“依《講話》自身來看,‘面向工農兵’系40年代黨就其對于文藝之所需,而提出來的權略。這要求及其附加的一些提法,本來都是以‘用’為務,順應著當時革命的實際,適合著根據地的文化面貌,甚至跟延安的物質水平、經濟條件亦不無關系,皆非永久之策。它們第一并不體現毛澤東內心真實的文化取向和尺度,第二也不代表毛澤東對將來整個國家文化發(fā)展的構想,主要是‘從實際出發(fā)’的產物,這一點,應該說是確定無疑的。”④
當然,經與權的內容要更為豐富,其核心議題包括:如何把握文藝的人民性?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角色?它們歸結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如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文藝?對于這些問題,即使毛澤東本人也未必完全自覺和思考成熟,一是囿于時代條件,二是缺乏理論參照。畢竟,社會主義文化應該什么樣,即使馬克思、恩格斯也未必清楚,因而沒有留下具體清晰的理論描述。但是,經歷80年歷史風雨,擁有前人不曾擁有的后見之明,我們至少應當明白,真正的社會主義文藝不應該是什么樣。這引導我們重新總結社會主義文藝建設的成就與經驗,也要求我們認真反省“人民文藝”發(fā)展的曲折與頓挫。
二、“人民性”的歷史展開
《講話》發(fā)表于1942年,隨著民族戰(zhàn)爭進入轉折時期,“階級矛盾”開始躍居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它指向的是建設一個什么性質的新的國家的問題。此一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因應這種歷史形勢而創(chuàng)作的。同一時期,延安還組織了對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批判。又破又立,勾畫了新中國的未來形象。服務于這樣的戰(zhàn)略需要,毛澤東將文化提升到“文化戰(zhàn)線”的高度來認識。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主主義論》原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將文化提升到和政治并列的高度,即:文化不僅是新民主主義政治能否成功的保障,它本身還是新民主主義的重要內容。至于新民主主義文化之后的社會主義文化,或“人民文藝”的“經”的內容,在當時的情勢下,是不太適宜突出的。因此,這些文章只是著重強調了文化作為政治側翼的功能性的一面。不過,毛澤東還是挑明了二者之間的歷史的也是邏輯的關系。“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yōu)橐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tǒng)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yōu)橐粋€被新文化統(tǒng)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⑤
新民主主義階段只是“經”的歷史展開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或序幕。此后進行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與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的物質實踐同步進行的,也是互為因果的。它們的最后成果,表現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以及最終的人類解放,人民獲得全面的主體性,既包括物質生產和分配的主體性,也包括文化創(chuàng)造的主體性。這才算實現了真正的“人民文藝”的目標。
在黨和文藝的關系、組織和知識分子的關系等問題上,表面上看,《講話》的確表現出某種列寧主義的特征,這也是被后世視為“經”的重要方面。其實,這不過是“權”的內容。正如莫里斯·邁斯納所指出的,在毛澤東思想中,一直存在著和列寧主義的重要差異,更強調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的“自我能動性”或“自發(fā)性”⑥。事實上,這才是“人民文藝”更為根本的方面。關于“組織”與工農兵甚至無產階級的一致性或代表性,如從“經”的角度看,后世的固化理解是成問題的。這是個經常性的誤解,即使在李楊反思《講話》經與權的富于洞見的文章中,仍然認為二者是同一的,恐怕就值得商榷⑦。真正的“人民文藝”,絕不可能由精英群體代勞,不管是知識分子還是政治精英,指導和幫助都只能是暫時的,權宜性的,更不能固化為一種體制性安排。在毛澤東思想中,一直存在著對人民自發(fā)性的肯定和對精英主義的排斥以及對科層管理體制的反感。如果說,在抗戰(zhàn)接近尾聲,走向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關頭,不得不刻意突顯列寧主義的一面,那只是為了應對緊急狀態(tài),帶有強烈的策略性考量,是“權”的表現。從“經”的意義上說,毛澤東對人民的理解,始終是“自己解放自己”。
當然,在初始階段,人民還不能創(chuàng)造自己的文化,因為人民本身還有待養(yǎng)成,由歷史實踐鍛造,也要由過渡時期的新文化培育。因而,無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至關重要。更準確的說,人民(作為政治概念的無產階級)正是和“新文化”同時成長的,而這個新主體的成熟過程也是社會主義趨于成熟的過程,普遍的自由解放不斷實現的過程。
人民概念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無產階級,也不能等同于特定時代條件下的工農兵,作為歷史的概念,被具體表述的人民(群眾)是混雜的,它對應于《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政體”和“聯合專政”理論,正如施拉姆所說:“1949年建立的國家之所以被稱作人民的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它被視作一種混合形式,以適應于從戰(zhàn)后恢復到社會主義建設這一‘轉折時期’。”⑧相對而言,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似乎更具有“經”的意味。所以,在新民主主義階段談政權形式,“人民”一般會和“民主”“聯合”合用,而1956年后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則往往帶有對巴黎公社式的革命自發(fā)性和自治的想象⑨。
《講話》似乎強調文藝作為手段的意義,主要內容仍然圍繞著文藝“為何要服務于現實政治”和“應如何服務于政治”而展開。它更強調文藝作為黨的組織的出版物的性質,在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中也更注重普及和大眾化。但其實,這些“權”的論述指向的真正目標是文藝的人民性,人民應當成為文化創(chuàng)造的主體。
文藝為人民服務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它不但是“經”的目標,也是“權”的手段,即為實現人民性的根本目標不斷創(chuàng)造政治的條件。在這一視野中,《講話》中文藝所要服務的具體政治,所要服務的“人民”,都是隨著無產階級的革命歷史的展開而要被克服和揚棄的對象。《講話》富于張力的表述暗示,文藝的人民性的長遠目標將是人民不再借助任何的中介,直接掌握文化,創(chuàng)造出高級的文化。大眾化或普及化,其實只是受制于現實條件而提出的階段性任務。按毛澤東的說法,159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qū),還有100萬多文盲,“現在老百姓連好的春聯都沒有,我們還只是談提高,這只能是空談”⑩。“普及”只是手段,根本目的還在于為“提高”創(chuàng)造條件。人民的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必須是高級的文化,不過,它不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意義上的高級,而是真正體現了人民性的全新的“高級”,也將是達到絕對歷史高度的“高級”,它將以其深刻的內容與新穎的形式而真正超克曾經輝煌的舊文化。從毛澤東本人的閱讀和寫作所顯現的高水平來說,他也不可能僅肯定“普及”的階段性目標11。
《講話》在談到普及與提高時說:“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yōu)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著。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什么意義呢?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12所謂“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突出的正是人民在文藝上的主體性地位和自發(fā)性。在這場“漫長的革命”中,人民知識分子化了,作為歷史現象的知識分子也人民化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歷史存在,表明著知識與人民的分離。在革命者的想象中,隨著社會主義的來臨,由社會異化導致的分離,也終將消失,知識分子概念,也將消融在人民的概念中。
不過,這種理想狀態(tài)的“人民文藝”畢竟是一個過于遙遠的目標。首先解決的還是底層民眾的主體性,所以不能求全責備。對于初始階段的“人民文藝”的粗糙簡陋,不能做過高要求,敢于發(fā)聲和表達就是勝利。在某種歷史目的論的視野中,尚不高級的群眾創(chuàng)作是代表未來的。延安時期對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的發(fā)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對高玉寶和浩然等作家的培養(yǎng),體現了對人民自發(fā)性或主體性的重視。這種狀況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漸被重新逆轉。
在社會主義文化的構想中,人民性是個外延不斷擴大的概念,是個聯合專政和人民民主的概念。左聯時期的大眾化,代表著文化生產的人民性的一次擴大,是對五四啟蒙主義的初步克服。而到了延安時期,則是對1930年代局限在城市的左翼文藝的進一步拓展。文學的主體,擴展到更為底層和邊緣的中西部內陸農民。這一過程體現了更為廣泛的人民性。
三、社會主義文藝的調整與重建
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開始之后的文藝,決不是延安文藝的擴大版,或簡單的在地域上的展開。它還意味著性質的不同,“人民文藝”已處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即邁向更高“人民性”的過渡階段。但是,受制于薄弱的物質基礎和嚴峻的政治環(huán)境,它仍陷于某種戰(zhàn)時狀態(tài)不能自拔,不得不依賴甚至還強化了列寧主義的特征。科層體制的管理方式依循強大慣性將《講話》的“權”固化為“經”。而置身于無法擺脫的歷史矛盾漩渦,即使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明確重申社會主義文藝“經”的方面。
無產階級文化,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期,將依靠自身的先進性贏得“共同文化”的領導權。不過,這種共識或霸權的獲得,必須經過市民社會領域的漫長的革命才能成功。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展開的文化斗爭,必須以民主的方式進行,以文化的成就“說服”競爭者。“文化統(tǒng)識”必須在陣地戰(zhàn)中扎扎實實一寸寸贏得,依靠體制性資源的壟斷進行暴力壓制無濟于事,甚至適得其反。但是,對于“人民文藝”的建設者來說,似乎缺乏寬松從容的環(huán)境。葛蘭西所設想的,從市民社會所發(fā)育出來的無產階級國家,對于中國革命者來說并不存在,這是中國現實和革命的特殊路徑所決定的。相反,這樣的市民社會正需要“人民文藝”去創(chuàng)造。重新檢討1950—1970年代的文藝經驗,我們應該承認,盡管成就巨大,但在創(chuàng)造黑格爾、馬克思意義上的現代市民文化上面,仍存在巨大的欠缺和偏頗。
將1940年代的“權”固化為“經”,并以官僚科層體制加以缺乏彈性的管理,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歷史基礎的薄弱和急切的躍進心態(tài),為“人民文藝”的長遠發(fā)展?jié)摬亓宋C,也為1970年代以后社會主義文藝的自我修正埋下了伏筆。
眾所周知,十七年文學的主要成就,表現在兩大題材,即革命歷史小說和農村題材小說,它們達到的歷史高度毋庸置疑,但也存在重要缺陷:很快模式化,而且具有題材本身的局限性,遠離更為開闊復雜的現代生活場景。總體來看,當代文學鎖定在中等發(fā)展水平陷阱,無法再向社會主義文藝的更高水平邁進。究其根源,除歷史條件和社會物質基礎欠缺之外,缺乏對傳統(tǒng)和外來文化資源的開放吸納能力,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限制了當代文藝在資產階級現代文藝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更豐富新穎的社會主義市民文藝,從而將“人民文藝”提升到更高水平。必須說明的是,這里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并非特指狹隘的資產階級市民社會,它有著古典城邦社會共和傳統(tǒng)的淵源,在現代意義上,它指向以現代生產和消費為基礎的公共性,代表了相對于國家的“自由聯合”的自治空間。即使資產階級市民文化,也是各階級創(chuàng)造的“共同文化”,是“進步的”公共生活的一個發(fā)展階段,因而,這種意義上的市民文化不必然局限在城市空間。
將“人民文藝”的“權”固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延續(xù)了1940年代對農民文化的政治評價和道德評價,這與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并不協(xié)調。眾所周知,為了快速工業(yè)化對農村的犧牲,使得農業(yè)集體化在推進鄉(xiāng)村生活的社會主義化方面,進展緩慢,1950年代中期以后實際上逐漸陷入停滯。它所達到的自由聯合的公共性和普遍富裕程度,遠沒有達到一般的現代水平。
這造成了一個重要的文學方面的后果,“人民文藝”無法消化過渡階段的復雜的社會經驗,將當代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充分發(fā)掘出來,并把握社會歷史自身的結構性矛盾從而將其轉化為總體化的美學敘述。當代文學未能將“人民性”推向新的廣度和深度——相反,“文革”反倒是以激進革命之名將“人”的豐富性極大地狹隘化了。
由于看待生活的視野局促,精神緊張,無法有效吸納和轉化現代傳統(tǒng)(本土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tǒng)和同時代的西方文化資源),“人民文學”難以兼容市民文學的現代源流,在如何處理日常生活和個人欲望方面越來越缺乏能力。面對社會主義過渡期的生活世界涌現出的矛盾,只能刻意回避或用教條化的“政治正確”強力取消。對《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顯示了當代文藝體制對城市生活經驗的政治性的本能恐懼。而到了1960年代,伴隨著從積累到消費的社會轉移在生活領域造成的沖突,《千萬不要忘記》則試圖訴諸舊有階級倫理加以克服13。
當代文學難以完成“總體化”的敘述。對于結構性的城鄉(xiāng)矛盾以及它造成的情感糾葛,尤其是那些鄉(xiāng)村青年們心中合理的抱負,胸中難以平復的委屈,以及集體召喚與個人欲望之間的撕扯,當代文藝無法有效應對和處理。它再也不能像《小二黑結婚》和《白毛女》那樣,以生動的形象和戲劇性的故事,激發(fā)起本能深處的情感激蕩。如果說,對于徐改霞舍棄鄉(xiāng)土,投奔更具社會主義氣息的城市,《創(chuàng)業(yè)史》還能表達態(tài)度矛盾的體諒,仍延續(xù)了“人民文藝”舊日的流風余韻。那么,到了《朝陽溝》,城鄉(xiāng)差別完全被合理化,“回鄉(xiāng)”問題被轉化為道德問題,內心沖突通過意識形態(tài)裁決獲得了勉強化解。這顯示出鄉(xiāng)村敘述已遭遇到危機。發(fā)展到《艷陽天》,只能強硬地上升到路線斗爭和階級沖突14。
新時期以后,社會主義文藝進行了自我修正,一方面,對被壓抑的合理欲望予以美學平反,努力協(xié)調社群價值與個體訴求之間的沖突,重新接通了人民文藝的源泉,從而迸發(fā)出積蓄已久的直擊人心的力量。在路遙(自認為柳青的私淑弟子)那里,暗中的精神繼承與表面上的社會批判并行,對集體主義時代,他給予了批判性致敬。這體現為《人生》式的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也體現為《平凡的世界》中的道德激情:孫少安繼承了梁生寶的賢良,孫少平的啟蒙主義自我理解中,潛伏著以個體苦行穿越異化勞動追求自由解放的社會主義原始沖動。盡管“傷痕”至“改革”文學的主流敘述對鄉(xiāng)村進行了貶低,在啟蒙主義視野中,城鄉(xiāng)關系被理解為文明與野蠻的沖突,但這也是一種偏激的報復性敘述。
事實上,社會主義文學的建設始終伴隨著對歷史實踐的自我批判,哪怕矯枉過正,它也是社會主義實踐本身的文化自反性的表現。1980年代的確表現出了某種社會主義文藝的應有品格,即阿多諾所謂否定性美學的氣質。
新時期或改革開放時代是社會主義文藝的第二個重要階段。以第四次文代會為標志,“人民文藝”進行了戰(zhàn)略性調整,試圖對1970年代文藝體制的缺陷進行彌補,從過于理念化的美學觀念適度后撤,為“人”的主體性注入更豐富的感性內容,從而為“人民文藝”重新奠基。1979年,鄧小平提出“小康之家”的概念,并把它作為四個現代化的標志。1984年,他再次重申“小康社會”理想,將它與“中國式的現代化”并稱。1992年中國改革開放正式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轉型。小康社會對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小康之后是大同,這是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另一種修辭,但卻強調了“過小日子”的政治價值——它既是人民的現代權利,也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從而成為“人民性”的貼切的時代表述。
隨著經濟發(fā)展,“人民文藝”獲得了社會物質基礎的強有力支撐。
“人民文藝”開始了第二次的“向下超越”,如果說第一次向下超越是將底層民眾本能領域中的生命潛能開發(fā)出來,并引領著向社會主義理想上升,那么,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第二次向下超越,則是從理念化的政治理想再次下沉到活潑的情感和本能空間。從這個意義上,文化啟蒙主義有著完全不同于五四的歷史內容,它在最初的意義上帶有社會主義的解放性,仍然是對社會主義理想的重申。不過,隨著啟蒙的現代邏輯逐步展開,與市場社會的充分發(fā)育,1990年代以后也逐漸導致了對消費欲望式個人主義的過度強調,從而慢慢偏離“人民文藝”的原初理想,這需要新世紀文學再度糾正與回歸。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人民性”具有了更為豐富和開闊的內涵。新時期伊始,傷痕文藝對十七年模式進行變革。一個重要的變化是,試圖超越階級斗爭敘事,從政治斗爭的社會場景退回家庭空間,重新強調被激進革命敘事所貶低的血緣、親情(盧新華《傷痕》),格外看重相濡以沫的婚姻愛情——這種轉向在謝晉電影中得到感人至深的體現。與此同時,“純潔”的愛情,迅速獲得了對抗宏大政治的象征意義,成為超越社會阻隔(階級)的“普遍而自然”的人性的隱喻(劉心武《如意》),并時時被拔高到神圣的精神高度(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愛,攜帶著被集體傷害的隱痛,那些不再信任社會的個人,試探著只與“另一半”建立社會性關系,既想保留最本己而私密的情感,又不愿成為孤獨的現代個人,于是,只好緊緊抓住“最小劑量的共產主義”以維系“自由聯合”的微縮夢想。
愛情在1980年代中期,逐漸過渡到肉身的欲望和本能驅力。但在高峰的啟蒙體驗中,性,仍然閃耀著馬爾庫塞式的理想性光芒(王安憶“三戀”),直到“新寫實小說”時期才耗盡解放性能量(池莉《不談愛情》),它要么被刻板的現代科層制壓抑掉原初的激情(劉震云《一地雞毛》),要么被循規(guī)蹈矩的大廠生活消磨掉生命的熱情(池莉《煩惱人生》)。“向下超越”之路開始出現堵塞。及至“新狀態(tài)”“新市民小說”(朱文《我愛美元》、何頓《生活無罪》、張欣《愛又如何》),這條解放之路終于難以為繼。
1990年代初興起的“新狀態(tài)”,其實最早的源頭來自1980年代“市井風俗”小說。社會主義文學在改革開放時代的轉折,最重要的變化表現在向城市的轉移。它和經濟重心的結構性輪轉緊密相關,也是“社會主義文藝”自我提升的關鍵,即:在葛蘭西市民社會的意義上邁向更高的美學現代性。盡管它并不意味著必須是城市生活場景,但是,不可否認,往往是以城市生活為先導和典型特征。1980年代初興起的市井風俗小說熱潮(鄧友梅、陸文夫、馮驥才),靜悄悄地開啟了補足“人民文藝”市民社會缺環(huán)的歷史任務。與此同時,鄉(xiāng)土也往往轉化為新的市民社會的領域,從汪曾祺的《受戒》到神神秘秘的“尋根”,它們的文化理想已不再是鄉(xiāng)土價值或“民粹式”的革命美德,而是市民社會的生活理想。盡管,尋根文學將自己現代主義先鋒氣質深埋在質樸民風之下。當然,它對現代生活的曖昧抵抗和意味復雜的文化鄉(xiāng)愁,還隱含著知青的青春記憶,以及對集體時代共同體和倫理生活不免解體的傷感。這是潛藏在市民生活敘事背后的政治潛意識。
二者之間的矛盾在1990年代初已無法調和,它最初表現為王朔故作灑脫卻內心痛楚的頹廢,繼而表現為邱華棟式的隨波逐流。最后,王安憶在1990年代中期以《長恨歌》對市民社會的矛盾進行了美學的審判,也宣告了向下超越的市民社會理想遭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15。
“人民文藝”又將迎來又一次的轉折。這是留給新世紀文學的任務。
【注釋】
①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60頁。
②③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42、243頁。
④李潔非、楊劼:《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第162頁。
⑤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63頁。
⑥參見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三章“列寧主義和毛澤東主義: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若干民粹主義觀點”。
⑦參見李楊:《“經”與“權”:〈講話〉的辯證法與“幽靈政治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期。
⑧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田松年、楊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105頁。
⑨參見莫里斯·邁斯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五章“巴黎公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中的反映”。
⑩毛澤東:《關于陜甘寧邊區(qū)的文化教育問題(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載《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18-119頁。
11丁玲1982年撰文回憶延安時代,談到毛澤東對文藝的個人趣味:“他自然會比較欣賞那些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會欣賞一些藝術性高而沒有什么政治性的東西。”她又說:“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時也不一定就是他個人最喜歡的。但他必須提倡它。”這里面顯示出經與權的辯證法與修辭術。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文學報》1982年4月29日。
12毛澤東:《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第65頁。
13參見唐小兵:《〈千萬不要忘記〉的歷史意義——關于日常生活的焦慮及其現代性》,載《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tài)》(增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或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第七章的討論。
14關于“改霞問題”及其連帶的鄉(xiāng)村敘事危機,參見劉復生:《此情可待成追憶——〈創(chuàng)業(yè)史〉與自由人的聯合體》,《小說評論》2018年第4期。
15參見劉復生:《一曲長恨,繁花落盡——“上海故事”的前世今生》,《小說評論》2018年第5期。
(劉復生,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9ZDA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