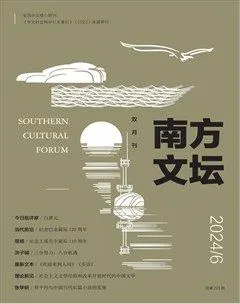左翼思想資源與《講話》的社會主義人民性生成
左翼文學是1930年代文藝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左翼文藝運動從理論到實踐推動著中國無產階級文化的發展。同時,中國左翼運動參與了“紅色30年代”的世界性革命浪潮,深刻嵌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中。國內政治與世界戰爭語境,使得夾縫之中的左翼加快了普羅列塔利亞階級觀念與民族革命話語的結合,在文藝大眾化的吁求與主體下沉中,關聯著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從“革命文學”論爭到1930年代左翼運動的發展,從文藝大眾化倡導到“民族形式”討論,從“大眾”到《講話》的“人民性”,作為民族國家構型的中國性不斷凸顯。
一、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與
大眾化的階級話語
1928年前后,蘇聯“拉普”、日本“納普”的無產階級思想及其組織方式的中國傳播為普羅列塔利亞階級意識的強調和論爭打開了路徑。這一時期關于革命與文藝關系的闡述逐漸成為重要的社會思潮,影響著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思想轉換。在此期間,受到俄蘇文藝理論家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波格丹諾夫以及日本、美國左翼知識分子藏原惟人、辛克萊等的文藝思想的影響,“革命文學”論爭以強調普羅列塔利亞階級意識的獲取,試圖形塑文藝作為政治留聲機的工具理性。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到與后期創造社、太陽社的論戰中來,這場論戰為左翼文藝思想在中國的移植和傳播創造了條件,正如魯迅所言:“我有一件事是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①1929年,魯迅在上海與馮雪峰、施蟄存、戴望舒等合作,致力于譯介蘇聯的文藝理論,并主持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現代文藝叢書”“文藝連叢”等三套翻譯叢書的工作,雖未能出齊全,但是由魯迅倡導的文藝思潮擴大了左翼文藝的影響,魯迅也逐漸成為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旗幟。
1930年,魯迅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中指出:“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是唯一的文藝運動。……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②同年3月,在中共“文委”的領導下,左聯成立大會召開,左聯的成立標志著左翼文化運動戰線的形成。縱觀左聯的發展歷程,體現了共產國際的無產階級文藝領導權思想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實踐,既有生硬挪用的“幼稚”,關門主義的教訓,也不乏革命知識人對普羅理念操演、走向民眾的自我批判經驗。以左聯官方名義發布的帶有鮮明階級革命立場的重要決議有《左聯理論綱領》(1930年3月)、《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1930年8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1931年11月)等。同時,左聯積極推動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和工農通信員運動;在富有實績的左翼文學中,更是豐富和發展了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敘事模式,形成了關切時代脈搏的左翼文學精神和敘事傳統,深刻影響著延安文藝乃至“十七年文學”的發展。左聯及其發動的文藝思潮逐漸成為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中心,“社聯”“劇聯”“美聯”“電影小組”“音樂小組”“文總”的成立也極大地拓展和豐富了左翼文藝運動。1930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為中國左翼文化的獨立性探索奠定了基礎,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左翼文藝運動對普羅階級理論的強調在1930年代深入到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中,成為《講話》“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先聲。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知識分子的階級主體觀在1920年代發生了新變,不僅知識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要被“奧伏赫變”,而且要到無產階級陣營之中去,獲得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意識。階級革命思想隨著國民大革命散播開,與之同時,中共在組織與宣傳陣線上始終將階級動員放在突出位置。1926年,郭沫若在《文藝家的覺悟》中指出傾向革命的作家“要把自己的生活堅實起來”“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③。這是在階級革命話語的發生階段就提出了革命作家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問題。1931年左聯執委會通過的決議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明確提出“只有通過大眾化的路線”“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現實命題④,從而確立起大眾化問題在左翼中的主導地位。
文藝大眾化討論時期,瞿秋白的《“我們”是誰》一文中認為:“我們發見‘大眾化’的更深刻的障礙。——這就是革命的文學家和‘文學青年’大半還站在大眾之外,企圖站在大眾之上去教訓大眾。”⑤如何從大眾之外進入到大眾之中,成為大眾當中的思想者、行動者、實踐者,這是左翼大眾化的現實要求。丁玲在1932年創作了帶有轉折意味的小說《水》之后也向中共黨組織提出希望能前往蘇區,與群眾生活在一起“體驗生活”的愿望。應該說,左翼話語不僅主導了大眾化的問題,也孕育著延安《講話》之后作家“深入生活”的1930年代邏輯線索,換言之,知識分子的自我革命與改造在現實革命話語的發展脈絡中有其思想連貫性。而這種階級之于革命、革命之于主體、主體之于實踐的迫切性是內置于20世紀革命邏輯的,并在左翼文化運動之后、1940年代延安文藝中得到深入、持續的論證。
左翼大眾化把民眾、大眾工作擺在了革命動員的突出位置,大眾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動力逐漸在左翼作家的革命言說中愈來愈重要。由話語言說到革命實踐,左翼為現代中國的階級革命理論注入了新的可能性。這也是立足于20世紀整體革命史觀,需要重新進行發掘與闡釋的重要論域。
二、作為民族國家構型的左翼時代性
1930年代既是世界經濟波動,不確定性加劇的時期,也是帝國主義結成法西斯聯盟,世界性反戰浪潮迭起的歷史階段。“九一八”之后,左聯率先發出《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民眾的文化組織書》,號召“把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革命的戰爭,變做真正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的革命的民族戰爭!”⑥左翼普羅階級的革命話語召喚在國際反法西斯戰線上的革命前衛性,這種前衛是必然要內爆于現實政治——所謂的“文藝統制政策”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文藝”,也將其鋒刃指向了試圖把“文學創作納入國家行為”⑦的黨國意識形態。
如果說階級革命是1930年代的底層邏輯,那么因外在國族(種族/族裔)威脅而“再造”的民族國家話語則是政黨政治謀求歷史合法性的顯在表達。在19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先后有兩次與“民族國家”話語發生直接對話。一次是1931年前后的“民族主義文學”論戰,另一次則是1930年代后期的“兩個口號”論爭。盡管說兩次論戰的對象與性質完全不一樣,前者是左翼陣營對國民黨文化政策的反擊,后者則是左翼文化內部的論爭,但是民族(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話語加持下的“抗戰建國”與“文化建國”的異質性論題的浮現,也為重新反思晚清—五四的現代民族國家構建提供了新的參照。
1930年6月,國民黨內陳果夫、陳立夫召集了王平陵、潘公展、黃震遐等人,以“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的名義在上海發起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稱要“形成一個對于文藝底中心意識”⑧。實則是將文藝與民族主義作觀念的拼接,進而站在“民族主義文藝”的立場上來否定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的正當性。發起宣言中用了大量篇幅來談民族主義,歷數東歐、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進而在“民族決斷論”的邏輯上來強調民族、民族性對于國家的重要性。從這個層面來說,國民黨的“民族國家”的話語延續了孫中山對民族革命的闡釋,但是這種“民族主義”為權力“中心意識”做注腳的話語策略性在黨—國的政治論述中又成為集團意志的顯現。在“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看來,“民族文藝底充分發展必須有待于政治上的民族國家的建立”,這在抗戰時期,則發展為“抗戰建國綱領”的產生。盡管說國民黨早期號召在民族情感上的民眾訓練、黨國統一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右翼、保守民族主義者那里,民族議題因對階級性、殖民主義的模糊化處理,使得其與左翼的民族國家產生了越來越深的沖突。
黃震遐的詩劇《黃人之血》就代表了“民族主義文藝”的民族觀。在作品中,作者以拔都來影射日本,用俄羅斯影射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歌頌黃色人種進攻俄羅斯的“偉績”,并將這次野蠻的民族侵略戰爭視為現代民族主義精神的詮釋。《黃人之血》作為應和“民族主義文藝”主張的創作,其創作出發點顯然也是遵循向“自命左翼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發起圍攻的政治目的。左翼陣營隨之發起了“反攻”,掀起了關于真偽“民族主義”的文化論戰。魯迅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中首先從抨擊《黃人之血》著手,駁斥其在所謂的“種族革命”旗號下實則把矛頭專門指向蘇聯,以及其民族主義的虛飾與“猥劣”。并進一步揭示“民族主義文藝”的“反革命”性及對帝國主義的諂媚姿態⑨。與魯迅相近,茅盾則指出《黃人之血》的法西斯化,“巧妙地盡了民族主義文藝的兩種任務,麻醉民族與法西斯蒂化”⑩。從晚清鄒容“革命者,變奴隸而為主人者”、章太炎“強國保種”的民族思想,到左翼革命話語當中求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根本愿景是一脈相承的。1930年初期,左翼陣營對“民族主義文藝”的批判,一方面為左翼文化的傳播鋪張了聲勢,無產階級立場的革命話語開始能夠與代表統治政權的文化策略相抗衡;另一方面,左翼參與的文化論戰深化了晚清以降的民族國家話語在革命知識群體乃至普羅大眾當中的認知,也對民族主義具有正本清源的效用,并為階級革命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注入了左翼立場。
在反撥國民黨當局的文化高壓政策的同時,左翼也在“民族形式”的論爭中回應了蔣介石“抗戰建國”的內在空洞。與國民黨的民族話語不同,抗日戰爭語境下的左翼“民族形式”論爭聚焦于文藝的民族化、中國化。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1。毛澤東的“中國氣派”顯然是解答了民族形式的現實難題,如在民族形式座談會上艾青所認為的“我對于民族形式的理解是這樣,覺得是和中國化是一個意思”12。“中國化”的理論邏輯是對抗戰語境下的民族精神重塑的內在強調,同時它也構成了對“擺脫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的理論壓力”“以建立起文化認同,進行政治和文化動員,完成自身意識形態建構”的理論譜系13。
汪暉將左翼至延安時期的“民族形式”問題論爭看作是在民族戰爭背景下“處理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和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所確立起來的階級論的文藝觀”與20世紀民族革命之間的歷史邏輯,實際是歸趨于“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中國的文化同一性問題”14。全球革命浪潮興起的1930年代,中國左翼所要面對的戰爭語境、階級斗爭的雙重議題使得其民族革命的意義不斷顯現,區別于不斷分化的國民黨左派,左翼知識分子在文藝大眾化、“民族形式”論爭中所提出的富有建設性的大眾文藝(“大眾語”)、“民族性”“中國化”的問題,正是對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文化同一性”的探討。從政治結構來看,這是非統治政黨對統治政黨的理念抗衡,也是“文化建國”對“抗戰建國”的邏輯顛覆,更是廣泛的左翼知識分子參與的、不斷下沉的革命實踐。而這在延安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與毛澤東《講話》這里,逐漸發展為以人民文藝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國”15。
三、浮出地表:《講話》的
社會主義人民性及其歷史蘊含
“紅色30年代”的國際背景,使得“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帶有不言自明的階級與民族雙重立場,從這個層面來看,中國革命也就兼具了民族革命與世界解放的雙重意義;而人民話語的深度闡釋與實踐,賦予了由階級革命的底層邏輯向現代民族國家(“新中國”)想象以歷史具體性。“人民性”凸顯了怎樣的時代命題?左翼思想資源與毛澤東《講話》的人民文藝有著怎樣的內在關聯性?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闡述的。
左翼一貫倡持的文藝大眾化立場,既承續了五四時期的民眾藝術觀,也開啟了1940年代解放區工農兵文藝實踐的先聲。瞿秋白從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出發提出“普洛文藝應該是民眾的”,反對“非大眾文藝”的存在16,對“非大眾文藝”的否定為文藝大眾化定下了基調,而對文藝大眾化與否的討論實際也集中在革命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問題上,這也是文藝大眾化討論與實踐的中心話題。左翼的文藝大眾化經由瞿秋白、魯迅等的闡發,形成了階級觀念—主體辯證法—人民性的理路。
無產階級觀念的強調是文藝大眾化的邏輯起點,最先提出大眾化的林伯修就指出:“普羅文學底大眾化,必要把握著普羅的意識,用這意識去觀察現實描寫現實。”而文學大眾化的目的就在于通過對普通大眾的教化,使他們獲得階級意識,從而達到“普羅的解放”17。無產階級觀念的獲取則將文學大眾化導向了階級斗爭的政治邏輯之中,何大白就指出,“普洛文學大眾化問題是普洛文學領導權的問題”,但是,“中國的普洛文學運動,不容諱飾,完全是急進的知識分子在領導著”,“普洛文學運動依然沉滯在小有產者的泥沼里”。因而,“我們認為大眾化的任務,是在工農大眾中間,造出真正的普洛作家”18。左翼作家的主體辯證法既區別于亭子間文人的“硬寫”,也不完全是從工農群眾中生長出來,帶有革命的啟蒙性,卻又置身于自我批判的歷史“空轉”之中,因此它需要來自群眾的再改造,找尋到堅實的有機體。左翼的“有機知識分子”在面對“文化結構同一性”時,他所想象的現代民族國家共同體成為極具歷史召喚的遠景。
而《講話》為左翼的階級—民族表達轉向主體的“向下超越”提供了現實和總體可能性。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國民黨統治區左翼作家呈現出對人民文藝探討的熱情,身處重慶的郭沫若提出“人民大眾是一切的主體”,左翼的作家應該“深入農村,深入工場地帶,努力接近人民大眾,了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俗,一切喜怒哀樂的內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人民的主位”19。林默涵也意識到,“我們的文藝既然是為人民服務的,就應當以工農為描寫和表現的主要對象”20。“人民文藝”概念本身的思想范式就對革命作家提出了內在規約,文藝大眾化在無產階級的政權結構實體中,已然突破了作家是否深入工場、農村的階級阻隔,按照柳青的觀點,深入生活是來自作家思想內部的革命,與時代的外在革命斗爭必然要趨向統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文藝不僅僅是作家階級出身的“歷史清算”,它的“人民性”實指也不僅局限于工農兵文藝的“普及”與“提高”,文藝形式的“傳統”與“現代”、“地方性”與“世界性”,而是歸于一個總體的問題系——朝向社會主義的民族國家建構的“中國性”。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已經揭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21。而民族的又必然是“中國性”的,這是社會主義人民性發生的內在邏輯,它所規定的為人民群眾服務也好,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好,都使得人民作為歷史的主體得以不斷浮現。費正清認為現代中國革命的研究理應有一個內置的視角,“中國不能僅僅用西方術語的轉移來理解的,它是一種與眾不同的生靈。它的政治必須從它內部的發生和發展去理解”22。正如溝口雄三在評論西順藏的“中國論”問題時所談及的,中國革命的關鍵在于“通過‘活學’‘總體人民的哲學’(毛澤東哲學)‘每個人都獲得了主體性’的‘總體’的‘我們中國人民’”23。在溝口雄三看來,“中國性”是與人民主體性相契合的,而這種“總體人民觀”則是經由革命—社會主義建國得以施展、延伸的。由此可見,階級革命—民族國家建構—人民性成為中國革命長久的內生動力,那么社會主義人民性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經”還是“權”?
這個問題必然要在中國化的革命理路中闡述的。社會主義人民性區別于傳統封建政體的君權與民權,也不同于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它的中國性內蘊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提出的問題——“一方面需要塑造作為革命實踐的政治主體即人民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人民政治的合法性需要借重并重構民族形式所涵納的文化共同體記憶與文化邏輯。”24將人民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也就是人民主體政治化,人民大眾組建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因而它對傳統中國的君主政權進行了祛魅,并超克了現代中國的“民權”,賦予了社會主義建國的歷史合法性。回到文藝大眾化,1930年代左翼文人所無法完成的人民性構建,在毛澤東《講話》中重新得以確立,“革命的政治家們,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學或政治藝術的政治專門家們,他們只是千千萬萬的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在于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25。所以要回答社會主義人民性是“經”或“權”的問題,顯然從延安想象中國,重新激發20世紀革命中國的內在潛能,這一邏輯本身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四、結語
左翼文藝運動是“紅色30年代”最具戰斗力的組成部分,它提出并嘗試解決的20世紀革命中國的諸多原點性問題——普羅階級理論、民族革命的歷史必然,成為延續到毛澤東《講話》以及社會主義人民文藝的關鍵命題。應該說左翼文藝作為承前啟后的革命浪潮,它所兼蓄的思想資源與主體價值,經由文藝大眾化實踐,為無產階級革命注入了深刻的、持續不竭的動力。《講話》對人民文藝的強調,進一步深化了左翼如何大眾化的歷史邏輯,“社會主義建國”生成于階級與民族革命的現代中國,但在某種意義上又超越了現代中國;它的革命遠景因社會主義人民性所內置的中國性視點而具有了實踐意義,這也構成了人民文藝發生的理論起點,對社會主義文藝產生了深遠影響。
【注釋】
①魯迅:《三閑集·序言》,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6頁。
②魯迅:《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載《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292頁。
③郭沫若:《文藝家的覺悟》,《洪水》1926年第2卷第16期。
④馮雪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文學導報》1931年第1卷第8期。
⑤瞿秋白:《“我們”是誰》,載《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第486頁。加重號為作者原文所加。
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告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民眾的文化組織書》,《文學導報》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28日。
⑦李鈞:《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1895—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第149頁。
⑧《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中央日報·大道》1930年7月4日第321號。
⑨晏敖:《“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⑩石崩:《〈黃人之血〉及其他》,《文學導報》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28日。
11毛澤東:《論新階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12《民族形式座談筆記》,《新華日報》1940年7月4日。
13畢海:《抗戰“民族形式”文藝論爭中的文化政治》,《文藝爭鳴》2016年第11期。
14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第344-345頁。
15盧燕娟:《中日戰爭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中國現代文化道路選擇》,載《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藝術手冊·2013》,河北出版傳媒集團,2013,第132頁。
16史鐵兒:《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文學》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25日。
17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于文藝的問題》,《海風周報》1929年第12期。
18何大白:《文學的大眾化與大眾文學》,《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19郭沫若:《向人民大眾學習》,《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
20林默涵:《關于人民文藝的幾個問題》,《群眾》第19期,1947年6月5日。
2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95、706頁。
22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王建朗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15頁。
23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第41-42頁。
24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第36頁。
25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66頁。
[覃昌琦,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9ZDA277;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現代中國革命主體視域中的左翼文藝運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HNSK(QN)23-109]